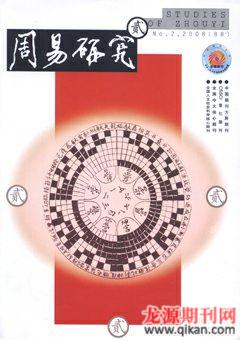顾炎武的易学研究成就
任利伟
摘要: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顾炎武博通群经,兼采众长,邃于经义,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和古韵都做过深人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同时又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经世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义理与致用并重的治《易》倾向,与先秦儒家《易传》一脉相承。研究中国易学史,应充分重视顾炎武的易学成就。
关键词:顾炎武;易学;义理;易音
中图分类号:B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2-0056-07
GU Yan-wus achievements in his Yi studies
REN Li-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As the founder of the Qian jia schoolin the Qing dynasty,GU Yan-wu had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classics,gathered different schools of strong points,profoundly learned the classics meaning,and gained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d in the realm of Yi-ology. By making good use of his strong points in textual research of literature,he systematically probed into the image-number Yi-olog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theory of River Map & Luo Chart of the Song Yi,as well as the Text,Commentaries and ancient phonology of the Zhouyi. GU set forth some enlightening academic views and expressed his emphasis on practice,reflecting his inclination of taking bot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use into account,a quality charactering the Yi zhuan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Zhouyi) in the pre-Qin period. So,GU's achievements in Yi-ology should be well adequately valued when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Yi-ology.
Key words:GU Yan-wu;Yi-ology;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phonology of Yi
顾炎武在治经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兼功众艺、会通群经的学术理念,强调如果“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1]。可以说在经学领域,顾炎武做到了不专治一经,不专攻一艺,却无经不通,无艺不精。为其如此,作为一代儒宗,顾炎武在专经研究方面也是多有创获、颇具特色,这其中当然包括他对《周易》和易学的研究。顾炎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不以易学名家,但他确实对《周易》之学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的研究,步入晚年,他日昃研思《周易》的兴致依然不减,年近六十仍受友人之邀,前往山东德州讲《易》三个月,可见一斑。顾炎武易学专著可考的只有《易解》一书,惜其不传,仅存的易学成果主要集中在其札记《日知录》、《音学五书》中的《易音》三卷,以及他与友人论学的信札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顾炎武的史地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他与友人交往的诗歌,其中也有许多与现实联系密切的治《易》心得,同样反映了他的治《易》理念和学术取向,对此以往学界关注不够,而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著作《易音》,学界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注:当代学人汪学群在其专著《清初易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中有专门一节“顾炎武的易学”,主要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顾炎武的易学成就。而本文的视域与之不同,侧重从易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相契合处切入,就顾炎武对《易》文本、既往易学的发展的认识以及他受易学启示、影响的思想主张等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对文本产生、流传及其性质的考辨
关于《周易》文本的产生,顾炎武坚持了《汉书·艺文志》认为的“人更三世,事历三古”以及由马融开其端的“人更四圣”的说法,进一步强化了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在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期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圣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日知录》卷一,三易)[2]并在《日知录·朱子周易本义》中更加明确地认为:“《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不惟如此,顾炎武在北游期间,为抒抗清复明之志而作的《书女娲庙》,也写有“剥复相乘除,包羲肇爻彖”(《亭林诗集》卷三)[1]的诗句,认为爻、象之说皆肇始于包羲。顾炎武正是力图廓清易学研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才对《周易》文本的产生作如是观的,他的这种认识正是对司马迁、刘向、班固等人的观点地继承和总结,只是现在看起来还不够准确,毕竟经过清末民初以来诸疑古学者的质疑,此类说法已经没有多少人信守。
就《周易》版本的流传,顾炎武也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考查,并对《周易》经与传之间安排上的混乱现象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2]也就是说,到西汉时期,《易》的经与传还是分开的,只是到了东汉时期,经与传才被经师合为一体。而顾炎武对这种“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它只能造成“经”、“传”间的淆乱,失去古经的原貌,对于经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其实,程颐与朱熹虽都是理学大家,亦都有专门的易学著作,而顾炎武恰是从“经”、“传”分合与否的角度对之作了高下的区分,认为朱熹的《周易本义》能依照晁氏(晁说之)、吕氏(吕祖谦)改订的《易经》古本,结构层次安排得较为合理,对朱熹志在恢复《周易》古本的价值和意义作了肯定,而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在这方面则略显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顾炎武对《周易》版本的流传以及“经”与“传”分和的考察是与他对明末现实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的思索不无关系。“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2]可见,在八股浊风的浸染下,当局为控制思想,士子为博取功名而对学风的破坏,无所不用其极。有感于此,顾炎武发出了“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的悲叹,不难理解,他对于《易》存亡的忧虑,实际上是与“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这一对经学复兴地企盼联系在一起的。
《周易》究竟为何书?其与卜筮的关系如何?顾炎武也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从义理的角度体悟出了新意。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卜筮,顾炎武引用《礼记·少仪》之言对卜筮进行了独到的分析:“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子孝臣忠,义也;违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怀仁义也。”(《日知录》卷一,卜筮)[2]从而认为“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当为,虽凶而不可避也”(《日知录》卷一,卜筮)[2],这也就批评了当时对于占筮目的从俗理解。再有,顾炎武始终强调卜筮的实质是“《易》以前民用也,非以为人前知也”(《日知录》卷一,卜筮)[2]。也就是说,古时卜筮最终结果是吉是凶,应该以君子的行为、德行能否遵从圣人之道,坚守忠孝的观念,怀仁去利为旨归。顾炎武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对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为善与后世术者或以休咎导人为不善作了严格的区分,因而他对于卜筮的认识能够摆脱单纯依靠爻辞判断凶吉的束缚,不仅强调了“孝”、“顺”、“忠”等儒家正统观念在君子行事、有为中的重要性,并试图剔除附着在《周易》上的神秘主义因素,这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二、以人伦日用为旨归的易学史批判
如前所述,顾炎武的专门易学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日知录》等其他的论著中的相关论述管窥顾炎武的易学思想。顾炎武的总体易学观认为,《周易》载圣人之道,易学乃是“圣人寡过反身之学”;治《易》应切于人伦日用,反对将《易》视为卜筮、方术之书。而且顾炎武在其诗作《德州讲易毕奉柬诸君》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昔尼父圣,韦编尚三绝。况于章句儒,未晓八卦列。……微言讵可寻,斯理庶不灭。寡过殊未能,岂厌丁宁说。……”(《亭林诗集》卷四)[1]我们知道,以八个单卦两两相重,组成六十四个重卦,据八卦重列解《易》,大多侧重象数一派,而顾炎武则偏说“未晓”,并谦虚的认为自己未能象孔子那样学《易》寡过。不难看出,顾炎武正是以黜数崇理的易学观为指导,不但对《周易》文本的起源、流传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同时也对易学史上各个时期有一定影响的易学名家及流派作了程度不同的梳理。
纵观易学史,汉代处于官方和主流学术地位的是象数易学,这一时期以京房、郑玄、荀爽和虞翻的易学较有代表性,其中,虞翻则是汉代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倡扬的诸多条例,如“旁通”、“互体”、“卦变”对《周易》卦象应用的形式与内容所作的多方面衍申和扩充,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顾炎武本着不偏离元典、不违背圣道的治《易》宗旨,对于汉代象数易学中拘泥卦象、杂入术数而支离破碎的弊病,作了颇为中肯、较有见地的分析。针对虞翻的卦象之说,顾炎武就认为,文王、周公,仅仅是设卦观象而系之以辞而已。孔子作传,传中更无别他象。孔子所说的卦之本象,除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外,惟《颐》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飞鸟之象,本之卦辞,并未尝凭空增设一象。可荀爽、虞翻之徒“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以为别有义”(《日知录》卷一,说卦杂卦互文)[2],看不到“古人之文,有广譬而求之者,有举隅而反之者”的用意,其结果,只能使对《易》的解读陷入“穿凿附会,象外生象”、“《易》之大指荒矣”(《日知录》卷一,卦爻外无别象)[2]的境地。顾炎武进而指出,“《易》之大指”只有通过“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论也”(《日知录》卷一,说卦杂卦互文)[2]的方式才能获得,舍此,便与孔子作传宗旨背道而驰。
虞翻解《易》又有所谓“旁通”、“反卦”之说。一般而言,“旁通”是谓两个六画卦相比,爻体阴阳互异,即此阴彼阳,此阳彼阴,两两旁交相通。“反卦”,与“旁通”相类,也是《周易》卦象的构成规律之一,是指六画卦中的六爻反转颠倒之后成另外一卦,后人亦以“反对”相称。明代易家来知德撰《周易集注》,发明的“综卦”一说即本于虞翻的“反卦”之例,时人称为“绝学”。而顾炎武对所谓的“旁通”、“反卦”之说经过细致的考辨,认为其并无特别之处。他认为:“《序卦》、《杂卦》皆旁通之说,先儒疑以为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来,承《泰》之小往大来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东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义也。《益》之六二即《损》之六五也,其辞皆曰‘十朋之龟;《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也,其辞皆曰‘臂无肤;《未济》之九四即《即济》之九三也,其辞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对之义也。必谓六十四卦皆然,则非《易》书之本意。或者夫子尝言之,而门人广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续经之作耳。”(《日知录》卷一,序卦杂卦)[2]也就是说“相受”、“反对”之义本来在《易》文本中是客观存在的,既然其并无特别之处,时人谓之的“绝学”也就无从谈起。在顾炎武看来,解《易》需要有体例,注意到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易》之本义,但前提是必须使之符合“《易》书之本意”,如果以之为僵化、固定的模式,将六十四卦全部生硬地套入其中,也就离圣人之义远矣。
除“旁通”、“反卦”之说之外,虞翻还有“互体”之说。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互体”中恪守凛遵孔子、程传的解易体例,以之为标准予以辩驳,指出了象数易学“互体”、“卦变”的荒诞不经:“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其说已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二年》:陈侯筮,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周公系《损》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荀爽)六子之变皆出于《乾》、《坤》,无所谓自《复》、《姤》、《临》、《遁》而来者,当从程传。”(《日知录》卷一,卦变)[2]
对于三国时期的王弼(辅嗣)的易学,顾炎武更是通过对易学发展流变的梳理,对其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汉代的京房、虞翻、荀爽之流以象数解《易》,穿凿附会之说横行,而王弼易学的出现,本身是对汉代象数易学的反动,后来的程颐《易传》逐其波,又继承了王弼所开创的以义理解《易》的传统。对此,顾炎武认为“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日知录》卷一,卦爻外别无象)[2],肯定了王弼的破除象数、开启新路之功。但瑕不掩瑜,顾炎武又指出了王弼解《易》在训诂方面的疏漏之处,比如,在《日知录》卷一“已日”中辨别“已日”之“已”的字义,就指出了王弼字义理解上的失误。
宋代以降,治《易》路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象数之学衍出的“图”、“书”之学灿然兴起,成为宋《易》的重要特征。对于宋《易》的转向,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易学研究者或是利用“图”、“书”来弥补儒家思想的不足,或是考察“图”、“书”的真实来历及其传授源流。这样,对“图”、“书”的研究与批判也就成为易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明末清初,随着反理学思潮的兴盛,以黄宗羲、黄宗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对“图”、“书”之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抨击,而顾炎武对《易》图所作的探讨和论辩既是受时风的影响,同时又是出于对明代空疏学风的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里专列一条“孔子论《易》”,将“孔子论《易》”与“希夷之图,康节之书”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无大过。”
很显然,针对受“二氏”影响的图书、象数淆乱“儒家之《易》”的倾向,顾炎武表现出高度的警惕,他秉承孔门易学精神,始终认为“文王、周公、孔子之《易》”是儒家之《易》,介于庸言、庸行之间,以崇德广业、反身寡过为宗,与“道家之《易》”有天壤之别。也就是说,顾炎武只准把《周易》纳入人们日常生活遵守礼法的轨道之中,不离“切实适人”、“望其致用”半步,否则便是离经叛道。曾有学者就此指出,由于观点最保守,摈斥易学向不同方向的发展,同样是最保守,也就做到了最信古。(第158页)[3]其实,顾炎武治《易》中的“信古”倾向,绝不是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四库馆臣所说的“喜谈经世之物,基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4]。“信古”、“复古”不是顾炎武治《易》的最终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信古”、“复古”具有强烈的古为今用、复古开新的意涵,也就是顾氏一贯倡导的“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惟有如此,人们在“所闻所见”中才能体悟《易》理,汲取论道经邦的智慧,以解决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而治《易》的真正价值亦体现于此。
三、重经世致用的易学思想
顾炎武对于经传的解释也常常自立新义,而这种新义——探究《周易》所得出的“微言斯理”,往往与他的历史发展观,和他时政危局的应对主张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作为其思想内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我们知道,《周易·系辞下》对于《易》书的特点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顾炎武依据自己的理解,把这段话总结为“《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亭林文集》卷三,与有人论学书)[1]可以说,顾炎武的历史观的思想核心在于“唯变所适”,而这一思想的源头活水却是《周易》。因此,顾炎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得出了“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着莫不更始焉”(《日知录》卷五,三年之丧)[2]的认识,既然万物“莫不更始”,社会历史发展也就“日新而无穷”(《日知录》卷一,易逆数也)[2],并认为“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1]。
顾炎武“唯变所适”的历史发展观禀于《易传》相关理论的沾溉,突出地表现在“顺势因时”与“变而适时”两个方面。和以往的进步思想家一样,顾炎武自觉地继承了司马迁所开创的用“势”来解释社会历史变动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将制度沿革、朝代更替以及风俗变迁纳入了他的“势”域。顾炎武认为,事物的演变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渐积渐变,以至于最终达到“不得不变”的程度,“天下之生久已,一治一乱。盛级之至,而乱萌焉”,“是知邪说之作与世升降,圣人之所不能除也。”(《日知录》卷一,姤)[2],也就是说,制度沿革、朝代更替以及风俗变迁均由势的作用而使然,其客观必然之势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扭转。正是由“唯变所适”的《易》理出发,顾炎武这一对“势”的理解,可以看出他试图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努力。就顾炎武的历史观而言,他对于“势”的认识并不是孤立的,顾炎武对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与“势”密切相关的“时”也极为重视。顾炎武关于“时”的思想除了遵循儒家思想自身演变的轨迹之外,最直接的来源也是《周易》。因为这种贵“时”、重“时”的思想在《易传》往往有充分的阐释,《易传·象传》就认为“旧中则昃,月满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蒙,亨,以亨行,时中也……”顾炎武依据对天象变化规律的把握,认为客观事物发展到“过中”则是应变的最佳时机,即所谓“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当过中而将变之时,然后革而人信之矣”(《日知录》卷一,已日)[2]。
顾炎武正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藉此反观明末时局流弊,从《周易》中发挥出“过中则变”的“时”与“变”之义。他认为只有善于审时度势,在事物发展“过中”时即开始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时,才是变革的最佳时机,也只有这样的变革才能够取信于人。例如,顾炎武的史地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在论及东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却不能平天下恢复中原的原因时,就认为,“《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属贤将而待可为之,时时而进焉,则无不成矣。晋既内无政事,外任属又非其人,虽有中原可胜之时,而我无以赴之,虽赴之,而败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5]可以说,顾炎武在《日知录·已日》中提出的“过中则变”的思想是对“待时而动”的最好注脚,因为“时”只有在贤将认属,政事已修,并取信于人的前提下才有积极的意义,否则只能“虽赴之,而败矣”。可见,顾炎武论“时”不尚空谈,虽处处言及它朝,却每每关注明末危局,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见解。
更值得关注的是,顾炎武对于《易》理地探讨并非仅仅局限于思想层面,作纯义理的探讨,而是将其易学思想主张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在水患、漕运、河渠、风俗等方面,顾炎武为改变民生而提出了大量解决问题的措施、方案,究其实,源于《易传》的“穷则变”思想始终贯穿其中。如在预防水患方面,顾炎武提出要“置堰闸以御潮沙”,认为“然自今而言,物既坏矣,而思所以新之之谓变,既揆度之,又丁宁之,则穷者可通,通者可久,而不复坏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五册,苏下)[5]。为减轻漕运造成的民萌之苦,顾炎武一再强调:“《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呼吁人君创宜民之法,如果“有味乎其言之”,“漕弊若此,非所谓变通时哉”(《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册,河南)[5]。为使河渠的修建能够“均蒙再造之仁”并最终出现“徭赋可供,盗贼衰息,民俗日厚”的局面,顾炎武依然禀法《周易》的经传思想,“夫《易》曰:‘已日乃革之,”主张“‘敝则张而相之,废则扫而更之。惟明台详加体察,勇往必行,则乂沂之功不在禹下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5]。此外,顾炎武还对统治阶级漠视民众疾苦、坐视民变的态度提出了警告,“以今则坐失耕稼之夫,以后则酿威盗刼之患,其为害不浅也,《阴符经》曰:“火生于不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至必溃。”顾炎武进而指出:“《易》曰:‘涣其群,元吉。此正识微虏远之君子所当涣之以元吉之治。勿使其时至而溃者也塞涓涓,以杜江河之流,伐毫釐以省斧柯之用,其在于兹乎!”他认为,只有重视民力,发挥出民众的凝聚力,“照之以明,断之以公,操之以信,果如当其罪必惩罔宥”,“则一举而民志定,民俗变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二册,浙江下)[5],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凡此种种都反映出《周易》变通思想对顾炎武的影响和濡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也正是顾炎武面对明末社会“财力诎”、“军政窳”的严重危局,传统的制度已出现不得不变之势,而表达出的强烈愿望。顾炎武为改变民生的努力,虽然客观的效果并非按顾炎武设想的那样,但勇于实践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
四、肇开创之功的易音韵研究
顾炎武不但在经学领域成就斐然,开一代新风,而且在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金石学等领域亦卓有建树,为后学导引治学门径。他的这种优势和特点在易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对《周易》古音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对于《周易》经传的音韵研究,顾炎武著有《易音》三卷,与另外四种即《音论》、《诗本音》、《唐韵正》、《古音表》,总称为《音学五书》。顾炎武从事音韵方面的研究是和他一贯倡导的学术理念分不开的。顾炎武以通晓音韵源流、变化为治学根基,认为舍此便无以明“六经之文”、“诸子之书”。因此,他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书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1],这就包括对《易》音韵研究。而且顾炎武对此颇为自信,他说:“《音学五书》之刻其功在注《毛诗》与《周易》。”(《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1]
《易音》三卷,体例略同于《诗本音》,但不像《诗本音》那样完整的抄录原文,仅仅节录《易》之用韵的文句,凡是与今韵不和者,证以他书,表明古音原作是读。凡是与今韵相同的,就注明在《广韵》的哪一部。例如,顾炎武在《易音》卷一“艮”条的注中,认为“艮其背不获其身”与“行其庭不见其人”两句中“身”与“人”二字同属《广韵》上平声的十七真部。接此又有所引申:“古者卜筮之辞多用音和以便人之玩诵,虽夏商之易不传于世,然意其不始于文王也。《易·彖》,文王所作,其用音止此。所以然者,易之体不同于诗,必欲连比象占牵和上下,以就其音,则圣人之意荒矣,故但取其属辞之切者。”(第152页)[6]很显然,顾炎武对《易》古韵的研究,同样是以崇尚义理反对象数的易学观为指导的。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对《易音》却有这样的评价,“……故炎武所注,凡与《诗》音不同者,皆以为偶用方音,而不韵者则阙焉。……炎武于不可韵者如乾九二、九四,中隔一爻,谓义相承则韵亦相承之类,未免穿凿。又如六十四卦彖辞,唯四卦有韵,殆出偶合,标以为例,亦未免附会,然其考核精确者于古音亦多有裨,固可存为旁证焉。”应该说,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对顾炎武的《易音》总体评价并不高,他们欣赏的仅仅是顾炎武的“考核精确”,而对于顾炎武辨审《易》古音以明儒家经典古义的学术宗旨,由于受乾嘉时期忽视致用学术风向的影响,四库馆臣们不可能有深彻的领会。因此,四库馆臣作出这样的评价就再所难免。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几乎成了评价《易音》的定论。以致后来学者在评论《易音》时,也往往言其“穿凿”、“附会”,要不再补上一条考据精审便草草了之。
如果我们就四库馆臣对顾炎武颇为自信的《易音》所作的评价作进一步地思考,就会发现,“义相承则韵亦相承”,只是顾炎武对《易》古音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符合实际地解释,毕竟年代久远,要把经书古音韵全部考证清楚已无可能,顾炎武正是根据音与义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作出的推断。钱大昕对顾炎武的这一观点也曾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古人因文字而定声音,因声音而得训诂,其理一以贯之。……学者读其文可得其最初之音。此顾氏讲求古音,其识高出于毛奇龄辈万倍,而大有功于艺林者也。”(《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十二)[7]对于顾炎武的方音说,钱大昕的评价更是一分为二:“顾氏谓一字一音,于古人异读者辄指为方音,固未免千虑之一失。而于古音之正者,斟酌允当,其论入声,犹中肯綮,后有作者,总莫出其范围也。”(《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十二)[7]其实,顾炎武考辨《易》古韵并非完全如钱大昕所言“于古人异读者辄指为方音”那样武断。如顾炎武在《易音》卷二“蒙”条注中,就“中”与“应”的用韵分析后认为:“而夫子传《易》于蒙、于比、于未济三用此字,皆从‘中字为韵,或亦出于方音,不敢强为之解,”这恰恰表现出了他严谨的学术态度。
更为关键的是,顾炎武通过对《易》韵的形成及其演变所作的较为合乎实际的历史主义考察,并指出了《易》古音韵在形成、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原则,即“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日知录》卷二十一,五经中多有用韵)[2]。而且,顾炎武还对“经”韵与“传”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强调“孔子作《彖象传》用韵,盖本经有韵而传亦韵,此见圣人述而不作,以古为师而不苟也”,并揭示了“经”与“传”在用韵体例上的不同,“《彖象传》犹今之笺注者,析字分句以为训也;《系辞》、《文言》以下犹今之笺注于字句明白之后,取一章一篇全书之义而通论之也,故其体不同。”(《日知录》卷二十一,易韵)[2]为其如此,章炳麟曾有言:“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第13页)[8]可见,有如此评价并不为过。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顾炎武就《易》音韵所作的具体研究确实还有不完善之处,还有待于后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纠正、细化、深入,但是他探究五经古韵而提出的一系列的原则、方法以及倡导谨严、求实的一代学风,为后人能够“扬其波,逐其流”,继续深入地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指导意义。
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有许多卓有成就的学者研读《周易》并承其惠沾,他们虽然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但同样为易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于学术史上这一独特的景观,台湾学者许芹庭的评价可谓精到:“其人虽不以《易》名家,而解《易》说《易》论《易》,或借事以论理,或引《易》以论证,咸有本有原,务实际而崇道本。”(第475页)[9]因此,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受《周易》及易学启示、影响的全部历史过程和学术文化现象上来”(第2页) [10],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末清初之际无论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在思想、学术领域,各种思潮交相激荡,激烈碰撞,顾炎武生处其中,其易学思想本身就不断地与之榫接从而形成一种助力,推动了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总之,顾炎武的易学思想与易学成就在中国易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6.
[3]赵俪生.日知录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2.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
[6]顾炎武.音学五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四部丛刊:三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影印本,1936.
[7]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8]章太炎,刘师培,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徐芹庭.易学源流:上册[M].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1987.
[10]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黎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