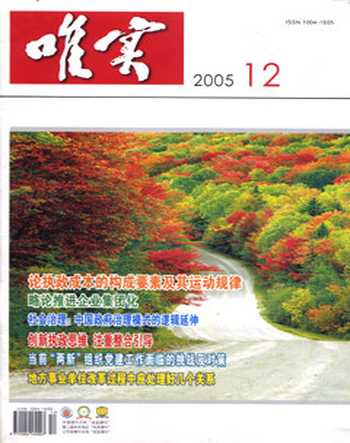社会治理: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逻辑延伸
贺龙栋
摘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从重政治统治向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换。因此,从逻辑上说,推进社会治理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还具有可行性。同时,面对全新的社会格局,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治理管理体制也是刻不容缓的。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治理;治理成本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5)12—0024一03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模式,是西方国家在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基本关系明确定位的前提下诞生出来的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支配社会的模式,缓解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来自于国家的顽强阻力;同时,培育了社会的自主性、自治性。社会治理打破了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垄断,使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创新。
一、社会治理理念与中国现实境况的逻辑契合
社会治理作为超越于新公共管理的一种理念,是在各国寻求公共管理新模式的进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构想。社会治理根植于治理理论。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公认的民主政治较为成熟的国家,民主政治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政治背景。民主政治意味着民众与政府之间不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而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即民众是公共权力的主人,民众作为委托人将公共权力托付给政府,使其代行公共管理的职责,政府的权力及其相应职责均来自于民众的这种委托一代理契约。这一经典的民主理论预设是治理理论得以兴起的基本理论前提。正因为如此,社会治理对于尚未开启民主化进程的国家而言只能是一件后现代的奢侈品。
社会治理体现了一种还权于民的努力方向。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理论也提请人们注意私营和志愿机构之愈来愈多地提供服务以及参与战略性决策这一事实”。政府一词往往指合法垄断社会强制性权力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而治理认为社会的权威应当多元化,强调除了政府以外的其它组织(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是对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置疑。如果说追问统治者占有权力的理由构成了近代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那么治理理论追问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理由则成为民主政治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逻辑起点。如果民众能从政府以外的组织获得公共产品,那么更多的具备自组织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将为民众提供更加广阔而真切的实现自我管理的民主思想的历史舞台。而这其实不过是使公众拥有选择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权利,不过是公众的自主权的拓展而已。因此,“社会治理蕴涵了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公众参与、民主、社会公正等等理念,以共同治理为本,谋求政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等多种社会管理主体之间沟通与交流,通过共同参与、协同解决、公共责任机制,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社会治理契合了人类实现自我管理的民主理想,它为民主政治的生长与完善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开始转变职能,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努力实现由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变,由宏观经济的“控制者”、“计划者”向“指导者”、“引导者”转变。中国在国家法治化建设中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化进程也有目共睹,社会公正的理念也正在得到张扬。《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也提出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社会”,“要适合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与此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也由过去政府管理更多地突出特殊集团的意志向更多地突出社会公众的意志转变;由突出政府管理活动以政府主体的规则为导向向突出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依归转变;由突出政府管理是直接进行统治的工具性作用向突出政府管理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作用转变;由突出对上级负责向突出对社会公众负责,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制转变。这一切意味着政府职能从重政治统治向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换。因此,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中国依托迅速发展的经济与已有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完全可能形成“后发态势”,在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进入先行探索的行列。所以,逻辑地说,当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治理得到实际运用的条件和空间。
二、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权威结构的变迁,为中国推进社会治理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国具有强政府的传统。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日趋深刻,依法治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公共生活中原有的权威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依托市场而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主个人的大量出现,使政府包揽社会事务处理的积极性和能力都大为减弱,主动转变职能和创新政府履行职能的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自身的要求。
中国自1978年开始了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权力结构的调整,由此为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基础。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经济改革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是以“下放权力”为特征的。如邓小平所说,“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主要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将作为农村公共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经营权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又推动了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合一”的体制向政企分开的体制转变,企业开始成为独立经营的法人团体。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目标是推动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逐步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以法的方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社会自治组织的出现。如个体私营工商业者协会、商会、消费者协会、各种学会、研究会、基金会、职业协会、兴趣组织等。而且大众传播也开始作为群众喉舌反映民众意见和要求,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参与讨论公共事务。
以上这些变化说明中国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自治性组织相对于国家具有自主性或非官方性特征,但在一定范围行使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公共决策。如消费者协会代表参与政府价格政策的听证会。公共权力的配置开始由政府一极向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分享权力转变,决定公共事务的主体不仅有政府(在中国语境下指广义政府,包括执政党、人大等),而且有各种国家法定权威认可的自治性组织。公共权力的运作开始由单一的自上而下运用向政府自上而下和公民通过其组织自下而上的双向运用。由此也意味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型。
如果围绕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利益卷入者能够有序而且有效地协商解决社会事务,则将不仅对于公共管理的效果和效率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推动,对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一个促进。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治理不但不构成对政府权威和职能的挑战,而且有利于政府找到新的发挥调控作用的载体和方式。因此,即使在仍然保有强政府色彩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也可能找到现实的空间,获得有效推进。
三、对消解社会问题和降低治理成本而言,社会治理不失是一种较理想的治理模式选择
社会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模式,但不是唯一的模式,更不是一种试图解决所有公共管理问题的模式。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其本身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缝隙”中萌发生成的。社会治理虽然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社会治理有自己的活动领域,也有自己的内在局限:它结合了国家的管理,但不能代替国家依法行使强制力;它利用了市场运作的机制,但也无法代替市场对各类资源自发进行有效的配置。社会治理是以国家和市场为基础的,是作为公共领域的政府、作为私人领域的企业和作为第三领域的社会或社群彼此结合而形成的共同管理,是对单纯国家或市场手段的辅助和补充。就社会资源配置而言,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同样也存在着社会治理的失灵。就其现实生活中适用的范围而言,社会治理的真正空间在于涉及具体群体利益的各类社会问题及其解决。
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由政府包揽社会一切事务显然十分困难,而且治理成本也很大。传统体制之所以需要改革正说明这一政府行为的“失败”。而当政府难以有效及时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时,社会成员自我组织满足自身特定的需要,显然可以弥补政府行为的不足,且所需治理成本也较低。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不可能考虑公共利益,对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也不可能负责。在对弱者的保护,对社会福利的追求方面,市场不仅会“失灵”,而且本身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社会治理坚持利益的多元化,制定社会政策、方针、对策、措施考虑各种不同社会利益需求,并且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取向,尤其注重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和体现。
科学消解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方法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四个多样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在原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他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发生了具体利益的分化,相互之间存在利益的差异、矛盾以至冲突。要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必须采取新的矛盾解决方法,即要使矛盾诸方各得其所,和谐结合,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阶层和群体所拥有的多寡不同、种类不同的社会资源能充分调动起来,相互补充,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
创新和开发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将成为全社会包括政府和卷入矛盾冲突的各方的共同要求。社会治理不但注重问题的解决,而且注重问题解决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得到社会和相关主体的认可。通过引入多方力量特别是主要利益相关方,协商解决问题,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各方解决问题的愿望和积极性,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案可以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可,在解决问题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利益结构可以具有最高的认同度,而不至于随便发生被否定或推倒,这样的结果符合现代公共管理关于“长效”的要求,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避免矛盾的延续和扩大。
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全新的社会格局,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治理管理体制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社会治理应成为政府通过民间组织同最广大的公民的亲密对话与合作机制,从而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最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钱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