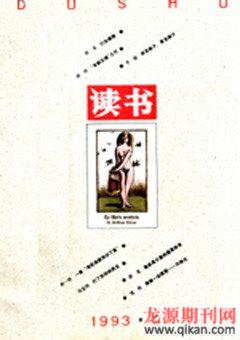旧籍中的新启示
刘 桢
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是被英国人强行翻开的。无论对英国的目的与手段作出怎样的评价,都不能否认中国社会在一八四○年之前没有自觉地考虑过如何使国家近代化的问题。李贽对传统教条和假道学的揭露,龚自珍对衰败、糜烂世风的鞭挞,都局限在封建主义的大范围之内,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有质的界限。明朝中叶以后,江浙地区私营手工作坊的兴盛,也不过是北宋汴梁河岸繁华景象的翻版,就像尚未受精的虫卵,还孕育不出新的工业革命。蒋廷黻一九三八年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鸦片战争爆发时,“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很显然,近代史以一八四○年为起点,并不是中国社会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而是靠了外力给予的加速度。蒋廷黻是学者兼外交家,所以,中外关系就成了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鸦片战争之前,中外有往来,却无邦交。中国藩封四夷,原是为了让他们替我们守边。他们要向我们进贡,我们也回赐他们一点好处,但他们必须遵守宗藩秩序与礼仪。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概念里,夷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以至于中国古代发达、完善的官僚机构中,唯独没有真正的外交机构,像“理藩院”之类的衙门,不过是为了表现天朝上国对臣服者的宽容与威严。英夷打到中国之前,曾尝试过和平外交,但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双方在海关税则、治外法权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这些都还提不上议事日程),而是“乾隆把他(英使马戛尔尼)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平心而论,英使马戛尔尼的条件并不过份,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对别的问题都可以通融,而在单方面跪拜这个问题上却不容商量。在中国政府看来,英夷平和地来华,那是他们有心向化;即便是舞刀弄枪地调皮捣蛋,也是为了求中国皇帝“代伸冤抑”,根本不涉及什么平等的问题。所以,当英国人弃文就武、气势汹汹地捶门叫板时,中国朝野还是迷迷糊糊,用对付匈奴、契丹、鲜卑的古法来对付所谓的“红毛番”。
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沿海一战,竟会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因为中外发生争端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以武力相威胁或干脆诉诸武力的情况并不罕见,长城的一修再修便是证明。连清廷自己在内,也要算作乱华之“胡”,否则,就没有理由骂吴三桂为汉奸了。汉人王朝处理夷夏争端的方法有两种:国盛兵强是痛剿,长驱千里,斩首万级,“不破楼兰终不还”;国衰民弱时是安抚,即和亲、纳币、献城、割地,以求边境的安宁。到了道光年间,英国人不守本份,前来寻衅滋事,朝野上下自然就要搬出古法。“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林则徐是主剿派的代表。至今有一种看法,认为英军移师北上,是因为害怕林则徐。这也难怪,林则徐在广东备了战,英国人却去攻浙江,双方未交上手,以致于留下了神话。不过,别的名臣、勇将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人抗英的决心与谋略大概不会和林则徐相差太远,但他们都血洒疆场,以身殉国。蒋著认为,“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林则徐对付英军的秘方是“民心可用”四个字。这种理论很动听,但也很模糊,没有精确的界定。如果避开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避开百孔千疮的社会现状,避开民族的变革与维新,孤立的“民心”之说就只是士大夫们传统的高谈阔论。试想一想,倘若“民心”真是召之即来、战无不胜的法宝,炎黄子孙何以口中念叨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却又飘飘然留着长辫、做了“鞑虏”二百余年的顺民而不以为羞?乡丁团勇杀几个散兵神甫、烧几座教堂医院并不困难,而要组织、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迎战一个甚至一群杀气腾腾的对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林则徐走后,主持粤政的徐广缙、叶名琛照猫画虎,实践林则徐的民心理论,他们吹嘘广州“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结果却连叶名琛本人都被“猾夷”捉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成为清朝出洋的第一位红顶大员。到了庚子年间,经载漪、刚毅、徐桐等一伙忠义之士的煽动,慈禧太后也居然想利用“民心”来“扶清灭洋”,但宣战不及两个月,义民们就一哄而散,太后和御驾只得仓皇出京“西狩”。
剿夷的效果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那么,抚夷派又能不能找到一条让英国人就范的捷径呢?琦善在天津轻率地对大沽口外的英国舰队说,新钦差将“秉公查办”当事者,只是交涉地点应该在广州。英军假话真听,同意南下谈判。“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实际上,他们连英军远征的基本目标都没搞清,等琦善到了广东,才知道空口耍滑头的代价有多大。按古法,对付匈奴,可以嫁几个未必漂亮的公主;对付契丹,可以赏赐“岁币”。而对付眼前的英吉利,就没有什么成例可寻了。他和他所处的社会不知道这就是近代外交的严酷现实。战而胜之,自然一切都好说。倘若不堪一击,任你口吐莲花,也不能将战场上的损失从谈判桌上捞回来。加之琦善们都有胎生的软骨病症,经英军用坚船利炮一通吓唬,只好胡乱答应对方。道光帝转喜为怒,反过来又将琦善革职锁拿。
第一次办理近代夷务,前后两位钦差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却都失败了,这说明在对待以英人为代表的外夷问题上,已经是宽严皆误,进退失据。这种状况不仅困扰着道光时代的一辈先人,也是后来者摆不脱的大难题。如果将制夷师夷等问题推而广之,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各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化变迁,那么,直到今天,恐怕也难说我们能够很自如地处理对外事务。
问题难就难在中国社会并未真正形成对近代化的内在渴求,一切原始的动力都产生于外部的强制、刺激和对比。由此而带来的屈辱与浮躁心理,更加剧了传统思维的两极对立。“剿”与“抚”的天朝对外模式行不通了,代之而起的是洋务与保守之争、体用之争、继承与借鉴之争等等。尽管鸦片战争的结果实质上是近代社会对中古社会的胜利,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封建主义的胜利,但由于道义原因与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中国社会心态变得特别复杂,甚至已扭曲变形。在不服与不得不服、激动与麻木的自我对抗状态中,要虚心地学习外夷,像俄国与日本一样,按照“近代化”的要求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自然不是什么小小的要求。因此,蒋廷黻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近代化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蒋先生描绘了从中兴名臣曾、李、左到变法先锋康、梁再到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历史曲线,连满清权贵奕
近百年过去了,按照教科书的标准分期,我们已步入了现代社会。如今,继开放沿海十四个口岸城市之后,我们又要开放沿江、沿边的城市,这比起举国皆骂五口通商的道光时代来,自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许多类似事例全部加在一起,不知是不是就能充分证明我们跨越了近代化的阶段。蒋著中没有提出近代化的具体标准,而只留下连在一起的三个问题,即:“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后两个问题不太好说,我们似乎做到了,又似乎没有做到。前一个问题则很明显,我们没能赶上西洋人。因此,现代化的任务中还包括了大量未完成的近代化任务,也因此,我们无法截然区分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正如我们无法截然区分中古社会与近代社会一样,中国社会的转换与过渡,总让人感到一种勉强与生硬,感到一种被动与马虎。
回顾中国近代史,蒋著中开头的一段话很值得深思:“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我们不会全盘接受蒋廷黻这部著作。但是,拿此书来印证当今读书界流传的“要获新知须读旧书”这句话,却不是没来由的。
(《中国近代史·外三种》,蒋廷黻著,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1.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