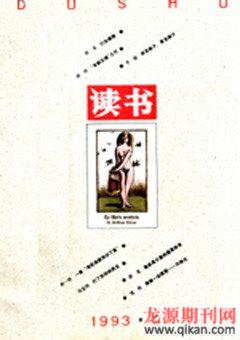灯火阑珊
舒 禾
闲话高阳和他的书
海内喜读高阳书者,不知凡几。这些年,大陆与港台文学渐通款曲。先是金庸的“新武侠”不胫而走,至今风头不弱,令诸多老少爷们儿走火入迷(一些书生朋友也成了铁杆“金迷”)。约七、八年前,高阳的历史小说亦悄然偕南风而至。虽然此间所见版本仅为高氏著述总目的一小部分,风神所在,反响大约也不能算小。偶闻一句话,道是:“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语近夸张,亦非无稽之谈。
半年前,消息来得突兀,高阳先生以痼疾不治,驾鹤西行了,据说是刚过了七十寿日不久。其人兴酣摇笔似乎总是不能自休,虽算不上名山大业,风景尚在佳处,想不到天不假年,煮字不能疗疾,“酒子书妻”(高阳自谓)一时俱杳。许多人都说了惋惜的话,那时我正在津津有味地读一本高著《金色昙花》(写民初政海及袁世凯“洪宪”前后旧事),不能释手之外,平添哲人其萎之念,无个去处。
遗著八十九部,其中于书林独步一方的历史小说占六十余部,高阳手笔,就我有限之见,无论小说一途(代表作如《慈禧全传》、《胡雪岩》、《红楼梦断》)或“二三雁行”般的文史杂著(如《高阳说诗》、《红楼一家言》、《梅丘生死摩耶梦》、《古今食事》、《明末四公子》、《清末四公子》)都可说好读、耐读。读了,一层,不妨广见闻,可药孤陋浅薄,二层是有品味,如黄垆买醉,不觉醺然。接着,或可由高阳此一掌故纷陈的“聊斋世界”,想到冯远村所谓“看书宜耐”:“贪游名山者,须耐仄路,贪食熊
高阳原名许晏骈,杭州人。杭州横河桥许氏为大家望族。乾、嘉至道光年间,一家七个兄弟先后乡试中举,其中三个两榜出身,御赐“七子登科”匾额。高祖许乃钊官至江苏巡抚,行七,行六的六老太爷许乃普是嘉庆庚辰榜眼,官吏部尚书。光绪初年的军机大臣许庚身,再早些入值南书房的许寿彭,皆为高阳的曾叔祖。不过,这翰林之家不可能世袭,也由于时代变动大,到许晏骈这一辈,钱塘韵事早已风流云散。他本人由于抗战关系失学,书生从军,辗转去台湾,一九六○年后服务于报界,主笔政,渐渐由读书而谈书论书而著书且大著特著了。寄身心于文史,尤其于清代史事掌故深研几索,别出蹊径,多半还有世家遗风的影响,所谓“其来有自”,又所谓“文章憎命达”。著书者别署“高阳”,有一说是取“酒徒”意思,另一说称高阳好酒,然佐酒者常是掌故、牢骚之类,故典出《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也有说是以许氏郡望为名,底细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
“华发酒痕每每新,可能蠲笔作闲人?乡关梦里疑曾到,世事杯中信不真……”这几句诗后面的影子,好像是一个与世飘零怅怀天涯归梦,托命于诗酒文章的高阳。所以台湾张大春先生悼高阳文,亦有这种对其人文心风度的感想,并引杜少陵诗作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知人见道,以杜陵野老荒台咏古之诗,为高阳的情怀、风格写照,理想不理想不论,概说其人“自封野翰林”的笔墨因缘,云山丘壑相通,也可称异数之遇了。
酒、书、梦、笔,故国平居,灯火阑珊,也许是传统中国文人寂寞中的生活所依,精神趣味所恋。从大处去作历史衡量,如修、齐、治、平等等,这便不够“及义”,也不必一定要说香草美人以喻忠贞之类,但不少传统的诗文书画或者戏剧、小说倒是在其中孕育了自己的品格、形态以及不同时代的知音者。尝想,许多文人墨客为什么写作?难道不正是要寄托他们那一份古今皆可“通感”,皆可“体味”的文化情怀吗?是否就是历史文化之灵性之神韵?至少不妨把“情怀”当作可感知意会的理解过去和现在的一个视角,关键不在于理论判断如何、分析方法如何,是否给出结论指导,与其堕于工具主义的操纵,被功利、目的所牵引,还不如把定见搁下,先来同历史作一番“相遇”,或者说“非强迫的响应”,也是“通感”的,具有开放性的“相遇”,不也好么?在这一点上,把“斗争”换了“对话”,“批判”换了“理解”,颇有意味。
许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剑拔弩张、爱憎分明地去“占领历史”,以史为鉴或古为今用,也几乎是开卷不忘的。读书,或热坐蒸笼或冷卧冰凌,难得平心。但头童齿豁,渐渐觉得事情原也不那么简单,更不必“实用”当头(一来不易“实用”,二来不免有负作用)。这时读高阳的历史小说,便觉天外有天,别有兴味,再好些,眉头心上,或许消遣中有启发,无意得之,更具一种滋味。这滋味如何大抵是说不清的复杂,总非“强说滋味”一类。好之者,即有同嗜焉的二三友人,谈论高阳,每以评论为难事,大约讲史如此,读史如此,不“强说”,却好在
一部甘四史,剪不断,理还乱,难怪欲说而无从说起;尤其晚清因变交织的史局,更令今人惑于泾渭之乱,充分理解和鉴往知来之乐每不易得。因此就了解历史而言,有隔膜,有武断扭曲,有笼统观之,有简化的认知等等。所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实在是一句无多少把握的话。稍有不同的是,高阳作历史小说(并非以史学自任),虽然重视钩沉抉隐索幽发微的学问功夫,却不大受历史理论的局限。换句话说,那不是“历史”,而又因其成为“不是历史的历史”,别具意味——说来也只是使描写的事情、人物有来历有血肉,更像那么回事而已——首先体现在有一种不大隔膜、造作的历史氛围感,它从容、充分地出现在高阳的故事里。不端架子,靠材料的揣摩讲故事。故事讲得有魅力,倒不一定靠虚构渲染,高阳的路子在于从故纸中挖掘本事材料,挖掘掌故逸闻以及历史人物活动的种种关联,用现在的说法,是一种信息处理。讲史者的情怀、气质、功力好像便是处理其信息库的软件。真工实料,其人野获冥搜、“采铜于山”不让裨官。世上史学家不少、小说家不少,这样的学者型而加才人型的“故事篓子”却不多。
不多即不庸,人才难得。除了脑筋不糊涂,思致敏达,做这一行,认认真真投入,以至于人磨墨、墨磨人,于书山裨海沉潜含玩,丹铅不辍,倒是得下一番苦功夫、笨功夫。对于古典知识“用力甚勤”,大概是高阳创作自立门户兼有厚重、不浮不虚的根基之一。如是,方能苦中有甘,拙中见妙。看得出,高阳在倾心注意于文史苑囿时,涉猎甚广,尤其是有清一代的史传、笔记、诗文集寓目既多,勾稽亦久,由庙堂之高九重之深到江湖之远市井之繁,种种朝章典故轶闻奇事谙熟于心。一旦酒酣心热,略定题旨,铺纸伸笔,似乎材料已罗于胸,信手拈来,不妨娓娓而叙,侃侃而谈。用“博闻强记”、“善体物情”八个字来评价高阳创作的苦与乐,是相宜的。此老腹笥之宽,几乎令人妒煞。书卷气,作为高阳小说的独家风味,恐怕为诸多同类作品最难替代。或谈礼、吏、兵、刑,或谈科场文卷,或谈票号典当,或谈梨园粉墨,或者就谈吃、喝、嫖、赌,世间制度、风物、人情种种,一样通已不多见,行行当行本色或只是略谙门道就更少。高阳的小说,可能又见长于这种“知识”风貌。一种让人“读掌故”的小说,可能不大合于一般“小说分类”或“小说理论规范”,换句话说,它既不大“传奇”,又不大塑造什么或有结构上的讲究。但他也写人、叙事,有裨官、说部的旧意思,说是“不是小说的小说”,可以承认,而且正别备一格。这在高阳,固然是“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在读者,也不妨性习相资,因其所好。
想到刘勰说过,“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矣”(《文心雕龙》)。在这儿,讲治学,讲构思为文,讲为研究或为创作而治史,博见与精识与贯一应该不仅不矛盾,而且总是基本的东西,如造屋的地基。而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就这一点而言,似乎比较更注重“贯一”。“博见”好是好,但非一日之功,恐怕是努力来不及或浮躁嚣然风气所不屑一及。于是种种宏言谠论,标榜为真理、规律之阐释的大话浮文,不旋踵来去。贫不能馈补,仍要作,势必流于空疏、勉强。此所以不耐读之作敷衍一时,热闹一时。“快餐文化”之所以时髦,原是自然的罢。与此相类似,今人忌讳“知识老化”,可曾忌讳“知识断挡”?忌讳“吊书袋”,可曾忌讳“没书袋”?诸如此类,读高阳的书,可能会有些这样的想法。不过,有读书癖、考据痴因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高氏本人,却未必会想那些,他一直记得幼年故宅老屋中清代大书家梁同书写的一副抱对:“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从幼稚起读书,有苦有乐。苦于读“致用”的书,乐于读“消闲”的书。而消闲的好去处,莫过于浸淫“封神”、“七侠”、“三国”之类,因其热闹,往往奇局莫测,有戏可看。这类文字,读而再三,其中或文或武、或神或俗,观成叹败,披奇揽秀,渐渐觉得,世事纷纭,往往不脱一个“争”字。某姓得了天下,就要保天下,防止别姓争了去,而别人仍复来争,所以有人说一部历史就是一部“相斫书”。当然,一个“争”字总包涵了极复杂多样的历史内容,故读史又不免有治丝愈棼之感。然而大致说,争这争那,多少都同“秩序”有关,故事一层,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层,似乎都有个建立秩序、破坏秩序以及又如何重建秩序的主题。如此,圣君、贤相、名臣、良将、高士不出,如苍生何!这是老谱,也就是许多叙事史、小说叙述模式负载的文化旨趣。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晚清史页,历史情况恐怕更呈现出深刻的困境与悲剧性。因而争端机牙错出,秩序的维持和修补面临内忧外患的空前挑战。如果说这是比较空洞的认识,那么读读高阳著《慈禧全传》六卷八本,环环相套的朝野故事,一场场戏,兼戏中戏、戏外戏,或许能得到具体的感受。又由于他主要是从“朝廷—秩序维持”的角度去落墨,似乎个中滋味对历史情况的体会感,更见复杂,颇耐琢磨。
譬如关于“争”,晚清政治生活在内外压力下如何“争”,政海波澜往往牵及“和与战”、“图变与守成”这一类攸关事体大局的矛盾冲突。这里实际上内含意愿与能力、自由与历史结构制约等一类难解开扣的矛盾。简化的写法是一种,快刀乱麻,褒贬鲜明。而高阳则写得不明确,且令人感觉这种状况是无可奈何的、自然而然的,你无法取消它、干涉它,因为它乃是困境的反映。《慈禧全传》中的人物,如西太后、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固然并不可敬可爱,但其人为政处事亦各有各的道理,他们是色彩并不相同的“演员”,但又可说其本色、体验无不具有角色意识,正好处在历史所规定的或正常或尴尬或荒诞的“戏剧情境”里。简单地捧和骂,都不是那么回事。高阳几次借人物之口说一句江南谚语:“看人挑担不觉沉”,话本身也挺有份量。作叙事史的人并不挑担子,可“看人挑担亦觉沉”,是否别见史眼史识,也值得人们往深里去琢磨呢?
细看,对晚清史的阐释,高阳不大“从众”,与我们长年耳濡目染信之不移的看法未尽合拍。譬如关于“义和团”、关于晚清的“教案”,就事情本末细想想,就觉得至少不似“爱国、卖国”的公式一套那么简单。又譬如戊戌年的维新和政变,《胭脂井》开头便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写起,有的情节关目细写,而全过程比较疏略,特别对康有为、梁启超着墨甚少,似乎对新政持含蓄的保留态度。同时对晚清此一大政潮的复杂性有所暗示,暗示个中阴谋自有玄机,真相难以大白天下。高阳的聪明之处往往在于并不写尽,只是从西太后、荣禄、袁世凯、刚毅、光绪帝、谭嗣同等每个人的角度,勾勒其动机和行为,这里面有明暗曲直、阴差阳错,让人想到历史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情的权力斗争如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后来在高阳的一篇短文(《慈禧太后与伊藤博文》)中,看到他对“戊戌阴谋”的考证研究,发人所未发,直揭此事波澜系刚毅等“后党”为夺权所引发、设计,而康有为,则被指为起栽赃诱饵作用的“奸细”。其立说大胆,而用心不粗,一时弄不清是高阳的笔深不可测还是历史事像惨雾重重了。
且把假说、测想搁到一旁,只说“平情度势”与“设身处地”,从《慈禧外传》写到《
有意味的叙事史,也许并不需要更多思想的装点,“作意开花是谢时”。而意味却更含蓄在历史生活自在状态的呈示中。那时的人生活在那时的世界中,悲欢离合,争斗与彷徨,耻辱与梦想,然后历史又翻到一页,仍然是光明与黑暗交织着,他们不知道所为何来,所为何往,正如我们也无法测度未来。这种历史画面其实又是沉重的。“海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谁又能说清悲剧的意味?
如果说“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剑桥中国晚清史·导言》)如果多少想形像地知道这场悲剧怎么演来的,《慈禧全传》还值得看看。看看这类“不是历史的历史”,不为无益。
人在尘世中,虽不无“山中岁月、海上心情”,毕竟难得彻悟。高阳先生学问文章,是可入文苑传的,文笔史识皆称练达。但是治史者“观山”,人亦难免在“山”中,此所以其人也不能自解矛盾心情。有人说,高阳抽丝剥茧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过程,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同时他又不甘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牢笼,于是便借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但这两方面会出现矛盾——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骚又何必有之?对此,高阳两杯酒落肚,也只能说:“那就不能谈了嘛!”
好像是小世界与大世界、此世界与彼世界的矛盾,所以终究还是免不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记得是某西哲说过,粗读哲学的人是无神论者,深读哲学的人,则是有神论者了。那么,历史的叩询者、对话者,沧海茫茫,一湾暂驻,又何能免知与不知的矛盾!
斯人已去,白云悠悠。台湾周弃子先生曾有四首诗评高阳,言其风格大旨,语颇扼要,就抄在下面作结。
载记文章托稗官,爬梳史乘扶丛残;
一千八百余万字,小道居然极巨观。
拄腹撑肠万卷书,要从博涉惩空疏;
天人性命冬烘语,持较雕虫傥不如。
世论悠悠薄九流,谁知野获费冥搜;
江湖杂学谈何易?惨绿消磨到白头。
倾囊都识酒人狂,煮字犹堪抵稻梁,
还似屯田柳三变,家家井水说高阳。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