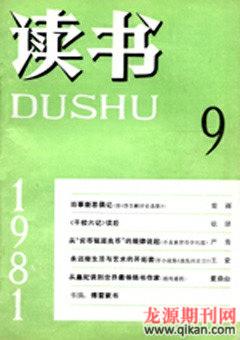《干校六记》读后
敏 泽
我有幸是《干校六记》的最早的读者之一。一天,我去看默存和季康,大家谈这谈那,谈得很热烈,也很投机,——象往常每次谈话一样。临走时,季康递给我一包手稿,即《干校六记》及默存为此书写的序言,让我带回看看,过些日子提点意见还她。我回来后,时间已经很晚,心想先看上一记,以后有机会再看。不想一看之后,真是“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了六记,这时已是深夜。但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于是连夜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自己读后的直观的感想。
是什么特点使《干校六记》具有这样引人思考的力量呢?
固然,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没有经过特殊历史形势下所谓的“干校”的“蒸”、“焙”的,大概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干校六记》以朴素的笔触描写了这一人人切身经历过的事件,使人们重温了那段逝去了的岁月中思想的流光,因而使人感到亲切有味,是一个原因。但却不是重要的,更非唯一的原因。历史将证明它比残缺不全的《浮生六记》将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在今天或者今后,那些不曾经过“干校”“蒸”、“焙”的人,也会怀着浓厚的兴趣去阅读它,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由于它有另外的原因在。
杨绛同志是一个有多方面文学修养的作家,她出版过剧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和《风絮》,出版过短篇小说《倒影集》,以及文学论文集《春泥集》等,并翻译出版过《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名著《小癞子》、《堂·吉诃德》,以及法国名著《吉尔·布拉斯》等。她有着精湛的艺术素养,以及驾驭和表现她所处理的题材的能力。
《干校六记》顾名思义,是属于记传体文学。我们都领略过的所谓“干校”,虽然不能概而论之,但是说它们是小异大同想来是不会错的。林彪、“四人帮”利用它摧残人材、摧残干部,有着触目惊心的事实。而季康的《干校六记》却有意回避了这一方面事实的叙述和描写,除第一则《下放记别》多少接触了一些大动乱的现实带给她女儿及她一家的令人心碎的事实外,其余五记可以说都选取的是“干校”生活中看来一些琐细的侧面。正如默存同志在《小引》中所说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但就在对这些琐琐细细的生活侧面的描写中,季康的观察和表现是那样纤细入微,而又切中要害、恰到好处,娓娓动听,并不失之繁琐:——这可以说是她的所有作品,如《倒影集》中的作品的共同的艺术特色。在《六记》中,她善于在冷酷的现实中发现诗意,并且写得那样淡雅优美,绘声绘彩,有时又很富有哲理气味,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和鼓舞。干校,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美好的名词,并且起过它的积极的作用,但十年动乱时期的“干校”,已经变了质,正象美好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也一度变成了历史上少有的那伙丑类推行最肮脏的反革命勾当的招牌一样。作者季康也和那时一切有理智和正常情感的人们一样,对那个特定环境是有“哀”和“怨”的,并且,在她的笔下,“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毫无半点文饰造作,“故能引人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抱经堂文集·后山诗注跋》)但在《干校六记》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恰切的分寸感,不仅很少正面的这类描写,而且,举凡涉及这类地方之处,她不仅不加铺叙,笔墨都极简省,点到为止,并且出之谈远、平和,言近旨远,余味无穷。有一位同志看了《干校六记》之后,曾经说了下面几句话:“悱侧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照我看,用这几句话概括《干校六记》的艺术特点,是很恰切、很准确的。
《干校六记》的这一特点,也正是它能够“引”我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这里,我们也就看出了作者的精湛的艺术素养与功底。
《干校六记》在思想上也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特点,这就是作者在困苦的境遇中,极力去发掘和描写知识分子在冷酷境遇中内心高尚的情操,特别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的情操。这些我国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在年已花甲的情况下,被投诸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里,虚度岁月,这是怎样的民族的和文化的悲剧啊。但在作者所写的《六记》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绝望、沉沦情绪的流露和表现,而是不时地流露出对生活、对未来的热切的追求和向往。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劳动所形成的“集体感”或“合群感”,曾经给人们精神上带来多少愉悦,甚至幽默感。这种美好的、引人向上的情操的叙述,渗透在作品中的许许多多描写里。如在《误传记妄》中的一段描写,就是隽永无穷,颇发人深思的: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拚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象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季康和默存是几十年的老夫妇,始终彼此相敬如宾,和好如一,关于他们之间的爱情的美好的传说,我就听到过不少,当然也有个别外国报刊无中生有地造过他们“离婚”的谣言的,季康和默存都曾为此感到好笑。从这一段平实的而又感人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他们彼此相知、相爱之深。他们的希求是多么少而又少啊!一个窝棚存身,就心满意足了,仿佛真有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味道,可什么享受都“罢得”,唯独没有书,对于嗜书如命的他们老俩口,可真就是一件最大的不幸。默存是一个国际上名震一时的知名的大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祖国他是怀着多么真挚的一颗赤子之心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拚得人憔悴。”即使在那样非人的逆境中,“时光倒流”,他也丝毫没有任何后悔解放初期他坚决留下的抉择。为了社会主义的祖国,真可以说是“虽九死其未悔”,这是我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德(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优美的品德,应该提倡,却反对那种对待知识分子抱着极“左”流毒的人的这类主张:你应该虽万死其犹未悔,我呢,怎样对待你都属理所当然)。我说这里的描写很感人,却又很平实无华,是有大量的事实在,而且是很雄辩的事实在。就拿近年“出洋”,包括送子女“出洋”成风的情况来说,默存却令女儿放弃了英国国籍(她女儿出生在英国),回国工作。季康和默存,特别是默存,每年收到国外数不清的单位的邀请,甚至是重金聘请,例如说,去年美国几个学术团体邀请他去讲三至五次,一切费用归对方负担外,另付本人一万八千美元酬金,八次邀请,概被拒绝;今年美国加州大学约他们夫妇俩个去半年,“不承担任何任务”,允诺给予更加丰厚得多的报酬,他们仍然是“不去”。不止一个人闻之,认为钱某(有时也包括杨某)太傻:——别人争都争不到“出洋”的机会,而“洋人”那样盛情邀请他,并给予那么丰厚的报酬,他却一概拒绝,真真有些“反常”。但从这“反常”的表现中表现了怎样的精神境界!近年来,人们判断人、事,更多地重“实”不重“名”了。本来是“名”从“实”出,“实”先于“名”的,可是多年来我们只重高唱革命“高调”,却不务“实”酿成的灾祸,教会了人们不得不改变观察事物的方法,把头脚倒置过来,脚踏实地,从“实”和“实践”出发判断人和事。照我看,在这一方面,季康和默存的精神境界要比某些自居“革命”、实际至今仍然极左的人,要高超多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才会出现“反常”之讥。
最后是钱先生在《小引》中提出的“记愧”的问题。我倒有一种想法,即使“明知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却还要去充当“旗手、鼓手、打手”之类,若属偶为,尽管很不足以为训,却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既非积习,改也容易。倒是那极少数每每明知不是那回事、却总要在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最有资格“记愧”,倒是很应由这类人来补上这一记。如果真的刨心析肝地写,也肯定会写出很精彩的记传文字来。但话又说回来,这几乎又是绝无可能的。因此,这样一类的记愧,未来的考据学家又是很不易发现的,如果不是伪造的“赝品”的话。
一九八一·七·十
(《干校六记》,杨绛著,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钱钟书(默存)为本书所写的《小引》,见本刊本期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