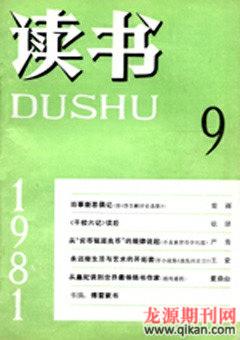旧事新思偶记
楚 雨
一想起邵荃麟同志,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温厚长者诚恳清瘤的面容。翻看了他的《评论选集》以后,才知道他在解放以前是如何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上海、汉口、桂林、重庆、香港等地,如何勤勤恳恳地在国统区和敌占区为进步的文艺运动而风夜匪懈地思索着、工作着。
早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荃麟同志就在《向深处挖掘》一文里说过一些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其深刻意义的话:
“今天我们……多少还是局限于新时代一般生活现象的描写……还未能更进一步的……反映出这历史发展的全貌,……因此直到今天我们没有产生史诗的作品……”
“新现实主义要求于我们的是艺术的真实,那是现实的最高真实,必须本质地去理解那些隐藏于生活和人物之后的社会与历史诸矛盾关系,……我们的作品才能表现这种现实的最高真实……”
“我们多少还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平面上,还没有从庸俗的现实主义中间解放出来。……”
“向深处挖掘,……从这伟大的历史场面中去探求人生、社会和宇宙的基本问题。”“首先我们认识生活的观点需要比现在更提高。这种提高只有从生活更深入的实践中才能获得,必须我们更亲切地去感觉当代人民怎样在爱、在憎、在悲痛、在愤怒,必须理解他们的思想形式,以及这种思想形式的变化过程。……艺术家必然是个真理的探求者……这些思想和理想,不仅不应被当前的单纯的政治概念所拘束,而且应该从新的现实的认识中间,去获取它更具体和充实的内容。作家的思想是与民族与社会的理想相关联的。历史的巨大变动,正在提供我们去探求一切问题的真理的最好机会。”
“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对于生活的战斗的实践,对于真与爱的热烈追求,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着的。”
我不得不抄录这么多的原话,因为这是荃麟同志文艺思想的概括与核心,是贯串于整个《选集》的思想,而且也大都是我们直到现在仍然在反复咀嚼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应该是非常令人惊异的吧?直到现在,不是还有人对于什么是“艺术的真实”,对于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对于怎样深化,对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包括生活实践)的关系,对于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在认识上仍然不很明确吗?
我们现在有没有“庸俗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呢?我看多少是有一些的。把“批判”与“暴露”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把批判看成只是揭露伤痕,只有否定的意义,而不是认为同时也有抚慰、医治、催发生机和肯定与歌颂正面事物的意义。又如,在批判思想僵化时,只停留在僵化者对于某个具体问题的思想认识上,而不知道去挖掘思想认识背后可能隐藏着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在反映因落实政策而引起的矛盾上,只是停留在政策在某个人身上应该落实、他的对立面如何反对落实这一平面上,而不知道去挖掘正面反面两种人物的两种心灵,两种生活态度,从而突破“问题”的框框,去阐发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做人的革命真理。还有,把“尖锐”与赤裸裸的刺激性混为一谈;写性格忘记了特定人物既具时代特色、又是特定个性的思维形式(包括语言特色);只注意写具体问题而忽略了历史性的大事件、大问题,也就是忽略了时代脉搏的大的跳动;强调了“针砭时弊”而忘记了深挖精神状态;不去注意强者与弱者两方面都有时代烙印的发展痕迹,从而去歌颂强者和唤醒弱者;容易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骄娇二气在或明或暗地滋长,以至于对争鸣和齐放形成了无形的阻力……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对于现实主义、对于“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以及“艺术的真实”、“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和作家的使命等等作了俗化或浅化的理解。无可否认,随着文艺事业的发展,有些现象正在克服中,但也有些现象似乎仍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邵荃麟同志的主张,其实就是要通过他后来所说的“现实主义深化”去克服“现实主义庸俗化”,而“深化”又与作家的思想认识、与理想、与世界观分不开,而世界观的提高又必须与战斗的生活实践和对于“真与爱的热烈追求”紧相关联。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他主张表现生活底蕴、表现时代矛盾的社会诸关系,以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这种艺术真实不但与正确的革命理想不是对立的关系,相反地是植根于生活实践的血肉相生的关系。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克服现实主义俗化和浅化的途径呢?我想也是的。
四年以后,即一九四六年夏天,邵荃麟同志又在《我们需要“深”与“广”》这篇文章里,对上述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以下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是具有比世界任何国家更深厚、更悠久的封建主义的传统……它的毒液浸透着广大的社会生活的土壤。”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终是要苏醒过来的,而且已经是在苏醒了。然而这个苏醒过程是痛苦而残酷的……这需要有正视伤痕的勇气,有刮骨疗毒那种忍受力。”“我们的青年朋友常常容易冲动和消沉,就是因为缺乏这种韧性的精神。我们往往容易作浮泛的呼喊,作伤感的呻吟,或者表现一些不痛不痒的‘人道主义,否则便是一套空虚无物的公式主义。”所谓主观的战斗力量,“也仍然是从客观的社会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所有这些话,也同样的并没有由于时移世易而完全失去其意义吧?
《选集》中还有两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即《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和《论主观问题》。它们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深沉的思虑,是捍卫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对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有力抨击。从《论马恩的文艺批评》一文可以看出,我在前面所摘录的那些话,都是荃麟同志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后,结合具体情况的具体发挥。
一九六二年八月,即《向深处挖掘》一文发表后过了二十年,荃麟同志参加了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作了《在会上的讲话》,于是形成了后来被“四人帮”列入“黑八论”的“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以至于被迫害至死。也许再过若干年后人们会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谈论现实主义问题和写什么人物的问题会有这么大的罪过?为什么历尽风霜艰险为革命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人,一位很有学问而又性情诚朴的老同志,会由于这样不成为理由的理由而变成了“反革命”?还是摘引一些他的发言的要点来加以研究吧:
“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没有现实主义为基础,也谈不到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就不可能不接触矛盾。粉饰、回避是写不好的。……写,是为了克服矛盾,是为了教育人民。为矛盾而写矛盾,也是不行的。”“这值得探讨,要从具体中去看,去解决,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有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写,我看不一定。”“比如农村有些干部,蜕化成敌我矛盾,象恶霸似的,能不能写?划条线也很难,编辑也很难,可以讨论一下。”
为什么这时提出要写矛盾和怎样写矛盾的问题来呢?因为当时是三年的大跃进刚刚过去,农村里的矛盾呈现得极为尖锐,不反映这些矛盾吗?那就没有现实主义,那就只好不写农村题材,那就会发生“创作危机”;因为,农村题材的作品在解放以后一直是数量最多和成绩最大的,可以说是文艺园地里的主要作物,是文艺刊物的主要支柱。但是,怎么写呢?从以上所引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文艺界从领导到作者和编辑都在这个问题面前感到为难——弄得不好就有戴上“修正主义”或“右倾”帽子的危险。
怎么办?于是荃麟同志(不仅是代表他个人)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问题。
“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只有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来写,不然性格不突出。”“所以,要研究人物与矛盾的关系。有些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似乎不是先进人物就不典型。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从这个理论出发,又发生拔高问题。”
简而言之,是要通过写中间人物及其矛盾,对农民、特别是对中间状态的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认为这样做既有助于宣传社会主义方向,又可以纠正干部的工作作风,还可以“反映现实的深度、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这就是“现实主义深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
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历史,也许比当时的当事人要清醒一些。需要考虑的是:通过写中间人物能不能较好地达到“现实主义深化”的目的呢?
“什么地方都有左中右”,这话从原则上讲也许是不错的。但划分左中右的标准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很准确,这是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用左倾的观点主观粗暴地划分左中右,从投机取巧的私心出发去肆意划定人们的政治面貌,曾经伤害过多少人!搞写作当然跟干具体工作和搞政治运动不同,作者不是对生活里的具体真人作鉴定和搞“政治排队”,但作者无疑的会受到某一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思潮的制约,于是就仍然避免不掉如下的可能性:没有把握就不写,于是农村题材的作品仍然不会多;跟着左倾的政策精神和政治思想转,写出了并不深化甚至极浅的、落后转变公式的作品;或者,只是有意无意地或欣赏或嘲笑中间状态人物以哗众取宠。这都是现实主义庸俗化的表现。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按照作者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认识,站在关心人民疾苦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立场,不管左中右的框框,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生活中的矛盾。
这后一种可能性在当时其实是不可能的。象《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绝对不会产生的。这也就是荃麟同志自己所说的并不是任何矛盾都可以写——他无疑的是考虑到当时可能发生的社会效果问题。
由此可知,“写中间人物”这一理论,并不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达到“现实主义深化”的有效途径。
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当时的创作思想仍然是有所突破的:第一,突破了只重视写英雄人物和以此为衡量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第二,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在现实主义受到极大打击的情况下,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于反映复杂的矛盾、对于现实主义、对于深化主题思想等问题的思考。第三,毕竟由于这一提倡而产生了一些所谓写中间人物的作品。因此,这一突破就有所触动:触动了由来已久的“只有写英雄人物才能反映时代精神”之类的理论;触动了当时左倾的政治思想;触动了不准真实地反映生活矛盾的禁锢;触动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
因此,后来对于荃麟同志大张旗鼓的批判是有特定的必然性的。其实不光是对他个人的批判,而是对整个大连会议、对所有与会同志的批判。
后来“四人帮”如此痛恨现实主义,把荃麟同志的“两论”同其他三个与现实主义有关的问题一起列入“黑八论”之中,说它们是文艺黑线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同样跟上述那些“触动”很有关系。
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历史不是已经作了回答吗?
(《邵荃麟评论选集》(共两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2.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