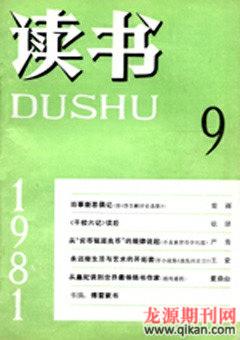一位“山野妙龄女郎”的出世
张启祥
二十五年前,范文澜同志在《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中,高度评价刘尧汉同志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下简称《过渡》)未刊稿,把它形象地赞誉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在文中热情洋溢地推荐说:
“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采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
“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而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下,摘出‘历史轮廓一项,借《史学》的地盘和吉士们会面。”(载《光明日报》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学》专刊)
刘尧汉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一书,已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他建国以来所写的包括《过渡》在内的十篇彝族民族学论文。这些论文题材广泛,资料丰富,富于创见,引人入胜,对彝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如彝族奴隶制的实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以及其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诸形态,都作了深入的探讨,这是建国以来出版的一部有分量的民族学论著,很值得大家一读。
正如范老在上文中所赞誉的,收入本书的论文都有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注重实地调查,主要是用实地调查得来的活材料,来印证历史阐明问题。作者在把现实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民族学资料,去探索解决一些长期被湮没或悬而未决的课题方面,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正因为这样,他的调查研究工作,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引起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前辈的重视,并有幸得到他们的亲切关怀和指导。
本书中发表最早的论文《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就是在史学前辈们的关怀下写成发表的。一九五三年,作者根据郭老、蔼老的指导,到云南哀牢山南诏开国君主的故乡深入查访,终于发现了彝文宗谱、灵台、巫画等资料,有力地证明唐代南诏王室蒙氏家族是彝族人,从而纠正了许多中外学者长期认为南诏王室属于傣族的旧说。这篇不见于史籍的《新证》,在郭老、翦老关注下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反映。泰国前总理乃沙立和英国的一位学者看到此文后,都信服地表示放弃他们原先认为南诏王室属于傣族的看法。
刘尧汉关于清代哀牢山区以彝族李文学为首的各族农民起义的调查材料,特别是他发现并抢救出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残稿一事,曾被范老誉为是对近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由于这些不见于“正史”的调查材料的发表,才使这次历时二十三年、以彝族为主体并有汉、白、哈尼、傈僳、傣、苗等民族参加的清代农民大起义,得以为世人所知晓,并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如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曾多次引用这些资料,肯定了这次农民起义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收入本书的《太平天国革命的一支洪流》一文,就是作者关于这次农民起义的研究成果之一。
解放初期,我国史学界仍多习惯于单纯依靠文献资料,而对考古资料,特别是民族学资料重视不够,甚至持有异议。针对这种情况,李亚农同志的《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一书,在援引刘尧汉《过渡》资料时指出:“拿中国现代的少数民族情况和古史作比较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是极正常、极普遍的研究方法,因为谁都知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其情况是大致相同的。”他并把《过渡》中收录的清代地主刘宇清总结其祖先统治经验的两篇短文视为“宝贵无比的两篇文献”,对其史料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见《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李维汉同志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一文中援引刘文上述资料时也指出:“从这篇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彝族社会由奴隶制度经过封建庄园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演变情形。”(见李维汉《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民族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
摩尔根致力于“印第安民族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类早期历史的原貌”,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刘尧汉对彝族民族学卓有成效的研究,也超出了彝族一个民族的界限,而具有着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
例如,他在《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一文中,通过对哀牢山彝族“祖灵葫芦”以及彝巫咒辞等民族学资料的剖析,结合对我国近二十个民族有关习俗及传说的考证,生动地阐明了我国各族原始先民曾有过母体崇拜——葫芦崇拜的共同经历。这种具有丰富内容的原始葫芦文化,形象地表明我国各民族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这是中华民族《创世纪》的神话传说。我国许多民族,语言各异,住地不同,但
再如,对曾在我国许多民族中流传的“十二兽”历法,过去中外学者多主张西来说,认为它是从外国传入的;虽有少数人认为应是中国的独立创造,但苦于缺乏证据;至于它起源于何时?为什么要用“十二兽”这种形式?则更是无从谈起了。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从历史文献考证“十二兽”历法起源得不出结果时指出:“考证起源的意义,看来完全属于考古学和人种学的范围。”刘尧汉正是利用民族学也即人种学的资料,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长期悬而未决难题的。前年他与严汝娴合写的《“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一文,通过对彝族原始图腾遗迹、纪日十二兽壁画、彝文《母虎日历》碑以及彝族祭祀、舞蹈等民族学资料的考证,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中国“十二兽”历法产生于原始狩猎、牧畜、农耕等生产及以此为基础的图腾崇拜,是我国各族先民自己创造的早于夏代干支历的原始历法。从而为祖国天文历法史研究做出了宝贵贡献。
收入本书的其他论文,也同样保持着“山野妙龄女郎”的青春魅力,读来令人兴味盎然,深受教益。例如在《羌戎、夏、彝同源小议——兼及汉族名称的由来》这篇不到五千字的短文里,作者根据彝族现实生活中保留的虎图腾崇拜和尚黑这两个突出的古俗特点,结合史料令人信服地论证:这些古俗与“三皇”之首的伏羲和“三王”之首的夏禹的密切关系,进而阐明了彝族与古羌戎先民(伏羲部落)、夏部落及汉族祖先之间的亲缘关系。本来,文献中的这些神话和传说,很多是真假难辨的,但作者凭借民族学资料这种“活化石”的帮助,就能使它们的社会历史意义得到复活。这说明在研究有关民族起源、民族形成这类史料少、难度大的史学项目时,从民族学的角度去进行探讨,是极为必要的。
刘尧汉同志是彝族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理事。他从解放初期一个在民族学领域学步的青年,成长为有成就的民族学学者,这反映了在党的关怀培养下,少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的一个侧影。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刘尧汉从解放初期参加工作时起,就立志要为祖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三十多年来,他一直为此奋斗不息。过去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我国民族学研究工作也走过曲折的道路,如曾出现过片面强调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忽视其他方面研究的偏向,甚至曾一度否定了民族学这个学科,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视为禁区,不准人们涉及。少数民族出身的刘尧汉同志,深知越是这些落后保守的方面,越较多地保留着原始因素和民族传统,其中不少是真实的历史资料,很有研究价值。因此,他一直排除干扰,顶住压力,锲而不舍地对这些资料进行抢救收集。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虽身处逆境,也从未中断过这种努力。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能很快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收入本书的十篇论文,有七篇是近几年来写成的。他这种不畏艰险、勤奋治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在忆及范老等前辈对他的关怀和教诲时,满怀深情地指出:这体现了党和老一辈学者对民族学的重视,体现了他们对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精心培育。作者深切体会到:这是出人才出成果的一个重要条件,自己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和党的培养、前辈们的关怀分不开的。这一直是激励他不断向前攀登的动力。
在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作者指出:“我在重视历史文献的同时,更侧重实际调查,这对民族学的研究至关重要。……我们研究历史,无非是依靠文献、考古和现实调查这三种资料。现实调查——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而言也就是民族学调查——所获的资料,因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关联,较前两种资料更为丰富、生动、充满活力,足以弥补前两种资料之不足。所以,范老把它形象地称为‘山野妙龄女郎,认为同她打交道往往是发现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得出新的结论的重要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解放三十年了,哪里还有什么‘山野妙龄女郎呢?事实上,不仅在远离交通线的深山密林中和海岛边境上,还有着未开垦的处女地;即使已经调查过的地区,也还有许许多多的‘妙龄女郎在向我们招手哩!”
在我国广阔的民族学研究领域里,确实还有许多“处女地”和“妙龄女郎”,急待人们去开垦、去结识。在祖国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这方面工作是很需要,也是大有可为的。刘尧汉同志目前正在川、滇交界的纳西族、普米族地区,为此进行着新的探索和努力。我们预祝他在与新的“妙龄女郎”打交道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刘尧汉著,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第一版,0.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