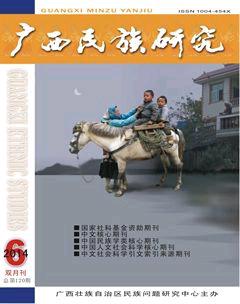近代华牧徐松石“中国认同”的三重变奏
[摘要]徐松石是近代著名华牧和“壮学先驱”。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汉一壮”交融的民族情感,中华大传统、岭南小传统与基督神学间的交织互动等元素,通过“知识一信仰”二元运行机制,总体促成了徐松石“中国认同”的三重变奏:早期延续家教传统,寄情于中华帝制往史和民国政治;居沪四十年,力推本色教会运动,希图“依照圣经真理,建立簇新的中国文化”,护教理念与国粹主义相始终,开创了“以文化成”的认同范式;晚岁流居港澳美加等地,信仰日趋保守而治学日见开放,力倡神本主义“灵治之道”的同时,欣然洞见“环太平洋”族群的华裔底蕴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并以之重构了海外浪者的“民族认同”。
[关键词]国家认同;本色教会;民族学;华侨华人
[作者]杨天保,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6-0123-007
引言:选题意义
近代时期,一方面,以古典经学体系为内核的东方价值系统行将解体;另一方面,受西学影响,中国近代科学也潜滋暗长,为知识全球化的到来奠定基础。中国多数士人在吸纳新知的同时,信仰日趋迷茫,知识与价值的分合离变,最甚于往昔。不过,作为一位带有壮族血统的近代学人,徐松石(1899~1999)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走出来,一步步地长成有影响的“岭南华牧”。学者论日:“松石先生走过一条学者兼牧师的生活道路。他一身二任,学术著作洋溢着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同时,字里行间又往往流露出悲天悯人的宗教情调。”
如其言,他“生平有三大兴味,第一是传道;第二是教学;第三是研究史地。而在史地研究中,尤其着重于东方民族历史的探讨。”宗教信仰、文教事业与民族研究,明显是他人生的三个内在变量。也正是此三者交相起作用,他的壮族血亲观与“汉裔情结”,他的儒家精神、基督关怀与佛老兴致,他那受多元文化陶灌后(含城乡文化、多民族文化、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等)的教育热忱,皆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集于一身,既推动了个性化的学术发展,呈现了别样的“中国认同”,也为今人再现了岭南儒学、近代西学和广西“壮学”交融互动、和谐发展的历史片段。
所以,以徐松石的学术发展和信仰变动为个案,基于其“环太平洋”华裔族群研究历程,考察儒学、西学和“壮学”三者交融互动的价值诉求,发现他个人重构“中国认同”的不同背景、资源、机制、路径和形态等,对于寻绎近代广西知识精英的崛起史事,以及在全球化时代里增进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皆不无帮助。
一、徐氏建构认同的知识背景、资源配置及运行机制
1.“西学东渐”格局
近现代广西,边患深重,战乱频仍,中外多种势力及其思潮交替渗透,广西传统乡土情结、民众信仰、知识体系和社会心态等倍受冲击。地方有识之士,以容县徐松石为代表,内承传统中原儒学迄于康、梁之际日趋彰显的经世理念,弘扬国粹,力践民族本位文化;外接西学体系中大肆活跃于岭南地区的基督普世情怀,关照心灵,推崇神性善意;内外并举,融民族文化、地方传统、边疆理念、宗教情怀、学者忧患于一身,创新“西学东渐”格局下的“中国认同”生成范式。
2.“汉-壮”交融的民族情感
徐松石生于岭南广西的一个汉(父系)、壮(母系)组合家庭,且属于“广东新兴县客家族”之后裔。一方面,他自幼就承接了中原历代专制王权向南力推的汉化进程,“汉裔情结”、客家风范等元素皆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激励于近代民族危机和西南边患现实,民族血亲观念和本土血缘结构日见清醒和强化,又顺利桥接出一种指向于壮族的自豪感。例如,他认为,“壮族在三代以前,布满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各省,这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土著,而且是今日最纯粹的汉人”。提出壮族族源“土著说”,强调了壮族和古代百越,特别是骆越、西瓯的关系,还相继阐发“壮族血缘荣耀观”、“壮族优秀论”与“两广居民含有70%壮族血质论”等。
于是,一种基于“壮一汉”交融的民族情感,既是他日后动态性建构“中国认同”的基石,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近代学人生命中的具体演绎。不可否认,土客间的矛盾纠葛,汉、壮族性的相异相吸,近代广西的“小传统”与动乱革命,西南边疆人口的流转迁徙,正好在其生命历程中,营造了一份持久的张力和紧张态势,皆为其建构“中国认同”带来力量和曲折离奇的过程。
3.中华“大传统”、岭南“小传统”与基督神学的交织
徐松石“幼读儒书,稍长兼爱佛老之学”,依赖于徐氏家学,他研读圣贤经典,续接了三教合流的南传脉络。其中,“君子言道”的人生抱负和精英救国的儒家理念,早已浮出水面。虽然他后来总体上完成了一篇“文化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宗教救国”的奇妙旅程,从最初依赖知识的再生产一步步转向去培育国人的信仰,但是,从中华“大传统”的角度来看,士人救国之志,明显已深入内骨,只是在不同时段的具体路径选择上,由原来的“外王”法度转向了追求“内圣”。
1916年,徐松石求学沪江大学,从此“税居沪上”,且开始系统接近西方文明,最终因为痴迷于基督关怀,让他的人生信仰发生了一次“教变”——在20世纪20年代初,皈依基督,成为一名基督徒,且逐步发展为“学教合一型”的著名牧师(信教-护教-传道)。为此,其父亲与徐松石这两代人之间,还引发出一次大决裂。可见,为争取心灵归属之自由权利,一是久别故园,已成难归之“游子”——“游子青衫有泪痕,伤心无路定晨昏。边城一点楼头月,岁岁烽烟锁梦魂。连年行役薄征裘,怅惜人间浊浪浮。家在梦中徒想念,生逢乱世动招尤。故园久别成千里,游子难归又一秋。主里韶光休自馁,好增灵命报亲筹。”二是长年“拒之”门外,流落他邦,代价尤重——“天伦诫命早开花,江汉滔滔是故家。总有福音传遍日,风情文物数中华。思亲有泪暗汰澜,俯仰乾坤意未闲。愧我奔驰常作客,靠袍怜悯独登山。东郊草色春晖在,南陌车尘塞鸟还。青露月明家国远,烟波魂梦渡津关。”
总之,居沪时期,传统家教体系与现代教育范式、岭南地方性知识与洋场新时尚、宗法权威与基督神权等新旧因子,盘旋周身,此起彼伏,个体生命已面临资源重组之亟。加之,抗日战火日盛,际遇遭逢,建构认同之路,复杂且艰涩!
1957年,徐松石离开大陆,先后侨寄于港澳、美加等地。时空虽异,但国学、“壮学”、基督教三者交织下的信仰格局,依旧是他建构“中国认同”的母体。三者间的磨合与冲突,作用于一身,基于资源、结构、旨向、风格等促成的个体生命一一做出全新的选择。
4.“知识-信仰”二元运行机制
在“西学东渐”的近代学术格局下,徐松石从广西内陆腹地(容县乡村),走入开放性的港口城市(广州→上海→香港→旧金山等),个人的学术趣向、视界和学品,也随着岭南“新学”浪潮、近代开放口岸文化、上海新文化运动、海外移民浪潮等多元因素的激励,总体上围绕着环太平洋族群研究这个中心点,已不断地向外拓展(岭南→大陆→东南亚→太平洋西部→太平洋东部→环太平洋),而东西兼采所形成的多学科间的科际整合(民族学、教育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地理学、人种学、语言文字学等),亦精彩纷呈。
但是,理性学术精神的开放式成长,并没有顺其自然地营造出一种开放性的信仰。相反,本色教会运动最终将晚年的徐松石推入到一个纯粹的宗教保守主义境地,个体生命中原有的民族情结、文化情感以及政治意念等,再度历经洗炼和重构。可以说,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理性”与“情感”二重分裂的命运(如王国维等),同样也在徐松石体内一一上演,且不断地修正并改写着他的“中国认同”。
二、“三重变奏”: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到民族认同
1.早期形态:政治认同
如上文所述,弥合因家庭出身(汉壮通婚)、出生地域(中原与岭南间的华夷分域)所带来的认同障碍,作为现实个体,徐松石当初最好的可选之路,就是仿照岭南客家前辈精英们调整政治“中心一边缘”模式的做法,极力地让西南边疆“小传统”归并且归正于中华“大传统”——通过对“中央王权”及其支撑系统——“正统”理念的认同,进而缓解、乃至于消匿自然存在的“夷夏”矛盾及其催生的心理负担。
于是,他早年认同的“中国”,明显就是留存于传统历史镜像中极具象征性的“中华帝制”,以及活跃在现实中的那个刚刚经由孙中山开启且日渐普及的“中华民国”。此期,他机械借助了新、旧“中央”的政治力度,去超越民族和地域上的隔膜,营造出“中国认同”的早期形态,难免既单纯稚嫩又不无模糊。所以,一旦遭遇波折,它就不攻自破。
例如,早年浏览广西金田村的心境是:“廿年成败说洪杨,民族英雄意味长。我过金田无限感,客家魂梦故园香。”景仰乡贤之情,溢于言表。但到了晚年,他却认为,洪秀全“所立宗教,则不伦不类,无补于基督教会。”更不用说,
“约五十万”之众的生命,亦因太平天国而终了。宗教保守立场已经完全改写了他对于“民族英雄”的乡土记忆。
又如,他的士人救国抱负也陷入困境。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国难之最后出路”,当在于“新国家的努力建设”,丝毫未曾失落对于民国政治的希望。但另一方面又一再宣扬:“以前所用各法均已失败,人心改正实为当今救国之要图”;“武昌起义是可庆的,然而中国的政治也就很不可庆了。”而且,自己著书立说,率然以“照流居士”自命。两相比较,国家政治建设之宏愿与个性自由之实践,已各为一枝,分流自便。1946年,上海市成立“助学联合会”反对国民党当局残杀学生、增加学费诸事,徐松石随同马叙伦、雷洁琼、许广平等一道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捐款事宜。对于民国政治的态度,实已走到了终点。
2.中期形态:文化认同
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格局中的“弱东方”形象、上海抗战的屡屡失利、西式教育科技的发达膨胀等,一步步解构了徐松石早年的“中国认同”。甚至于可以说,正是一种对于家、国的相对失望,一种“家国同构”传统观的大崩溃,刚好就为徐松石的认同嬗变洞开入口:他的坚持和信仰经历一种奇幻的“三步曲”——“决然断定欲使中国强盛,无需基督教道”→“欲使中国强盛,一切宗教都不需要”→“私衷以为欲救中国,只有基督教是可靠的”,一步步滑向反面,最终义无反顾地选取了基督!
由此,基于宗教信仰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开始在身体内急剧地分合换景。透过他此际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徐松石一方面皈依洋教,歌赞耶稣,与王治心等组建“中国基督教文社”,反击朱执信、李大钊等人掀起的“非宗教”和“非基督教运动”,信仰日趋于西化;另一方面却又与收回利权运动、“国粹”运动相呼应,强烈地坚守着一份东方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
所以,在信仰与知识这样一种双重保守性境遇之下,在“基督优势”与国学传统这样一种几近背反的框架下,在宗教情感与学术理性这样一种趋于分裂的状态下,他承接了吴雷川、王治心等人的做法——借用“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去寻求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出路,积极主倡“佛化基督”、“儒耶平等并存”、“儒化基督”、“以基补儒”等多种形式的宗教对话,希图以“本色教会”的调和方式,“让基督教配合中国的文化背景”,进而拥有“中国的形式”,最终去化解或圆通科学与宗教、知识与信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如其言:“宗教与科学全无冲突,科学须靠宗教,而宗教亦须多靠科学。二者非但各有园地,且实相依为命也。”
所有这些调整,皆为重构认同提供了契机。于是,此际他那对于中国神话、先秦民族史和南方地名学的兴致,他那力求“教学充实、人格感化、宗教实践”的人生新原则,他那相继出版发行的《耶稣眼里的中华民族》(1934)、《中华民族眼里的耶稣》(1935)等等,皆已超越“政治”视域,总体上换成一种文化的温和视角,既“采取耶稣基督的立场,以衡量中华民族的文化”,又要“用中华民族的意识去看基督教道”,逐渐将一个新生主题——“文化中国”,植入认同体系之中。东方、中华、本土等用辞,都只是“文化中国”的象征表达而已。
徐松石基本依循了张文开的“基督审判文化”路线,清醒地认识到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张力,大力号召中国基督徒必须对自己的文化具有欣赏和批判的能力。但与其他近代华牧相较,他对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缕述,最为系统、独到;既视《圣经》为真理,更强调“本土化”原则,以优补缺,最后“依照圣经真理,建立簇新的中国文化”。
当然,让西方新教伦理“中国化”,它颇似于在病体上嫁接新枝,流露出来的总归是一种绝望的文化本位主义。而且,思索进程越是理性、深刻,结果就越发让人惊悚,既悲怆又无奈。所以,徐松石中期致力于“以文化成”的中国认同观,最显辛苦沉重和煎熬苦痛。
3.晚期形态:民族认同
1957年,徐松石作别上海,潸然南下,异路赴港,别求生存发展空间。1962年出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将那份离别大陆的宗教信仰,推向保守固执的顶端,直接跳入到一个“神本位”的新阶段——自我否定和彻底批判在人本主义基础上实现“儒耶通约”、达成“优势互补”的种种神话,开始力图将跌人人本主义陷阱的本色教会运动和那一种朝向“东方的深坑,即通常所谓诸教合一”的大陆神学,引入神本主义的新轨道。由此,他响亮提出:“圣经的本色方才是真正的本色。”
可以说,入教初期,青年徐松石还只是视宗教为政治之辅助,且确信基督教的工具理性价值——“基督教非但是最大真理,而且是最大实用:第一能赐作事之能力及安慰,第二能使吾人感觉人生之真正兴味,第三常能增加吾人之人格感动。信主耶稣,确为人生最合实用之事,非仅得蒙救赎而已。”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它能促进“民主精神的发长、正当国家和国际主义的提倡、完美物质进步的取获”。但中晚年寄居海外,他转而以华侨的新身份坚信,宗教信仰本身就是改造中国的灵丹妙药,基督教就是一切,它已经包含了任何形式的政治努力和科学追求。显然,“在港十八年,常感惊弓之鸟,余下时间,全属于神,已非自己所有。”那一段“惊心蒿目”之类的流离命运,的确令他更加依赖于基督,将其作为心灵慰藉。同时,宗教系统本身的内在张力,也日久生情地让徐牧师最终走上了固执之路。
此时,宗教信仰及其象征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他原本对于耶稣的国家主义诉求。徐松石告诫信众:“其实基督教并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是非常独特的属灵启示和救恩。”而超越礼治、法治的“灵治之道”,因为坚守政教分离的古典原则,彻底脱尽了政治功能的羁绊,所以“才是人世间最高尚的道理”。
于是,他强调,“今日的问题,绝对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是否能够容纳基督教。更加不是基督教能否屈就,或配合中国固有的文明。问题的症结或重心,在于今日传扬中国的基督教,是否出于耶和华神,而与耶稣基督的启示相合。”“主耶稣基督”胜过了一切的“武备”、“物质进步”、“爱国心”和“新民族道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需要”。而且,“使基督教生根于中国文化环境,而同时在中国产生簇新的文化,最后的目标,只在令人靠主得救而已。”这其中的道理就是,“须知文化不能救赎人的灵魂,思想亦不能给人以灵魂的救赎。能够救人灵魂的,只有耶稣基督。”即便是去探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孝道,他还是提醒:“高尚的孝道永远是流,耶和华神和耶稣基督永远是源。”……显然,“文化中国”已时过境迁。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学术研究却又朝向了另一境界。
居港及赴美以后,随着学术视野和生活空间的拓展,徐松石已经将自己早期的中华族别史研究(以东夷诸族、客家学为重点,“壮学”研究为最著),推向中华民族形成史和国际民族关系史研究阶段,提出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是东方文化曙光的产生地”“马来族、日本大和族和中国的吴越闽粤族,以及苗瑶僮傣佬掸等族,实在是同出一个渊源”、“南支汉族和北支汉族的开化,最低限度,是出于同时”、“南洋民族的鸟田血统”、“华人发现和开辟美洲”等一系列新说。基此,一种“环太平洋地区”的新型“华化论”史观,已悄然形成;“目观平洋成内海”,即“把太平洋看作中国内海”的观念,最见活跃!
可以说,徐松石“离乱余生,专心传道、著述”,主观上虽然强迫自己背过身去,与往日认知的中华帝制、新旧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三大改造运动等,皆谨慎地保持一些距离,但是,一种超越于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道德文化的“民族”情结与“侨胞”诉求——“文化不能拯救世人的灵魂。但文化与民族气质的养成甚有关系。民族气质又关连到民族生存的命脉”;“鸟田同胞富于团结力及扩展力”……还是将他系于再建“中国认同”的历程之中。
“别后千山远,连年苦恨滋。干戈为客早,贫病寄书迟。辜负传经志,徒伤反哺私。羁情随鹜影,飞向故园湄。”徐松石置身海外,故土情结和回归本土的期望一直未断,一生写有大批此类诗作插附于各种著作。但与此同时,他通过潜心研究,以诸多的学术发见,补济了自己对于故国的思念和认同。作为一名逸出“东亚文化圈”的浪者,他终于解脱了多元民族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指标,而在全球民族史的比较研究中,不受其阻地发现了中华民族各部族“多元一体的奇象”:首先是“分后必合”(因),迈向民族融合始终都是主流,结果,“多元一体,巍然独存”(果),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文明历程依旧持续不断,创下了世界奇迹。接着就是,“无论怎样多元,中国实在是今日中国同胞生于斯、长于斯和老于斯的故国”(因),有了这一“故国”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无论天涯海角,“中国同胞本来是一体的”(果)……遥望故国的海外游子,已基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重塑了自己的“中国认同”。他确信,当时散布于世界的华侨教会,都“渴望有一天能够回到本土”。
三、余论:近代华侨学人建构“中国认同”的现代启示
徐松石生平几近纵跨3个世纪,亲历中国近代多次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集政教风俗、个人材性、多元区域文化于一身,既与胡适、李大钊等人文笔相较,检讨旧学,写就《粤江流域人民史》(1938年)等学术名著,提倡民族主义史论,震动学界;又与张文开、刘粤声等近代“岭南华牧”一起,倡导民族自觉和信仰自由,为建构独立的“心灵体系”而汇成流派,转引一代时风。所以,“一个学者,思不离业;一个牧者,信不离主”,带有壮族血统和客家风范的徐松石,个人建构“中国认同”的复杂历程及其丰富内涵,对于在今日全球化进程中,引领、重塑并刷新境外华人聚居区的中国认同(尤其是“环太平洋”华裔族群的中国认同),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意义深远。具体来说有以下启示:
1.积极开展全球性的“知识对话”,创新“中国认同”的建构范式
海外华人复杂的知识背景,是开拓价值空间的一切起点。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家族伦理、社会关系、教育历程、血缘结构、文化偏好等多类知识单元,皆是能独挡一面、举足轻重的影响因子,将其汇集一处,则更是建构“中国认同”的理想支点和社会资本。正因为如此,徐松石等近代华侨华人认同的“中国”极具多元形态。无论是政治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还是宗教的中国;也无论是理性化深思熟虑的认知,还是情感体验式的自然接受……它们都是华侨个体知识独特运行的价值产出。可以说,时代日新,观念日新,任何一位海外华人都很难坚守某种固定不变的“认同”形态。即便在同一时间断面上,他们也会由于某些知识因缘而形塑出不同的“中国认同”。所以,切忌以国人的标准、国内的尺度,去评判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
同时,在知识日趋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个理当清醒的事实就是,源出中国本土的知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全球化情景下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它并不一定必然建构唯一朝向“中国”的认同。因为任何知识教育的结果,它都开放性地去营造某种信仰系统和价值体系,但二者间常常缺乏可确知的限定性。例如,当下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习练本土知识、地方性知识越多者,个体就越发地解构了自身的乡土观念和在地意识!
就目前的海外华人主体而论,他们多数相当于徐松石的第三、第四代子辈。正如徐松石所论,他们与从1949年开始的“大批中国人的海外移殖”进程相比,其运动性质、与基督教发展之间的关系,皆已不同。家庭隔代传承的障碍,加之远隔大陆的教育环境,已让他们基本长成为东方文明的陌生人。但是,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空白,并不足以说明他们由此就无从建构“中国认同”。因为,东、西方的知识性对话与交接,同样能促成他们基于西方知识体系的理性立场,反观和欣赏“中国认同”的全球意义与价值旨向。所以,在“输出文化”、忙着为对方补济知识缺失的同时,开展全球性的知识对话,求同存异,基于“知识一信仰”二元运行机制,创新“中国认同”建构范式,才是调整侨务策略的有效选择。
2.紧扣学者型华侨精英,扩充象征资本的网络空间,实现更大的群体认同
一般而论,海外华人群体都组建有自己的社团,且已经是一个初步实现了自我管理的“自组织”。其中,它们自觉培育了自己的“知识精英”,构建了“智囊团”。历经发展壮大,精英们在侨团组织中的地位、声望与社会权威,已积累成为一种全新的象征资本,如东南亚华人政治的成功,与之不无关系。
由此,将侨务工作重点从以往单纯关注政治领袖人物,部分调整到知识精英及其象征资本身上,在设计政治对话之外,强调“学术对话”,以便借助于知识精英“权力的文化网络”,更加深入洞悉华人社团的规模分布、社会实力、权力结构、组织方式和信仰构成等,进而去建构一种更具群众基础的“中国认同”。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