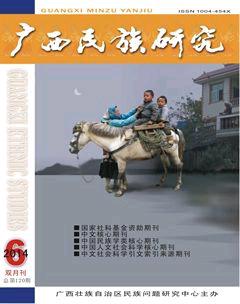论民族习惯法的生活伦理特性
[摘要]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地区适用的民间法具有丰富的生活意蕴和伦理内涵,并表现出鲜明的生活伦理特性。主要体现在:与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相对应,民族善恶观念表现出生活化多元性;与民族法渊源的习惯性相吻合,习惯法规范作用模式呈现出相对的封闭性;与民族习惯的法律化相联系,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丰富的道德生活属性。
[关键词]民族;习惯法;生活伦理
[作者]唐贤秋,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6-0032-007
习惯法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必要补充,在调节社会利益冲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内聚着不可低估的功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常常被法学界人士誉为“身边的法”、“现实生活中的‘活法”等等。而民族习惯法作为整个习惯法体系中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一种习惯法,是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在民族内部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用以调整民族社会内部成员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规范。目前,学界对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大多是从法人类学视角进行实证式的描述研究或文献资料整理研究,这种研究范式无疑是必需的。但由于民族习惯法具有鲜明的价值特性,故对其进行价值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尽管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一些积极探索,但依然没有跳出法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其实,民族习惯法作为关乎民族地区百姓生活的行为规则,寓于民族生活之中,并在维护民族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着法律的与道德的双重调节作用。因而,它在彰显出一定法律精神的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生活伦理意义。本文试图对民族习惯法的生活伦理做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与民族善恶观念的生活化多元性
(一)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
民族习惯法虽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的法律而只是民族地区的一种“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准法规范”,但它却在调节民族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一定的法律效力,并由此形成一定的民族习惯法关系。这种关系的主体是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或具有一定民族身份的人。在民族社会中,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促使不同民族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并决定了不同民族习惯法具有其特有的“民族习惯路径、个体心理依赖、民族文化传承的支撑”,由此决定了民族习惯法主体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
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主要是指习惯法主体因民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民族个性特点。民族性是对民族习惯法主体的性质定位,它表征的是民族习惯法关系主体的民族生活个性化。也就是说,某一具体民族的习惯法,是体现该民族生活特性而非其他民族生活特性的习惯法。比如,在壮族习惯法中,壮民族在生活中十分崇信地气龙脉,风水堪舆之术盛行。建房、立庙、下葬、修墓皆请地理风水先生来择地、测向。若掘地开荒,有地理公认为犯了村中的龙脉和方向时,可进行劝阻,不准动土。如果不听劝阻,以后村内不管人畜患难或损失,概由动土开荒者负完全责任。壮族习惯法中的这种禁犯龙脉的做法,便体现了壮民族的乡土生活性。又如,在侗族习惯法中,侗族利用“款条”的形式将侗族生活习惯形成一种公认的行为规范,为了保证村寨安全,侗族各寨联成大款,共同抵御外敌,倘若某村寨受到外敌入侵,则火速向联款各寨求援,若接到求援的村寨不履行应援的义务,事后则要按习惯法加以严惩,开除款籍,各村寨都会孤立不遵守约定的村寨。由此可以窥见侗族习惯法主体的侗族个性。再如,瑶族习惯法以特有的“石牌制”方式管理本族社会,从而体现出瑶族习惯法主体的瑶族生活特点,也使得“瑶族习惯法成为瑶人自我识别和民族认同的基本内容”。民族习惯法主体的这种民族性,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乃是“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这种因民族文化习惯的不同而体现出民族习惯法主体的生活个性,正是民族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体现。
民族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还表现出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生活区域性或族群性。即同一民族的习惯法因民族生活地域或族群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生活化形式。以瑶族为例,瑶族这一山地民族因分布地域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支系,而“不同支系、不同地区的瑶族习惯法也存在地域差异”。如广西金秀瑶族在社会组织方面实行石牌制,广东连南瑶族则实行瑶老制;广西金秀瑶族新娘婚后即在夫家长住开始家庭生活,广东连南瑶族则有新娘不落夫家的习惯。广西融水一带的红瑶规定同姓不通婚,而广西大瑶山一带的茶山瑶却可以同姓通婚。又如苗族习惯法中的“议榔”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管理生产劳动、调解民间纠纷以及抵御外侮外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民间议事会组织在苗族不同地域或族群中的表现形式却不同:即这种“议榔”制度在黔东南苗族那里称为“议榔”,而在湘西苗族那里称“合款”,在云南苗族中则叫“丛会”。由此可见苗族习惯法体现出主体的不同地域性或族群性特点。
(二)与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相对应,民族善恶观念呈现出生活化多元性
民族习惯法主体的民族性,固然表征出不同民族生活的文化特色和民族习惯法文化的丰富多彩。但是,由于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环境、心理特征与民族性格不同,导致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也具有很大的不同,由此使得不同民族的生活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如不同民族的善恶观念便呈现出一种生活化多元性。所谓民族善恶观念的生活化多元性,是指不同民族对善恶价值观念的理解,不是根据一种脱离生活的抽象化标准,而是依据具体的民族生活特点来诠释,从而赋予善恶价值观念以丰富多彩的生活化内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善恶观念在不同民族生活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二是民族善恶观念具有生活化多样性。
一方面,民族善恶观念在不同民族生活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在一个民族生活中是被禁止的行为,却在另一个民族生活中是被允许的事情;在甲民族生活中被认为是合法的事情,但却在乙民族生活中被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如未婚先孕在不少民族看来是很羞耻的事情而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与谴责。但在藏族部落中,未婚先孕却不受社会谴责,私生子也不受社会歧视。在婚姻习惯法中,彝族认为,族内通婚是一种可以强化民族自我意识的行为,因而对此加以提倡。彝族谚语说:“黄牛不入水牛圈,水牛不同黄牛牧。”广西南丹白裤瑶与贵州荔波青裤瑶则流行姑舅表婚。在他们看来,姑舅表婚可以亲上加亲,娘亲舅大,“舅爷大过天”、“舅爷要外甥,哼也不敢哼。”有的民族却反对族内通婚而实行单向氏族外婚,如独龙、景颇、德昂、阿昌、达斡尔等民族便是如此。他们认为,族内通婚形成一种“血倒流”现象,会给子孙带来灾难,因而认为这是一种恶行而必须加以制止。有的民族认可同姓通婚,如壮族历史上便有“婚不避姓”的记载,而有的民族则禁止同姓通婚,如彝族、佤族、水族、苗族、哈尼族等,在他们看来,同姓表示同宗、同族、血统相同,同姓结婚是对祖宗的不敬,会得罪老天而遭到惩罚。于是,他们便将同姓通婚视为一种恶行而加以惩罚。可见,一些民族对善恶观念的理解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恩格斯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如此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民族善恶观念又呈现出浓郁的生活化多样性。以禁止偷盗为例。禁止偷盗是所有民族习惯法中强令禁止的行为规范。但一些民族并不是一刀切地将那种私下变更他人财物所有权的行为视为恶行而纳入偷盗之列,而是依据生活中的具体情形而定。一些少数民族将那种在生活中遇到难处而不得已实施的偷窃行为并不视为偷窃,而只将那些轻轻松松不劳而获地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才视为一种偷盗现象。如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族,外出行猎者常常把猎获物挂在树上而继续行猎。若过往行人非常饥饿,将猎人挂在树上的猎物取来充饥而不算偷盗;但若吃饱后还把兽肉、兽皮带走,则算偷盗。在拉祜族,出远门的人若在出去时随便吃食他人放在路边蜂桶里的蜂蜜视为偷,要赔偿主人一桶蜂蜜;但若行人回程时处于饥饿状态而将他人路边蜂桶里的蜂蜜充饥则不算偷。他人地里栽种的玉米、黄瓜等可以取来充饥,但若带走则就算偷。在独龙族,行人路过玉米、马铃薯等庄稼地时若感到饥饿而取来吃食则不算偷,但要用两根竹片交叉插在地上,以向主人表示是饿了取食的。在贵州省贵定苗族那里,在山林里砍伐他人的树苗算偷,要处以罚款;但若砍伐他人干枯了的树枝则不算偷而不受惩罚。武陵山区的土家族人围山打猎时,有猎人为了追赶野兽常常翻山越岭而风餐露宿,土家族习惯法规定,如果此时猎人身上的干粮带得不够而吃食他人地里的包谷而不算偷,包谷的主人不能追究。这种根据生活中的具体情形来判断某种变更他人财物所有权的行为是否属于偷盗的民族习惯法,体现了不同民族善恶价值观念的生活化面向,他们在强化一种生活习惯的制度秩序的同时,特别照顾到在生活中遇到难处的人群,尽管在习惯法的司法实践中增加了判断操作的难度,但却观照出一些民族习惯法背后所包含的一种朴素纯洁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品质。
二、民族法渊源的习惯性与习惯法规范作用模式的相对封闭性
(一)民族习惯法渊源的习惯性
在多民族国家中,基于调整民族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民族习惯法,是以民族习惯作为其主要渊源的,其中包括成文的习惯和不成文的习惯。
关于习惯的解释很多,有认为习惯是“指经过练习或重复而被巩固下来并成为需要的一种行为方式”;也有认为习惯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一贯的、稳定的行为方式”;还有认为习惯是“人们的同一行为经多次重复而在实践中逐渐成为习性的行为方式”;另有认为习惯是指“相沿积久重复出现而形成的惯制、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尚习俗等的总称”等等,这些解释都强调了习惯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且这种行为方式是经过社会生活中的多次实践反复巩固而成的,因而具有一种积习性、持久性、稳定性和不易改变性等特征。据此,我们可以对民族习惯做出如下界定,即民族习惯是指在民族社会中,民族共同体成员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一种通行于某一民族内部的生活惯例或该民族内部成员自觉奉行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
当一种习惯只是符合个人需要时,它并不具有社会性。但当一种习惯符合社会的需要、并为社会所认可而被广泛接受时,则形成一种社会习惯。社会习惯与社会风俗一起成为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并产生一种行为约束力量,当社会习惯成为普遍公认的社会行为规则,并经过国家机构的确认而被赋予法律的效力时,习惯便因此演变成一种习惯法。对此,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的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
可见,习惯法是在习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习惯成为习惯法的主要渊源。许多思想家都强调了这一点。柏拉图说:“在古代,人们当时尚无立法者,……人们根据习惯和他们称之为他们祖先的法律而生活。”英国历史法学家梅因说:“在人类初生时代,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惯行。”马克思对此指出:“习惯法作为与制定法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法和法律并存,而习惯是制定法的预先实现的场合才是合理的。”恩格斯也指出说:古雅典和古罗马“两种立法,都是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这些表明,习惯法在渊源上具有突出的习惯性。同理,民族习惯法在调节民族社会的生活秩序中也主要沿用习惯这一基本形式,民族习惯法的形成由民族传统习惯演变而来,民族习惯法的内容和形式带有民族和地方乡土惯有的特色,民族习惯法的实施有赖于民族传统习惯的作用。譬如:将杀人者绳之以法,这在许多民族那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藏族、彝族等一些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他们更关注“赔命价”现象,即希冀通过偿付杀人命价的方式来消除命案之间的冲突。在藏族人看来,杀人偿命也是一种杀生,而杀生是有罪的,因而认为赔命价比对罪犯判处极刑更重要。彝族人也认为,偿付命价是化解侵害方与受害方之间矛盾冲突的最能让人接受的方式。这种讲求“对价”而不是形式“对等”的习惯法,在价值选择上否定了复仇式的冤冤相报,也在现实生活中排斥了那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冲动。有的民族习惯法是以成文的形式出现的,如瑶族习惯法中的“石牌律”,便来源于一种成文的习惯。有的民族习惯法则以不成文的形式出现,如在瑶族、土家族等民族生产习惯法中,有人要开荒种地,就在认准的地块上打上草标,置于地头显眼的地方,别人看见后,就不会来争地。又如一些民族内部发生各种纠纷时,往往请村寨内具有一定威望的头人出面调解,头人在调解期间的膳食等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还要支付头人一定的“服礼”费;而胜诉方也得给头人送礼以表示酬谢,等等。这些便是一种不成文的习惯。习惯以其突出的稳定性和对社会生活的调节性以及可接受性而在习惯法渊源中具有重要地位,以致有学者说:习惯法“来自于社会中业已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习惯;离开习惯,习惯法便无从产生”。“习惯法是以习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没有习惯就没有习惯法。”
(二)与民族法渊源的习惯性相吻合,习惯法规范的作用模式呈现出相对封闭性
民族习惯法是以一定规范形式而存在的,但这种习惯法规范的作用模式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即民族习惯法规范的作用范围只局限于某民族甚至是族群内部而对其他民族或族群并不产生作用效力,其作用面向只关注民族内部生活秩序而不关注民族外部生活状况,从而使得民族习惯法规范作用偏重于对内封闭的约束模式而不是对外开放的引导模式。
一般说来,国家制定法规范不仅以其强令否定的方式(即“不准如此”)告诫人们必须禁止什么和反对什么,而且以其带有命令式的肯定方式(即“必须如此”)昭示人们必须提倡什么和坚持什么。因此,国家制定法规范作用是一种约束与引导相结合的开放模式:即它不仅强化对人的行为约束,而且积极引导人培养法律思维与法律信仰,从而实现人对自身的超越;不仅关注内部关系的协调性,而且强调外部关系的和谐性。
民族习惯法虽然也以“必须”或“不准”的强制肯定或否定方式对民族社会及个体成员的行为发生作用,其中,“不准”,以强制否定的方式明确告诫民族社会及个体必须排斥相应的恶行;而“必须”,则以强令肯定的方式明确指示民族社会及个体必须遵循相应的善行。比如,侗族习惯法规定:“各家弟男子侄必须尊敬长上,和睦亲族”、“不准交结外人人村引诱人家子弟骄奢”、“不准打牌赌博,违者责罚钱三串文”、“不准持刀逞凶吃酒滋闹,违者公罚”、“妇女不准横行咒骂恐生祸端,违者责罚”、“春耕之田各有坝水灌济,不准拦腰截放”、“秋收之期毋得任畜践食五谷,违者量地赔还”、“茶桐油子熬期不准乱行摘取,获得责罚”、“早夜不准面生之人牵牛过境,务须盘查”等等,这些习惯法规范便是以“不准如此”的强制否定的方式来对相应行为进行规约的。广西金秀瑶族习惯法中的石牌制,也大多以“不准如此”的方式来对相应行为进行规制,其中虽然也包含了一种“必须如何”的肯定方式来对相应行为进行价值引导,但这种价值引导却是服从于对民族固有习惯进行维护而不是进行改造之需要的。
由于民族习惯法主要依靠民族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发生作用,而习惯是经过世代积淀而成的,表现出顽强的守旧性和超强的稳定性,于是,民族习惯法规范在发生作用时,在习惯与传统的后拉力中强化了对内的约束性,即强化对过去业已形成的传统习惯的遵循;但却弱化了向外的开放式引导性,即弱化对固有习惯进行改造的未来面向。民族习惯法规范作用模式的封闭性表明,基于民族习惯这一渊源的民族习惯法,反过来又延续了民族习惯的传统性,强化了民族习惯的守旧性,巩固了民族习惯的稳定性,从而在民族习惯与民族习惯法之间形成了一个内部封闭的循环系统。
三、民族习惯的法律化与习惯法的道德生活性
(一)民族习惯的法律化
从本质上说,民族习惯法是一种民族习惯的法律化。所谓民族习惯的法律化,是指民族习惯经过国家立法或司法等形式的认可而向法律规范的转化,从而实现民族社会在解决诸如生产、分配、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公共事务、民间纠纷等问题方面有法可依。一般说来,一种社会习惯要能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应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对相应的行为进行规约而国家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制;二是这种习惯必须以不违背公序良俗为前提,且为公众接受认可从而产生一种约束力。
民族习惯之所以需要法律化,是因为法律是社会治理中最有效的方式,而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不健全,迫切需要法律制度的规约;而在民族地区,民族习惯在弥补法制建设不足的同时,也明显表现出自身的不足:即民族习惯虽然因其稳定性而产生一种约束力,但由于民族习惯往往因为约定简单、笼统而具有不严密性和不系统性,加之法外的干预性因素多,必然使得民族习惯在调节民族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于是,民族习惯的约束力自然难以产生一种权威性影响,而民族习惯的法律化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可以说,民族习惯的法律化能够促使民族习惯的功用“借助于法律得以‘硬化或最大化。”
民族习惯之所以能够法律化,是因为习惯与法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人类历史上,法律最初是从习惯发展而来的,法律原本就具有习惯的特性。人类最初的法律来自于原始禁忌,马林诺夫斯基引用哈特兰先生的话强调了这一点:在原始社会中“法律的核心是一系列的禁忌”,“几乎所有的古代法典都由禁止性规定组成的”。其实,这种禁忌本身便带有习惯法性质,法国学者布律尔强调:“习惯法在暗中制定新的法律,犹如植物和动物还未出生时的潜在生命,它是法律规则的生命力,它的应用范围是无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法律的唯一渊源。”习惯不仅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而且成为制定法的重要考量因素。“无论你承认与否,习惯都将存在,都在生成,都在发展,都在对法律发生着某种影响。习惯将永远是法学家或立法者在分析设计制定法之运作和效果时不能忘记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在民族地区,民族习惯常常成为调节民族利益关系的巨大力量,它在调整民族社会的生活秩序中,有时甚至发挥着国家法都无法完成的作用。鉴于此,民族习惯的法律化,决非是在民族地区无视民族习惯去推行国家法的一元化,而是在尊重民族习惯的基础上,借助于法律促使民族习惯的功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民族习惯法正是顺应了民族习惯的法律化要求而产生的。
(二)与民族习惯的法律化相联系,民族习惯法呈现出丰富的道德生活性
民族习惯法具有丰富的道德生活属性。因为,“习惯是民众生活方式的一种主张,因而是生活化的。”作为关乎民族社会百姓生活的行为规则,民族习惯法既是准法律性质的规范,又是伦理道德规范。比如,在布依族、苗族、侗族、瑶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留存下来的习惯法碑文中,无不强调世人要遵守伦理道德,扬善去恶,远离犯罪。云南哈尼族习惯法规定:晚辈必须尊敬长辈、妇女应遵守妇道、村民村寨之间和睦相处等等。彝族习惯法汇编之《彝族礼法经》规定:人们要遵守法度、尊天敬地、尊师重道、团结友爱、迁善远恶,“心要想善事,手要做善事,身要行善事”、“唤醒民众心,要传伦和理”。这些习惯法规范因而又被称之为生活中的道德箴言集。一些少数民族将习惯法规范与伦理道德规范融合于生活之中,使得这种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性质的规范更具有了生活的意义。如土家族习惯法规定:称谓他人,无论亲友长幼,须显示尊敬对方。走亲访友,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未跨进门,要在门口提前打招呼,做到“人不到礼行先到”。若有人在行走山路中相遇,在路险窄处,都要礼貌让路,少让老,大让小,强让弱,等等。民族习惯法不仅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准则。许多少数民族生活在大山之中,他们深知森林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于是特别重视造林护林。如土家族习惯法规定:封山育林期间,禁止放牧牛羊,禁止打柴割草,禁止砍伐树木,禁止放火烧山等,如有违犯者,必受处罚。壮族习惯法规定,婴儿出世要种植几株树,待以后结婚,甚至送终之用。仡佬族习惯法规定:在人去世之后,要在坟墓旁种植泡水树、柏树、黄杨树、松树,作为纪念,称为风水树。在侗族习惯法中,侗族《款条》规定:“向来山林禁山,各有各的,山冲大梁为界。……莫贪心不足,过界砍树”。这些具有生活气息的民族习惯法,无不透露出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道德情怀。
当然,民族习惯法的道德生活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习惯法的道德性只是局限于本民族或族群内部,而对其他民族或族群是否具有道德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仍以禁止偷盗为例,如云南佤族、川西藏族等对发生在本民族部落内部的偷盗行为认定为恶行,于是对偷盗犯的惩处也非常严厉;但他们对本族人偷盗外族人的东西,或本部落成员偷盗其他部落财物的行为,却不加干涉和追究。云南小凉山彝族习惯法规定,偷盗本家支的财物,是违法行为而必须加以惩罚。但偷盗有冤仇家支的财物,则本部落不加追究和惩办。这固然与不同民族善恶观念的差异性相关,但还是折射出一些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道德性的民族局限性。在藏族一些地区,习惯法规定:对在部落内部行偷者,处没收一半家产;若偷本部落头人、牧主的财产,则处没收全部家产,打成残废,逐出部落。由此体现出一些民族习惯法适用对象的不平等性。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在面临着多元化纠纷而难以解决时,往往采用神判法,即借助于神的力量来强化人们对判决结果的信任度。他们甚至还采用诸如喊村、捞油锅、砍鸡头、砍鸡狗猫等方法来判决疑难案件,这些不仅表现出一定的愚昧性,而且与国家法发生明显冲突,也在事实上容易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因而,对民族习惯法中不适应社会时代发展的内容进行改造,以保持其与国家法的相适应性,乃是民族习惯法的未来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