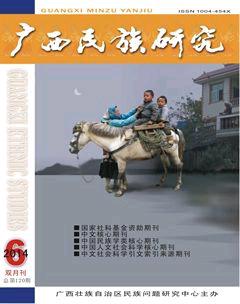再论仫佬族族称、族源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吴国富 林义雯
[摘要]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南方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民族之一的仫佬族族称、族源和民族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角度重新论证和探讨上述问题,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关键词]仫佬族;族称;族源;民族关系
[作者]吴国富,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宁,530006;林义雯,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11级本科生。上海,200042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6-0052-007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导、政府和学者共同推进的少数民族族别身份识别活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自报登记的民族称谓有400多个。为了弄清楚我国的民族状况,中央组成8个调查组到东北、西北、西南、华南、东南等地进行识别调查。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了38个民族。当时的广西省民委和中南民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广西境内的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等民族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先后整理出了《罗城仫佬人情况调查》等报告上报。1955年4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广西省的调查材料《关于桂北若干少数民族的识别问题》,经研究确定仫佬族、毛难族为独立民族。1956年2月21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给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的函中正式确认广西的仫佬族、毛难族各为单一民族((56)民政汪字第101/008号)。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到仫佬族聚居的广西罗城县进行实地调查,全面地搜集和整理关于仫佬族语言系属、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历史来源、风俗习惯、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资料。因时代条件和研究方法论局限,未充分考虑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仫佬族历史来源和民族形成及民族关系缺乏深入研究。不少学者对学术界有分歧的问题缺乏分析、研究,甚至以讹传讹。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认识仫佬族族称、族源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角度重新探讨上述问题,并提出一些新观点。欠妥之处,欢迎学术界同仁不吝批评指正!
一、仫佬族族称还原
1956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综合广西、贵州、云南省民委送呈的报告,根据“这些民族(指仫佬族、毛难族),大部分仍然保持着历史上形成的聚居区,并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历史来源和传说,有一定的经济联系,有的已形成一定的经济中心,而且他们大多数保持本民族独立的语言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民族内部也有密切的联系,并且迫切要求承认他们为独立民族”,向国务院呈报《关于确定仫佬、毛难、怒、独龙、仡佬等民族成分问题》((56)民政汪字第496/041号)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识别仫佬族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将仫佬族置于我国南方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民族之一的民族去认识。
由于仫佬族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历史上有关史籍对仫佬族先民的记载大多是根据汉语记音,加之汉字具有一字多音、一字多义、同音异写、假借等多种特点,不同的记录者对仫佬族的记音不尽相同。后人对史籍中的族称的传抄、解读存在诸多歧义。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仫佬族族称(他称和自称)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很多种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仫佬族自称“伶”,少数人自称“谨”,壮族称之为“布谨”,汉族称之为“仫佬”或“姆佬”。也有学者认为,仫佬族自称为“伶”或“君”、“金”。现今之“仫佬”一称应属于他称的范畴。这一观点关注到自称与他称的区别,由于是使用汉字记音,存在着无法准确记录仫佬族用本民族语言自称的缺陷,汉字的“伶”与仫佬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对自身的称谓存在巨大的差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仫佬族的族称,有自称的,也有他称的。当地汉族把他们称为“姆佬”,壮族称之为“PuN Kjamy”(即布谨)。仫佬族称很可能是由自称“母亲”为“姆佬”而来。仫佬之名,在贵州又作“木老”或“狇狫苗”。他称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根据元明清以来的历史文献对仫佬族的记载。《新元史·宋隆济传》中记载的‘木娄苗实际上就是最早出现的仫佬的先称。明、清以后,相继以“穆佬”“木老”“木佬”“姆佬”“木老苗”“狳”“狳獠”等名称见载于史册,它们都是同音异写。因而,贵州省木佬人是仫佬族。持此观点者,多将所有与上述汉语普通话发音相同的族称看作是仫佬族的族称,即“木佬”与“姆佬”同音同源。虽然有关学者也对仫佬族历史、分布等进行探讨和介绍,但大多没有对“木佬”族称和“木佬人”的历史来源进行专门的研究。
第三种观点认为,“木佬”是否是“姆佬”族称的同音异写,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王锺翰先生,绝大多数学者对王先生提出的这一问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第四种观点专门针对贵州省史志文献中出现的“木娄”“木老”“木老苗”“木佬”“穆佬”“木楼”“木楼苗”等族称与广西文献中出现的“姆佬”族称进行探讨。1984年,贵州民族学院的姜永兴先生在《木佬人风习》一文中指出,分布在贵州麻江、黄平、都匀、凯里等地的木佬人是当地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土著民族。木佬人自称(嘎窝),当地苗族、革家称之为“喀别”,意为“住在两坡两卡地方的人”。木佬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支,从语言学上看,跟仡佬语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其自身文化特征“跟仡佬族文化有相似之处”。在《贵州木佬人不是广西仫佬族》一文中,姜先生通过比较两者的语言、文化特征和史籍记载资料,指出“木佬人见于文献记载比仫佬族至少早五百年”,“史籍上记载的木佬材料,系指贵州的木佬人,似与仫佬族无关。”德国学者Inez de Beauclair根据大量汉文史料记载将“木佬”归入贵州仡佬族中。1995年,本文作者发表《“木佬”非“仫佬”——关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再认识》一文,通过对木佬人的自称、分布、主要姓氏、语言、经济生活特征、文化特征等深入探讨,否定了贵州木佬与广西仫佬族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初步论证木佬人在族源上应属于仡佬族。
除了民族史、民族学的研究外,语言学的研究也在同时进行,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很少受到民族史和民族学界的关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家梁敏、张均如对侗台语族的语言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两位学者在《侗台语概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仫佬族自称mu lam,mu是仫佬语表示‘人的量词。在罗城下里一带也有自称为kjam的,和侗族的自称kam基本相同。”在这里,梁、张两位先生指出仫佬族有两种自称,一种是mu lam,另一种是kjam,并认为lam和kjam可能有同源关系,但未能解释“mu lam”的全部含义。曾有学者指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仫佬族大多数自称,意为“种田人”。“木冷”这一汉字记音与用仫佬语对自称的发音十分接近。对于汉字记音的“冷”,仫佬族的有关专家、学者在《仫佬族通史》一书中解释,其意有两种:一种是“水塘”“池塘”“鱼塘”。“烂泥田”也称为“冷”(lam)。另一种是种庄稼的“种”(与水有关的农作物,如水稻、芋头等)的意思。此外,lam还有另一个意思。笔者身为聚居区仫佬族一员,从小就知道lam指的就是仫佬话。mu lam的含义其实就是“讲仫佬话的人”。至于罗城下里一带部分仫佬族自称的kjam的含义,梁、张两位先生仅指出“和侗族的自称kam基本相同”,而没有解释其含义。潘世雄先生在《仫佬族族称考略——兼论仡佬族侗族族称含义》一文中认为,因分布地域的差异,侗族有几种不同的自称。贵州侗人自称为“金”(gaeml),广西三江和湖南通道等地的侗族自称为“针”(jaeml),也有译作“kaml”或“jaml”的。无论是“金”或“针”,这两个语音都是声母音调的差异,它们都是侗语的同源词,与侗语对山洞、岩洞的读音相同。侗族先民因为长期停留在“随山洞而居”的生活状态而得名“峒民”或“洞人”。后来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凡居住在依山面水、有山有水、有平原小坝地方的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壮侗语族各民族)也被统称为“峒民”或“洞人”。仫佬族自称中的“谨”,则是由侗族自称的“金”或“针”音演化而来。
笔者基于仫佬族聚居地区保留下来的大量带有“峒”的地名和仫佬族与侗族的同源关系等方面考虑,赞同潘先生的这一见解。同时认为,罗城下里一带部分仫佬族自称的kjam的含义指的就是“峒民”或“洞人”。而当地壮族称仫佬族为‘布谨,其含义就是“居住在峒场的人”。仫佬族的两种自称mu lam和kjam可能存在时间先后关系,kjam可能是历史上居住在“垌场”、主要从事游猎采集生产的仫佬族先民的称谓,进入到定居农耕生产阶段以后,才出现表示自己是“种田人”和“讲仫佬话的人”的mu lam自称。清代文献中的“姆佬”和民国年间文献中出现的“母老”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对仫佬族的称呼,是他称。“仫佬族”族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有关国家事务机关和学术界对仫佬族的称谓,属于他称,因与其他民族交往和使用汉字标明民族身份需要,后来这一称谓逐渐演变成仫佬族的自称。
二、关于仫佬族族源问题
1963年,张介文分别在《广西日报》和《光明日报》(学术简版)发表《关于仫佬族的民族来源问题》和《探讨仫佬族的民族来源问题》两篇文章后,学术界对仫佬族民族来源的探讨才真正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仫佬族的民族来源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提出许多新的观点。概括起来,有几种不同的观点:(1)外来说。此观点根据仫佬族民间的宗支簿(族谱)、宗祠碑记、墓碑及相关老人关于祖先来历的传说等认为,仫佬族各姓氏的祖先来自湖南、广东、河南、江西、福建、浙江、山东等省份。(2)土著说。此观点根据语言学上的证据——仫佬族语言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壮族、侗族、毛南族、水族语言具有亲缘关系——和民族史上的证据认为,仫佬族起源于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百越族群中的西瓯或骆越,很早就居住在广西境内。(3)仫佬族的族源主体是罗城一带的土著居民,唐宋以后不断同化外省来的汉族和与之杂居的壮族及其他民族,形成今天的仫佬族。第一种观点把民族来源与有关姓氏祖先来源等同起来,似乎姓氏祖先来源就可以回答民族来源问题,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河南、山东等省份没有发现仫佬语及与壮侗语族诸民族语言有亲缘关系的遗迹。因而,外来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第二种观点充分考虑到了同源民族的分布地域和文化(尤其是语言)的亲缘关系,但忽略了西瓯或骆越是壮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仫佬族和毛南族等民族共同祖先的事实、古代民族的分化和新族称出现与民族形成所需的条件等问题。第三种观点在民族来源上基本成立,但未能解释唐宋时期侗水语支民族的共同先民“僚”、“伶”尚未分化问题,不能说分布在整个西南的“僚”和黔、湘、桂三省区的“伶”都是仫佬族的先民。
民族史学界一般认为,各姓氏的祖先来源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来源,民族形成需要一个由量变到质变、需要一段时间的历史过程,而族称的出现才是民族形成的主要标志。因为族称不仅意味着一个人们共同体内部已经具有一些可以与其他人们共同体区别开来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的文化特征(如语言和习俗),而且也意味着这些特征能够被周边其他人们共同体(族群或民族)辨别出来。虽然仫佬族的一些主要姓氏(如大梧村吴姓)的碑文记载其祖先早在明初就已经定居在罗城境内,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组与周边其他族群相区别的文化特征。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史籍记载罗城境内“土民有徭、僮、伶、俍之种。”可知当时“伶”人与“俍”、“徭”、“僮”已经有显著的区别。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主持编撰、历二十八年完成的10000卷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第172册“庆远府部”下才记载有“姆佬”之名,其文云:“天河县(今罗城境内)邑分四乡,县东八里,咸伶种,名曰‘姆佬。语言与汉迥别。”至此时,“姆佬”已经从“伶”人中分化出来,标志着仫佬族先民已经形成一个具有一组比较稳定的文化特征并与其他人们群体相区别的人们共同体,但“伶”人族称仍沿用。雍正五年(1728年)勒成的《建罗城学明伦堂记》碑铭上亦记载罗城有“苗、徭、伶、僮”。1784年重修的《大清一统志》卷464“庆远府条下”所载“姆佬即獠人……宜山、天河有之”,说到“姆佬”来源于当地的“獠人”。今天河镇东部的高岭、向阳、吊水峒、帮芒峒、大水坝、吊机石、塘峒、长风峒等自然村和与天河交界的四把镇集环、棉花行政村一带是仫佬族的聚居地。
笔者倾向于第四种观点,即仫佬族的主体来源于侗水语支民族共同先民“僚”“伶”,为其分布在今罗城及其邻近地区的一支,清代初期分化出“姆佬”,在发展过程中融入部分壮、汉、侗等其他民族,但不同意将元、明、清时期仅见于贵州史籍的“木老”“木娄苗”“穆佬”“狇佬”“木佬”等族称同于广西史籍中出现的“姆佬”族称,因为这两个群体在历史来源、分布区域、经济生活特征、语言和习俗等都存在明显的差异。笔者在《‘木老非‘仫佬——关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再认识》和《关于将“木佬人”归属仫佬族的问题——民族识别个案研究》两篇文章中已有专门探讨,兹不赘述。至于这两个群体的汉语记音为何如此接近,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仫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仫佬族主要分布在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宜州、柳城、忻城等地,与壮族、汉族、侗族交错杂居,与瑶族、苗族比邻而居。从唐宋时期到民国,天河县(今属罗城天河镇)分别隶属于宜州溪峒等处军民安抚司、庆远府。罗城分别隶属于融州、柳州。清初顺治年间,罗城知县于成龙在《治罗自纪并贻友人荆雪涛书》中说道,“(罗城)土民有猺、猹、狳、狼之种”。康熙年间,时任天河知县的黄谔在《康熙二十四年天河新建文庙记》中说,天河“其民与狳、狼、猹错处”。道光六年《天河县志》说“猺、猹杂居,天河、思恩又有狳、獠、姆狫、、犭羊、狼、狪之属”,天河“东为狳、獠,名曰姆狫;西为猹人;南则狼种,性稍纯朴;北则略与华同,呼为百姓”。综合有关史料记载,可以断定,最迟到清初,天河县壮、汉、仫佬3个主要民族的居住格局已经形成。
民国24年《罗城县县志》“民族”条下“本县民族之来源”记载,“查县属民族,除三防区(今属融水县)之苗山有猺、狪、猹各原始民族外,其余各地人民俱由外省迁来之汉人,其中以广东、福建、湖南、河南来者为多”。因当时没有民族识别,编者认为三防区的瑶族、侗族和壮族才是少数民族,当时罗城县境内的居民主体是汉族,占全县总人口的约70%,主要来自中原地区。其余苗、侗、壮约占总人口的30%,苗、壮几乎同化于汉族,侗族次之。而在“语言”部分,编者提到全县的11种方言中有“母佬语”,说明仫佬族是存在的。仫佬族与壮族、汉族杂居,与瑶族、苗族、侗族等为近邻。1952年,天河县与罗城县合并,设立罗城县。
仫佬族与壮族、侗族具有同源关系,而且长期在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因而在历史、语言和文化上关系十分密切。从文献上记载的族称上看,秦汉时期的西瓯、骆越,三国至魏晋时代的俚、乌浒,隋唐至宋元时代的僚等族称都是仫佬族和壮族先民共同的族称。宋代,壮族先民“僮”已经从僚人族群中分化出来。清代初期,仫佬族才从“伶”“僚”族群中分化出来。在语言上,仫佬语与壮语相比,在533个常用词汇中,同源词有285个,占53.5%。仫佬族村落与壮族村落错落分布,语言上相互影响,一些壮族已经融入仫佬族(如下里韦姓),操仫佬语言。一些仫佬族也融入壮族中,他们仍认同自己是仫佬族,如下里姚姓与刘姓。仫佬族和壮族之间经济上互通有无,社会交往中互相往来、互相通婚的现象普遍存在。仫佬族与壮族的风俗习惯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如饮食习惯上喜欢吃糯米、嗜酸辣;婚姻中的“依歌择配”和“不落夫家”习俗;丧葬礼仪中的“买水”浴尸的习俗等,在整个壮侗语族诸民族中都普遍存在。仫佬族民歌中的《刘三姐》就是取材于壮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宗教信仰方面,仫佬族在举行三年一度的依饭节,祭祀本民族的梁吴二帝(梁王梁善利、吴王吴广惠)时,要请36位善神来赴宴,其中也有莫一。而莫一大王正是河池、宜州一带壮族崇敬并供奉的神祗。每年都有固定的日期,供奉仪式隆重。在仫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嫁”的传说,内容与壮族莫一大王的传说大同小异。仫佬族的《伏羲兄妹造人伦》传说与壮族的《布伯》传说的内容基本一致。
仫佬族与侗族也是同源异流的关系。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资料表明,两个民族具有密切的联系。仫佬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或侗台语族)侗水语支,与侗语、毛南语、水语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家调查记录的349个基本词汇统计,仫佬语有42个词汇与侗语完全相同,占12%;部分相同的词汇有60个,占17%强;借词52个,占15%;完全不同的词汇有195个,占5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学家梁敏、张均如调查发现,仫佬语与侗语是比较接近。近年,有关语言学家对仫佬语与侗语的关系再次进行研究,发现在694个常用词中,仫佬语和侗语的同源词就有455个,占65.6%;不同源词239个,占34.4%。仫佬语与侗语之间基本可以使用母语交流。
仫佬族与汉族虽然不是同源民族,但两个民族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代,中原地区汉族就随着中央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立郡县制被调遣和随迁至岭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宋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饥荒等原因迁移至岭南的中原汉人逐渐增多。旧志记载,罗城属隋唐时“琳州峒地”,属武阳、临烊二县,后隶融州(即今融水县),“柳子厚(宗元)以理法教之”,说明汉族文化已经传人融州。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罗城的真正治理从明洪武年间“建邑设官”开始。明朝廷在罗城设置许多卫所、巡检司,派兵驻守。这些守军亦耕亦农,长期驻扎下来。明末清初,广西是南明政权的抗清基地,吴三桂叛乱时,广西是当时的主战场。多年的战争使广西的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以后,清政府在广西实行招民垦荒政策,大量无地少地的外省农民徙居广西,手工业者、商人也联袂而来,从而形成经济型移民徙居广西的新高潮。随着戍边和开发边疆地区的需要,被征调和因其他原因(逃难、经商、做官、服刑、盗匪等)迁移至广西地区的汉人迅速增多,逐渐改变了“蛮多民少”的人口分布格局。到了清代中期,从湖南、广东、江西三省徙居广西的汉族移民已占据优势,这些汉族移民多居住在沿河交通便利之地、河谷、平原地区和圩市、城镇,这一分布格局对广西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产生深刻的影响。汉族移民带来各地的方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宗教信仰,通过贸易、通婚等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交往,仫佬族分布地区也不例外。
历任知县、县令等都采取一系列措施,设兵防、置保甲、禁盗贼,“省民疾苦”,革除积弊,鼓励农耕,与民生息,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在县设学官、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机构,并设教谕、训导等官职,主管文治教化事务。著名的汉族官吏有明代的张志可、谭善继、楼得月和清代的于成龙、钱三锡、赵瑞晋等一大批人,为罗城的治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任罗城知县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整顿,亲民爱民,赏罚分明,境内“鸟言椎髻之众,皆听约束”、“教化大行”。此处“鸟言椎髻之众”就是当地的狼、猺、狳、猹各少数民族。于成龙离开罗城赴四川合州上任知州之日,“罗人遮道呼号,追送百里,哭而还”,足见其深得罗城各族人民的爱戴。
由于仫佬族长期与壮族、汉族交错杂居和经济文化交往,部分仫佬族人兼通壮语、汉语普通话与西南官话、挨话、土拐话、百姓话、福建话(闽南话)、阳山话等方言,或以之为母语。现代仫佬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在文化上,仫佬族的衣着、饮食、房屋、器用、节日等都受到汉族、壮族深刻的影响。仫佬族取汉族姓氏,罗、银、吴、谢、梁、潘等各姓都可以从汉族《百家姓》那里追溯到它们的起源,各姓关于祖先来历的传说与汉族地区有关(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山东、河南、浙江等地)。仫佬族建宗祠、立族谱,建立起与汉族相类似的宗法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同时,也存在父母包办婚、童养媳、男尊女卑、歧视赘婿、寡妇等旧俗、旧习。仫佬族在宗教经书、碑文、对联、族谱、契约、山歌歌本、学校课本和政府的各类文书档案中使用汉字,并创造出一些土俗字来记录本民族的文化,表达本民族的思想。仫佬族的山歌几乎全部使用土拐话唱,彩调剧则一律使用桂柳话演唱。民间故事、传说包含有大量汉族文化的内容,如《梁山泊与祝英台》《孟姜女》《仙女下凡》等。汉语、汉字在仫佬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承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宗教信仰方面,仫佬族先民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吸收了由汉族地区传入的道教、唐宋以后又传人的汉化的佛教。仫佬族最隆重的祭祖仪式——“依饭”就是由道教的梅山教法师来主持的。仫佬族信仰的许多神,如土地神、孔圣庙、三元、鲁班等,都是汉族地区普遍崇拜的神灵。汉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石敢当在仫佬族村寨也屡见不鲜。这些足见汉族宗教文化对仫佬族的信仰崇拜带来深刻的影响,从而使得仫佬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与汉族非常接近。
苗族主要分布在湘西、黔东南和四川、云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广西苗族主要分布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少部分分布在河池、环江和隆林等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是邻县,仫佬族分布在云贵高原的九万大山南麓,与大苗山相连。历史上,罗城曾是融水的一部分。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朝廷析桂林琳洲洞地置罗城县,先隶属于融州(今融水),后隶属于庆远(今属宜州),清代又隶属于柳州。新中国建国至今,先后隶属于庆远和河池管辖。仫佬族与苗族两个民族语言不同,文化习俗差别较大,如苗族实行族内婚,因而,仫佬族和苗族通婚的极少。但是,仫佬族和苗族因居住地邻近,彼此之间仍有一些往来。笔者小时候就曾听父亲说过,他年轻时(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到过融水和睦一带苗族村寨帮忙收割稻谷,换取工钱,苗人主家用大铁锅煮饭招待帮工。罗城也有个别仫佬族男子娶融水苗族女子为妻的事例。罗城县龙岸乡(今改镇)的龙岸、天宝、龙平、北源、高安、太和、物华等村委会,有汉族、壮族、苗族、仫佬族、侗族杂居的村屯。仫佬族和苗族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采取许多积极的措施消灭民族歧视和民族不平等的问题,从政治上、法律上切实保障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从经济上、文化上、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上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改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仫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如下观点:(1)仫佬族有两种自称,一种是mu lam,另一种是kjam。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时间先后关系,kjam可能是历史上居住在“垌场”、主要从事游猎采集生产的仫佬族先民的称谓,进入到定居农耕生产阶段以后,才出现表示自己是“种田人”和“讲仫佬话的人”的mu lam自称。清代文献中的“姆佬”和民国年间文献中出现的“母老”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对仫佬族的称呼,是他称。“仫佬族”族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有关国家事务机关和学术界对仫佬族的称谓,属于他称,后来这一称谓逐渐演变成仫佬族的自称。(2)仫佬族的主体来源于侗水语支民族共同先民“僚”、“伶”分布在今罗城及其邻近地区的一支,清代初期分化出“姆佬”,在发展过程中融入部分汉、壮、侗等民族。(3)仫佬族与壮族、侗族具有同源关系,在历史、语言和文化上具有许多共性。仫佬族与汉族虽然不是同源民族,但两个民族的关系源远流长。在语言文字、家庭与宗族组织、节日、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仫佬族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仫佬族与苗族在语言和文化习俗方面差别较大,历史上也发生过一定的联系。
[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