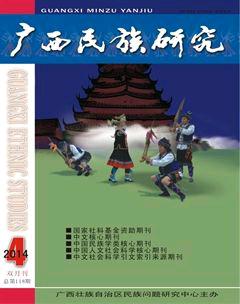宗教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图式
李晟赟 罗强强
【摘要】宗教在前现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进程中分别对应着宗教的世俗化、反世俗化以及多元化转向。这三个阶段的民族关系也随着宗教变迁衍生出各自的特点。文章探讨了三个阶段世界民族关系各自呈现的特点,认为宗教在后现代化阶段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更为让人担忧,其明显的多重化、星团化、不确定化使得未来世界民族关系的走向将会是一幅更加复杂、更加扑朔迷离的图景,单凭一国之力制定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将举步维艰。这也为我们积极寻求全球范围内推动建构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关键词】宗教;现代化;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4-0019-006
宗教现代化是指“宗教伴随着社会进步广泛地将现代自然科学新成果融入自身的教义中,并将实现宗教在物质上、管理手段上、生活方式上和思想内容上的现代化”。作为宗教社会学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三大社会学家都对此有过详细论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以及马克思之宗教与阶级革命的关系,实质上都预设了这一主线。然而,如此重要的主题却鲜有论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尽管国内其他学科探讨宗教与民族关系两个概念之间联系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无一例外都忽视了宗教本身的动态变迁属性而试图建构“大一统”型静态通用的理论框架。事实上,宗教、民族关系都具有显著的时代意涵和变迁特征,都需要从动态发展视角出发。宗教的不同历史演进阶段,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不同,后者会相应呈现出不同风貌。脱离了动态大前提,大多数探讨只有理论上的分析性、思辨性,不具有多少实践性。本文试图在宗教社会学框架下,从宗教动态变迁的视角,对这两个国内民族学者一直热议的原属不同范畴的概念所呈现出的牵连关系再次探讨。从动态的视角看,宗教现代化演进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世俗化、反世俗化与多元化三大阶段。先是由制度性宗教向弥散性宗教转变,后又颠倒逆转了这一过程,随后又出现了宗教新世纪运动。宗教现代化的动态变迁进程,使民族关系在动态演进中充满了变数。
一、前现代化时期:宗教世俗化下的协作型民族关系
(一)世俗化是宗教前现代化时期的主要表现
宗教在前现代化阶段主要表现为宗教世俗化。尽管学界对宗教世俗化的时间起点争议颇多,未能统一,但对其内涵却基本达成一致,即“去神圣化”、“从附魅到祛魅”。从宗教社会学来看,它是指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子系统相分离,从公共领域中大幅度撤退出来,从权威、垄断的社会地位逐渐退却到供人挑选的、边缘的社会角落;从行动者来看,宗教信仰日益私人化,成为个人主观选择的私人德行;从价值论来看,打破了总体上的宇宙神权中心主义,确立了人在世界秩序中的主体性,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高扬事物变化的多样性、差异性、零散性、特殊性和多元性,主张用多样性去超越统一性”。
(二)宗教世俗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图式
宗教世俗化以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全面减退,其日益式微使得宗教在内部民族关系中难以胜任担当民族共同体联系的纽带,在外部民族关系中不再成为民族分野的最显著标志,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力全面让位于全球化。全球化打破了长期以来相对比较封闭的民族地域经济环境,经济发展要素汹涌而至,把原先相对比较封闭的人群纳入到新经济秩序中。商品交易遵循价值规律,借助于经济要素各环节深入到民族日常生活世界。以往以血缘、地缘以及共同宗教文化缔造的伦理本位的静态社会关系渐趋被崇尚财富功利的物化本位的动态社会关系所取代。民族成员热衷于拜物取代了以往对神的崇拜,追求此岸世界“物质自我”的实现压倒了对彼岸世界“精神自我”的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发生、发展以及冲突调适主要从物质利益出发,使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来主导社会关系,理性选择自己的目标和手段。为了完成商品交易,交易双方都必须保持个人身份的相对独立性,对手中商品具有相对独立的所有权。为了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获取最大限度收益,交易对象必须保持可替代性。交易一方的行动者并不在意对方是否属于本民族集团、交易的主要目的是否能够最大程度上维护本民族整体利益。激烈的优胜劣汰市场竞争不断刺激行动者自我奋斗、发挥才能、施展个性,个人主义倾向愈发显著,原本作为群体——群体的宏观民族关系逐步解构为个人——个人的微观社会关系,同时,由共同宗教文化缔造的组织严密的民族共同体也被逐步瓦解解构为原子式堆积的机械抽象集合体。民族关系被物质关系、交换关系等一般经济社会关系所遮蔽,民族关系中的民族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民族关系个体化倾向日益明显,并蜕变为一般社会关系。
人们在主观精神世界不再受一元论权威控制,精神文化走向多元主义。宗教的社会基础也多元化了,宗教不得不打破封闭的神圣世界边界,向现实社会开放,其传播影响的空间日益碎片化。“各种宗教之间相互突破原有区域,淡化彼此的对抗,并且使自己的观念和方式更多地被世人接受。任何一种宗教企图完全影响、控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变得越来越难,许多宗教跨越不同各民族的血缘感情壁垒而迅速扎寨”。原本作为民族文化核心部分的宗教首先模糊了文化边界之后,民族的文化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人们在一个开放框架体系内不断进行互动,民族文化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转型。以宗教为核心的传统民族文化日益变成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根据各种现实利益需要被建构的“社会事实”。“民族”的概念在多元文化作用下变得模糊不清,族际边界也就日益模糊,此群与彼群,此族与彼族难以清晰区分,进而“民族关系”也就变成了模糊的、复合的、多元的甚至是主观臆造的概念。
宗教原本先验地预设了以神为中心,人处于边缘地位的世界秩序。宗教世俗化之后,人本主义兴起,“人”回归到生活秩序中心,神丧失了垄断地位,连带宗教本身也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退居一隅。原本由宗教所建构的确定性生活世界变成可疑的、不确定的以及不可预测的。人们不得不打起精神从关注彼岸世界转向直面此岸生活,一个个漂泊的心灵不断地在现实世界寻找新的崇拜对象以承载精神寄托。人们在与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子系统中找到了物质,在政治子系统中找到了权力作为新的崇拜对象,发现拜物、拜权也能满足人对于精神自我、人格自我的追求。因为较之于虚无缥缈的神,物质或权力更具有确定感,更能够缔造符合现实功利需要的工具型社会关系,更易满足绝大多数人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宗教这样一种社群主义文化体系,曾经在左右传统民族关系发展走向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如今在宗教边缘化的背景下,牵连民族关系这样一种具有民族因素的社会关系不得不让位于经济社会关系、政治社会关系,处于社会关系舞台的边缘地位。
人们社会行动日益“理性化”,行动者身份及选择日益“多元化”,理性化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空间,敦促人们在社会交往互动中摆脱了对宗教路径的依赖,竖立起精神上独立的自我。人们的身份日益开放、多元、复合,也不再强调建立统一的精神秩序交往规则。以宗教为边界的民族社群之间的藩篱被打破,人们之间的经济互动必须遵循契约法则,不断通过谈判、协商、交流、对话来达到合作共赢;人们之间的政治活动必须遵守“科层化”规则,按照国家法律、政策办事,不再受到宗教神权支配;人们之间的文化互动必须遵循多元共生法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开放多元、平等协商、交流对话等现代公共精神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主流模式,民族关系更强调开放性、流动性和协作性。形形色色的民族关系在更大范围内互动时,在更高层次上整合时,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趋于多重心、多层级、多领域、多类型。
二、现代化时期:宗教反世俗化下的封闭型民族关系
(一)反世俗化是宗教现代化时期的主要特征
宗教现代化在此处是狭义上的与前现代化(pre-modernization)相衔接的第二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宗教出现了反世俗化趋势。宗教经历了世俗化的长期沉寂后,不断自我反思,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深刻改变,努力适应新时代需求,以回归的姿态迅速走进人们的生活世界,掀起了反世俗化的高潮。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回归热潮兴起,宗教传播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界限,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球频频爆发的民族关系恶性冲突事件中处处可见宗教的影子,宗教在很多民族地区重新回归到社会关系的中心地位,民族关系与宗教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诱发宏观民族关系产生颠覆性逆转。
(二)宗教反世俗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图式
在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市场经济卷入的程度越深,族际间在行业、职业、收入水平等经济社会分层结构中占据的地位差异越凸显。种种发展不平衡往往会引发一些民族焦虑心理,产生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受挫感和危机感,对其他民族产生抵触情绪,愤愤不平,甚至将不满情绪归因于其他民族的掠夺或压迫,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全球化使得时间与空间分离并处于不断流动中,行动者得以从具体化地域中抽离出来,政治、经济、文化都能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产生跨越国界的行为。互动、权力运作等一系列交流为民族组织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他们将宗教、民族原本并不直接相关的两个领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跨越种族、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政治动员力量。它在信仰同一宗教的不同民族之间建立起群际联盟型民族关系,在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则发展出整体型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恨关系,民族关系重新回归到群体性层面。即,大多数民族成员介入民族关系,成员内部基本立场、基本目标一致。他们在处理民族共同体外部事务时,个体成员、部分成员与其他民族的和解、协商无效。一旦发生族际冲突,卷入人口多,持续时间长,波及地域广,协商谈判难,破坏性极强。可以说,宏观民族关系颠覆性地从个体性逆转为群体性走向。
在现代化进程中,拜物主义导致文化子系统发展空间被大大挤压,人类社会结构发展失衡,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过分理性、科层制的行政体系限制精神人格释放,人被殖民化关进了“铁笼”。浩如烟海的科技信息以“尖端文化”名义轮番轰炸人们的生活世界,克隆人技术、转基因技术、核技术等等直接瓦解了传统知识带来的确定感和理性精神,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高风险文化盛行的时代,颠覆了日常生活中人们传统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念,人们精神世界陷入恐惧和混乱,怀疑、否定、解构一切,需要新的精神寄托载体。
“宗教信仰是宗教信徒群体对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的集体关切,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体验和群体承诺。”在集体意识这个层面上,宗教作为民族群体的精神纽带,所勾画出的群体边界比一般的社会群体往往更加牢固和清晰,群体成员的归属感往往更加强烈,经历了民族情感动员之后形成的民族认同其共同价值蕴含也往往更加饱满。为争取民族利益,民族成员纷纷回归到宗教信仰者行列,一些民族国家强化了传统宗教所形成的群体认同,构筑强大的心理防御机制。宗教扮演了清晰族群边界的工具性角色。
在反对现代文化霸权过程中,宗教以地方性知识、本土性文化的名义重新被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卷入到全球文化大博弈中。宗教文化相似的民族国家、民族群体极容易结成强大的文化共同体,来对付异民族或异文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热急剧升温,人们找到了新精神寄托,大批年轻人从盲目羡慕崇拜西方文化转变为重拾《古兰经》,从伊斯兰宗教文化中重新思考自我、心灵与社会,回到清真寺参加严格的礼拜活动。伊斯兰教重新成为许多伊斯兰国家统领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强烈的民族宗教情绪影响下,驱赶穆斯林聚居区的西方文化,要求居民严格遵守原教旨宗教思想,保持本色。宗教重新主导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发展群体民族关系中起到重大作用,民族关系借此一跃登上社会关系舞台中心。在相当多领域,宗教民族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经济民族关系、政治民族关系。
每个民族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有差别,弱小民族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话语权处处被削弱,在国际政治环境中的地位步步恶化。在多民族国家内,教职人员在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博弈过程中,往往会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情感与宗教仪式等方式吸引信徒和鼓动信徒去参与社会活动,以此来影响民族社会政治生活。宗教重新卷入政治系统,冲击多民族政治体系。当前最典型的是宗教民族主义的出现与持续高涨。它强调宗教的普世性及突出本民族的独特性,从心理上将“信徒身份”与“民族身份”进行叠加,缔造更为牢固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使得我群与他群的边界区分更加严密且僵化。同时坚持以宗教的“理想国”价值观作为判断社会现状的标准尺度,难以谈判、妥协,常常蜕变为过激的民族主义。以不同宗教信仰作为民族边界划分的符号,宗教充当着激发民族情感,凝聚民族战斗力的工具。民族仇恨与宗教纷争紧密交织在一起,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在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暗杀、爆炸以及武装进攻此起彼伏,对世界民族关系造成了灾难性破坏。概而言之,宗教反世俗化诱发民族关系日益走向群体性、清晰性、主导性和冲突性的轨道上来。
三、后现代化时期:宗教多元化下的星团化民族关系
(一)宗教多元化是后现代时期的主要特点
宗教后现代化大幅度解构了宗教传统价值观、运作模式,教会内部日趋复杂和多元,派系林立,信徒身份差异大,信教人口从聚居到向全球扩散,教会领导权从神定职员向草根转变,教会结构从制度性向自由性转变。各种新的教义和学说风起云涌,流变性强,令人眼花缭乱。仅就基督教而言,就出现了“危机神学”、“辩证神学”、“过程神学”、“新正统派神学”、“革命神学”、“生态神学”等等。一些新兴宗教出现,“新纪元运动”、“灵性运动”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它们尝试超越过去上千年宗教传统的范式,“借助于自然科学技术与东方神秘智慧,在方法上却又借助传统的占星术、巫术等崇拜手段,在实践上则倡导超常的心理体验和心理治疗活动,尤其追求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发挥和灵性所达到的奇效,倾向于信奉自称具有超凡能力的宗教领袖——人间的神——教主”,本土性、跨国性、自发性、多重心性的特点日益突出。
(二)宗教多元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图式
宗教多元主义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呈现出比上文所述世俗化、反世俗化阶段更为复杂纠葛的多侧面样貌。因为后现代社会关系、交易空间和组织变革的过程,产生了更大范围的跨区域的流动以及交往、权力的网络化。传统以主权为疆界的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民族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以宗教为纽带的跨空间民族组织会使民族关系不断经历解构与建构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加之局部区域的宗教世俗化与反世俗化在当今世界同时共存,交织缠绕,三者对世界民族关系都产生影响,促使世界民族关系宏观上呈现出多重化、碎片化、星团化特征,不确定性越发明显。这种不确定性在当下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虚与实的跨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社交多媒体工具彻底颠覆了宗教传统的传教方式,各种宗教组织纷纷利用互联网传播教义,举行宗教仪式。它突破民族种族界限,超越语言文字障碍,实现跨越疆际交流。虚拟教会、虚拟社区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互动交流,也促使民族关系呈现出虚与实动态演进的特点。信徒兼具“网民”与“民族成员”双重身份,其在网上的发言,难以保持客观中立立场。一件很小的民族成员间的个体普通纠纷传播到互联网,非理性表达很可能被放大成为民族群体矛盾。一两句对宗教文化缺乏了解的随意发言,可能会招致全区范围内宗教民族主义者的暴力攻击。虚与实之间的宗教,会促使“民族”的概念发生动态改变,我群与他群,我族与他族,都变成了边界不断移动的虚虚实实的模糊边界,会衍生出在虚与实之间穿越的民族关系。
其二,总与分的并行。宗教、民族都是复合型、多层次的大体系,具有很大的地区差异性。现代化一方面使得宗教越来越向着个体化、社区化、小型化发展,结合本土文化衍生出新兴宗教文化。另一方面却又借助与多种现代传播方式向着群体化方向发展。地域不同,信徒结构不同,民族关系也呈现出区域民族关系与整体民族关系之别。整体民族关系与区域民族关系纵横交错并行,这种多元立体的网状格局很难用一、两种模型框架进行概括总结,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较之以往更不易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三,静与动的交织。宗教的基本教义历经上千年沉淀形成稳固的体系,在数量庞大的信徒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有些内容难免落后于时代潮流,想要及时修改做到与时俱进常常遭遇到宗教的宇宙观、价值论重新建构难题,不可能轻易进行。宗教后现代化阶段,教义与实际宗教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张力或合力。决定民族关系的社会交往行动又往往受到外部因素的猛烈冲击,不得不依据具体的时间、空间境况而重构,呈现出“名”与“实”分离的特点。在宗教不断进行的动与静、虚与实、总与分的演进中,民族关系格局也出现了理想民族关系与现实民族关系的落差、困惑。
结语
从本质来看,宗教现代化的核心是宗教的文化属性发生了现代性变迁。它导致了民族成员精神层面的震荡,诱使民族认同不断产生分化和变异危机,影响着民族关系不断分化和变异,在不断解构与建构中蜿蜒前行,呈现出复杂的多面向特点,从而使得宗教与民族关系的关联性比任何时代都要紧密和凸显。
从过程来看,宗教的前现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分别对应了世俗化、反世俗化和宗教多元三大化阶段。宗教世俗化阶段民族关系呈现出的特征,有利于打破族群边界,促进更大范围的多元交流,为民族团结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而在宗教反世俗化影响下民族关系的变化却极易诱发“民族结团”,以维护小团体利益为核心目标,社群主义再度复兴,其自我封闭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然而,值得我们担忧的并不是宗教反世俗化阶段民族关系的紧张冲突,而是宗教后现代化阶段民族关系的碎片化状态。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它是宗教的“自反性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它将全球民族关系与地方民族关系特征联系起来,民族关系既有共同特征又有局部各自特点。影响民族关系的自变量除了宗教因素之外,尚且还有国际以及本土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一方面本身也在经历不断解构与建构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又作为自变量直接作用于民族关系,也作用于宗教,使得宗教发生变异之后作为中介变量再作用于民族关系,使民族关系更加纠葛缠绕,混乱无序。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全球民族关系的走向将会是一幅更加碎片化、更加扑朔迷离的图景。单凭一国之力要准确勾勒出民族、宗教关系的边界,以及制定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当然,这也为我们敞开胸襟、积极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多层级、多领域协作推动建构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