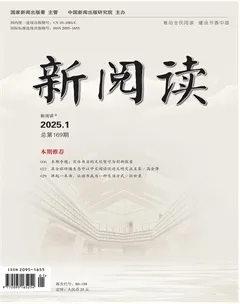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达德”及其现代价值
摘要:《中庸》提出的“三达德”,以仁为体,以知和勇为用。知、仁、勇这三个基本命题,不仅是君子应具备的三种品格,亦是为政中不可或缺之道。在当今社会,知、仁、勇仍然具有教化人心、导归良俗的现代价值,应为今人所继承和发展。因此,应从传统文化的日用性、教化性方面出发,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全社会建立文化自信。
关键词:“三达德”" 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 现代价值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化问题备受关注,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学界对文化“全盘西化”的反思。钱穆先生早在1942年即展望了中国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走向,提出中国的救亡图存在于立足传统进行文化更新和自救,即“从中国自己传统中来救中国”[1]。此后,这一反思多有继承和发展。二是近年来国家对文化自信的提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坚定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是重要的时代课题。三是民众自发寻找文化信仰、心灵故土的结果。在社会文化寻根的过程中,人们自发地继承和诠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找到归属感。各地民间书院、人文大讲堂、国学培训、经典诵读、汉服复兴等活动方兴未艾,传统文化产业也日趋繁荣,大众传媒以及工商界人士的介入,更加助力了近年的“国学热”。
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文化需要传承、如何传承,以及如何识别和挖掘它们的现代价值,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如一一详述,百万言难全其义。若略述其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大端,而儒家文化又可以集中体现在知、仁、勇这三个基本命题之中。孔子曾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仁、勇是三个重要的道德范畴,是格物致知之本,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三达德”既解决了人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又解决了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传统文化之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达德”
释“知”。“知”同“智”,孔子认为知“人”为知;孟子则发展为知“是非之心”;曾子认为“格物”为知。至宋明理学对“知”亦各有发展,朱熹言必称格物;王阳明强调心性、良知之知。可以说,“知”大抵可包括两种含义:一种为格物之知,也就是知识;另一种为道德之知,也就是知人和知是非等。
“知”的实现途径有三种:从为政角度来讲,教以致知,即通过道德教化引导百姓获得智德。不教而杀谓之虐,这是孔子认为的大恶。从修身角度而言,学而思则致知。孔子认为,除了那些“生而知之”的上者,中等者应“学而知之”,如果遇到困境还不学,则更为低劣。从形而上角度而言,知生于仁,即智慧来源于仁爱之心。
释“仁”。“仁”,从人从二,说明仁是在人我关系中体现的道德价值。孔子认为“爱人”为仁,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为仁,朱熹认为“爱之理”为仁。仁的内涵围绕“爱”而展开。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即仁爱从人之情感出发,推己及亲,推亲及人,推人及众,推众及物,自内而外,由近而远。
“仁”的概念抽象微妙,“仁爱”的外延也非常广博,但略而述之,可根据差等之爱,理解为三个层次:一为亲亲。爱人始于“爱亲”,亲亲就是对父母、兄弟的孝悌之道。二为仁民。处在血缘之外的关系当如何对待呢?为此,儒家提出了“仁民”“爱众”的主张,即扩展爱的范围,及于其他民众。这也就是孔子所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仁民爱众,可具化为忠恕之道。三为爱物。亲亲、仁民之后,爱的范围再扩展到万物,即“民胞物与”思想。天下百姓皆我同胞,世间万物皆可相亲。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体现了仁的“不忍”之心。
由这三个层次,仁的概念远可至宇宙万物、草木鸟兽,近则于己、于亲细微精深。朱熹也说:“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及难。”
释“勇”。“勇”在古代有多种字形,有从“力”、从“戈”、从“心”等写法,若从“力”、从“戈”,则与武力相关,若从“心”,则强调内在的心理状态,包括对善和义等的力行和抉择。孔子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左传》也讲:“违强陵弱,非勇也。”这解释了勇其实是对义的力行,并不单纯与武力相关。要实现勇需要其他的德行来匹配,即“知耻近乎勇”“勇而无礼则乱”等,可知儒家所提倡的勇德是指一种与义、礼、知耻等道德相关的气概。
孟子把勇分为小勇和大勇。所谓的小勇,是只敌一人的匹夫之勇;而大勇,则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文武王之勇。荀子还提到了与义相反的勇——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等。这种勇的特征是:不知是非无有廉耻、不畏众强猛贪而戾、为争货财无有辞让、轻死而暴等,是不足取的。真正的勇德是大勇,也是士君子之勇,即能够持守道德标准而不畏外部的权力,不改其志,是“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的一种气概。勇是对仁义的力行,是仁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孔子才会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而无勇,则必无仁。匹夫之勇源于力,君子之勇源于仁。
“三达德”的现代价值
“知”的现代价值。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一环,但目前各种教育理念纷至沓来、各种教育培训技巧铺天盖地,很多人反而更加迷茫,甚至忘记了教育的根本是什么。在这种过分重视技巧和知识,却缺乏道德目标和宗旨的教育潮流下,一些人被教育成高知高能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当今教育的悲哀。其实,古代圣贤所说的学,并不是单纯为了提升能力来获得名利,而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应从以下两方面重新树立当前教育的主旨。
第一是学者为己。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大有深意,有些人对此话误读误解,认为孔子提倡的学习目的是自私的,其实恰恰相反。古之学者“为己”,是“修己”“正己”“克己”,也就是说古人学习是为了修正自己的错误、提高自身的境界。“为己”之学是向内求,“为人”之学是向外求,若向外求,所学都是为了追逐名利,实不足取。所以,为学应当更加注重向内求,逐步完善人格,使生命臻于圆满。第二是学为天下。古代学者学习是为国、为天下、为万民,“学而优则仕”并不是求仕途顺畅,而是求学以致用、以所学安天下,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仁”的现代价值。当前社会问题凸显,传统文化教育断层的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老人讹诈、官商腐败、校园霸凌等现象层出不穷,反映了老中青三代都面临着道德困境。社会的价值观取向发生转向,利益诉求泛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流行、感官欲望不断合理化、大众消费文化泛滥等,人们在对自我利益的过度关注中失去对终极价值和形而上的追求。而仁德思想教育,可以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益尝试。
第一,当代社会道德遭遇集体困境,究其实质就在于对自我及自我利益的过度关注。而“仁”将道德生活作为关注的重点,以道德生活为根据设计人类理想,即通过对心的约束在人心中形成一种道德自觉。再者,传统仁德文化彰显的家国情怀把个人价值放在更大的范畴和视野内,从而对狭隘的自我的价值观进行纠偏,培养整个社会的浩然之气。第二,应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仁德的教育提供了一种根本的解决办法。从人与动物的关系来讲,若人回归“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仁德情怀,则必能促进自然界生物的和谐共生。从人与生态的关系来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其实就体现了传统仁德思想的底色。因为传统文化着眼于天人关系,故而在发展科技经济之余,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勇”的现代价值。功利主义的盛行,对传统勇德的传承造成了很大阻碍。过去青少年对古惑仔的模仿、近年的校园霸凌事件等,彰显出人们对“勇”的误解。对力量的原始崇拜未得到正确引导以致于出现了以好勇斗狠、违强凌弱为勇的现象。由此观之,重新倡导古代文化的勇德教育有其必要性。第一,勇德教育有利于在青少年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树立真正的勇的概念,勇的内在理念是“仁”,凡是离开了仁的勇是不足为道的,并以仁导勇,则使戾气化为大勇。事实上,勇德与仁德一样,也是从心上的教育,勇敢是出于善的需要而抵制对于危险的恐惧的道德力量[2]。第二,勇德教育有利于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念,使道德始终处于不越底线的自我规制和约束中,从而形成“不逾矩”的社会道德底线。
传统文化现代价值实现的可能性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古代中国盛行千年不衰,其生命力在于它为农耕社会提供了一套很实用的社会治理制度和道德体系。但随着现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形成,传统思想、文化遭到了现代性的解构。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现代化,很多学人的态度并不是很乐观,认为其要么成为彻底的宗教,要么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退缩到学术内部。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然腐朽无用的陈词滥调,其中有许多内容值得直接或进行现代化转型后为今人学习和继承。
那么,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落地呢?客观而论,传统文化包罗万象,但缺乏逻辑性强的有建设性的内在体系,有“博而寡要”的特点。随着近代各种社会、政治、伦理学的建立,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早已经被现代理论所取代。故而当代新儒家人物一直努力将传统儒学与现代相结合,探讨儒学的突破,但这些探索目前而言尚局限于学术范围的研讨,有曲高和寡之感。此外,传统文化的社会大同理想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兼容使其面临的困境也日益凸显,正如余英时所说:“建制既已一去不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3]适合儒学的社会制度解体之后,儒学再也不能凭借其所依赖的建制(典章礼仪、礼法族规等)来实现其社会影响。如果说,从学术地位上讲,传统文化只是丧失了过去的荣光,那么从社会政治上讲,传统文化基本已经失去了主流的地位。
余英时曾指出:“一方面儒学已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论说,另一方面,儒家的价值却和现代的人伦日用愈来愈疏远了。”[3]面对困境,学界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用融贯中西、融贯释儒的方法来重新解读,以求保持其学术活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对传统文化的另一特征给予更多的关注,即传统文化重视践行和体认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具有日用性、教化性。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要想实现,也许应从精英之学转为民众之学,走一条现代平民儒学的道路。
但同时应该明确,复兴传统文化并非全面复兴,我们应直面其已经不适应现代政治制度的部分理念,挖掘其核心精神,并把可用之处切实用于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伦日用性、教化性,使现代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在实现其现代价值的过程中,要避免两种偏堕:一种是仍然希望传统文化借助其实用性恢复往昔的正统地位;一种是把传统文化的平民化进行庸俗化,从而鄙薄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弘扬。楼宇烈先生也认为,就当今社会的现状和发展来看,把传统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剥离出来是必要的,儒学中那些关于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学说更为社会所需要[4]。故而,传统文化实现现代价值可以从其民众化、日用化上寻找突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批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且能践行和推广的人才,把传统文化的精神、儒家的精神活学活用,切实解决当下的人生问题,指导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建构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让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
参考文献
[1]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2][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三联书店,2012.
[4]楼宇烈.从中国儒学的历史展望未来[J].商业文化,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