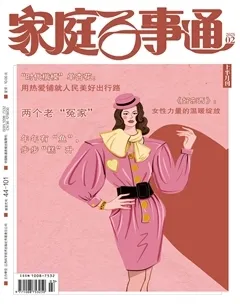人生不过三场雨

年少时熟背过唐宋时期的一些经典篇目,那些平平仄仄的句段里有着无限美好的唐宋风光,而蒋捷的那首《虞美人·听雨》,始终在我的心头萦绕。
我家住在四楼,西边户的横厅有一长串的玻璃,隔着玻璃是树龄近百年的梧桐树。春天,树上小小的嫩芽冒出来,随着一场接着一场的春雨渐渐长大,颜色也从早春的新绿到夏日的深绿色。到了深秋和初冬,巴掌大的梧桐叶子渐渐从青黄到红褐色。每逢下雨天,我在窗前读书,写字,雨点打在梧桐叶子上,蒋捷的这首词作就不自觉在我心头泛起波澜。
由此我想到,人生的一生,也大抵是这三场雨。
年少时的雨,多少是浸润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情思,也带着些许天真和烂漫,“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大概是因为年轻,对红尘世事充盈着追逐、向往、努力,在此追逐过程中,有很多困惑、迷茫、不解、冲动、莽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我们都曾在那场雨中追逐过、淋湿过、哭泣过,哪怕当时的我们在雨中没有伞,但依旧尽兴。当懂得如何珍惜和把握机会时,我们发现已经回不到年少时的那场雨中了,那场年少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终究是镜中花与水中月。
而壮年时的雨,那是拥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的自我认知、自我救赎。蒋捷写道:“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这是中年游子在客舟中的惆怅,回望小半生已过,大约有遗憾、有离别、有悔恨、有不甘、有不舍……每个远离故乡的人,会在中年时对乡愁产生格外清晰的自我认知与注解。年少时想到“好男儿志在四方”,不做井底之蛙,世界那么大,要出去看看。几年下来惊觉,异地的美食再丰富,可能还是没有儿时母亲腌制的咸菜、酱瓜可口;异地的风景再美,可能还是没有家乡的小河亲切、灵动;异地的朋友再热忱,可能还是没有家乡的亲友掏心窝……中年的听雨,是在回味小半生的雨声。记得母亲当年无论如何也挽留不住我远嫁的心,临了无奈地对我说:“只有等你有了孩子,你才能体会到!”如今想来,这话就如同那场回不到从前的雨,那场雨和雨中人始终无法同频,等雨中人领悟真谛,那场雨已经结束。
晚年时的雨,大抵带着怅然。蒋捷写道:“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晚年的他,白发苍苍,临时寄宿在一简陋的僧庐之下,窗外是雨,点点滴滴,雨未停、他未眠……或许他想到的是这大半生的人情世故与怅然别离,人间有太多的阴晴圆缺、悲欢离合。人生本是一趟单行线,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不断在和别人告别。有的人可能在你毫无防备之时,轻描淡写地说出“再见”,后来就真的再也见不到……
从蒋词中深悟这三场雨,除了惆怅,当然也有启发。古人云“晴耕雨读”,晴天时忘我工作,雨天时不妨坐下来好好读书和思考,临窗听雨,捧一杯热茶,给自己一些身心休息和调整的时间。雨夜里也许伴随着雨声,生出丝丝惆怅,忽然分外思念故乡、故人,那么等雨停了、天晴了,不妨立刻驱车去看看故乡、访访故人。
因为人生不过三万天,人生不过三场雨。
编辑|郭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