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满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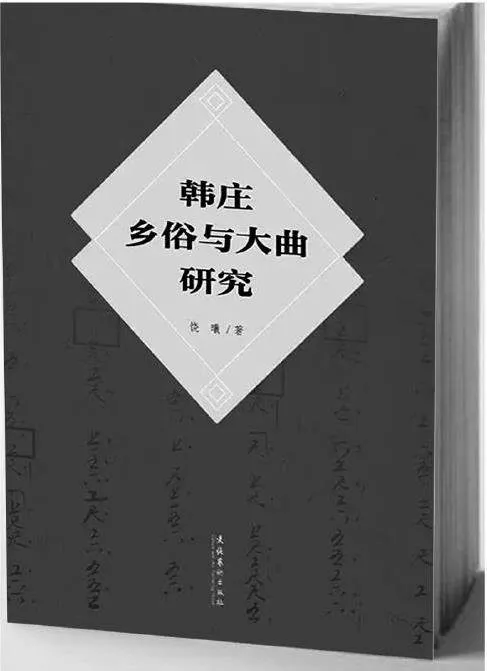
饶曦著《韩庄乡俗与大曲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一、韩庄记忆1993年8月的一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了,这是到冀中雄县韩庄采访的日子。七拐八拐,终于找到一个从来没有音乐学家去过当然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韩庄。下车打听村干部,村里人告诉,支书正在地头盖房子。开车到了地头,几十个男人盖的不是“房子”,是“厕所”。县文化馆提前通知他们,说北京的专家要带一名外国人来听“音乐”。村干部一下子紧张起来,四处脏兮兮的村里没有个像样的接待外国人的地方,于是决定到村外地头为外国人演奏,而村外又没有厕所,所以决定盖一间厕所。为了接待外国人,竟然动用十几个壮劳力在村头盖一间厕所! 这个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故事,既显出了村干部的厚道,又显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接待外国人的郑重其事和可笑程度。田头上孤零零起了半截厕所, 我们不知道该说是好还是不好,不知道是该说他们重视还是说他们做过了头。今天想起来依然忍不住喷饭的举动,让人想到改革开放之初接待外宾的隆重。一个单位的人甚至一座城市的人,不分级别高低,全体动员,打扫卫生,擦桌子、抹玻璃、洗茶具、挂标语,只是为了接待一个外国老百姓,让被接待者感到在自己国家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皇家”待遇。这就是“面子”,村干部把“面子”发挥到了田头上。
见到我们既没有穿西服也没有打领带,既没有轿车也没有领导陪同,既没有前呼后拥也没有记者随从,书记大为失望,也大为光火:“为什么你们不事先打个招呼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来了? ”潜台词自然是:“为什么不等我们把厕所盖起来再来! ”
面对他的光火,我们无言以对,气氛一时有些紧张。我只好动用了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告诉他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的级别。我指着乔建中说:“你知道雄县县长的官多大吗?你知道保定市市长的官多大吗?这位所长与市长的级别一样!”这一招够损,却十分管用! 一辈子没见过县长更没见过市长的村长,一下子哑巴了,再也不说话了。
回过神儿来的村长意识到,“所长” 不是普通人,也是个“大人物”。因为没有风风光光从事一次“国际交流”“外事活动”而憋了一肚子气的村长,终于压下心头火,吩咐会员接待我们,自己则溜之大吉,再也没露面。
“招商引资”“合作交流”“对外开放”是八九十年代最时髦、最闪烁的词儿。外国人到访,不用费太大劲儿,村干部就能明白对一穷二白的乡村来说的意义。天上掉馅饼,那是期待中的“商机”。然而,我们太让人家失望了。原以为“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事到临头才发现来了个刘姥姥。什么好处也没有,还搭上一批壮劳力,糟蹋了一堆砖瓦木料,盖了一间离居住区八丈远、全村人谁也用不上的厕所。眼瞅着什么都没捞到,村长焉能不气! 穿得像普通中国人一样甚至比中国人“还土老帽”的英国人,狠狠一脚把村长踹到了现实土地上。我们既看到了商业风潮冲昏头脑、忽视承受力的“面子”,也看到乡村干部一心一意为本村谋福祉的苦心。望着那间我们最终也没有留下一点遗物的厕所,始终觉得对不起人家。
人类学家项飙谈到记录浙江村里的“小人物”时说:他们并没有因我记录了不一定光彩的事而感到不高兴,相反他们很开心——历史长河中被记录的普通百姓的欣慰。后来,与韩庄音乐会的会员成为朋友,谈起这件事,他们依然很开心。
随着会员回到村里,会员们都逐渐到齐,但就是不演奏, 非要等到住在县里的解永祥回来才行。我们不知道等的人是谁, 更不知道他有多重要,但在怎么催促就是不动家伙的等待中,知道了他的地位。所以,只能等。过了个把小时(当时觉得好长),一位耄耋老翁,面色红润,身材微胖,分开众人,走到面前。他的话不多,吩咐大家演奏什么,寥寥几句,简洁有力。田野中很少发现谈吐不俗、满腹经纶、知礼知乐,记忆力超强的人,解永祥是之一。
他住在县城儿子家, 后来我们多次拜访他,才意识到他的价值。“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就是他在韩庄乐社的地位。他为我们解开了许多疑惑,许多问题只有他说得清。可惜当时未能长久追踪,错过了机会。这种后悔就是我让饶曦选择这家乐社、抓住这个典型的动因。
二、乐师徐纪新
我的田野作业经验之一,是找到一位记忆力超群的民间乐师。这类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饶曦没有遇到解永祥,却发现了徐纪新。每个时代都塑造过几位乐师,杨荫浏时代塑造过河北子位村的杨元亨、西安鼓乐的安来绪,乔建中时代塑造过屈家营的林中树……他们都是翘楚。杨元亨步之于前,林中树继之于后,徐纪新再劈一域,让相信“高手在民间”“真诗在民间”的人一次次不敢相信又不得不相信且惊叹不已。他以超量的背谱和韵谱,发出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声音,成为民间乐师中的新知识类型。
徐纪新在红木厂打工,出村干活,骑自行车。乡村土道,枯燥无寄,他利用一来一往的时间,默诵大曲。这段路程刚好背默两套大曲。一路行一路背,持续了整整40年! 三套大曲, 一天背两遍, 一年下来,等于背了七百遍。40年下来,等于背了两万八千遍。如果把三套大曲均分为三,每套大曲,各背了九千三百遍。
饶曦所做的精彩统计, 让我想起来罗曼·罗兰的话,人们“看惯了茂密的森林,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发见在那些僭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炼而质朴的艺术。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特尼平原的中心”。
强烈的爱好和非凡的毅力,不但使徐纪新温故知新,而且根据韵谱规律,探索起未学过的大曲。冀中大曲的难点在于谱面上没有的“字”,全靠师傅口传心授,以此补足实践中存在的“字”。若没有师傅引路,谁也不敢独自尝试韵谱。常年在肚子里默背大曲的徐纪新,参透底蕴,竟然挑战了这项无人敢碰的技术难关, 做出了前人未敢也未能做出的壮举。四十余载,反复琢磨,硬是把七八套大曲,全部顺了下来,成为冀中乐社唯一能够把十几套大曲韵唱下来的人,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饶曦开始疑问,记录徐纪新这些带有某种“创腔”的韵谱,是否具有本真性?这是个民族音乐学的好问题,她想到了前头。徐纪新遵循传统规律,口头恢复了早已退出实践的大曲。这类案例,绝无仅有。学者是否应该尊重乐师的“创腔”,还是把“创腔”视为背离传统?饶曦采取了尊重现实也尊重民间话语权的做法。这样的站位甚至比尊重民间文化产权的讨论更能带来思考。她没有高高在上,干预“被观察者”,而是看他怎样做,做什么,采取“他者”与“我者”的另一种共处方式,目的是一起忠实记录。时代产生了这类人物,在传承中断的情况下,按照每天数小时、每年数千小时、积累整整四十年的经验,以韵谱规律和地方性知识,尝试恢复大曲。面对这样的人物,我们到底是认定为冀中平原上的披荆斩棘还是一意孤行? 是弱者的声音还是不甘示弱者的呼号? 好在这些都是真实的声音,虽然不合过去规矩(谁定的规矩)。饶曦找准了传承的“魂儿”,或者传承的“命门”,绕过误解、歪曲甚至扭曲文化持有人必须保持“本真性”的解读套路,让小人物变成重量级人物,让小事件变成重量级事件,抓住一个具备充足技术含量的个案,在对视和聆听中,记录了一叠厚厚的乐谱,向具有独创性的民间乐师表达了由衷的尊敬。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马克·斯洛宾(Mark Slobin) 说:“民间承认那些特别有才华的人对集体享受和记忆的贡献。但他们把这些分散的努力浓缩起来成一个表述的资源库和策略的公共池。”作家哈金在《沉默之间·前言》说:“作为一个幸运者,我为那些不幸的人发言,他们受苦受难,忍辱负重,在生活的底层消亡;他们创造了历史,同时又被历史愚弄或毁灭……他们有权张口并被提到。”
饶曦关注底层,尊重草根,对“遵循传统”的本真主义规矩,既予纠偏,也予扬弃。
三、记谱程序设计
我探讨冀中音乐会的最初规划,略可分为三部曲,第一部是乐律学研究,即《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第二部是社会学研究,即《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第三部是大曲研究。前两部按计划完成, 第三部遇到了担任行政职务的缠绕,一晃十余年,遥遥无期。这让我意识到,没有精力完成了,应该找志同道合的同好,接续下去,最容易找的对象,就是学生。我于1993年对雄县北沙口村音乐会的老乐师崔志清录音和记谱时,发现了同均三宫的实践,在《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一书中发表了一小段用三行谱格式记录的曲牌《琵琶轮》。之所以没有参与学界讨论,就在于拿不出一套完整的大曲记谱,以此展示“旋宫不转调,移宫不出均,一调含三宫,诸宫成一调”的规律。发现问题却没有精力解决问题,皆因没有一套大曲记谱。
探寻深层结构,需要合适工具。我设计的记谱程序是:先把演奏谱记下来,再把乐师韵谱(阿口、哼哈)记下来,以此对照工尺谱,将演奏谱、韵谱、工尺谱字三行竖排,上下并列,最后按照乐律学规律,修订讹误,还原旧貌。这个程序意味着,半小时左右的大曲,必须记谱三次。一次演奏谱,一次韵谱,一次填写工尺字,最后校改为定谱。三行排列,上下参验,历史与当下、前景与背景、应有与实有、原版与演绎之间的繁简差异、音律差异以及渐变痕迹,就逐渐显现出来了。这个程序,需要时间,这就是我无力完成三部曲最后一部的瓶颈。
我把这个设计,交给饶曦。宫调布局的深层结构,学生短期内发现不了,但可以把前人发现的问题,层层剖离,步步求证。饶曦不惜功夫,把雄县韩庄音乐会的大曲《泣颜回》《锦堂月》,按照三行谱格式,全部记录下来。她用了小半年时间,完成了记谱学渴望呈现的传统乐谱、西方乐谱、当代订谱的三重对照,获得了展示大曲宫调布局与演绎方式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让人看到了一套大曲分布着同均三宫框架的完整版本,即一首作品中体现同均三宫实践的事例。
工尺谱字变为演奏谱的过程,产生了繁复的添加信息。以西方乐谱记录旋律,无法看到工尺谱骨干音延伸信息的过程。单行旋律谱,无法呈现那个迷离扑朔的迹象。上下参验, 既保留工尺骨干内核,又展现线记谱细节,还通观两者的演绎迹象。这就是三重对照文本的设计理念。
如果要在技术屏障略高的乐谱学中选择一个民间乐师发明的独特术语,那就是“韵谱”“哼哈”“阿口”。这是民间传承中最提神的一道程序。西安鼓乐称“哼哈”,京畿乐社称“阿口”。书面谱字进入演奏前,必须经过这道工序,这是乐师“学事”的第一步。有了这道工序,就可以让工尺骨干,显迹赋形。韵谱是一份值得大书特书的资源, 符号学的“主位—客位”,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现实”,乐谱学的“规约—灵活”,民间口碑的“死谱—活腔”,音乐分析的“前景—中景—背景”, 乐律学的“均宫调”,非遗理论的“文本—活态”等,均能获得通盘体现。拥有大量抄谱的笙管乐,不同于民歌,纸面文本尤其“韵谱” 最具特色, 典型地反映了纸质媒介进入操作层面的过程中既依靠文本又依靠身体记忆的双重释义结构。提供了窥见当下与古代双重信息的蛛丝马迹。韵谱在保留纸面符号的基础上,添枝接叶,遣语延脉,变为口头元素,最后完成于器乐语言的蝶变。韵谱是文化持有人阐释纸质文本、借助口头文本、演绎器乐文本的中介,白纸黑字变为源头活水,照本宣科变为活态传承。真的有必要大书特书这份资源,这是建立本土理论的一片沃土,可以使人畅顺地接过遗产。
三重记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申克分析法”本末倒置的相反程序——先呈现骨干, 再饰以韵谱,再通过演奏,变为枝繁叶茂的中国法则。简单的《老八板》, 在江南丝竹的一系列变奏中演变为无法辨认母体的分支,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乐谱分析,中国西方,路径相反,先简后繁,移简崇繁,最后演变为不复辨认的支系。三重记谱, 立足本土,押高就下,观外探内,印证细节并与历史互文,提供了整体把握的方式。
七声音阶如何五声化, 声乐曲牌如何器乐化,是个极为复杂同时缠绕着多条线头的话题,一定程度上成为尖端议案。中国音乐学试图以线谱、简谱的简便,摆脱传统记谱的麻烦,却发现了工尺谱呈现曲调深层内核的难以舍弃的合理性。这让音乐学意识到,不能简单地丢弃这种记谱法。我们渴望解读的事项, 如七声音阶五声化、昆曲曲牌器乐化、曲牌只曲大曲化等,都可以在工尺谱字的显迹赋形过程中找到蛛丝马迹。追寻骨干谱字的底色,可为探索找到切入口。
记谱规约性(prescriptive)的讨论持续了许多年,中国音乐学家一直努力追求一套具有本土特色并兼具现代信息的方式,包容工尺谱、减字谱与简谱、线谱两种信息的文本。三重对照,经过三代学者的尝试,最终成为双重信息并存的本文,让理论解读获得了记谱法上的对应样本。杨荫浏首开简谱、线谱与工尺谱、减字谱对照之先河,后人接踵而至,拾级增高,循序以进,渐靡以成。突破瓶颈,在于操作手段。计算机提供了手段。绘谱瓶颈,原先在于中国谱字的书写不便,这类麻烦在计算机面前夷为平地。工尺记谱与现代排版对接,让乐谱学走出西方。
饶曦利用现代排版技术,完成当代乐谱的书写格式。三层谱式,以一当两,化解了本土书法与西方符号之间书写上的不对等,破除了本土法则与西方规约之间的屏障。古今对照,中西互补,平等齐观,弃置轩轾,有效衔接了现代信息与本土信息,获得了记谱法上的双重势能。
四、对话
我原来把云锣音位定在“反调”中,是为了符合四宫框架中体现“凡字调”宫音而以部分乐社的云锣音位所下的结论。其实,大部分乐社以正调音位排列。为了遵循杨荫浏、黄翔鹏的“四宫”说,不愿意承认民间不能演奏四调的现实, 遮蔽民间简陋,从而掩盖了真相。其实,冀中乐社自有一套简便的转调实践。北乐会与南乐会, 整套乐器相差四度。这意味着曾经有过一套乐器不能演奏,采用另一套乐器转调的可能。这种实践,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在冀中还发现了称为“咪咪”的小管子,配搭的又是另一套调高的乐器。这意味着这一地区至少存在着三套不同调高的乐器,如果把北方笙管乐不同调高的乐器连接起来,可以看到七种调高。这个视野彻底改写了杨荫浏、黄翔鹏的四宫布局,当然也不是陈应时的七宫布局。今天我们之所以敢下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比前辈多跑了更广阔的地方。
饶曦在论文中指出了我的错误。她指出,韩庄云锣的正调排列是常规排列,在实践中,当《泣颜回》写为凡字调时,乐师则把凡字调谱字直接等同于正调谱字,毫无障碍地移过去。换句话说,正调云锣在观念上变成了凡字调,即固定唱名法直接改为首调唱名法。这就是民间乐师面对简陋,采用的做法。没有多套乐器,只在观念上移调。唱名法是凡字调,演奏是正调。这类实践,让人看到民间乐师的通融,人家根本不在一套乐器上转调。
学府的最大好处是教学相长,可以遇到一批富有创造力的学生。他们思想活跃,充满热情,下乡采风,不畏劳苦,没有在现实重压下改变求知愿望。他们自然是老师所能找到的最单纯的朋友。每届新生, 都会结识这种学生, 这自然是幸福的源泉。进校时,他们对书本内容,毫不怀疑,经过训练,渐渐发现书本与田野间的差距。于是, 抛开书本,独立思考。维特根斯坦总结教学目标,用《李尔王》的话说:“我将教你看到差异。”我们是否也是通过田野让学生看到了“差异”?
老师学生,各师其师,各徒其徒。我们遵循了不一样的原则,结果证明,她遵循的立足实践的原则好于我遵循的跟随老师说法的原则。老师学生,“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同方”。这就是做老师的好处。数年下来,你可以感到,可以与她对话了。
五、携手前行
2021年初的寒冬,鸟巢附近刚建成的“中国工艺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在布展,乱糟糟的门道与楼道里布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纸皮箱。我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李宏锋所长、冯卓慧副所长、林晨研究员和一批学生,穿梭于两个大展厅的乱象之间,为迎接与冬奥会开幕式一起开馆的“中国乐器展”和“古琴文化展”布展。没有人愿意从城东头赶到城南头,花数十天时间干这类杂事。但穿着全身羽绒服的饶曦每天必到。为了核对展柜每件乐器与展签上的文字, 她拿着卡片,俯身展柜,一一核实,从早到晚,直到半夜。这使我重温了几十年前为《中国音乐年鉴》从北京到济南跑来跑去、为首次对外乐器展在香港跑来跑去时体验过的集体主义精神。冯卓慧评价饶曦,“不避事”! 这使我发现了她身上以前没有发现的品质。研究机构的下一代学者依然能在自顾不暇的社会氛围中维护集体主义精神,让我感到了寒冬中的丝丝暖意。
音乐系的学生喜欢用“恭王府的一代、新源里的一代、赵全营的一代”划分代际,居住地不同,但观念相同。讲课时常在教室里一边踱步一边暗忖,他们能不被课堂外的扭曲所扭曲、判断学术正义并塑造自身的抗压力吗? 现在看来, 他们虽有苦恼,但依然比想象的更具耐压力并富于牺牲精神。
一个新群体出现了。他们的成果开始成批地进入视野。50年前,有几份油印翻译资料就可能获得“话语权”;30年前,有个洋文凭、加点新概念就是“知识霸权”;现在,饶曦一代学者则毫无愧色地端着数套大曲的记谱和十几万字的论文, 站到前列。她们既掌握理论,又深入田野,不迷信权威,扑下身子实干,如同她在展厅里所表现的那样。
同均三宫的理论框架到底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实践依据,全靠实践检验。口说无凭,实践为证,依据实践记录的谱例为证。现在,整套大曲的谱例完整地端出来了,这自然可以证明我们为什么坚持这个理论框架的底气。发表全部谱例,就是这部著作应该被翻阅的地方。
张振涛 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