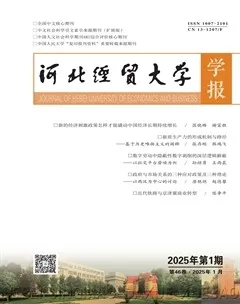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三种应对政策及三种理论
摘 要: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历史上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非常丰厚。到汉代,已经形成了多种理论、多种政策方案。西汉早期政府遵循黄老学说,奉行无为而治,实行经济放任政策,国富民富,司马迁据此抽象出政府与市场关系之“善因论”。汉武帝治下遵循法家理论,政府专营盐铁酒业,满足了国家求强任务的财政需求,桑弘羊总结出“政府干预有效论”。东汉前期政府基于以“中庸之道”为特色、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精华的儒学理论,实行折衷政策,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班固据此抽象出“政府适中干预论”。在政策和实践互动过程中孕育的上述三种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生动的历史场景与思想资源。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善因论;政府干预有效论;政府适中干预论;历史场景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5)01-0092-10
收稿日期:2024-0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经济史学起源和形成考察”(21BJL1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15AZD051)
作者简介:
唐艳艳(1974-),女,湖北京山人,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赵德馨(1932-),男,湖南湘潭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商业成为社会的一个独立行业,出现了以从事商品交换为职业的私商阶层,金属铸造的货币成为真正的货币,各种生活必需品与奢侈品市场涌现,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市场以及买卖奴婢的市场。中国社会开始迈入商品货币经济时期①,出现了各种与市场相关的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政府面临着如何对待市场的问题。周初的姜太公和春秋时的管仲先后在齐国“通商工之业”[1]1480,“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1]1487,这是政府对市场的引导,通过政策偏好促进经济增长,百姓增收。其后范蠡在越国实施“平粜齐物”的政策,政府作为经济的稳定器,将谷价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1]3256区间,以达“农末俱利”,并称之为治国之道,肯定政府介入市场运转的合理性。这种平粜也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干预市场活动。商鞅在秦国变法,实施的“耕战”政策,“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1]2230,其本质是通过政府权力强制民众从事农桑耕织,抑制商贾末业。凡此种种都是早期政府尝试参与引导市场的活动,同时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到两汉时期,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兴旺,迈入中国商业史与市场史上的第一个繁荣高峰和多变时期,在实践中产生了三种政府创新性的应对政策,当时的学者们抽象出三种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政府与市场关系三种理论模式的基础。
一、放任政策与“善因论”
西汉立国之初,国贫民穷,“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1]1417。国家需要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刘邦提出要从总结秦朝速亡的原因入手,制订相应的政策。陆贾认为,“朝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道莫大于无为”, [2]这个观点得到刘邦的认可,“约法省禁”的无为放任政策胜出。
(一)汉初的政府放任政策
汉惠帝、高后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1]412文帝、景帝力主“扫除烦苛,与民休息”[3]153。汉初政府这种“无为”态度,表现为政府对于市场的放任,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放松对商人的限制。刘邦在建国之初,为了解决商人“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1]1417的问题,除了制订直接打击商人投机倒把行为的政策外,还在政治上贱商,“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1]1418,且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到汉惠帝、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1]1418,抑商政策逐渐放松;文景时进一步允许商人入粟拜爵。商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1]3282。故当时实际情况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3]1133,富商们实际上较高的经济收入,使得名义上低贱的商人群体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就如南阳冶铁世家孔氏,因富有得以“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1]3278。
第二,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其一是国内通关去塞,任民周流。汉文帝时“除苛解娆,宽大爱人……通关去塞”[3]2296,后又诏:“除关,无用传”[3]123,即取消进出关卡检查“符传”的规定。景帝时虽曾考虑到当时七国新反而“复置传”,但关塞仍然开放,而且免征关税。其二是开放边境关市。边塞开斥,与民无禁,允许边关自由贸易。北边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在南方,高后时,一度禁南越关市铁器与某些种类的马牛,其他商品照常进行。相对开放的内外市场,促进了商品贸易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3261。
第三,放松对部分工商行业的限制。最重要的有两项。其一是冶铁、煮盐。秦时为国家管制,汉高祖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吕后在位期间虽然一度对盐铁私营有过禁令,但文帝即位后仍“纵民冶铁、煮盐”[4]52,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其二是货币的铸造。汉高祖“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1]1417,允许民间铸币。此后颁布过“盗铸令”,至文帝时废除盗铸令,“令民纵得自铸钱”[1]1419,成为汉初持续时间最长的货币铸造与发行制度。货币民间私铸,货币供给充足,商品交易方便快捷,人们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1]3274千金之家生活得像一都之君,巨万者甚至能与王者同乐。
(二)司马迁的“善因论”
西汉早期,政府的放任治理,成就“文景之治”。工商业繁荣、商人富裕,同时农业、畜牧业也很发达,政府的财政状态良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学者型官员司马迁本着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反思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文、景至武帝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政策及其绩效,创造性地抽象出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典论述。
第一,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五种政策类型。“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3253“善者”即最好、最高明的,“因之”是因循经济与市场自身发展的逻辑。春秋早期郑桓公的政策,汉代文景时期的政策,都收到民富国富的良好效果。“利道(导)之”,即国家通过政策因势利导经济的运行,缓解市场物价大波动及由此带来的贫富不均等问题。春秋晚期范蠡在越国和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实施的“平粜齐物”政策,收到显著的效果。“教诲之”,即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与立法、政策的导向,告诉商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诸侯国在大多数时间里采取的措施,效果不错。“整齐之”,就是国家对私人市场活动,用强有力的政策进行管制,使他们“整齐”于政府的需要。秦国商鞅变法过程中关于重农抑商的宣传、政策和有关商业商人的立法,效果也还可以。“最下者与之争”,最下者即最坏的,是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以与商人争利。司马迁所指极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的盐铁酒专营、均输等政策。在上述五种类型政策中,司马迁认定“因之”为善,并为之做了论证。
第二,为什么“因之”为善?司马迁指出,历史事实是:“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3254这就是说,在经济的运行中,上至宏观的农、虞、工、商的产业大分工,下至人各任其能、各劝其业的个体经济活动,都是如水向下流,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与道相符,而不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在这个层面上,“因之”因的是经济发展的自在规律。司马迁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 [1]3253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并因此追求物质财富,出于人的本能欲望,是人性的本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每个人为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而竭其力、乐其事地去创造财富,社会的财富必然迅猛增加,且大家心情舒畅。在这个层面上,“因之”因的是人性的内在要求。对于经济与市场的发展,政府只要因循经济发展的自在趋势和人们的求富欲望,就会获得最好的成绩,因而才是最佳的路径。对于经济发展的自在趋势和人们的求富欲望,既不需要政府提倡、教化,也不需要政府去阻挡、干扰,政府是无法通过强权予以扭转的。政府的最好态度是实行无为而治。
第三,无为而治的理论依据是黄老学说。汉初,黄老学派在政府决策层中占主导地位,同时也是司马迁的家学。黄老学说主张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5]。“道常无为”就是不去违反、干预自然的运行,是为循道;“而无不为”,则是政府也不能不顺万物之性,乘万物之势,顺应自然地“为”。因而“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恣意妄为;政府要因自然趋势,循“道”而行,循理而为,制订因势利导的政策法规,顺水推舟地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样一来,万事万物因顺应无所作为的道而生生不息,无所不为。君主治国“无为而治”,政府不作过多干涉,清静而民自定。在经济领域内,无为而治的就是使政府与市场关系适度,从而经济繁荣昌盛,人们生活愉悦的最佳境界,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在实践中,政府面临社会经济与市场发展中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压力下,政府有管理市场经济活动的动机与责任,因而一定会借鉴和延续春秋战国以来政府参与市场活动思路,明确“道”即自然趋势是什么,认识到“为”与“不为”的边界在哪里,才能因之。这种趋势和边界,只有在实践的不断试错中去探寻。在司马迁心目中实行无为而治的汉初,对于商人商业的政策,从管制、轻贱到部分放开;对于货币铸造发行,从私人自铸、地方政府铸造到中央政府铸造,诸方面此类措施,都是有为的表现。
近人将司马迁的这套理论概括为“善因论”是合适的。善因论的出发点、论点与逻辑,与1 800多年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表达关于政府与市场自由放任关系的出发点、论点与逻辑点类似。[6]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类上,司马迁的五种类型与五个层次的划分,比当代经济学中常见的两分法或三分法更为细致。
二、专营政策与“政府干预有效论”
西汉历经文景盛世,家富国富,到汉武帝时国家任务发生大转变,首先是要从富国转变为强国,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对外解除安全威胁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其次是要解决放任政策的负面影响,主要是贫富差距和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等问题。对于任务一,财政支持是关键和基础;对于任务二,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总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问题,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仅靠清静无为是不够的,因此黄老之学逐渐退出舞台中心,以管商思想为核心的法家思想胜出,政府政策也发生大转变。
(一)汉武帝时期的政府直接干预政策
新任务急需国家财政支持,汉武帝要求寻求新的方法,强调“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3]173。以桑弘羊为代表的理财专家,创造性地实施一系列新的政策,支持国家的新任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筹措强国资金,汉初无为之治下的经济理论和与之相适应的政策都发生了转变,其中涉及的重要工商政策有三条。
第一,实施盐、铁、酒和货币专营政策。“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3]1165山川大海里的自然资源本身是属于统治者——帝王家的私产,因此政府有权禁止私人对山林川泽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由自己直接专营。其一是政府专营盐、铁、酒。政府将原来私人盐、铁产业收归国有,在中央和各地设立机构,配置官员(部分盐铁官员由原来的私人盐铁从业者担当),管理盐、铁的生产、运输及销售。铁器由政府统一生产、统一定价销售。盐的生产则
招募百姓进行。用政府器具煮盐,再由政府收购,实行专卖。为了保证专营,政府制定严格的制度惩罚私盐和私铁器的生产。除了专营盐铁,政府后续又垄断了酒的经营,采取的也是官酿官卖,禁止私人酿酒售酒。其二是收回民间和地方政府的铸币权,中央政府垄断货币的铸造与发行。汉初70多年间,或令民纵得自铸钱,或禁民铸钱,铸币权多次反复。到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1]1435至此,中央政府完全垄断货币铸造与发行,由朝廷控制货币铸造权和铸钱原材料,建立完整的钱币铸造、发行的管理体制,也为财政开辟了新的稳定财源。
第二,实施平准均输政策。平准是政府设平准官,贵卖贱买以平抑物价,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管制。均输则是政府建立运输队伍,直接选运合适的地方物产充作贡赋以提高地方实物贡赋的效率,“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1]1441,事实上形成政府跨区域经商,贱买贵卖。因均输,政府(大农是具体管理部门)才能有足够的物资平抑价格,“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4]4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政府以平粜或平籴平抑粮价之说,平准则扩展到对市场一般物价的管制。鉴于粮价稳定的重要性,汉宣帝时耿寿昌还设立了专门的常平仓以稳定粮价,“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3]1141官方认为桑弘羊的平准均输政策非常有效,既能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也能保证公平交易,
避免纵强夺弱的弊端;
国家的交通运输组织既扩展了市场、提高了商品流通能力,也能增加政府收入,“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3]1175
第三,强化对工商从业人员的限制。在制度层面上,商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没有新的抑商或者是贱商令,相反,“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3]1159,商人有机会缴纳钱财买爵,还能赎得免除商人不得为官的禁锢。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等本身是大商人或出生于商人之家,而官至大司农、御史等高位。与此同时,加强对商人活动及其财富的管理。(1)规定他们的经营范围,也就是对商业资本的活动范围予以限制。在第一层次上,规定商人(包括其家属)经营范围限于工商业,不得进入农业。在第二层次上,在工商业领域内,不得进入国家专营的冶铁、铸钱等领域。私铸铁器煮盐的要受到严厉惩罚。(2)出台算缗政策,向富人(主要是中等以上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3)严厉惩罚不遵守政策的违法商人及其违法行为。其中影响大的如下:一是因私铸货币而判死刑的数不尽数,“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 [3]1168,其中不少是商人;二是告缗令,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揭发有违法行为的商人,予以重奖。由于有违法行为的商人,特别是资产多的中等以上的商人甚多,“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3]1170。
(二)桑弘羊的“政府干预有效论”
与西汉初期相比,政府从无为转而直接干预市场,从政府的视角以及财政收支问题完成度来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1441的效果,解决了财政困难,加强了政权的力量,消除了豪强大富分裂政权的可能性。但从民间或市场的视角来看,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开利孔为民罪梯”[4]4,以至于在社会上引发广泛争议。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在政府主办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和官方代表就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利弊进行了长达近半年的辩论。桑弘羊作为这些政策的提出者和实践者之一,在辩论中结合经济实践阐明了政府直接经营、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理论依据,在事实上提出了政府干预有效论。
第一,国家直接干预市场的合法性。桑弘羊主张政府可以直接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他正面界定商业的地位和功用,主张农商皆重,本末并利;强调山海川泽及其蕴藏的资源天然归皇室所有,明确政府有权自己经营。“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4]60从产权上看,盐、铁等源自山川大海的资源属于皇室所有,因此国家有权自己经营管理盐铁产业。政府合理合法进入市场,直接专营暴利性行业(盐铁等),将这些潜在的巨大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利润。
另外,政府基于其职能也应该参与工商业经营。汉代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是,一个地区的某种产品如若歉收,便会价格上涨;如若丰收,难以顺利地交换出去,价格便会下跌,造成谷贱伤农等现象。政府采用均输、平准等办法,从供求上加以调剂,实为补救之道。维护市场平稳,对统治者十分重要,这就形成一种传统,一种政府的职责。[7]220汉武帝时期,政府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以应对国家任务的转换,国家财政应该为上述职能提供资金支持。在农业财政收入来源有限以及重农主导思想下,桑弘羊基于汉初工商业发达条件,开辟工商业新财源。盐、铁、币、酒业这些当时主要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都是暴利性的好财源。据此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4]27,“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4]2。
第二,国家有必要干预市场,以抑制大富民,赈困乏,缓解贫富差距加剧的矛盾。桑弘羊说,“山海有禁,而民不倾”[4]61,其原因在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4]60。盐铁铸币行业因技术和地域特点,在开放市场情况下,最终会集中于大户豪民手中,形成事实上的私人垄断。在盐铁铸币三大行业官营之前,正是民间豪强分享这三业的暴利。例如临邛卓氏和程郑、南阳孔氏、鲁人曹邴氏、齐地刀间等,就是这类独专山海之利的豪强大家代表。这些豪民富贾因“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1]1425。更甚者如诸侯吴王刘濞因“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1]2822。吴王因此聚集了很大力量,进而反叛中央政权。
赈困乏,缩小贫富差距,也要求政府干预市场。《商君书》早已把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性提到“治国之举”的高度。将暴利性行业官营,直接减少富人财富积累,抑制以工商业资本进行土地兼并,进而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另外,除了私人因垄断暴利性行业带来贫富差距,民众本身能力差异,也会造成贫富悬殊,因此政府专营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4]166即便是均输政策也可以助力赈灾济贫,因此,政府参与市场活动,不仅仅为了直接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禁溢羡,厄利涂 ”[4]51,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的稳定。
第三,政府干预市场,形成官营与私营并存的结构,是可行的,两者可以互补。桑弘羊时代划分官营与私营活动的范围,除了政府专营垄断的盐铁酒币四业私人不能参与经营外,同时鼓励私人经营非国家专营的工商业。政府自己经商,但大多数商品是私人在经销;政府自己屯田,出租田地,但大多数土地是私人经营的;政府参与民间借贷,但大量的借贷活动是在私人之间进行的。桑弘羊从未提出过反对私人工商业的主张,相反他承认工商业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性,认为本末是互补的。“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墝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4]39经济是一个循环体,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功能,商的功能是“通”和“均”,即促使财货在不同地区流通流转,达到均衡各地供给与需求之目的。“均输”主要是起到补充、调节私人商业的作用,对私人工商业活动打击沉重的告缗政策是杨可提议实行,桑弘羊提议废除的,废除的原因是它伤商太甚,其目的是保护私营工商业者。就汉代的商业而言,在桑弘羊之后,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参与走向衰亡,而是有了新特征:官营商业扩展,在商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私营商业不再经营盐铁,旧的盐铁商人衰落,新的大商人兴起。在四川,“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钜万。”[3]3690在关中地区,“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钜万矣。” [3]3694这些商人多经营丹、豆豉等产业,进行长距离贩卖和金融借贷。这就是说,在国家经营范围之外的工商业领域,私人经营在发展,官营与私营是共存的,共存的原因在于二者各有其活动领域,各司其职,职能互补。在这方面,桑弘羊与商鞅所主张的“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8]等“抑商”“贱商”政策显然是不同的。
第四,桑弘羊“政府干预有效论”的思想源泉。桑弘羊的政府干预市场思路与历史上齐太公、齐桓公、管仲的政策一脉相承。他解释齐国强大的原因在于,“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4]165而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4]85,是秦并六国而成帝业的原因。历史上这些成功的例子,都是以政府之手主导市场要素和资源的轻重,在国家和民众之间进行分配,其理论源于法家思想或者管商之学。汉武帝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董仲舒迎合国家任务转换及由此带来的统治者力图强化君主权威的心理,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并改造其他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建构起的一个“新儒家”思想体系,其特色是儒法合一。正如汉宣帝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3]277表面上“独尊儒术”,但治国原则是“外儒内法”,政治和经济上遵从法家,文化和教育上倡导儒家。法家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达到富国强兵目的,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在不同的时期,法家的富国术都会强调政府(国家)的作用,以政府的力量去聚合国家的各种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变得富强,但具体的专注点不同。战国时代的商鞅主张通过发展农业富国,重农抑商,奖励耕织,重征商税;而桑弘羊则基于当时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与时俱进,偏好通过经营工商业求财。当然,在具体经营的微观层面,当时的人们也认识到国家专营的缺点,例如缺少便利性、产品多样性不足以及成本过高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的政府干预实践从财政以及完成国家任务角度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支撑了汉武帝时期长达44年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河工赈灾等。汉帝国由富国变为强国,成就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名号。我们将桑弘羊阐述的这些论点,概括为“政府干预有效论”。经济学理论中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也有。15—18世纪的欧洲,普遍盛行重商主义思潮,在政策上强调行政干预和政府垄断,其出发点与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一样,也是富国强兵。另外,18世纪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地主、政府等是“非生产消费者”的理论,实际上是主张政府参与市场,把政府作为市场上最大的购买者和调节者,是想通过政府措施以解决滞销或滞涨。[7]221-222这与政府参与商业的平准均输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折衷政策与“政府适中干预论”
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历史上的商品货币关系发生了由盛转衰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生产力进步,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使用僮奴生产的经济模式的主导地位,让位于使用庄客生产的经济模式,社会经济形态从奴主制演变为庄主制。与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这种进步变化相适应的,是社会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的衰退。[9]在庄园里,庄户生产庄主和庄园内人们需要的物品,并在庄园内进行交换,从而将庄园组织成一个经济自给体。庄园经济是一种新的双层结构,它具有双重自给性(庄户家庭和庄园)。在这种结构下,交换主要发生在庄园内部。[10]庄主经济强化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11]因而,桑弘羊主张的政府干预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基础——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同时东汉初历经多年战乱,政府的核心任务是维持政权稳定,政府对市场以及相关政策因任务而变化,国家财政又回归传统,即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户。《后汉书》没有专门的“食货志”。《晋书·食货志》补记的东汉经济史也没有专门涉及政府干预或专营政策,但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可以厘清东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政策及其变化。
(一)东汉政府在干预市场方面的折衷政策
东汉政府在确立工商业政策,即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政策时,可资借鉴的西汉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主要是:以“文景之治”为代表的政府善因论;以汉武帝时期“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1441为代表的政府干预有效论;王莽政府极端的干预政策。东汉是综合考虑这三种政策及其在实践中的优缺点,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主要任务,采取“中和”的态度制订政策的。具体表现有如下三点。
1.放松对私人工商业和商人的从业限制,允许兼业。西汉的商人分为有市籍和无市籍两类,前者地位低贱,与赘婿等同;而后者属于编户齐民。东汉已经不见有关市籍商人的记载,应该是已经废除了。也未见其时有关“贱商”“抑商”的记载。东汉初年,桓谭上书光武帝,谓“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仕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12]958。强调“举本业”“抑末利”。光武帝未予理会。汉明帝时,刘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12]1305主张废止“禁人二业”政策,明帝“悉从之”。于是禁止民众兼商贾的规定也取消了。之后,社会上层“四民兼业”,儒生、官僚、奴主、商人四位一体的现象逐渐普遍,东汉樊氏、阴氏、郭氏、马防兄弟、梁氏等大家族都是如此,人们不再以逐市井之利为耻。
2.政府专营政策在多次反复中逐渐松弛。西汉昭帝“盐铁会议”之后“罢酒酤”和关内铁官。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3]1176。王莽时期扩大了政府专营和对市场管制的范围,号称“五均六筦”②。东汉初期政府的原则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12]2457,源自前朝的政府干预逐渐松弛。在市场价格管制方面,王莽时代的“五均”等政府对市场运行多方面的干预监管被废止,掌管物价的平准令仍在, 其职能已变成是掌知物价,兼掌练染,不再与均输相联。对常平仓、均输法曾有过讨论,但没有恢复。盐铁酒的专营则有所不同。
第一,酒类专卖变成临时性的、局部地域性的偶然政策。东汉的“禁沽酒”多是延续汉武帝之前的旧例,一般因自然灾害而设,少数因财政原因禁私沽酒。例如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二月己未,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12]192。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禁沽酒,此处未提任何灾害,却把恢复酒酤与减少官俸和向王侯借贷并提,应是国家财政困难之故。[12]273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以旱蝗饥馑,“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12]300。汉末,曹操因天灾和战争造成粮食短缺,表奏酒禁。[12]2272灾情缓解,禁令自然也就放松,听任民间私营并收取酒税,当时私营酿酒卖酒很盛,是一个重要工商业部门。
第二,盐铁民营、官营政策有反复,总体而言盐铁经营权限下放至郡县,官营私营兼有,不实行国家专卖。《后汉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注:“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12]3590东汉在中央已经不设统管盐铁的机构,只是在郡县设立盐铁官管理。“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12]3625这表明郡县因为出产不同而设置盐铁机构进行灵活管理。若某地有盐池产盐,有一定规模,国家就会设置盐官进行监管,直接征税;如果没有规模,则不设,任由私营。铁器又不一样,铁资源丰富的地方设置铁官,一般要负责铸造政府所用的兵器、车马用具和生活用具等;其他铁器类产品人民自由经营。但各地具体操作不统一,时有地方政府官营。例如东汉初年,卫飒在建武中(25—56年)为桂阳太守郡时,“又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12]2459同时期的彭宠,“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12]503杜诗建武七年(31年)迁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12]1094,说明在政策层面上,盐铁业向民间有条件地开放,地方政府可因时因势变通,与汉武帝时期的全面专营相比,松弛了许多。汉章帝因财政原因,恢复中央政权盐铁官营专卖制度,并于元和三年(86年)秋亲自“幸安邑,观盐池”[12]156。但其时政府专营政策也没有严格执行,时有例外。如章和元年(87年)广陵太守马稜因本郡“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赢,薄税赋,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12]862。官方规定的盐铁专营也仅仅实施了几年就停止了。章和二年(88年)下诏,“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12]167废除禁民开采盐铁的禁令,允许百姓煮盐铸铁,正常纳税即可。这也并非全部罢除盐铁官,“永元十五年(103年)复置涿郡故安铁官。”[12]191这说明东汉盐铁官职掌大体是双重的,既主持官营,又管理民营,征收税金。即便是官营,政府也不再是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全盘掌控,因而也鲜有汉武帝时期专营带来的负面作用。从此之后一直到东汉末季,政策没有大的变化。
3.货币铸造、管理体制的变化与松弛。自西汉末年开始,一些儒生将贫富两极分化原因归结为货币的使用,取消金属货币的议论时有出现。汉元帝时,贡禹认为“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 [3]1176,建议废除金属铸币,用布、帛、谷交易。汉哀帝时师丹也建议:“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3]3506王莽肆意变更币制以便攫取铸币税,加剧了人们对金属货币的负面看法。因而东汉章帝元和年间有关是否使用货币的争论也不少。如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12]1460东汉经学家刘陶谓:“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12]1846在有汉一代,虽然没有废除金属货币,但东汉政府对货币铸造、发行垄断方面的控制日益松弛,开始下放铸币管制权。西汉武帝铸币集中于都城长安附近并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严禁民间私铸乃至郡国铸钱。王莽时期货币铸造与发行也都是政府垄断。东汉时期铸币权下放到地方郡县,由地方郡县来负责具体的冶铸事宜,中央政府管理货币铸造的部门是太尉属下的金曹,但是它只是进行宏观的调控,并不参与具体的货币铸造。[13]
东汉前期政府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采取折衷政策,对市场放松干预、管制,虽然许多人通过经商发财,但是东汉历史上鲜见盐铁起家的豪商巨贾;人口增长,东汉人口峰值达6 500万,[14]不仅有与“文景之治”齐名的“光武中兴”(25—57年),其后还有“明章之治”(57—88年)和“永元之隆”(88—105年)。
(二)班固的“政府适中干预论”
班固经历东汉前期的全过程(东汉始于公元25年,班固生于公元32年,公元92年去世),是东汉新儒家的代表、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也是东汉帝国皇家政典《白虎通》和前四史之一《汉书》的撰写者。他对桑弘羊的经济才能评价颇高,“汉之得人,于兹为盛……运筹则桑弘羊”[3]2634。将桑弘羊与董仲舒、张骞、卫青等同列为各行业的代表。班固对文景之治也推崇备至,类比周朝的成康之治,“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3]153因此他没有如有些学者那样,采取非此即彼的观点,他既不否定政府干预,也不要求放任无为。班固在其著作中,尝试从经济整体的角度,全面总结西汉经济政策得失;并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视角证明政府适中干预市场、参与经济活动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班固还直面政府干预产生的问题,探讨如何完善政府干预,从而提炼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第一,在考察西汉经济史实中,发现政府完全放任是不行的,政府的某些干预是必要的;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前者首先表现在班固写《汉书·食货志》时,强调了西汉初期因实行放任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严重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3]1137,“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3]4111这动摇了王朝统治的根基。其次表现在班固对汉文帝货币放任政策的评价上。《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都记载了汉文帝坚持“放铸”造成的后果:“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3]1157对此事,司马迁的评价到此为止,班固却进一步引用贾谊600多字的奏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奏文中,贾谊正面论证政府垄断货币发行与铸造可给社会带来“七福”,即“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3]1156又从反面阐述民间自由铸币带来的货币混乱妨碍交易;铸造不合格货币,黥罪泛滥;弃捐农事,采铜者日蕃等祸端。由此可见,班固在对政府放铸政策这个问题上,与司马迁的观点不同,即货币官营是必要的。班固进而指出,在历史上,类似官营的政策早已有之,且成功的事例不少。“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3]1186
后者则是班固在考察新莽的经济政策和实践的史实中,发现政府的过度干预更是社会的灾难。在《汉书·食货志》中班固着力描述了王莽时期的土地、货币和其他方面政府管制政策与前朝的差异,以及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极大痛苦。其一,极端的土地无偿均平改革的结果是:“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3]1144。其二,新朝立国16年,政府肆意更变货币,狂敛铸币税。“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3]1184。其三,王莽推行的直接干预市场价格的“五均六筦”政策,结果是“民摇手触禁”[3]1185。总之,这些过度的干预政策使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政权衰败。
第二,班固尝试从理论上探讨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他所撰《白虎通》是东汉的最高政典。他在其中指出,作为天子的君主,是民之父母,其下属政府的行政目的是“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15]85。所以政府的具体职能不仅仅只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征伐以保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还应该包括经济和社会目标。“天子亲耕以供郊庙之祭,后之亲桑以供祭服。”[15]276这是帝王们日常的规范,表示对耕织经济的重视。在对各级官员的考绩黜陟中也专门提及政府对于保证民众物资生活的职能,“能安民,故赐车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仓廪实,故赐衣服,以彰其体。能使民和乐,故赐之乐则,以事其先也。”[15]304各级官员安民富民,最终达到他们的理想社会:“安民然后富足,富足而后乐,乐而后众,乃多贤,多贤乃能进善,进善乃能退恶,退恶乃能断刑。”[15]304这些观点表明政府首先应该履行其经济职能,才能实现其最终目标。
班固还进一步阐述了政府实现经济职能的落脚点:其一,“《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书》云‘楙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3]1185,《易经》和《书经》等圣人们的经典著作早就指明了需要相关政策促进物资流通供需平衡,互通有无,稳定物价。其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3]1186孟子也早就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因此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抑制贫富差距是政府经济政策应该包含的目标,也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直接动机。
第三,直面政府干预政策的负面作用,探讨完善政府干预的途径,总结出政府适中干预论。班固在评价王莽的经济政策时,指明政府干预政策效果差或失败的原因在于“制度失中,奸轨弄权”[3]1186。这里所说的“制度失中”,指的是政府干预的面太广和干预的程度过深,政府之手基本代替市场的作用(五均六筦)。这种政府过度干预在实践中又给官商勾结创造机会,其结果是无论政策的出发点多么合理,最终都是官民俱竭,政策遭到民众反对,改革失败,政权颠覆。
“制度失中”的反义词是“制度适中”。班固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的制度不能失中,也就是要适中。如何做到适中而不失中?首先是政府干预的范围要适中,其次是干预的具体方法也要适中。王莽的做法显然是在两方面都失中了。汉武帝时期,就范围而言,对盐、铁、酒、货币等行业实行官营垄断;在方法上,在全国范围内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地全方位干预。在班固的眼中,这种制度也是失中的,这表现在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指出的那些弊端。东汉时期吸取教训,在范围上,对暴利性行业允许私营同时不放弃官营,不是政府不参与、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是政府完全垄断、直接自己经营,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管有放。在方法上,变为依据区域资源特征不同,灵活设置职能不同的盐铁机构。这种做法就是趋于中。制度失中和制度适中的核心是“中”,中即度也。政府和市场各自处于什么地位,官营和私营各占多大的比重,都要有个度。提出这个度的问题,是班固的一大贡献。解决这个问题,则是他身后两千多年人们孜孜以求的。
班固反对制度失中、主张制度适中是很自然的事。在他生活的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是以中庸为特色的儒学思想。汉儒郑玄说,“名曰中庸,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16],强调“中和”才有用。中庸也要求循中和之道而为之,倡导不固守过时之事理,也要因时而宜,包纳多元思想。班固是儒家思想的代表,而制度失中本质上是政策缺乏在实践中应有的理性精神,失掉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总之,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东汉政府在建国之初,是综合考虑以前各种政策以及实践中的优缺点,对西汉以来的政府干预政策有因有革,主张适中。我们将东汉政府的这种政策和班固等人对它的阐述与概括,称之为“政府适中干预论”。
四、结语
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实践经验教训是理论创新的土壤;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的,经过实践检验和审视,进而得以指导实践。在两汉400多年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和学者型官员,例如西汉的陆贾、淮南王刘安(《淮南子》)、贾谊、晁错、董仲舒、耿寿昌,东汉的桓谭、王充、王符、崔寔、荀悦、仲长统等,都提及过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观点,其中,理论内涵比较丰富、比较系统、比较有特色的是本文所述三人。他们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观点孕育出中国传统经济学中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三种基本理论模型,即善因论、政府干预有效论和政府适中干预论。这三种理论都是当时特殊情况的产物,都解决了当时的实际问题,因而无优劣之分;也为后世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三条思路,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历史场景与思想资源。
注释:
①本文作者赵德馨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以前。从其萌生到现在,经历了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商品货币关系指远古至汉,又细分为商品货币关系萌生(氏族社会后期:公元前21世纪以前)、形成(家族社会时期:夏、商、西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和繁荣(奴婢主社会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2世纪)三个小阶段。见赵德馨:《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市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②六筦,“筦”即“管”,就是政府管理、主导六种经济活动,即盐、铁、酒、铁布铜冶、名山大川和“五均”。盐、铁、酒这三种商品由国家统一生产经营;铁布铜冶,是指冶铜铸币由国家控制;名山大川,即名山大泽产出归国家所有,这是汉武帝时已有的政府专营政策。王莽政府又加上“五均”,合称为“六筦”。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陆贾.新语[M].庄大钧,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5]老子[M].汤漳平,王朝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138.
[6]亚当·斯密.国富论[M].胡长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9-11.
[7]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8]商君书[M].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1.
[9]赵德馨.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22-123.
[10]赵德馨.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市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2):77-82+116.
[11]冷鹏飞.论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1):34-38.
[12]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徐承泰.秦汉货币若干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3.
[14]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435.
[15]陈立.白虎通疏证[M].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16]礼记正义[M].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87.
责任编辑:韩曾丽
Three Coping Policies and Three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y
Tang Yanyan1,Zhao Dexin2
(1.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s a core issue in economic research. Due to China's long history, vast territory and large population, there are abundant though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history. By the Han dynasty, various theories and policies had been formed.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Huang-Lao School, pursued a policy of laissez-faire, and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resulting in prosperity for both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Si Maqian abstracted the \"Shanyin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based on this. Under the rule of 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 the government monopolized the salt, iron, and wine industries, following the theories of the Legalists, which met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e country's quest for strength. Sang Hongyang summed up the theory of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Confucian theory characterized by the \"Zhongyong\" and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Taoism and Legalism, implemented a compromise policy and realized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n this basis, Ban Gu abstracted the theory of moderat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three theories mentioned above, which were nurtur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cy and practice, provide vivid historical scenarios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government and market; Shanyin thought; the theory of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theory of moderat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istorical scenar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