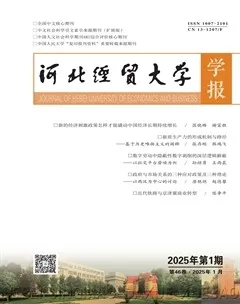新的经济刺激政策怎样才能撬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摘 要:
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政府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增量政策,旨在刺激经济增长。在已经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数十年但提振总需求效果有限的情况下,新的刺激政策资金应该投向何处的问题亟需解答。当前我国总需求不足、内循环疲软的症结在供给侧,大规模生产方式对多样化需求的不适应导致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无法建立。当务之急是把刺激政策的资金投向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解决企业经营困难、提供就业,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拉动内需,为企业生产方式转型创造条件。在长期中,发挥市场的力量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变革,构建以国内为主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重新建立供需良性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
经济增长;刺激计划;乡村振兴;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5)01-0001-09
收稿日期:2024-10-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21amp;ZD070)
作者简介:
匡晓璐(1995-),女,安徽合肥人,清华大学助理教授;谢富胜(1972-),男,安徽枞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通讯作者。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随着世界市场萎缩和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经济也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实体经济内部循环不畅,供给和需求面临双向冲击。2024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①,表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2024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加大宏观调控力度[1]。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明确提出要加力推出增量政策,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2]。2024年国庆节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先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运用增量政策着力惠民生、促消费,加大助企帮扶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等②。诸多重磅刺激政策的出台,点燃了市场热情,带来股市楼市双回暖,摩根大通、高盛等外资投行也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在官方酝酿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前后,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呼吁“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3] ,并热烈讨论刺激政策投向哪里才能推动持续繁荣。经济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通过债务、扩大货币供应等信用创造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刺激政策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资金的去向,比如资金流向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居民消费补贴,效果将十分不同。有效的刺激政策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拉动有效需求,还能帮助畅通经济循环,在长期中促进实体经济领域的价值创造,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反之,则有可能陷入政策陷阱,加剧产能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出现不良贷款问题,等等。究竟把资金投向何处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是当前亟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当大力投资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在吸收过剩产能的同时打造新的生产生活空间,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发挥市场力量推动企业生产方式转型,构建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形成更高水平的良性经济循环,帮助经济重回扩张性增长轨道。
一、总需求不足、内循环疲弱的问题症结在供给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逐渐开始暴露,成为各方关注讨论的焦点。2024年以来,我国GDP平减指数持续低迷,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为3.7%,低于2023年同期增速8.2%,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处于有统计以来的较低水平。③在投资方面,近两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下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低迷,2023年增速仅为2.8%。④总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推行刺激政策,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恰逢其时。实际上,2012年以来我国就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降低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但提振总需求的效果比较有限,甚至有声音认为中国陷入了有钱不投资也不消费的“流动性陷阱”[4] 。因此,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首先需要识别造成当前总需求不足、内循环疲软、经济持续承压的问题症结,才能精准施策,否则刺激政策不但难以见效,反而可能会导致新的政策陷阱。
如果仅从需求侧考虑当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无疑是盲人摸象。没有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持续提高,无论是刺激消费还是刺激投资,带来的增长都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要提高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也不能长期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否则只会让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都源于生产体系创造的价值,这又有赖于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经济内循环。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一般而言,需求侧管理注重短期调控,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解决总量性问题;供给侧管理则注重激发经济长期活力,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解决结构性问题。[5]253一旦涉及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就必须以供给侧为主要视角来看待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5]255;从国内来看,回顾我国历次扩大内需的经验就可以发现,通过供给侧(生产端)的重塑,创造出供给适应需求的良性经济循环,才是使扩大内需的刺激政策有效的关键。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外需急剧收缩,党中央立足扩大国内需求,通过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连续下调基准利率等,着力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不仅稳定了经济增长,更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21世纪初加入WTO后,我国企业以生产和加工模块化部件的方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强劲的外需带动企业出口,创造大量就业,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加工贸易业、房地产业、汽车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进而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上游产业产能扩张,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创造出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这一时期,我国主导型企业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其基本特征是流水线精细分工、专用型机器设备投资和多层次的管理结构,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规模经济和开发标准化产品,这不仅能为全球生产网络大规模地生产标准化零部件,而且与国内城镇化加速发展释放出的大规模标准化需求相匹配。供给适应需求,产品能够卖得出去,上游产业产能得到消化,从经济整体来看企业就有利润,员工就有收入,政府就有税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并且不会造成严重的政府债务,形成了良性的经济循环,中国经济进入兼具增长率效应和增长规模效应的黄金增长期。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国出台了以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为主要内容的一揽子稳增长措施,被称为“四万亿刺激计划”,在短期内稳定了市场预期,使经济迅速触底反弹。但2011年以后,刺激政策的效果越来越有限,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各界也开始讨论这轮刺激计划是否导致通胀高企、加剧产能过剩等问题。
同样是在金融危机后出台刺激计划,同样是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2008年和1998年的政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21世纪初以来形成的供需良性循环已经被打破,2008年的刺激政策却没能促进新的内循环建立,生产体系价值创造步伐放缓,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乏力,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内循环疲弱,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5]253-254由于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产品没有市场,导致企业营收增速放缓,利润率下降,投资没有预期回报,企业不愿意投资。2024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5.34%,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21年的13.5%下降为2023年的6.5%。⑤企业不愿意投资就无法新增就业,人民收入和消费的提高就会受到限制,2024年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分别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约为5.3%和6.7%⑥。在企业利润、人民收入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益加剧,在不考虑隐性债务的情况下,2023年末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已超40万亿元。⑦
供给不适应需求反映的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支撑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转变,大规模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国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不再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由于精细分工生产中的产品缺陷无法及时发现,专用型机器设备投资会导致价值回流具有不确定性,多层次纵向管理结构会因为信息收集处理环节多而导致决策迟缓,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职能分工会导致产品创新缓慢等问题,大规模生产方式能够供给的高质量、高水平产品十分有限,无法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长期作为代工厂的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专用型机器设备需要大量能源资源投入等因素,我国很多企业还十分依赖国外的高技术和资源供给。一旦持续稳定的标准化需求和高技术资源供给发生变化,这种发展模式就会立刻暴露出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需疲软的冲击直接导致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下游加工企业产能过剩,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传导至固定资本投入更大的上游能源、原材料企业,加剧了全产业链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等事件频发,关键核心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问题也成隐患。随着国际循环动能弱化,国内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暴露出来,成为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根本性问题。在需求端,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已经形成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和标准化消费并存的需求结构。但在供给端,大规模生产方式难以满足消费者功能多元、品质优良的产品需求,导致大量消费能力外流。此外,在外需下降的冲击下,大批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就业的劳动者的就业不稳定性增强,潜在消费需求没有稳定收入支撑,不利于标准化消费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导致了“能买不想买、想买买不起”的矛盾局面。居民不消费,企业就没有利润,投资、就业和居民收入都会受到影响,并陷入恶性循环。经济新常态叠加新冠疫情冲击,近年来以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为代表的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真实工资水平也开始下降,进一步增加了消费和投资的下行压力,导致许多经济发达省份出现了投资动力弱化的问题。
二、经济刺激政策应当投向哪里?
随着一系列增量政策的出台,经济刺激已经迫在眉睫。那么,针对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究竟把资金投向哪里才能最有效地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目前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需要加以讨论。
第一种观点主张以刺激消费为主,提振有效需求。我国内需市场广阔,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的一半以上,可挖掘的消费潜力很大。⑧但同时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低迷,很多学者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关于如何改善消费需求,又形成了不同观点。一种流行的主张是效仿发达国家的“直升机撒钱”,以各种方式向居民发放消费补贴。但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消费补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更为重要的发展型消费杯水车薪;对于中高收入人群而言,基本的温饱消费已经满足,在国内产品供给质量没有提升之前,消费补贴也不会增加他们对国内产品的消费。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应当有针对性地刺激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发展型消费,大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并进一步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以上两种主张都有可取之处,但仅从需求端出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有供给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不适应人民需求的问题。只要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国内有效供给依然不足,就难以建立起供需良性经济循环,居民收入就得不到改善,一旦政策红利消耗殆尽,消费依然要面临居民部门预算约束的限制。2023年中国居民部门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已达144.8%,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赶不上债务增长,⑨这将严重影响家庭消费支出。
第二种观点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切实提高人民收入。居民收入已经成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扩大内需、提振消费要求改善收入再分配,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但直接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收入并不一定能使收入转化为消费。如前所述,在供给不适应需求的情况下,居民不愿意消费,供需良性循环建立不起来,收入增长不可持续。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有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民营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⑩提高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短期内将进一步加重中小企业的成本负担。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不足6%、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提高劳动者收入意味着要么压缩企业利润率、要么增加地方政府支出,但将进一步抑制企业的实体投资意愿或加重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因此,改善收入分配的前提,还是提高企业利润率,创造更多的生产和就业。
第三种观点强调要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实际上,2013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各地也不断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的新举措。2021年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成本增速持续下降,到2023年仅为1.2%[11]。但税费只是企业综合成本的一部分,降税费并不能直接提高企业利润率,更关键的问题是营业收入有没有显著提升。2021年以来,虽然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成本增速下降,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导致利润率在2022、2023年出现了负增长。[12]有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指数持续向好。[6]但是,企业的投资意愿依然低迷,这表明即使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只要预期利润率得不到改善,企业依然不会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减税降费还是优化营商环境都会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尽管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置换地方债的方式来恢复地方政府活力,但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终究有限,即使当前地方债存量被消化,如果未来仍不能建立起供需良性循环,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就依然难以持续提高,仅靠地方政府支出来维系,依然会陷入地方财政困境。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当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权、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创新驱动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但创新过程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长期持续的大规模投资和组织学习,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可观的回报,难以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经营困难。并且,在企业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持续进行大规模的研发,将进一步恶化企业的盈利能力。
以上几种措施对促进经济增长都有积极作用,但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并不能解决供给不适应需求的核心问题。若不建立起供需良性循环,刺激政策退场后也无法扭转经济下行的局面。从根本上来说,解决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需要企业转变大规模生产方式,适应需求的灵活变化。但由于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固定资本投入巨大所带来的沉没成本,以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转变生产方式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当前最紧迫的是改变企业经营困难的局面,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利润、创造就业、增加收入,为提振有效需求提供支撑。考虑到经济循环是环环相扣的动态系统,刺激政策的资金投向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能在短期内拉动有效需求,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二是能在长期中为未来发展创造物质基础,特别是创造出推动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有利条件;三是不增加额外产能,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把刺激政策的资金主要投向乡村空间的现代化建设。
三、当前最有效的刺激方向在投资乡村空间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扩展和重构地理空间是化解过剩产能、扩大有效需求、疏通经济循环、恢复经济增长的有效策略。以美国为例,二战期间美国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扩张。1939—1944年,美国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产量翻了一番,整体生产能力提高了50%,仅1944年一年内飞机产量就达到了96 318架。[7]但随着二战结束,战时工业品需求下降,美国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经济循环面临困难,必须为过剩的产能找到出口。美国政府通过扩展和重构地理空间,将欧洲和国内乡村作为新的地缘投资空间。在国外实施“马歇尔计划”,通过对欧洲的战后援助输出过剩产能。在国内发展“郊区化”,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拓展和改造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把郊区打造为新型生活空间,
成为参战归来的人们理想中家庭生活的载体
,创造出家用汽车等耐用品需求,基础设施建设、住宅、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在消化大量产能的同时,通过广泛的产业关联效应进一步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增长。类似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标准化需求饱和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美国经济循环再次受阻,发生了严重的滞胀危机。通过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纳入世界生产体系,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和完备的工业体系转移制造业环节,美国再次恢复了经济活力。结合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当前疏通经济循环的最优地理投资空间在乡村。
首先,我国的有效投资项目没有饱和,乡村有广阔空间。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相当完善了,继续投资基建不仅不能拉动增长,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仍有相当多领域还有投资空间。[8]其中,乡村既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又是巨大的要素市场,但乡村建设的短板还有很多,投资空间巨大。浙江的“千万工程”以农村新社区建设为重点,整治了农村人居环境,改变了农村“脏、乱、散、差”的普遍现象,带动了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民生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提供了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范例。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乡村劳动力不断流入东南沿海地区,支撑了我国经济发展,使东南沿海城市快速繁荣起来,并带动周围乡村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及其乡村发展则较为落后,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和消费潜力。以地下管网建设为例,地下管网是保障城市高效运行的“生命线”,能够满足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等各种现代化生产生活需要,却几乎未在我国乡村布局,发展空间巨大。
其次,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能够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推动相关产业链发展,促进国民收入加倍提高。全面推广“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将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作为主要投资方向,以县域为中心,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条件现代化,强化农村生态治理,将不断吸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但不会增加产能。不仅不会加剧产能过剩,还能够消化上游钢铁、水泥等产业的过剩产能,并提供更多就业和收入,进而拉动消费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帮助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的重要方面。据初步估算,若每年投资3万亿元,将建成8万千米地下管网,可用于8 000平方千米建成区,相当于惠及80多个平均面积为100平方千米的小城镇;还将带动3 000万人就业,拉动GDP增长约6万亿元,以2023年我国GDP规模计算,这将使经济增速额外提高4.76个百分点。如果连续投资10年将更新再造8万平方千米乡镇建成区,约为已有乡镇建成区的两倍,而全国农村土地总面积约为436万平方千米,更新再造8万平方千米乡镇建成区不仅可行,还将大大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经济发展。[13]考虑到建设工程的长期影响,推动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会释放巨大的创造动能和消费潜能,有助于构建国内的大规模消费市场,使生产、就业、收入同步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最后,乡村空间现代化将为产业转移提供物质基础,是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在乡村建设现代化的生产生活空间,是吸引劳动力和现代生产要素流入的前提,也为企业入驻乡村提供了物质保障,有助于形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分工的县域经济。地方政府应当做好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协调发展生态产业、绿色农业,同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2016年,浙江蒋村村在腾退“低小散”企业、土地流转归集后,建起了高科技产业园,吸引高科技企业入驻,并以村集体为单位共同出资成立公司,投资园区的开发建设,每年从中获得投资额10%的保底分红,切实提高了农民收入。
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需要持续的大规模投资,那么数万亿的资金从何而来?2024年以来,我国开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5年将继续发行并进一步优化投向。如果能腾挪出一部分资金持续用于乡村空间的现代化建设,释放出的增长潜力将不可限量。然而,大规模的发债也引发是否会加重财政负担、导致通货膨胀、抽走市场流动性的担忧。首先,长期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有30~50年的腾挪空间,并且建设工程能够创造出大量就业,提高收入,带动内需,帮助企业恢复利润,长期来看不会加重财政负担。例如,1998年发行的30年期的2 700亿元特别国债,在当年来看占到财政支出的25%,但放到今天来看已经不到1%。其次,在经济下行、物价下降的情况下,生产资料价格较低,大规模发债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只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协调配合,就不会抽走市场流动性。如果财政部公开向市场发行超预期额度特别国债,确实可能会冲击市场流动性。但从过去发行特别国债的经验来看,我国主要采取定向发行的形式,由央行降准或额外投放资金等方式最终购买这些特别国债,对市场流动性影响较小。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9]。只要供需良性循环建立起来,经济有规律地扩张,今天发行的货币就能够在未来形成对应的价值,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会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除此之外,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集中化投资,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进行顶层设计,并集中资源有序推进。一方面,应当利用城市辐射效应,重点在国家规划的19个城市群周边开展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集中化的投资必然涉及合村并居,要由农业农村部牵头设计,各部门与各级政府通力合作,集中社会资源,以农村居民的利益为核心,遵循村庄演变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同时,应当填补、充实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村集体组织“统”的职能,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集体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作用。
四、发挥市场力量推动经济重回扩张性增长轨道
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还将创造出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和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能够在短期内帮助企业纾困,但地理空间扩展和重组始终建立在既定的企业生产方式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供给能力。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来看,经济的持续增长依靠的是生产方式变革,重建供需良性循环。美国在战后和20世纪90年代分别形成了大规模生产和全球生产网络两种典型生产方式,分别与当时的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和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相匹配,才得以在地理空间扩展和重组后持续获得经济增长。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低成本地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多样化需求,新的生产方式必须将生产的大规模和品种的多样化结合起来,这是现有的劳动密集型流水线工厂难以做到的。转变生产方式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依靠市场力量推动,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就为企业变革生产方式提供了前提条件。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会吸引更多农民工回乡回土,这一方面将提高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也就是提高居民收入),促使企业革新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为县域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原来布局在核心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大规模生产企业可以加速向非核心城市和县城转移,有助于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一旦在县域有了一定规模的稳定的产业、人口和收入,就可以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社会保障项目,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融合,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
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环节向非核心地区疏解,为核心城市重点打造创新型领头核心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创造了条件。核心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剥离非核心的生产制造单元,简化业务流程,使组织结构扁平化,以关键核心部件为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专注产品开发设计、关键部件创新、品牌经营和系统集成等附加值更高的环节。作为关键节点的专精特新企业则专注于某一子系统的研发和技术创新。领头核心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布局在国内各城市群的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利用人才、金融等资源优势形成创新中心,打造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同时,疏解到非核心地区的企业,可以继续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保证大批量生产。核心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集成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供应、生产、批发、销售等各项业务活动,并由物联网平台按需调度,与其他层次的企业协同生产,及时响应多样的需求、多变的市场和频繁的技术更新,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和高效率,最终构建一个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
新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利用了我国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以国内为主体,很好地规避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缺陷。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虽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由于将制造环节外包到其他国家,大量曾经在大规模生产企业就业的美国工人失去了稳定的工作,或是转向低端服务业就业,或是参与零工经济,收入更低、就业极不稳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不仅如此,由于本国核心企业外包了制造环节,只需进行供应链管理,释放了大量原本用于固定资本投资的资金,这些资金转向金融领域,加速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这些变化趋势相叠加,最终造成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在空间上分离,实体和金融不平衡发展,利润和工资不同步增长,财富不平等程度加剧。我国如果通过乡村空间现代化建设,为制造环节向县域转移提供条件,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免于国际逐底竞争的稳定就业,能够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同时,专注研发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能够创造出大量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当前中国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再造4亿规模,经济潜力不可限量。
在实际的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除了市场力量外,还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各城市群要找准定位,主动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建立产业体系新支柱。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定位,建设供应链配套的工业园区,打通城市群内部的物流交通网络,积极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或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财政支持和融资渠道。随着国内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的建立,更高水平的供给体系能够满足国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保障就业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利润,这将大大改善居民收入分配,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更高水平的良性经济循环,使人口分布更加均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收入分配更加优化、城乡和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世界发展与繁荣注入不竭动力,1979—202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居世界首位[14],中国未来能否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虽然面临挑战,但只要抓住机遇,就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世界典范国家。要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就要充分利用“绿色”和“数字”两个赛道,在短期内大量投资乡村空间的现代化建设,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在广阔的乡村腹地创造出吸引人才、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聚集的新的生产生活空间,恢复企业的盈利能力;在长期中,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企业生产方式转型,以国内为主构建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提升供给体系适应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能力,在全社会建立起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就业、收入同步增长,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不断缩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注释:
①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7/t20240715_1955618.html,2024年7月15日。
②《国务院新闻办就“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 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410/content_6981015.htm,2024年10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就“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410/content_6981031.htm,2024年10月12日。
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7/t20240715_1955618.html,2024年7月15日;《2023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7/t20230715_1941269.html,2023年7月17日。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数据来自CEIC经济数据库。
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参见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amp;zb=A0201amp;sj=2023。
⑤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24年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0.5%》,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9/t20240927_1956742.html,2024年9月27日;《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4.9%》,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1/t20220117_1826439.html,2022年1月17日;《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401/t20240117_1946635.html,2024年1月17日。
⑥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24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7/t20240715_1955615.html,2024年7月15日。
⑦《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09/t20240913_439617.html,2024年9月13日。
⑧最终消费和GDP数据参见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amp;zb=A020C0205amp;sj=2023。
⑨计算所用数据参见: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http://114.115.232.154:8080;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amp;zb=A0A01amp;sj=2023。
⑩《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介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关情况》,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457.htm,2023年7月21日。
[11]2021—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成本增速分别为19.1%、7.1%、1.2%。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4.3% 两年平均增长18.2%》,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360.html,2022年1月27日;《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4.0%》,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1/t20230131_1892601.html,2023年1月31日;《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3%》,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26_1946914.html,2024年1月27日。
[12]2021—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9.4%、5.9%、1.1%,利润率分别为6.81%、6.09%、5.76%。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4.3% 两年平均增长18.2%》,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 0203_1901360.html,2022年1月27日;《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4.0%》,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1/t20230131_1892601.html,2023年1月31日;《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3%》,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26_1946914.html,2024年1月27日。
[13]此数据为综合各个公开统计数据进行的初步估算。第一,考虑到“七通一平”中通路是最为基础的,计算地下管网的合理密度时参考路网密度,假设每条主干道下方铺设一条地下管网,且每平方千米的辅助道路和小区道路需要额外的管网支持,参考2022年中国建成区约7.6千米/每平方千米路网密度,假定地下管网密度以10千米/每平方千米计。第二,综合各方公开数据,假定地下管网每千米平均造价为5 000万元。第三,投资乘数使用最新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局部闭模型,将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和消费内生化计算得到。第四,根据住建部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我国乡镇建成区面积约为4.3万平方千米,根据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宫鹏研究组统计,2017年我国农村建成区面积约为6.4万平方千米。
[14]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七十五载长歌奋进 赓续前行再奏华章——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fx/xzg75njjshfzcj/202409/t20240911_1956384.html,2024年9月9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N].人民日报,2024-07-31.
[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N].人民日报,2024-09-27.
[3]刘世锦.以一揽子“刺激+改革”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内需[N].中国经济时报,2024-10-09.
[4]曹韵仪.增发的钱流向何处[N].国际金融报,2023-06-19.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6]王小鲁,樊纲,李爱莉.中国分省营商环境指数2023年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2.
[7]MORGAN T D.The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of world war II: America goes to war[J].Army History,1994 (30): 31-35.
[8]余永定.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N].大众日报,2024-10-22.
[9]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59.
责任编辑:韩曾丽
How Can the New Economic Stimulus Policy Incite China's
Long-term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Taking the \"Second
Kuang Xiaolu1,Xie Fusheng2,3
(1.School of Marxism,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China is currently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advancing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countr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all respects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ced with downward economic pressure domestically, th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and introduced a series of incremental policies aimed at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after decades of implementing active fiscal policies with limited success in boosting overall demand,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new stimulus policy funds should be allocated has become urgent. Currently, the root cause of insufficient overall demand and weak internal circulation lies o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inadaptability of large-scale production mode to diversified demand leads to the inability to establish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immediate priority is to direct the funds of the stimulus policy towards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paces, addressing business difficulties of enterprises, providing employment, and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while resolving overcapacity. This would als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models. In the long term, it is essential to harness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to drive changes in enterprise production methods, build a digital industrial ecosystem with a domestic focus, and re-establish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reby promoting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stimulus pack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 of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