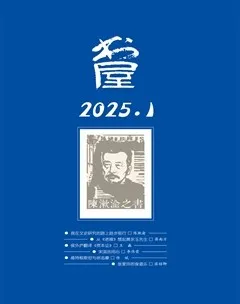钱穆的辩护
晚清鸦片战争以来,甚至更早,面对外来的西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凌厉攻势,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力图寻求自强自救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制度和西方制度的态度不断变化,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对我国传统制度一度几乎全盘否定。近代部分学者认为,秦代以来传统政治无不是黑暗专制。梁启超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萧公权认为中国从秦汉到清末,“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即使是倾向传统的新儒家张君劢,在晚年也断定中国古代政治为“专制君主政治”。照此逻辑,落后挨打都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要自立自强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对此,钱穆自然进行了长期深刻的思考,并做出了系列回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他的回应之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选择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从“政府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入手,分析评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这四项制度,绵延两千余年,汉代的制度最受钱穆的肯定。一开篇即论述“皇室与政府”的关系:“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照此看来,皇帝只是“虚君”,宰相对皇帝有监督作用,简直等同近代的君主立宪政体。接下来还有例证的史料:皇帝的秘书机构“六尚”,相对于宰相的秘书机构“十三曹”,无论是人员规模还是职责、权力等都小得多;宰相可以管到皇室的一切,如少府掌管皇室经费,而宰相可以支配少府,即皇室经济也由宰相支配。其他如中央和地方关系、地方行政制度、官员选拔制度、赋税制度、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更加受到钱穆的推崇。“‘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汉武帝以后的太学制度、乡举里选制度,突破了封建世袭,有利于读书人进入政府且良性流动,实现了教育、行政实习、选举和考试的全链条衔接。汉代公私分税、盐铁专卖、田赋三十税一,达到了轻徭薄赋的理想状态。汉代到中央做“卫”兵,来回旅费由中央政府供给,初到和期满退役,皇帝备酒席款待,平时吃穿都是国家负担,待遇十分优厚;到边郡做“戍”卒或者原地服兵“役”,只要服役三天,也可以交钱代替,人人平等,宰相的儿子也去戍边。钱穆注意运用史料,注意与西方国家的对比,增强说服力。
汉代制度大致如此,后来的朝代尽管有败坏,有改进,但基本制度还是沿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度、租庸调制度等明显是进步了,钱穆对“定旨出命”“五花判事”“涂归”“封驳”“驳还”“政事堂会议”“斜封墨敕”等很看重,作为相权制约皇权的重要例证。对于那些明显异化甚至走向反面的制度,钱穆联系时代变化来分析原因,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但是,明代废除了宰相,清朝变本加厉设立军机处,皇帝一人独裁走向极端,对此如何辩护?钱穆创造出“法术”这一概念:“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
明代尤其是清代,制定了大量特别恶劣的制度。例如:明伦堂的卧碑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残害知识分子,愚民政策用到极致。钱穆将诸如此类的特别恶劣的制度统统归类为“法术”,并踢出制度的范畴,从而达到补正论点的目的。不过,钱穆自己也承认,制度和法术难以区分,清朝几乎是全无制度。显然,恶劣的制度也是制度,钱穆如此处理只是行文的技术策略,回避了论点包含的矛盾,仍然无法自圆其说。
钱穆为制度辩护,但目的显然不止于此。制度的背后是文化,作为受传统文化所化之人,传统文化融入其血液和精神,文化认同尊崇已经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钱穆在《国史大纲》序言就提出,本书读者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这其实是钱穆的文化态度,不单单针对《国史大纲》,而是适用于他所有的著作,包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谓的“已往历史”就是广义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心理和器物等各个方面。“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先在肯定和辩护。钱穆经常从制度看到背后的文化,在与西方制度、文化的对比之下,往往自豪感、自信心油然而生。例如说到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这种精神说明白了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共识,对知识改变命运、公平竞争的社会共尊共信。钱穆甚至非常自信地表示:
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般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
钱穆对西方各国政治素无研究,单纯从立国历史、地理特点、政体稳定性等方面来比较,收获满满自信心。他还坚定地认为,汉代实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西方则是到了俾斯麦时期才发明,优越感非常强烈。他没有意识到普鲁士义务兵役制度现代化而高效,汉代兵役制度虽然看起来与之类似,其实无法相提并论。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力强盛,这些钱穆都视而不见,其说服力自然大打折扣。
在该书的序言和正文,钱穆多次强调: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是钱穆最看重的论据。钱穆最为推崇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然而,有学者列举了汉武帝的五位宰相的命运:李广的从弟李蔡在元狩二年(前121)由御史大夫迁丞相,任职第四年,因在景帝陵园前大道两旁的空地上埋葬了家人而获罪,在监狱里自杀。武强侯庄青翟在元狩六年(前117)四月任丞相,元鼎二年(前115)十二月被捕,在监狱里自杀。高陵侯赵周元鼎二年任丞相,元鼎五年九月被控告明知列侯所献黄金不足却不上报而被捕,在监狱里自杀。葛绎侯公孙贺在太初二年(前103)迁丞相,因前三位丞相都死于非命,跪地磕头哭辞未果,征和二年(前91)获罪被诛并被灭族。彭城侯刘屈牦在征和二年任左丞相,一年后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腰斩示众,其妻儿被枭首。五位宰相无一不是家破人亡,哪里有监督皇室的可能?事实上,对于秦代以后君主专制的反人性、黑暗残酷及严重负面影响,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早有定论,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等基本上是沿袭观点而已。
除了“不是”专制以外,钱穆还提出了“不能”专制。他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因为国家太大了很难掌握。这明显低估了专制制度与武力结合的残酷威力,忽略了长期陈陈相因的专制文化、社会心理的强大影响,更加忽略了大量帝王专制独裁的历史事实。往往是国家越大,皇帝能支配的资源就越多,拥有的武装力量就越强,独裁程度就越深,范围就越广。例如,明代和清代相比宋代,国土更加广阔,财政和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因而皇帝的独裁专制程度更深、范围更广。
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自然无意卷入政治漩涡,但实际上产生了为专制独裁辩护的效果,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宪政的拥趸自然不用说,即使是倾向传统文化的新儒家也看不下去。新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以三十万言的专著《中国专制君主政制评议》来回应。张君劢认为,钱穆观点偏颇,对国人政治思想负面影响极大,从逻辑方法、专制君主、宰相、三省制、铨选、台谏、地方自治、政党、法治与人治、安定与革政等方面对钱穆一一批驳。另一位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在《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指出:“我和钱穆先生有相同之处,都是要把历史中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但钱先生所发掘的两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成见太深,而又喜新好异,随便使用新名词,所以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连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做直感的、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
徐复观对钱穆的批评严厉而愤怒,显然超越了具体学术问题,上升到了价值观念、学术品格和学风等层面,断言钱穆已经站在科学、民主和良知的对立面。李敖是钱穆的学生,曾经因为钱穆未评上“中央研究院院士”迁怒胡适。但他也认定钱穆是“一位反动的学者”,是为专制独裁辩护。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其优秀之处数不胜数,钱穆的辩护在纠正全盘西化、树立文化自信心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章士钊在欧洲寻求民主政治范式,被外国政治家告知:“中国历代相沿之科举制度,与民主精神相契合。”蔡锷遗书云:“今日之政体孰善,尚乏绝端证断。”前者自然有道理,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正面文化精神,但显然也包含了异国人士眼前的陌生化效应。蔡锷所论者一方面是针对政体而言,另一方面是为杨度说话,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在文化自信和文化保守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钱穆没有准确把握这一分界线。从原始时代以来,民主的火种隐隐闪现,一直绵延不断。尤其是近代以来,民主、科学和反专制反独裁的潮流滚滚向前,钱穆的辩护脱不了为专制辩护的嫌疑,自然要受到质疑和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