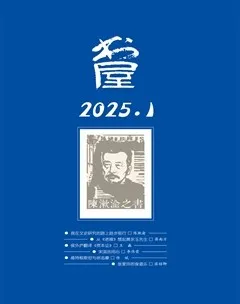张伯驹与梨园界
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文化人士,一生最在意者有四件事:诗词、收藏、戏曲、书画。张伯驹醉心于传统戏曲艺术,是知名“票友”,有“天下第一名票”“当世票友耆宿”“票友大王”“票界名宿”等美誉,熟稔梨园界各种人物行状、掌故趣闻,带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张伯驹说,梨园界在清末前“以票友转为伶者谓之‘下海’,皆名‘处’,如孙菊仙名‘孙处’,许荫棠名‘许处’”。此等说法,对于笔者而言,简直闻所未闻。原来“下海”“处”等词汇,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语境中,还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含义,真是令人眼界大开,着实长见识了。
张伯驹诗云:“八旗子弟气轩昂,歌唱从军号票房。”诗下的注释是:“非伶人演戏者称票友,其聚集排演处称票房。”原来如此呀,非专业演员唱戏者被称为“票友”,他们聚集在一起排练的地方,则叫作“票房”,这与现今特指电影或戏剧商业销售情况的“票房”一词,意义就相差甚远了。“对啃一场精彩甚,真如锦上更添花。”说的是,旧时艺人演出时如果大为卖力,极其投入,那么“内行谓之曰‘啃’”。“啃”字竟有此意,恐怕绝大多数人很难想到。
张伯驹还给我们讲述了很多梨园行的逸闻趣事,这些“冷知识”让读者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大长见识,还能“于茶余酒后,聊破岑寂”,如饮甘醴,直呼过瘾。
对于艺人的精彩表演,观众往往如痴如醉,对于心中偶像艺人的追捧,“粉丝”们也是十分狂热,甚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独占花魁三庆园,望梅难解口垂涎。此生一吻真如愿,顺手掏来五十元。”张伯驹的这首诗,讲述的就是一件关于“粉丝”的趣事。民国初年的警察条例规定,凡是调戏妇女者,罚大洋五十元。坤伶刘喜奎色艺并佳,最擅演《独占花魁》,“人即以‘花魁’称之,为其颠倒者甚众”。有一天晚上,刘喜奎在三庆园演出散场后卸妆,刚走出戏院大门,“遽有某人向前拥抱吻之,警察来干涉,某即掏出银元五十元,曰:‘今日如愿矣!’扬长而去”。“粉丝”的狂热,对所喜爱演员的追捧,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名河南人,张伯驹对河南的地方戏也很喜欢,并有深入的研究。他说:“河南剧种颇多,主要为梆子戏,有豫东梆子、豫西梆子,另有南阳曲子戏、越调、漯确戏、二家弦等剧种。戏班中以老生为主角,但不曰‘老生戏’而曰‘红脸戏’。红脸非关羽,乃赵匡胤也。”河南以梆子戏流传最广,豫东梆子陈素真、豫西梆子常香玉,都是河南的知名旦角演员,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张伯驹说:“难把东西论后先,闻香一队满秦川。洛阳因预同场会,我亦名登捧狗团。”陈素真和常香玉才艺精绝,声名远播,因而也都有各自的“粉丝团”。常香玉的“粉丝团”名为“闻香队”;而陈素真有一小名曰“狗妞”,所以其“粉丝团”名为“捧狗团”。张伯驹自述:“余在洛阳曾与陈同场演出《战太平》,名因列入‘捧狗团’矣,且余亦豫东人也。”张伯驹的故乡河南项城,位于豫东大野,张伯驹身为豫东人,亦力捧豫东梆子陈素真,成为“捧狗团”之一员。
坊间流传甚广的“民国四公子”,一般指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和张伯驹。溥侗乃前清宗室,世袭镇国将军,“号红豆馆主,能戏,文武昆乱不挡,皆学自名老艺人”。袁克文为袁世凯次子,号寒云,亦能戏。“将军红豆问如何,昆乱兼全腹笥多。惨睹当推曹子建,搜山传自沈金戈。”张伯驹和溥侗、袁克文相熟,同时也都是京剧“名票”,曾和溥侗、袁克文一起票戏,故而对溥侗、袁克文演戏的品评十分精准到位,而且知人论世,结合溥侗、袁克文的身世谈论其扮演角色,更有他人无法企及的精辟见解。比如,张伯驹认为,《惨睹》一剧必须由袁克文来演,“因寒云有家国身世之感,演来凄凉悲壮,合其身份”。而《搜山打车》一剧,则“红豆演来更生动沉郁”。这些都是客观公允之语。“慷慨淋漓唱八阳,悲歌权当哭先皇。”袁世凯去世以后,袁克文曾和溥侗一起演戏,袁克文饰演《惨睹》中的建文帝一角,“悲壮苍凉,似作先皇之哭”。真的是有感而发,情真意切。“漂泊天涯剩琵琶,故京犹念帝王家。更看烽火连三月,风景江南正落花。”诗歌用杜甫咏李龟年流落江南的典故,感慨溥侗的晚景凄惨:“红豆无人闻问,贫病以死,以王孙而结局尚不及李龟年,可惨也。”溥侗以末代王孙的身份,最终却贫病而死,着实令人唏嘘。
文武小生茹富兰,眼睛高度近视,“对面只见人影,但在台上对打及《群英会》舞剑,进退步法不失尺寸”。何以至此?“因有武工根柢、台上经验,始能如此也。”什么叫游刃有余,茹富兰演《群英会》,就是最好的注解。“短视小生茹富兰,歌台尺寸走如盘。试看舞剑群英会,进退都无步法难。”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武工根柢、台上经验是何其重要,台上经验丰富的演员,早已将一招一式刻在了骨子里,只要一登台,立马自然而然、行云流水般展示出来,宛如庖丁解牛,闭着眼也能把牛肢解了。茹富兰的这种造诣,正如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所说,任何高超的技艺都没有别的奥妙,只不过是手熟练罢了。在背后,茹富兰是下了苦功夫的。
“歌来断续比诗吟,遮月微云半哑音。”这两句诗讲的是京剧演员贾洪林,“嗓音时哑时亮,如微云遮月,唱法时断时续,比诗人之吟,极饶韵味”。贾洪林的嗓音时哑时亮,听上去如微云遮月,就像诗人的吟诵一样,抑扬顿挫,饶有韵味,人们把这种唱法称为“云遮月”,张伯驹对这种唱法极为欣赏。其实,不少听过张伯驹唱戏的亲朋挚友回忆,张伯驹的嗓音也是典型的“云遮月”。“遮月嗓音近似余”,张伯驹也曾自述,他的嗓音和一代京剧艺术大师余叔岩一样,皆为“云遮月”:“余嗓音亦为云遮月,故唱颇能近于(余)叔岩。”
张伯驹诗曰:“请来翰苑为题鸿,俗吏堪嗤礼未通。岂可哀荣分贵贱,王三杨大不相同。”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张伯驹既有一代名士之风,又有现代的民主平等观念,更显示了其刚直耿介的性格和疾恶如仇的精神。在旧时代,人死后有所谓“题主”之俗,即立一木牌,上写死者衔名,用墨笔先写作“某某之神王”,然后于出殡之前,延请德高望重且有功名的长者,用朱笔在“王”字上加点成为“主”字,谓之“题主”,亦称“点主”。1938年,京剧武生杨派创始人杨小楼病逝,其女婿刘砚芳找张伯驹帮忙,请人为杨小楼“题主”。张伯驹欣然应承,请了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著名学者傅增湘为杨小楼“题主”,这对于逝者及其家属都是一种荣耀。张伯驹后来回忆:“对此事,有人谓余曰:‘杨小楼伶人也,也要题主?’时北京沦陷,日人组伪政府,王叔鲁克敏任委员长,值其六十岁生日,广发征寿文启,设筳庆寿,余对曰:‘王三老爷汉奸能作寿,杨大老爷伶人岂不能题主乎?’其人不能答。一时梨园传为快事。”
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与程砚秋,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王瑶卿曾对“四大名旦”各有一字之评,甚为恰当。张伯驹则分别以诗记之。王对梅兰芳评一“样”字,谓其扮相雍容华贵,俨若天神,无人可比。“严妆仪态谁能比?此是梨园富贵花。”对尚小云一字之评为“棒”字,说其武工有根柢,交友重然诺,能急人之难。“更是武工根柢好,鼓声犹忆战金山。”对荀慧生一字之评为“浪”字,言其演花旦戏能入神。“梆子休从论出身,浮花浪蕊亦天真。”对程砚秋一字之评则为“唱”字,谓其注重唱功,身段武工皆在其次。“梅去美苏程去法,张冠李戴至今传。”
张伯驹诗曰:“东瀛有客号行家,论戏评人或不差。接洽时常称种种,报端自署辻听花。”当时的《顺天时报》曾专门开辟一个评戏专栏,所刊文章由日本人辻听花执笔,一时间,“竟有坤伶为能常名见报端,而认其为义父者”。这就是典型的认贼作父了,对此等艺人,张伯驹不屑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