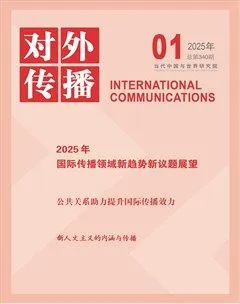回顾与前瞻:2025年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新趋势
【内容提要】在国际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和技术飞速演进交织的背景下,2024年的国际传播研究聚焦“全球南方”的视野转向、地方的国际传播潜力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审慎应用三大核心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2025年国际传播实务进行前瞻:调动多元主体和拓宽传播渠道,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和推进文化传播机制建设,构建以“效力”为核心的国际传播体系将成为今后开展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国际传播 全球传播 全球南方 生成式人工智能 数智技术
2024年是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和国际秩序加速重塑的一年。一方面,长期危机(Permacrisis)背景下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仍,俄乌冲突拉锯超过千日,中东局势又增添新变数,局部地区紧张气氛不断。与此同时超级大选年带来了全球主要力量的政策转向,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全球右翼势力抬头和欧洲、日韩等的政局变换给世界局势带来了更多不稳定性;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的正式扩容,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在拉美国家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彰显了“全球南方”作为代表和平发展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除了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媒介技术的飞速演进也成为未来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变量。
本文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和传播技术带来的国际舆论生态的改变为两条主线,首先对2024年的国际传播研究进行整理和回顾,从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选择“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战略传播”和“全球传播”等主题关键词检索2024年1月1日至12月9日时段内的相关期刊论文,共得到有效文献2203篇,从中重点归纳和梳理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几条主要关键进路。同时基于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和对国内外相关前沿文献和数据的分析,本文对2025年的国际传播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以期通过对国际传播前沿议题和趋势的把握,供学界和业界镜鉴,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2024年国际传播研究回顾
(一)“南方转向”:拓展全球南方视野
2024年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一年:从年初的金砖国家正式扩员到10月的喀山金砖国家峰会,从北京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到巴西举办的G20峰会和秘鲁举办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全球南方”在遍布危机和冲突的世界格局中扮演着合作共赢的重要角色。全球传播的“南方转向”也成为2024年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从理论构建的角度看,“全球南方”代表了“去西方化”视角下的研究范式革新。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传播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去西方化”和“去殖民/后殖民”的呼声此起彼伏,①然而由于媒体和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这类呼声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全球南方”的共同崛起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为其彰显本土智慧和“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铺平了道路。构建“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时机业已成熟,编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知网”成为新时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②
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来看,“全球南方”更加关注和平与安全、合作与发展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等传播议题。③这些议题是“全球南方”的共同关切和切身的痛点,同时代表性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些议题中具备独特的叙事视角,但往往因在国际社会的弱势地位和话语权的缺失而被忽视。如何设置属于“全球南方”的世界议程,构建“全球南方”的集体记忆和共通的话语体系,是“全球南方”国家构建传播共同体的方向。
当前全球文化格局呈现出政治文化“北退南进”、文化产业“北降南升”和文化技术“北领南追”的格局。④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和潜在的文化吸引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在全球的“反向流动”。今后,南方国家应当抓住技术革新的契机形成创新合力,借由“转文化传播”的理念实现“破圈”,推动构建更加多元和谐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南方”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面临着一些困局。从内部看,尽管对话和合作为主流,但异质性较强的“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依旧存在一定竞争,仍需求同存异和凝聚共识,构建传播共同体,为推动国际格局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建设性力量。从外部环境来看,少数北方国家凭借其传统实力和话语权力,介入“全球南方”的合作和发展,将其“阵营化”和“武器化”,进而渗透和阻挠“全球南方”的发展与中国的国际合作。厘清内外部的机遇和挑战,制定更为精准和灵活的对策,推动“全球南方”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是2025年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的重点战略方向。
(二)关注地方:搭建全球与本土桥梁
随着国际传播逐渐上升到战略传播的高度,我国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正不断向纵深推进。在以六大中央媒体为核心的国际传播“国家队”的引领下,众多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挂牌成立。据统计,2024年我国已有至少27个省份设立了国际传播中心,更有部分市县开始涉足和探索国际传播,形成国际传播力量的涓涓支流。地方如何发挥其独特优势,成为联通全球与本土的桥梁和纽带,成为2024年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方向。
从理念维度来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通过“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理念融合,⑤抓住自身的文化特色和独特的在地故事,充分考虑到自身所辐射的目标受众的接受习惯进行精准传播,从而实现本土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双重建构。云南省重点打造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外宣IP,借力亚洲象“北上南归”和红河“蝴蝶大爆发”等多个媒介事件推动多主体、立体化的复调传播,不仅与世界各国分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独特经验,还有力回应了与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相关的全球性“长期危机”议题,在国际舆论场上收获了大量关注和赞誉。
从实践维度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采用了央地合作、报业自建、广电自建、“报业+广电”共建共推和搭建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等多种方式,⑥在实践中发挥了阐释国家发展理念、服务重大主题外宣工作、传播多元区域形象和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等功能。⑦目前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初级阶段,在发展潜力巨大的同时也出现了资金受限、人才不足和经验缺乏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部分省市的先行先试的有益探索和不同区域之间交流合作加以解决。
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看,我国的地方视角、基层经验与“全球南方”议题的结合也推动了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2024年的哈拉雷非洲论坛展示了“南南传播”事业下乡村故事的多重面向,从政治、经济和生态三个角度讲述了全球视野和城乡关系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凸显了“地方”在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创新中的引领作用。⑧
随着我国的不断开放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增强,地方正逐步成为“全球地方”,在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范畴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倡导的“世界交往体系”的落地生根。⑨如何从理论上为地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普遍性和规律性指引,并结合地方特色进行案例分析和研究,是2025年我国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又一个重点方向。
(三)审视技术:人工智能的赋能与治理
2024年,ChatGPT、Gemini和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更新迭代。语言类大模型在数据收集与预处理、智能交互和推理能力上持续进化,视觉和多模态大模型在内容的动态与创造性生成维度上取得重大突破,加速了信息生产与消费行业的变革与重塑。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低门槛和应用开源化为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的路径,不仅从内容生产上极大推动了文图声像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产出,10而且在传播过程中通过算法提升了精准性和互动性。112024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了我国首部文生视频AI系列200集动画片《千秋诗颂》和首部AI全流程微短剧《中国神话》及其多语种版的制作、首部AI译制英文版系列微纪录片《来龙去脉》,12通过人机协同高效实现了跨文化和跨语际产品的生产和输出,成为了利用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为国际传播生态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首先,ChatGPT等大模型技术使得国际舆论格局由互联网时期的“去中心化”特征向人工智能时期“超级中心化”特征发生转变。13少数技术领先者通过资金和数据优势,不断研发和优化模型,形成核心技术和用户体量上的垄断地位;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意识形态传播由强势输出向隐蔽渗透的模式演进。ChatGPT等西方大模型背后的训练数据集合资本力量将决定了其会以隐蔽的方式输出意识形态。而不少大模型正日渐适应用户的深度需要,甚至获取了用户信任从而剥夺了用户主体性;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剧了原本网络环境中的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社交机器人拥有更为自然流畅的多轮对话能力,算法推荐能提供更强大细致的人物画像和多语言能力更有针对性进行干扰,深度伪造(deepfake)走向多模态从而更加真假难辨。
对此,关键技术的反制和自主大模型的研发、更具针对性的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协同共治才是有效的应对之道。2024年6月,中国领导人在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时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的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以此为路径开展的人工智能共治在国际社会的推进和落地有助于有效把控风险,发挥其积极力量,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二、2025年国际传播实务前瞻
(一)发挥多元主体力量,布局国际传播新渠道
2009年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形成了“1+6+N”的大外宣格局。随着数智传播生态的形成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构建多元化、立体化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从主体和渠道拓展的视角看,企业、智库等组织的多元传播主体力量仍未充分调动,播客、“新闻信”以及以网文、网游、网剧、网购为代表的平台出海“四小金花”等诸多渠道“蓝海”的传播潜力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有鉴于此,主体和渠道的创新成为接下来一年国际传播实务创新的主要方向。
首先,要推动企业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成为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主体。十余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大量企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文化往来与世界各地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在跨文化交流中创造了不少国际合作的佳话,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通过真实生动的故事化叙事和细节化表达,借助本地员工之口和国际多元媒体渠道,企业能够讲好履行国际社会责任的故事并传递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从而在实现自身国际声誉提升的同时,推动国家形象的同步提升。
其次,智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国际舆论环境与部分西方智库“炮制”的报告和“炒作”的话题密切相关,智库正成为当下全球认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4以美国为例,美国智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中立研究机构向政党化转变的轨迹。而目前我国智库仍然以传统的研究和咨询为主要功能定位,亟需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进行战略转型,开拓国际传播的战略视野,通过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和开展跨国智库合作,提升智库的全球舆论影响力。在这方面,新华社研究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等新型智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壮大,正逐步打破美西方智库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垄断地位。CGTN智库抓住国际时事和涉华相关热点事件的契机,使用科学的方法开展民调,全面展现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民众的观念和态度,以驳论和立论相结合的方式体现真实的全球主流民意。15
最后,要加强对国际传播新渠道的布局和挖掘,深入调研海外受众信息传播渠道的迁移,关注“Z世代”等关键群体的渠道偏好。近年来,传统的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和X)逐步呈现颓势,以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和以播客(Podcast)为代表的音频平台成为信息传播的新兴渠道,各类层出不穷的垂类平台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全球目前拥有近五亿播客用户,并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播客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节目成为了两党候选人竞相抢占的新型传播平台。播客以其真实性、个人化、充满亲近感的方式触达受众,在各细分群体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具有强大的传播效果。2025年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创新应当高度关注渠道的迁移和更新,加强第三方平台的布局和自有平台的打造。16
(二)深挖传统文化“富矿”,汇聚“数智华流”的传播合力
“第二个结合”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实践创新的理论指南。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科技深度融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被全球受众理解和接受,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际传播转型升级的突破点。
纵观近年来在国际传播的诸多“爆款”案例,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科技相结合,从而赋予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下的全新样貌和巨大的传播潜能。2024年8月,国产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发布便风靡全球,截至年底销量已经突破了2300万份。该游戏扎根古典名著《西游记》,在各处细节中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众多符号,从游戏剧情中对取经路的重现和金箍棒的重点设定,到游戏音乐中古筝、琵琶、笛子等中国传统乐器的高频使用,使海外用户能够在沉浸游戏互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式文化熏陶和价值观的感召。17
另一款近年来在海外取得巨大成功的游戏《原神》同样将传统戏剧符号元素杂糅至游戏动画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融通多重文化想象,并在玩家的互动参与中形成了“游戏-媒介-文化解放性”的传播路径。18此外,2024年Reelshort开发的微短剧、以Talkie为代表的AI语音聊天工具等数智产品在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地区成为“爆款”,“数智华流”的平台矩阵和覆盖范围获得了进一步拓展。
当前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虽然“爆款”频现,但具有一定的偶发性。要想实现文化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整体增强仍需健全文化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从文化产品生产上来看,要以市场机制激励文化产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推动文化产品在立足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融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创新语境建构的新模式。19加强细分领域的机制研究和实践探索,在电影、电视剧、音乐、游戏、舞蹈、文学、戏剧和文博等领域形成符合媒介形态特征的“出海”产品。从平台搭建的角度看,要借助互联网和数智技术的优势,融入“平台世界主义”的理念,汇聚“数智华流”的传播合力,在“四小金花”的基础上打造更多有影响的产品和平台矩阵,引领世界互联网媒体平台发展潮流,推动更多中国文化“造船出海”。
(三)以效力为导向,推进叙事和话语体系构建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改革目标,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际传播的实践指南。从“国际传播能力”到“国际传播效能”,再到“国际传播效力”的表述变化,反映了对国际传播影响力的更高要求。早在2009年我们提出推进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把传播效果放到能力的前面,是因为我们通过主流媒体走向全球的硬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覆盖面已经达到了国际传播的基本要求,但是效果仍与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有距离,所以党的二十大提出效能的提升,更重视效果与能力的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有效力”比效能又提升了一步。效力意味着国际传播既要有效果、能力,还要有影响力,包括国际舆论引导力、重大议题设置能力,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从“能力”到“效力”的转变体现了在新形势下国际传播摆脱粗放的传统模式和内宣的路径依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效力作为传播链路中的最后一环,不仅决定了传播的成败,更是衡量传播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当下国际舆论场呈现信息过载和信任度降低并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传播效力的重要性尤为凸显。
首先,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前置效力思维。传播效果需要在内容策划、制作和分发的最初阶段就被纳入考量,成为传播的逻辑起点和重要评估维度。“效力思维”包含了针对目标受众的需求、兴趣和痛点的分析,对不同地区语言、文化和语境的适配以及对于不同媒介接触习惯的渠道选择等多层面的整合。
其次,要创新开展多种形态的传播效力评估。数智时代相关主管部门亟需引入计算和实验等全新评估模式以适应复杂的传播环境。国际传播实践者应当结合自身的目标,评估其平台和产品在用户态度转变、行为改变和长期认知塑造等不同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并借助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动态调整传播策略。
最后,国际传播的效力不仅体现在信息的成功触达,更是叙事形态和话语权的争夺。加快构建有别于西方的“替代性叙事”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提升国际传播效力的关键。面临着西方文化霸权逐步松动和瓦解的重要历史机遇期,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叙事体系,不断探索基础性话语、共通性话语、引领性话语和斗争性话语建设,形成叙事库和话语库。在实践中推动国际传播从“照着讲”“顺着讲”转向“接着讲”乃至于“领着讲”的转变,从而实现从传播能力的增强到传播效力提升的质的飞跃。
三、结语
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正从以易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为特征的“乌卡”(VUCA)时代转向以脆弱性(Brittle)、焦虑性(Anxious)、非线性(Nonlinear)和不可知性(Incomprehensible)为特征的“巴尼”(BANI)时代。“巴尼”时代的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作家和未来学家贾迈斯·卡西欧(Jamais Cascio)提出,相较于“乌卡”增添了对大众心理层面的“焦虑”情绪和时代变化不可控的非线性的关注。在“乌卡”时代,个体还能通过自身的提升和系统的正常运转对抗风险社会,而到了“巴尼”时代则需要全人类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秩序和环境,共同对抗世界混沌和无序。
展望2025年,全球将迎来超级大选年后政治经济的政策转变和世界格局的逐步重构,ChatGPT等语言大模型的持续快速迭代和Sora等多模态大模型的正式开放使用带来了更多未知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将继续承袭“南方转向”的趋势,搭建全球和本土地方的桥梁,在创新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防控风险,趋利避害。对于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者和从业者而言,调动多元主体和拓展新兴渠道,重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发展更适应国际传播需要的文化体制机制,突出效力的全新导向,推进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将成为未来国际传播工作开展的重点方向。
杨晨晞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史安斌、郑恩《:全球传播的“南方转向”:理论重构与范式创新》,《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1期,第158-166页。
②朱泓宇、史安斌:《“全球南方”传播理论的历史与命题:全球“知”网的想象力》,《对外传播》2024年第10期,第8-12页。
③孙吉胜:《“全球南方”共同话语的塑造与国际传播》《,对外传播》2024年第10期,第4-7页。
④史安斌、戴润韬:《全球文化新格局与国际传播新使命“:南方转向”的视角》,《对外传播》2024年第4期,第4-8页。
⑤周亭、白耘溪:《弥合全球与本土: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理念与路径》,《对外传播》2024年第11期,第19-21页。
⑥唐瑞峰、陈浩洲:《地方主流媒体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主要模式、难点与趋势》,《传媒》2024年第21期,第66-68页。
⑦曾祥敏、黄睿思:《地方叙事、国家站位、全球视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战略定位与差异化路径》,《青年记者》2024年第7期,第18-25页。
⑧赵月枝、俞雅芸、杜学志:《国际传播“南方转向”下的乡村故事与中国道路——以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为例》,《对外传播》2024年第10期,第18-22、61页。
⑨张毓强、姬德强:《“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对外传播》2024年第1期,第66-70页。
⑩张夏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传播新格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第112-124、128页。
11唐琳:《人工智能对国际新闻传播精准性提升的审思》,《东南传播》2024年第10期,第88-90页。
12蒋生元、周宇博、全会:《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赋能文化产业和国际传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中国视听》2024年第2期,第80-82页。
13吴瑛、孙鸣伟:《AIGC时代涉华国际舆论的演变、风险与敏捷治理——以ChatGPT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5期,第105-115、171-172页。
14王文:《全球认知战中的智库作用及应对建议》,《新华智库研究》2024年第1期,第67页。
15全会:《以国际民调助力提升中国话语权——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智库的国际民调创新实践》,《智库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9期,第71-78页。
16惠锋、蒋玉鼐:《主流媒体如何吸引海外年轻受众?——基于Z世代媒介消费偏好与外媒相关策略的分析思考》,《中国记者》2024年第6期,第102-105页。
17李俊欣、周子涵:《数字游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以<黑神话:悟空>为例,《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https://doi. org/10.14071/j.1008-8105(2024)-3017,2024年11月8日。
18史安斌、张自中、朱泓宇:《数字华流视域下国际传播的增效赋能——以〈原神〉为例》,《当代传播》2024年第3期,第88-94页。
19张铮、刘钰潭、陈雪薇:《“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我国影视文化产业海外传播的实践升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61-69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