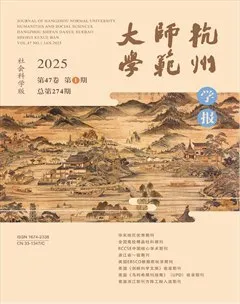朱子对告子形象之重塑
摘 要:朱子对告子进行了不同于孟子的形塑。关于告子的记载,现今可考者甚少,大抵只见于《孟子》“知言养气”章、《孟子·告子上》、《孟子》前六章“孟告之辩”处,以及《墨子》少数几篇文章中。由于流传下来的文章太少,且不易解读,因此关于其思想之判定,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有以为告子属前期古传统之儒者,亦有谓其近墨、近道,甚至近似佛学、禅学。朱子对告子进行了一番创造性诠释,而有别于孟子。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朱子与孟子所欲应付的时代不同。孟子忧心时代风气将如杨、墨之无父无君,而离禽兽不远,因此辟邪说、放淫辞,与告子辩论,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至于朱子则是面对当时禅学之兴盛而欲辟之,故将告子转为近禅或心学的形象,以便一并提出反省与革新。
关键词:朱熹(朱子);告子;孟子;义外;言;心;禅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5)01-0001-08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5.01.001
一、前言
《孟子》一书大致发挥了儒家义理,包括内圣外王、保民养民、立人极之德性等要点;其进于前人之处,在于人性本善与浩然之气的发挥。书中义理基本上不难理解,但还是有些例外,如象山所见:“《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尝美矣’以下可常读之,其浸灌、培植之益,当日新日固也。其卷首与告子论性处,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则反惑乱精神,后日不患不通也。”[1](《与邵中孚》,P.92)此指出对于《孟子·告子上》的前七章,或许不必深考,恐学子未能受益,反倒惑乱精神。而这几章便是孟、告之间的性论之辩。此外,《孟子》书中最长的一篇“不动心”章(“知言养气”章),其中亦涉及孟、告的观点,可惜同样义理晦涩,不易理解。
上述两处,大概是《孟子》一书最难解者。其中涉及告子的性论、义外之说,以及何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等主张,由于记述过简,而其他古书相关告子之记载亦不多,大致仅余《墨子》的数篇文章中尚提及相关主张。由于可研究的文章过少,致使至今关于告子思想之判定,总未能定于一尊。
本文将孟子与朱子对于告子的理解进行了比对,从而看出朱子对告子的理解有别于孟子,并对告子进行了重塑,以期在当时心学与禅学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借此力挽狂澜,而展现出朱子独特的时代关怀。在对《孟子》原文的理解上,笔者借助了《孟子》《墨子》关于告子的形容,以及唐君毅先生名著《中国哲学原论》的评析,希望能尽量做到贴近原意。
当孟、告之辩时,孟子所面对的是诸子百家,尤以杨、墨为甚;而朱子所面对的挑战,在外部为佛学、禅学,在内部则是理学与心学之争。两人所处情境迥异,是故后来的朱子对告子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从而开启了一番崭新的思辨。
二、孟子对告子的诠释
关于孟子对告子的诠释,笔者将参考《孟子》《墨子》,以及唐君毅先生的相关文章。唐先生对于告子思想做出了革命性评论,所作诠释亦能前后一贯。
依《孟子》所载,孟子视告子有以下主张,所谓“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子还抄出告子所述,包括“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性,犹湍水也……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性无善无不善”“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等。 告子主张仁内、义外,他解释道:“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以外在对象之长为悦,故为义外;以血缘亲情为生而有之,故为仁(爱)内。参见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4—300页。若只依于《孟子》一书,则历来诸说纷纭,难以论定告子之主张。不过,若能再把《墨子》所载部分加入,则较易厘清。
关于告子的思想,历来有判其归于儒家、墨家或道家等学派,意见分歧。如唐先生尝言:“赵岐注《孟子·告子》篇谓告子在儒墨之间,乃意告子问学于孟子而为言。实则告子与孟子辩,固非问学于孟子者,而当谓其思想实近墨者;而克就其即生言性,重性之可变化义言,则近道家者也。” [2](P.13)唐先生认为,告子学术可谓近于墨家与道家,而赵岐则认为告子在儒、墨之间。赵岐与唐先生虽认定不同,却有一共识,即告子近墨。以下分就儒、墨、道等三家之言,尝试分析告子主张之归属。
(一)近于儒家?
如赵岐尝言:“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3](《告子章句上》,P.293)赵岐认定告子为孟子的弟子,尝学于孟子。 《孟子》一书有7篇,除《尽心篇》外,都以人名为篇名,而这些人名并非都是孟子的学生,如梁惠王、离娄等。因此,赵岐之认定,并不恰当。然此说法在《孟子》一书难有证据。依书中所显,告子大致是孟子的论辩友人,而不是学生。
至于牟宗三先生则认为,“生之谓性”是一种古传统,至于为何家、何派所传,则未明言。另有台湾地区学者朱湘钰亦主张告子是儒家传统,其曰:“1993 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推其年代应属战国中期偏晚,内容包括《老子》《太一生水》《五行》《性自命出》等16篇道家及儒家著作,其中直接关涉儒家思想核心——心性论者,即《性自命出》一篇,专家学者针对此篇已做过不少的讨论,综合目前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有关《性自命出》论性为自然之性,迥异于孟子之说。”[4](PP.19-35)这里直接以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属于自然之性说,且为儒家思想;又说此批竹简约于战国中期,接近孟子年代。意思是,当时的性说有二:一是孟子的性善,一是儒家另一支派的自然之性,后者与告子接近。
而“性自命出”说法,也许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相近,但《中庸》亦不似自然之性说;其尽己性、尽人之性,乃是性之德,合内外之道,是三达德者也,是道德之性。
于此,笔者只能先做描述,而未能判断告子是否归属于儒家。至于唐先生则否定告子尝问学于孟子之说,不过唐先生去世时,《性自命出》尚未出土,也许还留有讨论空间。
(二)近于墨家?
唐君毅先生与赵岐都认为告子学有近墨之处,其中唐先生更进行了一番论证。在此笔者先引《墨子》书中,载有告子言论处而检视之。例如告子曰“不得于言”一段,其中的“言”乃是学说、主张的意思,墨子言“争一言以相杀” 《墨子·贵义》:“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杀身而予天下,不为,乃因身贵于天下,但争一言而相杀于身,则此言贵于身。亦是说,此言乃义之所在,即墨子所主张的公义、道义,即客观外在之义。又言、义相近,言者即是一种主义。此近于庄子所谓“物论”。参见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85页。,此“言”字即谓一客观之主张、学说或主义;若以此来诠释告子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段,则告子的主张标准以言最高,心为次,而气最后,又其中所谓“言”者,乃指外在客观之公义、主义。而孟子则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3](《公孙丑章句上》,P.74)前半段以心高于气,后半段则反对告子,以为心也要能高于言,方可。此如同论辩输人,但心知其误,故回求于心。孟子属于心学,以义在心内,乃集义所生之浩气之然,因此,心必然高于言与气。至于言与气孰高?则孟子未谈。
若把墨子的“言”与“义”之相近,用以诠释告子,则告子的外义可以从“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3](《告子章句上》,P.296)这段话清楚诠释:告子近似客观之素朴实在论。当所面对的是年长者,那么我的心便敬之以年长者;对象若是白,我亦称之为白;我总是遵从于客观外在之定义,主体自我不会妄下判断。故以此义在外,标准系由客观之外在所决定。
可见“孟告之辩”,特就辩“义外”与“不得于言”之“可”与“不可”处,实则近于孟、墨之争。唐君毅先生即曾将诸子百家做一年代先后与义理上的排序,以为孟子排在墨子之后,墨子又在孔子之后。理由是,孔子继于周公之礼乐秩序,而墨家则起而反儒,主张非乐、薄丧等,后又有孟子起而反墨,批评杨、墨。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3](《滕文公章句下》,P.179)
至于孟子之驳告子,亦未尝不是拒斥墨子之一端。如孟子批告子“祸仁义者” 《孟子注疏·告子章句上》第一章:“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参见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第294页。,此因告子将“义”视为人工制品,乃后天矫揉而成,非依性而有,故孟子与之争辩,强调义之为内,而不为外;质问告子: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所谓的“义”,系内在于仁心者,敬长之心才是义,而非以客观外在的长者作为义的标准。又如孟子面对墨者夷之,辨析丧礼之由来,其曰:“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3](《滕文公章句上》,P.156)丧礼之须,根本起于内心道义感之不安与不忍,而非外在为了什么人。以上二例,说明孟子之义内,全不同于墨家二本之外义。故孟子反对告子,与反对墨子相似。 《墨子·公孟》:“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有人于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犹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参见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第708页。告子认为,墨子虽主张仁义,在行为上却有偏差。墨子弟子把这件事告诉墨子,请墨子不要与告子来往。不过墨子回答,告子虽批评我的行为,却是赞成我的仁义主张,这总比什么都没有来得好。这里的“言”,即指主张;墨子主张公义,此义是为客观外在之说。
(三)近于道家?
唐先生认为,告子以无善无恶论性,近于道家的善恶两忘。孟子曾借公都子之口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这与告子其他的“生之谓性”“性如湍水”“性如杞柳”等说法,可谓一致。至于庄子的性论,《庄子》内篇之中并无“性”之概念,而外杂篇所言“性”,则常指个别之性格,而非指普遍之人性。若就普遍之人性,如“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5](《盗跖》,P.915)。此则近于告子的“生之谓性”“食色性也”。
庄子亦曰:“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5](《骈拇》,PP.275-276)人之“情”不是仁义;此“情”指的是实情、本性,如所云“性长”“性短”亦然。故可知庄子言性,近于性朴、自然之论,可往善走,亦可往不善走,近于告子的“无善无不善”,所谓的“即生言性”。而孟子所反对的杨朱,亦有近于道家之嫌。 “今如必本历史之所确证者为论,则孔子以后之道家型思想,盖首当以杨朱为代表。杨朱之书未有闻。”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国哲学中之“道”之建立及其发展(一)》,《唐君毅全集》第19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此视杨朱为道家型思想。看来杨朱、告子、道家等,都是孟子所反对的对象。
历史上以为告子近于道家者,还有戴震。其曰:
其 此指告子。问者问及告子,而戴氏答之。指归与老、庄、释氏不异也。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虽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觉也;然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与雌雄牝牡之相爱,同类之不相噬,习处之不相啮,进乎怀生畏死矣。一私于身,一及于身之所亲,皆仁之属也。私于身者,仁其身也;及于身之所亲者,仁其所亲也;心知之发乎自然有如是。人之异于禽兽亦不在是。告子以自然为性使之然,以义为非自然,转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故言“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立说之指归,保其生而已矣。陆子静云:“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此言实老、庄、告子、释氏之宗指,贵其自然以保其生。诚见穷人欲而流于恶者适足害生,即慕仁义为善,劳于问学,殚思竭虑,亦于生耗损,于此见定而心不动。其“生之谓性”之说如是也,岂得合于孔子哉
告子以仁为内,乃是“贵生”,而“贵生”的观念儒、道相同,甚至人与禽兽皆然,皆爱自身、爱惜亲属之身。戴氏把告子的“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等说法,等同于爱生之仁。即儒、道所同者,在于能仁其亲,人自然能爱亲、爱子、爱生,而禽兽亦然,皆贵重自然之保生,如《庄子》一书即强调养生、贵生。至于儒、道所不同者,在于义;义为分别,儒家则有人、禽之辨之分别。
告子所主张的“仁为内”或“食、色,性也”等说,孟子皆未反驳。可见以仁为内,以及保生、贵生等观念,乃儒、道所同。而儒、道所异者,如孟子与告子之异,孟子言性善,告子言无善无不善;孟子以义为内,而告子以义为外等。 《孟子注疏·告子章句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参见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第296页。戴氏以为告子近于道家,此说亦有合理处,但在庄子,却不以“仁义”为性,不以“仁”为内,因此算不上完整之诠释。
关于道家之以仁为内,笔者尚可举《论语》一段为证:“(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7](《微子》,P.251)此荷蓧丈人可视为道家隐士之属,虽不欲出仕救国救民,但仍保有爱子、爱亲之仁心。可见道家、告子等皆有仁内之主张。
三、朱子对告子的诠释
朱子对告子的诠释,重点在于把告子的“义外”与“性无善无不善”两处融合为一,而视告子近于佛氏与心学。然其中朱子似已削去义外之说,释曰“只是一味勃然不顾义理” “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只是一味勃然不顾义理。”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52卷《孟子二·公孙丑上之上》“问夫子加齐之卿相”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61页。,此解未必合于告子。告子所言“彼长而我长之……”,此有随从、顾望于外在准则的意思,并非全然不顾,因此朱子显然已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以下逐一分析。
(一)“义外”:悍然不顾而已尔
朱子在《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处言:
盖惟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告子之学,与此正相反。其不动心,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尔。[8](P.231)
这里的“冥然无觉”,本是指要如孟子之“以心知觉于理”。然告子之近释氏却又无理,或认错气性以为理,其理为空,故为“悍然不顾”,乃不顾理、不顾道义的意思。
不过,细究之,告子本意并非如此,其原文:“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此显然依于外在之标准,不令自心有所判断,而绝非不顾不从外在之义。又朱子释曰:“我长之,我以彼为长也;我白之,我以彼为白也。”[8](P.326)这里文字太略,不易确定朱子的意思,依字面上,大致是说:我心自以为白,自以为长,我心便依此而认定。或许这便是朱子“悍然不顾”的意思吧。
再如朱子释“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其曰:“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8](P.230)此中之“言”,如上所释,当指客观之主义、主张,而告子未曾有“舍置其言”的意思,只是强调“从之于外”,如同彼白而我白之;我心中学说、主张之确立,乃是依于客观外在而来。
又于“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一处,朱子注曰:“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内义外,而不复以义为事,则必不能集义以生浩然之气矣。上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外义之意。”[8](P.232)朱子的“外义”是指:推之于外而不顾。此如柳下惠之遇女子坐怀而不乱,这也不难,只要把心一横,你是你,我是我,我不睬你,你便乱不了我 孟子对柳下惠的形容:“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参见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万章章句下》,第269页。;亦近似宋荣子之不顾举世之毁誉等。
朱子又认定告子“不复以义为事”,然告子固以义为事,只是其义为外,视外在之公义、主义为事。朱子又曰:“如告子不能集义,而欲强制其心,则必不能免于正助之病。”[8](P.232)此亦不然。告子亦集“外义”,亦非强制其心,当是以心顺任于外,令心之主体服从于客观外在之义而行。
对于告子所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朱子注曰:“告子以人之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故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学者但当用力于仁,而不必求合于义也。”[8](P.326)然告子的“义外”是以外在之公义为准,并非“不必求合于义也”。
由上可知,朱子已重塑告子,而非告子原意,因告子明显欲“从其白、从其长于外义”。而朱子则将告子理解为“不顾、不睬于义”,如此一来,似则恰好近于佛教空性之真谛,而违反于儒家之以实义、实理的教义。
(二)告子近于佛氏
朱子遵从伊川的“性即理”说,而告子既然对于义理全然不顾,那么对于“性”亦是舍弃不顾。此性在孟子,便是仁义礼智,属于内在,然告子外之,甚且不顾,此则近于佛教之空义,以至于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岂非更近佛氏;以佛教讲求缘起性空,善与不善都不应执。不过,细究告子原意,他虽认定人性无善无恶,此性却能随后天所矫而为善或为恶,并无佛教万物皆空、离执的意思,因为外物仍有实理之客观外义以为标准,此与佛教不甚相类。
告子又言:“生之谓性。”朱子释曰:“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告子论性,前后四章,语虽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与近世佛氏所谓作用是性者略相似。”[8](P.326)这一段话有以下两个重点。
一是,朱子称告子“四变其说”,这是为了套用孟子的“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而所谓的四变,指的是:性之为杞柳、犹湍水,以及“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等四说。在此四变之中,是否毫无一致的贯穿精神?有的。朱子也认为有,其根本精神便在“生之谓性”一句,性者,生也,而“生”是中性字,无关乎善与不善。而朱子又言告子“认性为气”,不知性之为理。
二是,朱子以为,告子的“生之谓性”近于佛氏的“作用是性”。如若以禅宗来说,所谓“作用是性”有以下意思:“其作用是性解,略曰:大觉无思,乃遍知于法界;识情有着,徒妄起于尘劳。佛与众生,本同一体,但因迷悟,见有殊途。佛性只在眼耳鼻舌之间,妙用不离见闻觉知之际。直是一尘不受,一法不舍,名为直至道场,顿见本来面目。”[9](P.716)这里的“作用是性”,指佛性未曾离于眼耳鼻舌之间,未曾离于精魂之昭昭灵灵;于用处不执于见闻之际,不即于六识,亦不离于六根六尘,若能知之,则知本来面目。又此佛性之不执,能于作用处,起妙用而为空。佛氏的作用见性,乃不离于气性者,即不离于所以知觉运动者;而在知觉作用之不执下,则知佛性之为空,而不用离其作用,所谓真空妙有也。
然如前所述,告子之以外义为准,仍与佛氏之缘起性空说不类。告子所主张的义外,大抵可近于洛克(John Locke)的西方经验主义;洛克以天生经验、天生心灵为白板,吾心系依于客观外物之经验而定,外物曰白,吾心亦随之曰白;只是告子关心的是人生哲学,而洛克关心的则是知识论、知识的起源等问题,但两者形式相似。至于佛氏则与此二者皆不同,它不认为存在着客观外在之实理,亦无所谓内外;万法只是因缘生,本性为空,因缘聚则生,因缘散则灭。
不管如何,朱子视佛教为异端邪说,如同孟子之视杨墨。朱子于《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章,亦诠释如下:
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8](P.57)
孔子之时并无杨、墨与佛氏,但朱子此时则将杨墨、佛氏视为异端。自然这指的是“观念上的灾害”,惧其无父无君而为禽兽,或是远离人伦而出家,致使人文精神守不住。
不过,指责杨、墨、佛氏为异端,却有“让古人穿新装”之嫌,恐怕不是孔子的原意。甚至连“异端”二字,不见得就能被诠释为“邪说”;比如日本学者伊藤仁斋解释“异端”为“其端相异而不一也,言不用力于根本,而徒治其端之所异,则无益而有害”[10](PP.30-31)。此指未能对治根本,而徒劳费神于相异之末端,则反而有害。
伊藤亦反对朱子的诠释,其曰:“异端之称,自古有之。后人专指佛老之教为异端者,误矣。孟子之时,或称邪说暴行,或直称杨墨之徒,可见其时犹未以异端称之。若夫佛老之教,即所谓邪说暴行,而亦在异端之上,岂待攻而后有害耶!”[10](PP.30-31)这是指朱子所谓的“异端”,不见得就是孔子当时的意思。
不过话说回来,朱子之反对佛氏,乃是其念兹在兹者。他的用意是将告子与佛氏比拟一起,而后再一并反对。
(三)心学家近于告子
朱子在《孟子·告子上》前几章的诠释中,除了将佛氏和告子进行比配之外,提到更多的是儒家的人物,包括荀子、扬雄、苏氏、胡氏等。其中,在“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一处,朱子将告子比配于苏氏与胡氏,前者指苏东坡,乃杂有儒、道、释三家之学,所谓的“阳儒阴释”一类,朱子斥其为不纯之儒。即朱子所担心的“异端”,除了佛、道人士,还包括儒家之内部学者,这些人的学问大抵混杂佛老,朱子便将他们比配为告子之徒。
另外的胡氏,则指胡五峰。牟宗三与唐君毅先生都认同五峰下开象山这一脉。牟先生认为,明道传五峰,而五峰可开象山;五峰为“心即理”(有心亦有天理),其中的理,乃存有且活动者,而象山属心学,但五峰与象山之间可以相通。至于唐先生同样承认五峰可开象山,理由则是,原本二程的学问便已包含了心学与理学,而五峰亦然,因此,象山便由五峰的心学这部分发展出来。
而朱子曾归纳五峰的《知言》一书计有“八端”,其中的前二端为“性无善恶、心无死生”。朱子以为,五峰之说近于象山的“心即理”:心能立即就理,而不须涵养工夫,如所谓的“性体心用”。然朱子强调,儒家主张性善,所依者乃实理、性理,而不是依于心,况且要让心立即显性,却不做中间的涵养工夫,这便容易导致气象迫狭的结果。总之,朱子不甚满意五峰,而将五峰归类为近于告子,包括一干的心学家等,皆是由儒家内部产生的异端。朱子即曾与张栻、吕祖谦等人书信往来,而批评五峰,作《知言疑义》以反对之。
此外,象山作为心学家的代表人物,自然免不了要被朱子批评一番,且被归为近于告子一类。《朱子语类》载:“象山死,先生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此说得之文卿。泳)”[11](卷124,P.2979)可见朱子已将心学一派等同于告子,甚至比配于佛氏;乃不归于理者,即归于气,后者认性为气,所谓的“生之谓性”。
朱、陆曾论辩“无极太极”,其中有一段双方互批对方为禅。朱子言:
太极固未尝隐于人,然人之识太极者则少矣。往往只是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便谓此是太极。而不知所谓太极,乃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颠扑不破者也。……非如他人阴实祖用其说而改头换面、阳讳其所自来也。如曰“私其说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奸”,又曰“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则恐世间自有此人,可当此语。[12](P.595)
这是批评象山近禅,只是说得含蓄,没有指名道姓。朱子认为,太极乃是性理,不是心所能当之,心是气之灵,属于形下,至于性与太极,则是形上;有些人以为昭昭灵灵之心可以为太极,或以精魂为性,这都是佛家禅学“作用是性”的另一翻版。而这样说的人,例如象山,便是那种“阳儒阴释”之徒。
四、结语与反思
孟子惧告子之言论恐沦为邪说暴行,惧其诐、淫、邪、遁四辞而生心害政,同时担忧告子可能往杨、墨方向走,以致无父无君,遂不得已而好辩之,提出批评。到了朱子,此时墨家学说已不时兴,因此他也未曾提及告子之近墨,但也许近于杨朱的自私个人主义,这时仍然蔓延着,而更猖獗的,便是佛教与心学这两种异端的流行。如朱子言:“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8](《大学章句序》,P.2)这里表现了朱子的忧心,前半段指的是汉儒的词章记诵之学,后半段则指责佛氏的虚无寂灭之说。
又于《中庸章句序》提到:“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8](P.15)儒家学说之“不越文字”,此暗批佛氏禅学之不立文字;又所幸有程氏兄弟之挺身而出,来批判佛、老。其中的老氏,指道家,即前述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近于道家之论;至于佛氏,则有告子“生之谓性”说法,近于佛氏的“作用是性”。此二氏正是令朱子忧怀不已而必欲辟之者。
然朱子所忧心的,还不止于外部之佛、老学说。他认为,儒家之心学家们,不依理学路线,主张“心即理”,径立本心大体,而不先做去蔽、涵养的工夫,这也是一种危害,也是一种异端。如朱子批评象山:“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且其为说,吃紧是不肯教人读书,只恁地摸索悟处。……某道他断然是异端!断然是曲学!断然非圣人之道!但学者稍肯低心向平实处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难见。”[11](卷27,P.684)
此批评象山不得曾子的一贯之旨,所谓一贯,指要有散钱来贯,此喻工夫的积累。而象山却只是发明本心,以为只要发明本心,便能即于理。朱子对此亦感忧虑而嗤之以鼻,更以“异端”来形容象山之说。
朱子对告子之诠释,大致已异于孟子之视其近于杨、墨,乃重塑告子近于佛、老等异端之形象。而此重塑,则应非朱子明知而故意之举,而是自诩如此的判断便是正义,能够符合孟子的本义。如在“养气”一段,朱子很郑重地说道:若非孟子本义,则天厌之。 黎季成问:“伊川于‘以直’处点句,先生却于‘刚’字下点句。”曰:“若于‘直’字断句,则‘养’字全无骨肋。只是‘自反而缩’,是‘以直养而无害’也。”又问“配义与道”。曰:“道义在人。须是将浩然之气衬贴起,则道义自然张主,所谓‘配合而助之’者,乃是贴起来也。”先生作而言曰:“此语若与孟子不合者,天厌之!天厌之!”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52卷 《孟子二·公孙丑上之上》“问夫子加齐之卿相章”,第1250页。因为无论知言或养气的工夫,都是针对告子“不动心”的主张,且孟子亦反对告子以言在心前、言尊于心的说法。朱子强调,若欲知言,要先格物穷理,而这便是针对佛氏之以理为空、不做穷理工夫。至于“养气”,亦是要依心之集义所由来,而告子则无此心气之养,只是袭取于外,而为“义外”。朱子自认对浩然之气的认定,便是孟子本义,而对于告子所作的批评与诠释,以及视告子近于佛、老的说法,应当也不会违于孟子本义。
朱子对告子之重塑,一方面因应了时代课题,防堵异端邪说之扩大,另一方面创构了自己的学说内涵,此可谓殚精竭虑,亦有所贡献。末后,再对前文中,朱子与唐君毅先生的说法,提出若干反思。
第一,朱子未能照顾到告子近于墨家的义外之说。
告子明言道:“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3](《告子章句上》,P.296)也就是其“义外”之说,是指依从于外在之标准,而不是如朱子所说的那般推之于外、完全不顾的意思。但这也许可以看成一种创造性诠释;可能在孟子眼中,告子属于异端,而在朱子眼中,佛氏等也是异端,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把告子与佛氏等结合一起。
第二,告子之学如何既近道,亦近墨?
唐君毅先生认为,赵岐以告子问学于孟子,而归属于儒家的这种说法并没有依据。经过一番研究,他以为,告子既近墨家,亦近道家。然道与墨可谓两个极端,一个为人,一个为己,故孟子言“逃墨必归于杨”,那么告子的学问如何折合于此二家之间呢?唐先生并未进一步说明。
笔者上文曾提到,告子之性无所主,性无善无不善,生之谓性也,而求合于外,称为“义外”。此近于素朴之实在论,承认客观外在的实在性,如英人经验论者洛克之主张。但洛克解决的是知识与外物观念的问题,而告子解决的是人生问题,如“彼长而我长之”云云,这里面含有道德之判断,认为要遵从于外在的价值标准。又告子所主张的“不动心”亦是一种人生哲学,属于客观主义或道德实在论。 李明辉教授借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的用语,将这种观点称为“道德实在论”。李教授对告子的判断,亦采用唐君毅的看法。参见李明辉《〈孟子〉知言养气章的义理结构》,李明辉主编《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第132页。
参考文献:
[1]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哲学中人性思想之发展》,《唐君毅全集》第18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3]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朱湘钰:《告子性论定位之省思――从〈性自命出〉与告子性论之比较谈起》,《师大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类》,2007年第52期。
[5]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
[6] 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7]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
[9] 霁仑超永:《五灯全书》第120卷,《续正藏》第8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10] 伊藤仁斋:《论语古义》,东京:合资会社六盟馆,1909年。
[1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2]" 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吴光编:《黄宗羲全集》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Zhu Xi’s Remodeling of Gao Zi’s Image
CAI Jia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40704, China)
Abstract: Zhu Xi portrayed Gao Zi in a different manner of that of Mencius. There have been few records available about Gao Zi to this day, mostly are found in the chapter of Key words: Zhu Xi(Zhu Zi); Gao Zi; Mencius; righteousness beyond words; speech; mind; Zen
(责任编辑:蒋金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