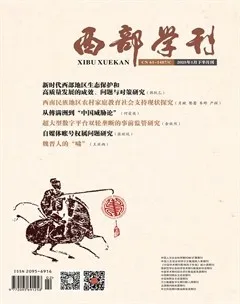“两个结合”与家族宗法性国家的特色关系研究
摘要:中国由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而形成了特定的国情,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立足于家族宗法性社会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立足于家族宗法性传承的精神追求,如家风与家学、宗法与民族、信仰与国家,并且形成了宗法性国家的管理体系,这种以宗法性家族为上层,以郡县为主要单位从上到下的运行体系,伴以大一统儒家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观念,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保持了稳固。中华复兴需要“两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文化是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石,要完善自身文化的话语体系与社会人文结构,提高思想道德建设水平,使中国走向“文化上多样,结构上恰当,道德上合理,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之路。
关键词:“两个结合”;宗法性国家;家族;民族与信仰;制度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A81;D61;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5)02-0144-04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mbinations”
and the Family Patriarchal Country
Dong Ning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China’s unique national context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millennia-old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inherently tied to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that forms the basis of Chinese society. The essenc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lso grounded in this patriarchal clan-based inheritance, encompassing aspects such as family ethos and scholarship, clan laws and ethnicity, and beliefs and nationhood. This has culmin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 management system that is inherently patriarchal, with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led by clan-based families and organized primarily around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is system, coupled with a unified Confucian ideology and collectivist value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Chinese society.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lls for the “two combinations”: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rounding in the realities of China while delving into the excellent qual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 can thu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i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ety’s long-term development. To perfect our own cultural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structur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o elevat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China must embark on a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at is culturally diverse, structurally appropriate, morally sound, and institutionally complete, following a Chinese-style path to civilization.
Keywords: two combinations; the patriarchal country; patriarchal clan; ethnicity and belief;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与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从辩证的角度而言,不同国家或者民族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需要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做出具体不同分析,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进而形成最合理的决策。中华民族由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而形成的特定国情,特别是宗法性社会的家庭基础、教育、信仰等国家特性,始终影响了制度化的建设进程。
一、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立足于家族宗法性社会的基础
中华民族,是由“各种血缘关系的众多家族”为主导组成的“宗法性社会”[2]群体,其中少数民族等群体的不断融合,也提升了华夏子孙的团结性与凝聚力。因而,中国是一个极具包容性与融合性,而民族、信仰与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国家。
对于宗法性社会的存在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例如,先秦的《仪礼》等文献中即有相关记载。古代中国以血缘关系管理氏族、宗族的制度,是维持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秩序运转的主要方式。这种制度所涉及的阶层以士卿、大夫、周天子及其分封的诸侯国国君为主,而多数的这些诸侯国,则由姬姓家族及有功的臣子家族及附属组成。这种家族性的王朝统治,由于长期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在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与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以及数千年来的各种社会变革后,最终走向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世界。但是,人类家族的血缘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宗法性社会强调家族性、集体性、民族性的固有特点,伴随着社会的需要,会长期持续留存,并形成特有的国情。
时至今日,人们的思想随着生活的改善、社会的进步,以及时代、科技等变化而变化。但是,大至国家建设,小至家族村落——这种集体性的观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得到了历朝历代的重视,并形成了当下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传承不息。中国长期以一姓一氏的门阀家族为管理中心,同时周围围绕着各个家族,他们的思想由官僚体系影响,延伸至整个社会与国家。这种情况,在魏晋时期达到了高峰,成为以门阀氏族联合管理国家的特定政权形式。无论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出于稳固社会、建设国家等因素,嬴刘李赵朱等帝王家族一直到爱新觉罗氏,期间经历了“分封制、郡县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等形式,以此引发出了关于家族教育、官僚体系、王朝周期更替的内容,特别是在“上下阶层关系如何进行辨证处理”的问题上——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对此进行了深入交谈,黄说道:“我生六十多年……一人,一家……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答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可以看出,无论是黄炎培还是毛泽东,都对此有着各自深刻的理解。
近代的中国,发挥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所形成的集体性智慧。人民群众在各种困难面前,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当家作主而英勇奋斗。在经历了不断的变革后,中国一步一步地从农业文明踏入了工业文明的世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引领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商业社会的发达,带来了全球贸易与分工,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使得社会关系与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中国与全球的联系也越发频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广大人民群众做出艰辛的努力和付出,终于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就已经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立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所形成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是中国发展到当下的几千年文明史的经验所组成的。因此,“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4]只有把握好“两个结合”,才能让社会得以稳定、获得长足的发展,才能把握好新时代的特征,从而更快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家族宗法性传承的精神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与文脉,是丰富理论思想的源头,也是立足于家族传承的精神追求。这些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思维与方向,无论在治国理政、经济发展、家族传承、道德修养乃至思想水平的建设方面。
(一)传统文化的传承:家风与家学、宗法与民族、信仰与国家
《大学》之中“修身、齐家以能够治国、平天下”的身国共治观念,时刻影响着国人的内心价值与共同目标。
特别是在汉魏家族的教育中,“这些大族普遍重视宗族内的儒学教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定的‘家风’和‘家学’,以维持他们的地位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坠”[5]。这些家族的子弟们普遍具备高于普通人的文化学识与道德修养,并且他们之间还相互关联与照应。他们的影响代代相传,以至于这种情况延续至今,并使得现代的族谱修缮行为日益繁盛。同时,这也反映出了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体现出了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使得炎黄子孙形成了“寻根问祖”的良好风气。
与“西方家国关系在王权与宗教体系上所建立的社会、群体与私人范畴”不同,中国文化中的“家国同构”持久而深入影响了家庭传统教育的特征[6]。这种与人伦、宗法关系密切相连的性质,尤其是《孝经》的影响,更是强化了集体和国家,而形成了国家主义。如著名的王氏、谢氏家族,他们家族的家风、家学即体现于家族子弟“为学为仕、修身齐家”的思想行为之中,并且身国共治与世代传承。某种意义上而言,“经学研习与传承的家族化,使得以官学方式存在的经学传授得以延续”[7]。门阀士族希望家族子弟,包括父兄表亲在家教、仕途等,都能做到敬老爱幼、顾及同胞,并文史皆通、声名远播。“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最终成为了‘家风’与‘家学’。”[8]这种由经学沿袭产生的家风、家学,由魏晋延续到宋明时期,最终由下至上带来了真正的“国风、国学”,形成以家庭传递为基础的国家思想持续影响到了近现代。
在信仰与习俗之中,宗法性的传统宗教,则以祖先与天神的崇拜为主流,以自然崇拜为辅助、其他崇拜为补充而出现的“郊社、宗庙与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主要内容——这也是维护整个社会秩序、家族体系、国家精神的力量与保证。中华民族的宗法性文化、信仰与传承特征,也使得外来宗教融合于本土之中。例如,琅琊王氏家族所呈现出的思想变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戎等人受玄学影响而成为玄学人物;佛道流行时,王导尊崇佛教,而王羲之信仰道教;三教融合时,王褒则尊孔并均学习之。
中国是一个民族、信仰、宗教都充满多样性的大国,它们在差异、交流、互动中走向了融合与发展。无论是儒释道或基督教等方面的跨文化、跨地域传播,都存在受众共同的兴趣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并能产生情感共鸣,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而,建构了符合受众群体的话语方式与文化故事,达到不同群体性认同的效果。这些都丰富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内涵,在家风、国风、文化、信仰的共同影响下,促进了中华人民的大团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道德与信仰的重要传承,是文化、思想、精神融合的巨大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离不开整个社会的积极参与。
(二)宗法性国家的管理体系:个体与民族、制度与文化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形成了民族的大融合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最终在秦汉得以成型,并随着朝代的更替而长期并存。这种以宗法性家族作为上层建筑,以郡县为主要单位而从上到下的运行体系,使得农业社会的发展得以较长时期的稳固。尤其是以帝王、宰相搭配的形式所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度,成为古代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成就了两千年来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
作为民族性国家,由汉代先哲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天人三策”: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理论,使得“大一统”思维令中国的国家凝聚力越发提升,也让国家越发稳定与团结。同时,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历朝历代的各个阶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持续性叙事的记载情况,伴随着各个家族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包容万象、百花齐放的人文精神,更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各个阶段的特色历史经验。
唐宋以来,科举制度的千年盛行形成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君臣父子”[9]各居其位的思想,形成了秩序性的现象。这种情况如《旧唐书》中,“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10]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使得各个阶层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整体。因而,科举所创造出的制度性地位,使得官僚阶层将共同的价值观进一步带给了地方社会群体,从而完成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联结[11]。自魏晋时期繁盛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使得汉代以来那些世家大族最终发展成了门阀士族,而皇室只是门阀士族中的第一家族。这种情况经历魏晋南北朝,而延续至隋唐时期。在唐末及宋元至明清的阶段,地方的乡绅贵族、宗族家长等基层的力量更加强大,并且他们通过以联姻、结拜、依附等方式在几乎所有的行政范围内,直接拥有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权力。
在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科举在唐、宋、元、明之时,形成了千年来固有的制度性特征。这种情况可见于《明史》的选举志部分,无论是包括经义、诗赋、策论还是其他的科考内容,都“沿唐宋之旧”[12]。这些传统特色的官方行为,使得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思想走向了一致性。因此,制度性的选拔导致了“任何观念上的偏见,都会倾向于将世界构建成某种特定形态”[13]。
中华文明从夏商周,从秦汉至明清,积累了数千年的集体性文明传承经验,并使得绝大多数人具有集体观。“中国古代文明十分强调集体性,尤以王朝国家的强化为目标。”[14]这些特征,也是王朝周期率的诞生原因。随着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的时代,由于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形式的纷争,在中华大地上曾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局面。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的频繁接触伴随着思想与经济矛盾、各种战争等,使得王朝模式遭受了冲击,并带来了国人的激烈情绪与奋勇争斗。在多重复杂的心态下,这些运动最终促使中国驶离了旧有形式的轨道,而转向了现代化的道路[15]。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生成的,也是与中国具体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结果。
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更是中国走向成熟世界的根本需要。
三、结论:中华复兴需要与“两个结合”形成特色关系
“两个结合”的出现,对中国国情下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深入影响,中华民族在不断地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随之“两个结合”的应用,显得更为极其迫切与需要。
(一)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更需要注重“家国情怀”的教育。社会在实践层面中需要避免形式化,以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真正要义——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征,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两千多年来,以血缘亲疏与上下秩序关系产生的家族宗法性社会的国情,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在“家风与国风、制度与文化、民族与信仰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下,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维护了社会的团结与稳定,产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在“两个结合”的引领下,完善自身文化的话语体系与社会人文结构,提高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能够使中国走向“文化上多样,结构上恰当,道德上合理,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式文明之路。
(三)文化是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在家族宗法性传承的国家之中,体现出了相当的重要性。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加应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中华的复兴,需要以“两个结合”为指南,开阔视野与胸怀,增强自信。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动力,科学把握好国家与社会的努力方向,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与政策,进一步实现民族的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王伟光.实现“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J].理论导报,2023(9):4-8.
[2]彭新武,周瑞春.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20-27.
[3]池轶.说说“窑洞对”[N].人民政协报,2021-05-31(9).
[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7.
[5]王永平.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59-66.
[6]戴红宇,成若彤.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私人性与公共性[J].集美大学学报,2022(3):52-59.
[7]孙杰.经学传承与家风养成: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6):14-21.
[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3册[M].上海:三联书店,2019:178-179.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8.
[10]旧唐书:卷43[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25.
[11]李磊.官僚类型变迁:科举制与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J].文化纵横,2021(6):118-127.
[12]明史:卷70[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3.
[13]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M].蔡金栋,梁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1.
[14]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M].张鹤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1-62.
[15]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6-10.
作者简介:董宁(1989—),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为中西哲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