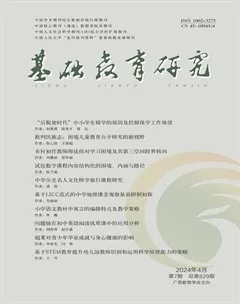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困境及其第三空间跨界转向
【摘 要】师徒结对学习是教师成长的重要举措。然而,目前乡村初任教师呈现出师徒结对学习中的角色认知错位、师徒结对学习关系的二元对立以及师徒结对学习的被动与失配。基于第三空间理论,运用第三空间跨界特点与学习机制,重塑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新形式。
【关键词】师徒结对学习 第三空间 乡村初任教师 跨界
【中图分类号】G451"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75(2024)07-17-04
2020年3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印发《教师培训者团队研修指南》等文件,强调教师在岗实践中要发挥好师徒结对的重要作用。作为教育领域的新人,初任教师在师徒结对学习过程,指导教师以“传、带、帮”[1]的方式帮助初任教师提高专业能力。然而,现实中这种“传、带、帮”的效果并不理想,在乡村师徒结对学习中异化出一种“授与受”现象,即指导教师是结对学习中的知识与技能“传授者”,青年教师则是结对学习过程中的“接受者”。这种“授与受”制约着师徒结对学习质量效果。因此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应当“健全传帮带机制”,“按照乡村教师的实际需求”,“帮助青年教师提高专业发展能力”。第三空间强调互动式的合作,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分割,协助多元主体共筑专业发展知识。将第三空间引入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打破师徒结对学习背后的线性关系,重构师徒结对学习机制,为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构建出更加开放、融合、共生、跨界的第三空间。
一、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中的困境
(一)“我是谁”:师徒结对学习中的角色认知错位
乡村初任教师作为教育领域的新人,他们不仅面临着由教育专业的学生向正式教师角色的转换,而且存在所学理论知识和具体教学实践的磨合期。为了帮助乡村初任教师尽快进入教育事业,师徒结对学习应需而生。
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过程中,指导教师的专业素养以及乡村初任教师的综合素质影响着师徒结对学习的成效。由于缺乏指导培训,(师傅)指导教师在与(徒弟)初任教师结对学习便以自己所有的经验来进行指导,而指导时往往会将乡村初任教师当作自己所教的学生,并且将自己在教学的各种方法直接套用在指导初任教师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指导过程中,指导教师没有认清自我的角色定位。指导教师不仅仅是教师,同时也是教师教育者。作为教师教育者,在结对学习的过程中就应该从初任教师的特点和自身具备的资源出发,为乡村初任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脚手架以及合作学习资源。同时指导教师在结对学习中过于关注“指导”二字,而忽视自身作为教师的角色成长。乡村初任教师在结对学习过程中,不仅是教学经验的接受者,而且是反思者与实践者。乡村初任教师不仅要习得教学经验,而且应当实现自我角色的反思与建构,实现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融入,弄清“我是谁”,进行“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教师”的角色认知。
(二)“我与他的关系”:师徒结对学习关系的二元对立
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在乡村教师培训上应当“引导师范院校教师与乡村教师形成学习共同体、研究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乡村师徒结对学习中也应体现出共同体理念。然而,如今的师徒结对学习过程不是建立在连续共同体之上,而是建立在师为师、徒为徒的割裂空间的两个独立个体。结对学习中富有经验的指导教师实际上拥有的多为实践性知识,缺乏从实践到理论的凝练与深化,作为乡村初任教师储备的多为理论的知识,缺乏相应理论到实践的检验。在这种缺乏理论与实践分割的师徒学习过程中,指导教师与初任教师所展开的结对学习,仅仅是对教学实践的表层进行解读与探讨,而非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师徒学习关系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上,是将权威性在师傅和徒弟关系上的再确定,即教育话语权的把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师道尊严”传统下的师徒学习关系存在着二者在专业发展上的矛盾。这种矛盾要么转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屈服,要么破坏结对学习形式,无法满足指导教师和乡村初任教师学习需求。
(三)“我该怎么做”:师徒结对学习的被动与失配
结对学习大部分都是通过学校来安排的,并且多以一对一的方式来进行结对。在学校安排之下的结对学习往往存在着被动与失配现象。师徒结对学习是学习者之间互惠并获得共同发展的过程,其本质是社会交换的过程[2],强调的是主体双方在实践活动中互惠共同发展的过程。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过程中,乡村初任教师依赖指导教师,缺乏自我思考与反思,缺乏自主发展意识。结对学习过程中的单一形式上的结对学习所带来的是师徒双方在专业成长实践的形式主义。在这种关系下,师傅对徒弟的教育和培训不够认真、用心和全面,而且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徒弟仅仅是按照师傅的要求完成任务和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师傅和徒弟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等、态度不友好等问题,使得师徒结对学习难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一对一的结对学习也会对师徒双方的学习造成失配效应,乡村初任教师依靠彼此间的交流沟通,会造成他们在教师信仰、教学理念和教学风格等方面的失配。这种失配效应会削弱乡村初任教师的专业自信和教学满意度,进而影响他们的教学质量和职业成长。
二、第三空间:冲破“授与受”的师徒结对学习
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过程中所出现角色认知错位,结对学习关系的二元对立,以及在结对学习过程中的被动与失配,促使师徒结对学习“传、帮、带”异化成一种“授与受”的关系。结对学习就会转变成师傅机械的传授个人教学经验和教学管理知识、徒弟的被动学习,陷入机械主义,很难实现结对学习的真正意义。第三空间的跨界特点与学习机制,有助于打破师徒结对身份认知界限,重组学习形式,实现真正的结对学习。
(一)第三空间理论及其跨界特点
爱德华·W.索亚首次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在他的著作中,他对第三空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第三空间其实是对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的解构与重构。[3]用简单的话来说,索亚继承列斐弗尔的空间理论,将第一空间归为物质空间,第二空间归为精神空间,第三空间就是超越物质与精神的空间,并借以“他者化”的角度来思考。索亚对于第三空间功能的认识就是,他认为所有以二元角度来思考分析的,譬如主体性与客体性、理论与实践、具体与抽象都可以在第三空间中以他者化的角度来进行反思重构。[4]第三空间的概念也应用到文化研究中去。霍米·巴巴也着重阐发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他将自己放置在具有差异性的界限位置来审视文化。从文化差异书写之中,巴巴引出了“杂交性”,并将它放置在“作为他者的第三化范型”之中。他认为个体可以通过多元话语来理解世界。知识的所有形式都是处于不断杂合的过程中,不同主体可以通过跨界来获得新的知识形式。恩格斯托姆的跨界理论也极大地丰富了第三空间理论,恩格斯托姆认为不同活动系统的主体进入彼此的领域,就各自面临的矛盾借助“边界客体”进行互动,通过拓展学习获得新的知识。[5]第三空间也强调以开放性和流动性来促使不同主体进行交流。Akkerman和Bakker的研究也被应用到这些不同但相关的专业背景之间的边界空间或第三空间中学习的本质。Akkerman和Bakker认为,当不同的专业实践地点连接或重叠时所创造的空间(第三空间),为那些从事这些地点的不同实践的人提供了丰富的专业学习的潜力。[6]
从上述研究者的论述可知,第三空间理论应用于不同领域,但其本质上强调的是第三空间具有开放性,能够突破原有事物的界限,并且用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理解事物。
(二)第三空间跨界学习机制
Akkerman和Bakker认为在边界空间或第三空间中有四种学习机制。这四种学习机制分别是识别(identification)、协调(coordination)、反思(reflection)和转化(transformation)。[7]
在第三空间的学习过程中,多个主体之间会考虑其自我身份与他人的相似与不同,而这个过程就叫作识别。识别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一种实践方式来定义另一种实践方式,进而描述两者实践的不同。二是在第三空间之中,不同身份并不总是和谐共存,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通过承认和接受差异而不是试图克服差异来达到“合法化共存”[8]。并且这种识别的过程促使个人在实践领域、问题领域获得新见解,并有助于学习和个人身份发展,以及探索自己的工作与他人的关系。
协调描述的是在第三空间为了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而采取的特定的方法和措施。在协调过程中,多主体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联系,形成主体间在实践与观点的交流。协调机制的潜力不在于重建,而在于克服第三空间的边界,即要在第三空间中建立协调的连续性,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由于主体之间在实践方面的认识和解释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能为主体在实践方面提供新的认知,形成不同主体对于同一实践的不同理解方式。
Akkerman和Bakker认为第三空间内的反思学习机制能够实现视角获取以及视角形成。前者使主体能够以新的视角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实践,后者能明确他们对特定实践和信念的理解以及认知。反思是借助他人的眼睛来看世界,形成新的想法和知识,其本质上是一个对话和创造性的过程。
转化可以说是第三空间中最强大的学习机制,它以识别、协调、反思为基础,形成一个新的学习机制。这种转化是理论走向实践的桥梁。
Akkerman和Bakker在探讨其功能时,指出转化会导致实践的深刻变化,甚至可能创造一种新的、介乎两者之间的实践……有时也被称为边界实践。然而转化的过程并不一定是一个平稳或无问题的变化。实践的真正转化的来源需要某种程度的对抗,或者是一个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当前的实践和关系的问题。需要对(新的)意义进行协商,尽管这有时会令人担忧,但是它可能导致承认一个共享的问题空间,参与者可以共同工作,创造新的和共享的理解和实践。
三、第三空间跨界特点与学习机制跟结对学习融合
结对学习是将知识交换的过程。知识交换包括知识共享(向他人提供知识)和知识寻求(他人寻求知识)这两个过程。[9]然而,知识具有边界性,结对学习的主体在其知识交换过程中需要跨越知识的边界性。[10]第三空间的跨界特点与学习机制正是为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提供理论支持,在结对学习中所有产生的知识在第三空间不断杂合,结对学习主体间不断通过对方的话语、经验、实践,打破结对学习所产生的问题界限,突破双方身份认识、原有经验、双方关系,以及学习实践界限,达到知识交换目的,促使结对学习双方各自成长。将第三空间跨界学习机制识别、协调、反思和转化引入到乡村初任教师结对学习,为结对学习构建新形式。
(一)识别:第三空间中结对主体自我身份的认识的跨界
第三空间学习机制中的识别能够帮助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的身份的认识。第三空间中,师傅与徒弟的身份认识进行新的重构,在对自我认知上经历了转变。师徒结对学习过程中,师傅通常被视为知识的传授者和指导者,而徒弟则是接受和遵从的对象。然而,在第三空间领域中,师傅与徒弟的角色不再局限于这种传统的定义。首先,师傅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者和激励者。他们与徒弟共同探索知识的边界,促进跨领域的学习和思考,激发徒弟的创造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其次,徒弟在第三空间中也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和遵从者,而是积极参与和共同构建知识的合作者。结对学习过程中,通过重构彼此身份,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多样化途径,并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和发展。在第三空间中,师徒更注重双方的平等尊重和合作,进而达到合法的共存状态。这种合法性的共存状态要求彼此双方承认差异,在此基础上建立沟通交流。师傅与徒弟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的关系,共同面对挑战和探求。在分享经验、交流观念上,承认彼此在专业成长过程中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发展。师傅与徒弟的身份向着更开放、平等和互动的方向重构,赋予了师傅与徒弟更大的自由度和创造力,实现师徒双方的成长。
(二)协调、反思:第三空间发挥结对学习边界潜力
在第三空间中,乡村初任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师徒结对学习不再是单向的传授与被动的接受,而是转变为协商与反思。通过协商,乡村初任教师结对学习不仅仅要建立学习关系,更需要建立持续有效的协调沟通联系机制。乡村初任教师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积极的合作者。在结对学习过程中,乡村初任教师需要积极与师傅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建立对某一教育问题、难题形成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但由于教育事业的复杂性,师徒结对学习也有边界,为了解决师徒结对学习中的边界问题,这种协调沟通必须将多元教育主体纳入教师结对学习之中,形成多主体间沟通协调,跨越教师结对学习边界。
同时,结对学习也应当有反思环节。反思的作用具有两种作用,新的视角的获取和新的视角的确定。乡村初任教师在师徒结对学习过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关于自我在教育实践中的反思,同时也是思考其师傅的教育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初任教师在师徒结对中不断形成对教育教学实践新的看法与观点,并将其结合到具体教育问题之中。
第三空间中乡村初任教师师徒结对学习中所构建的协调反思机制所带来的互补性和交流共赢的关系推动了结对学习的进一步推进。乡村初任教师与老教师之间的话语权得到了保证,并且专业成长的问题成为他们共同探讨的焦点。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并通过协商和反思寻求解决方案。这样的协调反思学习机制能够促进开放对话的进行和批判性思维的提升,为乡村初任教师结对学习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三)转化:第三空间实现跨界的结对学习
第三空间中的转化机制是形成新的实践的过程,通过第三空间中识别、协调、反思形成新的问题实践,形成新的共享问题空间,为结对学习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第三空间的转化是为各个主体创造积极性以及多选择的可能性。师徒结对学习的构建从被动失配到主动匹配,师徒结对学习的构建强调相互了解、尊重和平等对待。乡村初任教师结对学习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安排之下,而是教师主动结对学习的过程。第三空间之下,师徒结对学习的过程是建立在双方沟通、互相选择的基础之上。乡村初任教师通过与不同老教师交流来了解彼此,老教师与乡村初任教师之间形成匹配机制,形成多对一、多对多的师徒形式,建立结对学习共同体。同时,乡村初任教师结对学习的构建也可通过多向的合作和互助来实现主动匹配。师傅可以分享自己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体验和知识,为乡村初任教师提供指导和支持。同时,乡村初任教师也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结对学习,例如教学活动、教研活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创新教学方法,为师傅提供新颖的想法和视角。平等和开放的合作关系可以激发师徒双方的主动性,促进共同成长和学习。同时通过第三空间的外延网络空间来实现主动匹配。乡村初任教师可以与其他教师、专家和研究者进行交流和合作,分享经验和资源。这样的多元化结对学习关系不仅可以拓宽乡村初任教师的视野和知识范围,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和发展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初任教师可以主动寻找适合自己需求和发展的合作伙伴,进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家传.优化“师徒结对”的实施策略[J].中小学教师培训,2006(11):14-16.
[2]张思.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网络学习空间知识共享行为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7(7):26-33,47,80.
[3]陆扬.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05(2):32-37.
[4]同[3].
[5]WILLIAMS J.Teacher educator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the third space:implications for identity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14,65(4):316.
[6]AKKERMAN S F,BAKKER A.Boundary crossing and boundary objects[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1,81(2):133.
[7]同[6]132.
[8]同[6]142-143.
[9]WANG S,NOE R A.Knowledge sharing: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2010,20(2):117.
[10]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