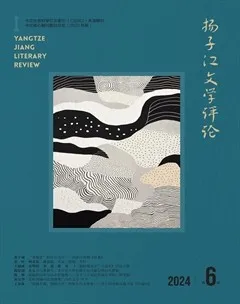“话语实践性”与作为方法的“口述史”
虽然说常常被混同于访谈录和个人回忆录,口述史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却是有其“总问题领域”(阿尔都塞)的相关性特征在。口述史之为口述史,其既区别于访谈录和个人回忆录,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书写史(或传统史学),甚至也区别于“口头证据”。某种程度上,口述史的意义正在于其对口头证据的“单独使用”,并把它上升到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口述史的方法也被许多学者所使用”,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口述史学家”:“非常有可能,他们的焦点是针对所选择的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针对用来解决它的方法;并且他们通常将选择与其他信息来源一起使用口头证据,而不是单独使用它。”a这段话容易让人想起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引言部分对传统史学的描述。即是说,当“口头证据”被传统历史学家作为“其他信息来源一起使用”的时候,它们是为“历史问题”服务的,“口头证据”的使用似乎只是为了达到以下效果:“揭示出一些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不可逆过程、不间断调节、一些持续了数百年后仍呈现起伏不定趋势的现象、积累的演变和缓慢的饱和以及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b概言之,“口头证据”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新闻记者那里,是为了长时段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的连续性服务的,也即为福柯所说的“传统史学”服务的。当“口头证据”从传统史学中挣脱出来,开始与“口述史”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所具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就被凸显出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口述史虽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但作为事件的口述史却是与新历史主义等“后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后理论”作为背景存在,是无法想象并确认口述史的价值的。口述史与新历史主义一起充当着传统史学的扬弃者的角色。
但口述史终究不同于新历史主义,自然也不同于新历史小说写作。中国的口述史写作者们却多忽略了这点,他们从“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出发,刻意重写历史,殊不知这种重写其实也是某种二元论的表现c,口述史写作的限度意识始终是口述史写作者们忽略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个人口述史”d写作的盛行是这种倾向的集中表征。从这个角度看,王尧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提供了“非个人化口述史”写作的典范,它有效避开了“现在生活中的兴趣”的困扰,而试图还原文学现场的丰富、立体和驳杂;虽然说这样的还原也仍旧不免显示“现在生活中的兴趣”e的影响,但它是把这种兴趣视为多种兴趣中的一种呈现的,历史所显现给我们的,与其说是复调,而毋宁说是杂语共生。
一
口述史和访谈录之间的异同很容易被指认,虽然口述史中“访谈者”更多是采用隐匿的和议题设定的形式呈现,而访谈录中却是以在场的方式凸显,两者中都有对话的痕迹,都有“讲述者”之外的“记录者”或“访谈者”的介入。这就给人以初步印象,似乎两种文类之间并无根本的不同。但恰如王尧所指出的:“当访谈和访谈文本进一步追问和记录文学史的发生过程时,文学口述史作为文学史的一种形态就初步呈现出来,并将口述史和访谈录区分开来。”f即是说,访谈录不是历史,口述史却可以成为历史的一种形态。这应该是两者最为显著而且根本的区别。一篇访谈录,往往是一次访谈的结果(当然也可以分成系列篇什),但在口述史中,却可以因为议题设定的多样化而把同一次访谈分散到口述史的各个部分。王尧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采用的就是这种做法,这是以事件为核心组织口述史的写作,文学事件构成这一口述史的脉络。访谈录通常是以被访谈人为中心“抢救和保留记忆”,口述史则可以是以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记忆史。这也决定了访谈录常常只能作为传统史学的补充和史料而存在,以访谈人为中心的访谈录(单篇的或多篇的集合)只是再一次强化和确认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g口述史的写作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呈现,它不应被理解为再解读式的重写历史。有些称为口述史的文献,并不能真正成为口述史,其关键就在这里。
而也正是这点,决定了口述史不同于回忆录。回忆录有其自洽性和逻辑上的连贯性,口述史却可以充满内在的张力关系。比如冯骥才的《无路可逃:自我口述史(1966—1976)》,虽然也称之为口述史,但更像是个人回忆录。说它是回忆录是因为,这里并没有“讲述者”和“记录者”的差异,有的只是“讲述者”和“记录者”的同一(同一个叫作冯骥才的人)。回忆录会执着于个人的情绪、情感和与历史无关的细节,口述史则应以历史事件作为线索或以之为中心展开口述实践。口述史虽然也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主观性和主体性,但这却体现了“讲述者”和“记录者”的双重性,甚或多个讲述者的个体性的集合,它展现的是历史制约下的历史现场的多重复杂性内涵。比如说在《“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中,关于卢新华《伤痕》的发表一事,不同的当事人呈现出来的就是不同的情况,卢新华说是他“1978年的4月中旬投给《文汇报》的”h,但据陈思和回忆是高他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孙小琪把《伤痕》推荐到《文汇报》去了”i。在这里,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作者卢新华说的是事实,还是陈思和说的是事实,而事实上,口述史也无意去告诉我们,哪个才是事实。口述史所提供的是针对历史事件的回忆与解释。记忆(不同讲述者之间的,或者说同一个讲述者不同时期的记忆)的偏差,往往会造成历史事件的确定性和细节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这恰恰是口述史的特有魅力及其张力关系之所在。个人回忆录则无法做到这点。它所呈现的常常只是个人记忆中的细节,细节和细节之间是不会或很少会彼此冲突的。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口述史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事件与细节之间的新型关系上:事件是(或被假设为)确定不移的存在,细节之间却可以彼此颉颃乃至出现矛盾。可以说,正是以事件为起点,口述史与传统史学开始分道扬镳。传统史学追求的是事件之间的起承转合、细节之间的协调共生,以及情节与细节间的彼此契合。口述史则在上述三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面目来。如果说口述史中历史事件是确定不移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则呈开放性状态,它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细节去填充,一方面也需要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但因为口述史中细节之间的彼此冲突,不仅使得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无法确立,情节与细节之间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稳固的逻辑关联。对口述史而言,围绕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讲述者或同一个讲述者在不同时期,其讲述往往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史学聚焦的是必然性,口述史则倾向于历史必然性下偶然性的发掘与呈现,这看似是它的不足之处,其实正是它的内在规定性的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的叙事学意义及其价值凸显出来。口述史最被人称道同时也最被质疑的,是其真实性问题,诚如冯骥才所说“口述史最难被确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实性”j,这里的真实性应被理解为文学或叙事的真实性,而不是历史的真实性。它是在真切、逼真和细节之间的可感的层面上显示其真实性的内涵的。口述史不应仅仅理解为历史的重述,而应理解为历史的文学呈现:口述史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它与口述(或采访)时的具体时空息息相关,具有现场性和情境性的特点,即是说,离开了具体语境及其话语实践层面,便无法谈论和确定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
二
对于口述史而言,记忆的文化政治学内涵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如果避开个体和整体的复杂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口述史是‘个体经历’最充分的表述,它将影响我们对‘整体’的看法。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对受访者的影响不仅在‘现场’,更主要的是对整个口述史框架的设计。访问谁,谈什么?在由声音转为文字时,删除了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k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口述史学家王尧意识到,好的口述史写作应该是阐释学而非实证论(因为针对单个人的记忆,往往是无法准确判断其真伪对错的),既要有多重声音的喧嚣和对一元论的警惕,又要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中去。保持中间姿态应该是口述史写作时比较好的立场。
这一中间姿态,落实到口述史的写作中,王尧采取的做法是以事件为核心组织口述史的写作,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书中都是以文学史事件的当事人或重要代表为讲述者的。比如说“伤痕文学”部分,讲述者有崔道怡(发表《班主任》的编辑)、卢新华(《伤痕》的作者)、陈思和(卢新华的同学和读者)和冯骥才(“伤痕文学”《铺花的歧路》的作者)。“杭州会议”部分,讲述者有李子云(《上海文学》编辑、批评家)、李庆西(批评家、小说家、供职于浙江文艺出版社)、李杭育(小说家、“寻根文学”代表作家)、蔡翔(《上海文学》编辑、批评家)、李陀(《北京文学》编辑、批评家)、韩少功(小说家、“寻根文学”代表作家)、陈思和(批评家)。作者是就“伤痕文学”和“杭州会议”这两个议题(或事件)而选择这些讲述者的,虽然作者对这些人进行访谈时,谈论的话题不止一个(书中常常是把对一个人的访谈内容分散到口述的不同部分),但却是有明显的话题导向的,与一般的访谈不太一样(一般的访谈会出现偏离话题的闲话和逸出),作者是就话题的设定来选择口述讲述者的。
这也是“‘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不同于“新时期文学史”的地方:文学史总是倾向于以作家或作家群为中心设计论述框架并确定等级秩序。以事件为中心,决定了对讲述者的范围选择。虽然“沉默的另一面”中被忽略的大多数(比如文学编辑),常常被作为口述史的讲述者,但这里的讲述者首先必须是历史事件(文学史、政治史、经济史等)的现场参与者或介入者。旁观者或远离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是很难充当口述史的讲述者的。因为旁观者既不参与历史的进程,对历史事件的感受也受时空的限制而有偏差,如若以旁观者的角度参与口述史的讲述,其显然是预设了一种传统史学之外的重写策略:预设的先在性限制了口述史的写作。好的口述史写作却应尽量避免这种显而易见的预设。口述史首先是“史”,然后才能是如何讲述,和谁讲述的问题。口述史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历史,但却不是也不必然是重述历史。
其次,讲述的现场性和记录的事后性的结合。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讲述的现场性与记录的事后性。比如说“杭州会议”部分李子云的讲述。李子云曾写过相关文章,专门记述了“杭州会议”。他在这里的讲述与回忆文章不尽一致,两者各有侧重。王尧在编辑这部分时,采取了补白的方式,以注释的形式呈现李庆西的回忆文章《开会记》中的相关段落。这里,对照阅读讲述和回忆文章是很有意思的。另一方面是讲述者的误差和记录者的编辑方式。因为是事后的回忆,难免会有细节上的出入,这时的口述就往往会出现与事实不符的细节,口述史的写作一般不会刻意抹去这种讹误或误差。《“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做法是,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这样就形成了正文和注释相互补充、相互映照的叙述风格。
应该看到,这两种处理讲述的方式,看似在还原口述时的现场感,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口述史的限度问题。口述史的持久的价值就表现在这种限度意识上——既不是重写,也不是反写,而是立意于客观的呈现。对于口述讲述者而言,他是在回忆,因此就难免带有对话的倾向。这里的对话性,既是口述讲述者的两个时代的自我之间的对话,也是讲述者与采访记录者的对话,同时也是其对历史的态度的表现。口述史的限度是与口述史的对话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认为,口述史的意义在于弥补传统史学之细节的贫乏和传统史学的单一逻辑关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口述史既然是以细节的丰富,甚至是彼此冲突构筑历史,这其实也是参与了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因此,口述史某种程度上属于解释学的范畴。口述史其实是把历史的必然性还原成解释学命题。
在这当中,口述史的历史框架问题就与解释学模式之间有了内在关联。王尧指出:“当我们以口述史的方式努力返回文学话语的实践场所时,口述者相同的和不同的讲述都表明,文学思潮和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作者把这种方式视为“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l之体现。这里的“文学话语的实践场所”是指,文学的现场具有同时性特征,并不是各个思潮流派此起彼伏、依次展开的,文学是并行并列和多元决定的,因此也就可以多元呈现。而这,某种程度上使得《“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呈现出福柯意义上的“去主体化”倾向,即重制度(或事件)而轻人的倾向,重作品而轻作家的倾向。口述史聚焦“怎么样”(即事件如何发生),而不是“是什么”(即历史事件的真伪)的问题。在上编中,虽然也有一节“周扬与‘新时期文学’”涉及周扬,但只是围绕“关于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展开,即是说,这是从事件的层面突出周扬的意义。事件仍旧具有主宰性,是主要的。没有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这一事件,就不会有周扬的报告。同样,下编中,也是主要谈论作品,而无意谈论作家。主要是围绕具体作品,谈论作品的发表、出版、影响或接受情况。综合看来,“人”并不是这一口述史聚焦的对象。这说明作者十分清楚,所谓个体的主体性和独创性,必须放在特定的语境中,置于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实践”的层面才能加以理解,不能过于夸大其个人的突出性和主观性。从这个角度看,《“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是把事件(会议、争论、思潮)、个人(作者、编辑、读者、参与者等)、作品等等放在一个“话语实践”的层面上加以呈现,试图还原话语实践的非连续性(或同时性)而不是延续性;口述所要塑造的是这样一个“共有空间”和“话语的统一体”:“某话语的统一体并非是由对象的永恒性和独特性所造就的,而是由众多对象显露于其中的并持续地在其中得到改造的共有空间所造就的。”m从这个角度看,《“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在做“话语实践”的还原工作。
这一方面凸显了个人的主观性,同时也扬弃了个人的主体性。因为在历史确定的背景下,个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其实是十分有限的,有的只是一些偶然和意外。比如在《伤痕》的发表中,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的女儿所起到的作用,就包含一个极具偶然性的细节。“她看了之后,哭着对她爸爸说:爸爸一定要发,不发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后来洪泽就签字了,马达也跟着发了。”n再比如1980年4月的“南宁会议”中孙绍振的“大放厥词”源自张炯的鼓动。o再比如孙绍振和徐敬亚的两个“崛起”(文章),本来初衷是为了当作批判“朦胧诗”潮的“靶子”而发表,结果却适得其反,促成了“朦胧诗”在更大范围的同情和支持,成为“朦胧诗”潮中的两个重要文献。p与“崛起论”的发表情况相似的,是汪曾祺的《受戒》的发表。《受戒》的发表源于《北京文学》的主编李清泉在一个汇报会上听到北京京剧团团长的汇报中提到汪曾祺的小说,但这个团长以“不能发表”“送不出去”和“不往外传”等理由表明了其立场态度,其结果是更加激起了李清泉的兴趣,小说最后得以顺利发表。q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和逸出,但这些偶然又是内在于必然之中的:没有1980年代相对开放的背景环境和思想解放共识,这些偶然既很难出现,也不可能演变成文学史事件。口述史的意义正在于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必然当中的偶然和意外,其所显示出来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诡计。这种偶然,显然不同于新历史写作中的反写历史的冲动,历史不是吃“小鸡子”和“玩寡妇”(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历史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一个个蕴含着历史必然性的丰富的偶然的细节所构成。但《“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所呈现的,终究不同于传统史学,因为这时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个人在历史的进程中常常不能自主,个人的主体性在历史的强大面前因而也就常常显得微不足道了。
三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r在恩格斯看来,逻辑的对象身上因为汇聚了历史对象的发展的必然进程,因而更具典型性和阐释力,比起历史的对象来,也就更有研究价值和意义。这段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就某一个话题选择研究对象时,经典或典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王尧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提供了“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的范本,以其为核心展开考察,关于口述史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和澄清。
大体上说,与众多回忆录和个人口述史相比,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体现在方法论和本体论上。如果说个人口述史和回忆录,构成了历史的丰富性内涵和“沉默的另一面”,《“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则是在话语实践的层面上展开的口述史实践。它让我们明白一点,历史乃多元决定下的话语实践。即是说,口述史写作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个层面的内涵表现为历史事件的单一性特征。作为话语实践的结果,历史事件以单一的形式呈现,这是确定不移的和具有单一性的。但这背后,是多重的声音s、多重的“声明”(福柯语)所构成的杂多。单一历史事件背后的多元性构成历史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既需要注意第一个层面的历史,也需要关注第二个层面的历史,口述史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了两个层面的历史内涵的有效结合:杂多与单一的对立统一,正是历史“话语实践”性的显现。从这个角度看,《“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具有方法论的创新意义。它提出了口述史写作的范式的意义:这既是历史的文学化,也是对文学史事件的重新讲述和解释学实践。整体事件的确定性与细节之间的不确定性构成这部口述史的张力及魅力之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有《“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当代文学口述史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一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当代文学口述史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a[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b[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c参见张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d“个人口述史”即从单个讲述者的角度展开口述史的讲述、记录和整理。个人视角是其重要特征。中国的称之为“口述史”的著作多属于“个人口述史”,比如蔡德贵整理:《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羡林口述史》,红旗出版社2019年版;冯骥才:《炼狱·天堂:韩美林口述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e[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参见何兆武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2页。
fkl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7页、6-7页、8页。
g甚至围绕某一主题展开的系列访谈,也很难说是口述史的一种形态,比如说王东亮、罗湉、史阳主编:《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6卷)·口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hin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21页、29页、26页。
j冯骥才:《无路可逃:我的口述史(1966-1976)·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m[法]米歇尔·福柯:《论科学的考古学》,《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
opq参见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95页、104页、179页。
r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s王尧在《“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前言中说到两种声音——讲述者的声音和记录者的声音——的存在,但因为讲述者往往并不是一个人,因此,这里的声音其实就是多重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