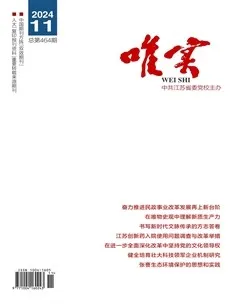用法治思维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1]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建设是立规矩、立法度的过程,是建立党内规章制度体系与党员干部行为准则的过程,更是搭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组织架构、为权力行使划定边界的过程。从本质上看,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建设就是通过党内法规制定和制度建设,为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建章立制,划定行为边界,建立惩戒机制,从而有效地进行监督,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建设离不开科学的规则设计和公正的规则执行,更离不开以规则意识、程序思维为内核的法治思维的规范、引领和支撑。
一、法治思维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关联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2]。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上就是运用治理理念和法治思维,通过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建设党的过程。
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党和政府共同履行国家公共职能,党和政府都是国家治理的权力主体。在我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依法治国不仅局限于政府依法治理,更离不开党的依法治理。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依法治国的实现离不开依规治党的全面落实,只有抓住依规治党这个关键核心,依法治国才能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提出的,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逻辑延展,是‘依法治国的党内实践’,同时,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深刻影响依法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正所谓‘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3]。
法治思维是依规治党的应有之义。法治思维本质上就是规则思维,是以规则为行为指南,尊重规则,按照规则办事的思维。依规治党是党的领导机构依据党内法规约束、管理和惩戒党组织和党员,进而实现党的规则治理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树立规则意识,划定行为边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依规治党既是党依规治理党组织和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过程,也是党员干部树立规则意识的过程。法治思维贯穿于依规治党的整个过程,即要依据党内法规,遵循党内法规规定的法定程序,对党组织和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管理、监督和惩治。例如,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和事后惩戒,必须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开展监督和惩治工作。而在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规则意识的过程中,离不开法治思维。“依规治党,就是依照体现现代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的党内法规,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和形式,规范、管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活动与行为,有效协调、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政党与市场、社会,执政党与参政党以及执政党内部的关系,明确执政党的权力运行内容、边界、程序、机制、责任等,逐步推进与实现党的领导与执政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并通过依法治理与建设,最终推动整个政治治理的有效性与规范性”[4]。
法治思维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实践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实践,是一场宽布局、多体系的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健全党管干部选任制度、完善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在管党治党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方面自我革新、直面问题。“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和非线性特征日渐显著的内部环境,政党治理不能采取传统的运动式治理,而必须采取制度化方略、通过制度化方式”[5]。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明确标准,以严格的规则意识执行标准,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才能真正落地落实,从而避免贯彻不足和过度执行的风险。而这种建立规则标准、执行规则标准的思维正是法治思维,只有坚持法治思维,才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才能真正建立党的自我革命长效机制。
二、法治思维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设计的指引功能
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保障,“全面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做好顶层设计、查漏补缺、提质增效文章,面向实践需要,及时将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法规制度轨道上向纵深发展。”[7]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长期性、稳定性和规范化的前提与保障,而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离不开以法治思维为指引的系统化制度设计。
以法治思维指引党内法规制度设计。党内法规的设计与确立,本质上是党内立法的过程。党内法规制定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乎党内法规质量好坏,党内法规体系完善与否关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立法的科学性要求党内法规的设计和确立必须以法治思维为指引,在遵循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原则下进行。一是党内法规必须具有实体正义性。从形式上看,党内法规作为党内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是党员的行动指南和行为依据,发挥着行为规训和行为指引功能,应当具有明确性或相对明确性。党内法规的条文设计,应当避免模糊性或有歧义的语词适用,避免前后矛盾或冲突的条文表述。从实质上看,党内法规具有配置党员权利、分配党员义务的效果。因此,党内法规的条文设计还必须符合尊重基本人权、权利和义务相协调统一、违纪与惩戒相匹配等原则。既应避免片面强化义务、忽视权利的“义务立法”,也应避免过度强调权利、忽略义务的“权利立法”。二是党内法规必须具有程序正义性。党内法规的确立与修改,与党员的权利义务息息相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定程序进行。法定程序是保证党内法规确立与修改合法的关键要素,也是保证党内法规体现全党集体意志的必然要求。只有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才能保障全党集体意志在转化为党内法规的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
以法治思维指引党内法规设计和国家法律一体化衔接。《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特别指出,要“坚持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党内法规是我国法治体系的有机内容与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8]30。在党和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现实背景下,只有建立起衔接有效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治理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公共权力行使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需要法治思维的“穿针引线”。一方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根本意志的体现,二者具有价值内核上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党内法规的设计必须尊重国家法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基本原则和法治基本精神,警惕以党内法规为名偏离法治的现象出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关键是要实现党内法规的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9]。另一方面,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应形成体系与内容上的衔接关系。党内法规所确立的纪律规范是党内前置法,国家法律所确立的法律规则则是党员的基本道德底线,从而形成“严要求、守底线”的双重规范格局。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体系安排与条文表述上,就与国家法律体系和条文表述形成了基本的适应性衔接。
以法治思维指引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具体内容对接。党内法规是对于党员有着更为严格要求的党的内部法规,是在尊重法律制度精神基础上的从严立法。“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10]25。因此,二者是高标准、严要求,与底线标准、底线要求的关系,而非冲突对立或并驾齐驱的关系。这就要求党内法规的设计必须以法治思维为指引,在全面领悟并尊重国家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和规则立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衔接时更多是行为轻重或标准差异,而非行为类型差异。这种以行为同一性为基础构造的阶梯性行为规制体系,必然要求行为的规则描述应具有体系的一致性,即以法治思维为指引,在借鉴国家法律条文相关表述的基础上,遵循概念同一性、行为一致性的要求,进行党内法规的制度设定和条文设计。例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5条,通过增加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和特定关系人谋利的党内纪律处分条款,实现了党内法规与《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内容上的有机衔接。
三、法治思维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的指引功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赖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贯彻执行。只有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真正地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才能真正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因此,制度执行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关键,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是执行党内法规的过程,是将党内法规内化为每一个党员行动准则的过程。这一转化过程的稳定性、预期性和规范性,离不开法治思维的方向指引。
以法治思维强化主体责任制的权责一致。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全面从严治党的建设成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指出,地方党委应将党的建设同经济社会发展、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和同考核,强化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的责任担当,并指出党委(党组)书记是本地区、本单位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责任的层层分解与层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在各条线、各条块内得以梯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制,既事关党的治理权力的分配,也事关党的治理义务划分和治理责任追究。在权力分配、义务划分和责任分解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法治思维、强化治理主体“权力—义务—责任”的有机统一,坚持有权力就有义务、有义务才有责任的法治化责任归咎逻辑,避免以后果反推责任现象的出现。将领导责任、“第一责任”泛化为无所不包、无法规避的绝对责任,极易不当加重主体责任人员和组织的负担。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准确把握‘三个区分开来’,严格划分‘失误、错误’与‘违纪、违法’的界线,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11],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同时,在权力判断的过程中也应当以法治思维为底层逻辑,以党内法规为规范依据,以法无授权则权力不可为为基本理念,准确厘清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内涵与权力边界,避免“权力飞地”和“九龙治水”等现象的出现。
以法治思维保障制度运作的实体正义。实体正义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核心要义,实现实体正义离不开法治思维的贯彻和保障。党委(党组)、党组(党组)领导班子和党委(党组)书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制的落实,离不开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的权力行使。但权力行使应有其边界,有其法度,“各级领导干部要把依法办事理念根植于头脑中,自觉用法律厘清权力边界,用法律约束权力行使,确保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用法治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10]145。既应警惕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名大包大揽、代位行权、越位行权等现象的出现,更应警惕“鸵鸟心态”,当“甩手掌柜”,纸面落实、纸面行权现象的出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落实,应充分体现权力行使实效,既应避免无效的僭权行为,更应防范权力“空转”。
以法治思维保障制度运作的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序正义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应有之义,更是永葆其制度“初心”的原则底线。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实施,绝不是单纯地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制度,而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党内法治制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坚持正确人权观,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等工作机制,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依法查处利用职权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8]31。这就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责任落实中,必须坚持程序正义,尤其是在相关主体因没有落实或落实不力的责任追究过程中,更应强调程序正义的保障功能。在责任的调查环节,应严格遵循党内法规的程序性要求,在尊重和保障党员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开展调查,形成调查文书和调查结论。在责任的认定和追究环节,应在尊重客观调查事实的基础上,以党内法规的处罚规定为依据准确认定行为性质,确保惩罚有据、过罚相当;严格遵循党内管理权限,经具有管理权的组织和个人批准后以法定形式公布和执行,并自觉接受全体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50.
[2]习近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J].求是,2023(12):4—7.
[3]邓联荣.运用法治思维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J].法学论坛,2023(4):27—36.
[4]雷厚礼,雷蕾.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6.
[5]陈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演进脉络与效能释放[J].江苏社会科学,2023(5):35—44.
[6]燕继荣等.新时代国家治理变革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42.
[7]习近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N].人民日报,2024-06-29(1).
[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9]汪习根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53.
[10]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