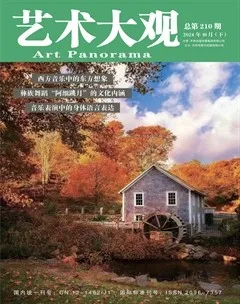论戏曲舞台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时空观念
摘要:戏曲是一门综合性时空表演艺术,中国传统绘画是一门空间造型艺术,它们在时间和空间的处理上有极大的相同相似之处,都是以超脱的时空来观察事物、表现事物。同时,戏曲舞台、中国传统绘画的时空观念均源自民族的哲学观、美学观,体现着独特的宇宙观和审美精神。在时空的表达上,戏曲舞台所展现出的是主观心灵化的世界观,体现在“戏点”或“卖点”的调配和穿插上,并通过“寓时于空”和“以时帅空”的方式,创造出充满生命力和诗意的戏曲舞台时空。
关键词:戏曲舞台;中国传统绘画;时空观念
戏曲艺术和传统绘画,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中孕育出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具有深厚的民族性。这两种艺术门类看似隶属于不同的艺术范畴,一个是多元的综合性艺术,另一个是注重形态塑造的造型艺术,然而,它们在文化底蕴、艺术理念及审美风范上,却因共同的民族特性而紧密相融。它们在哲学基础和美学属性上存在着本质的共鸣。韩羽先生曾说:“中国戏,中国画,虽不同名,却是同姓,似是姐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空观念,是由其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同时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时空观。戏曲舞台上的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是十分自由灵活的,与中国画一样是超越了客观时间、空间而生成的,是一种心灵化的艺术时空。关于戏曲舞台形式的研究,可以从中国传统绘画的深厚底蕴中探寻灵感,并将二者巧妙融合,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那么,戏曲舞台形式从中国传统绘画中汲取哪些元素?是流畅的线条描绘、独特的皴擦技法、奔放的泼墨手法、细腻的点染技巧?抑或是均匀的平涂、清新的淡彩、富丽堂皇的装饰色?还是散点透视和留白?虽然这些具体的技法可以被吸收和借鉴,它们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技法、特点,但笔者认为,从传统绘画中吸取的精髓不应仅仅局限于这些具体的技艺,而是传统绘画中的审美意识和美学特征。出于上述思考,笔者重新拈起这一旧题试加探讨。
一、直观感悟式的思维方式
直观感悟式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古代先民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先民主要以原始农业为主,原始农业主要依靠的是“天作”而非“人为”。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是无言的,“天”在“四时”运行流变中孕生着宇宙万物,那么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均是天生的。故在中国古代先民的意识里,一切皆然,只要对“天地之道”作切身的体悟和遵循即可,在这种文化心理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必然是纯经验的直观感悟式的思维,自上古三代,特别是在自孔子始至汉初董仲舒的近八百年的子学时代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得到加强和固定化。
直观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其思维的特点即在“悟”。“悟”是种纯经验的静态直观的思维方式,其省略了逻辑思维过程中的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在对个体生活、人生经验静默直观和反复体验中,实现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和理解。“悟”的本质则是一种纯粹的直接心灵体验。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文、歌、赋、画的审美倾向中,亦体现在戏曲艺术中,尤其是对戏曲艺术时空观念的影响最为深入。中国人的空间意识如同《易经》中写的“无往不返,天地际也”,是一种以内心视像俯仰自得的流动的、体验性的空间意识。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中“十八里相送到长亭”,一路上,经凤凰山则思牡丹与芍药同圃,绕池塘则羡游鱼相戏,睹白鹅比翼合鸣则思永不分离,临井台照影则情深意长,过独木桥而喜得相扶相搀,登庙堂则效拜天地永结同心。舞台上并无一物,观众在演员表演的引导下,随着人物行动的不断变化而游走,舞台空间在行云流水中变幻,使观众获得极大的审美感受。
二、中国传统绘画的时空观念
中国传统绘画的时空观念与戏曲舞台的时空观念均是在这种直观感悟式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形成的。在中国山水空间建构中,空间意识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从属于物理世界的构造,而是带有鲜明的心灵意识特征。在这种主观性的心灵里,外物对主体来说已逐渐失去意义,只有时间之流流注心灵而昭示着宇宙存在的意义。时间的刹那流动,恰与人的心灵活动特点相契合,意识活动亦是一个个刹那生灭的心念所组成,如流水迁变不息,时间之流亦是心灵之流。
故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时间寓于空间的转换之轨迹,甚至统帅空间,在这种绘画精神的影响下,其体现出的外在特征便是浓郁的抒情性和强烈的写意性。如明代画家石涛的《狂壑晴岚图》,当观者面对整幅画面时能够在三个层面上感到时间的流动,其一,在展开画卷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木枯树遮掩下的茅亭,画家强烈的主观意识使观者仿佛置身其中,顺着茅亭向后走,能见到潺潺流动的小溪。再向前走去,是山岚笼罩下的数不清的杂树和野草,驻足在一棵树下举目眺望,叠嶂的山川迎面而起。而在峰峦叠嶂中,一脉小溪飘然而过,它使观者自然联想到这是茅草亭旁一弯小溪的活水源头。此时,当观者的主观意识在从茅草亭至远山的“游览”中,那么自然会感觉到那脉脉不断的时间之流在整幅画中流动。其二,在山树掩映的茅亭里,两人对弈,一人旁观。在这静静的对弈中,万籁俱寂,只有飘零的枯叶在悄悄地落地。在这幽静的环境中,观者体会到的恐怕只有时间静静地流逝,以及造化万物的再生和衰老。其三,笔者以为,那远山流过来的一脉溪流,也昭示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对时光易逝的感叹。所以,中国传统绘画不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而是对心灵的、生命本真的抒写,在流动的时光中体现出的是对生命的理解。
三、戏曲舞台的时空观念
民族的时空观念,对艺术创作者的创作行为会产生一定限制,并影响其艺术面貌。对于这一点,学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戏曲舞台的时间、空间均是无限自由的。1956年,著名导演阿甲在国家戏剧工作者研讨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戏曲舞台)一个趟马百十里,驰骋沙场数十回合,在舞台上同场表演,都是常见的事。至于时间的处理,它是和处理舞台空间的特殊手法一致的。如果说,几十里的路程只要跑一个圆场,那么几十里路的跑路时间只要几秒就行了。[1]”剧作家范钧宏先生在论及戏曲舞台的时间与空间时,曾提出戏曲的特征是“集中、精练、夸张”,而在戏曲舞台的时空处理上主要体现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把不必要的情节精练到最小限度,以便腾出手来,用夸张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描写那些最动人的场景。譬如越剧《梁祝》,梁山伯、祝英台同学三载的过程,可以一带而过,但对《十八相送》一场却尽情描绘,大做文章,通过一路不断变换的环境,刻画两个人依依惜别的情感和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再如《穆桂英挂帅》中的一场,有段唱词竟达一百余句之多,非常细致地剖析了穆桂英的精神面貌,写了历尽沧桑的今昔之感……从生活上讲,这只能是穆桂英登上帅台之前刹那间的内心活动,但在舞台上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加以夸张。[2]”为何戏曲舞台会采取“无限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在“无限自由”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有待探寻的规律。在探讨戏曲舞台形式时,学者指出,由于叙事性的需要或为了表达角色的缘故,舞台时间可以缩短或者延长。
(一)主观心灵化的时间观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时间观念是指观者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审美欣赏的过程中,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其时间的流动和存在,是观者与画家在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共同的人文环境中心理感应的结果。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精神一致,戏曲舞台上的时间也是主观心灵化的时间,它存在于观众和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中,是与观众和创作主体内心体验紧密相连的心理过程,时而快时而慢,角色依据自身的情感波动与内心需求从而驾驭着时间,时而缓慢时而迅疾,呈现不一的节奏感。戏曲舞台是一方观念化的时空,当戏曲文本或创作主体意识中被观念化的现实存在或历史存在中的人物和事件,尚未以演员扮演的人物和道具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之前,戏曲舞台上的时空是不确定的。客观存在的物理时间从其周围漫流过去,一旦观念化的现实存在或历史存在,以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和充满符号意味的道具形式呈现在舞台上时,整个舞台时空又随着人物的活动被确定下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节的演进而流动不息、变幻无穷。所以,戏曲舞台上的时空是创作主体心灵时空的外现,同时又因观者的“在场”而流动、变幻于观者的主体意识中。如戏曲舞台上夜间时间的流逝是用几声更鼓来交代的,这几声更鼓仅为审美主体提供了联想指向,而整个夜间时间的流逝情境却主要形成于观者的意识中。戏曲舞台,在空灵超脱的时空中充分实现了人之心灵的对象化。
(二)戏曲舞台的时空关系——“寓时于空”与“以时帅空”
戏曲的舞台上,时间并非自然的时间,而是充满生命精神的艺术时间;空间亦非客观的空间,而是蕴含着主观情感的时空合一的生命化的空间,如此就形成了中国戏曲空灵多变的舞台形式。戏曲表演空间,是一种主观心灵化的表现形态,它依托于联想与想象构建的心理图景,涵盖演员与观众内心的映射,是纯观念性的范畴,不具有物象形态,仅以时间的流转为存在方式。现实的舞台是演员内在映射物化的领域,因此它的时空界定均是模糊的。故演员上场前是一片空白,只有演员上场后,内心的图景逐渐在舞台上显现,空间才开始流动变化起来。而戏曲中所表现的空间也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是由内心创造的空间形象。它与人的创造性活动紧密相连,蕴含着时间的节律和诗的意境,处于不断地流转与变化中。戏曲中时间与空间的交融无所不在,其表现为空间向时间的转化。恰如黑格尔的观点:“空间的真理是时间,因此空间就变为时间;并不是我们很主观地过渡到时间,而是空间本身过渡到时间。”
(三)戏曲舞台时空观念的体现
解玉峰教授在《“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中描述,中国戏曲的“戏点”或“卖点”大致有四类:第一类是“情志”,即通过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内向感受和思考,选取情节“线”上的某一“点”来重点突出,如《宝剑记·夜奔》《白蛇传·断桥》《牡丹亭·游园惊梦》等剧目,通常以独角戏或主要由某一角色表演的形式呈现。第二类是“有戏”,观众事先已经了解所有剧情和秘密,在此基础上,重点表现的是角色伪善面纱脱落的那一刻,通过角色间的互动和碰撞,呈现出戏剧情节的趣味性,如《十五贯·猜字》《玉簪记·琴挑》《梁祝·长亭送别》等。第三类为“谐趣”,这类作品以净、丑角色为主,运用幽默诙谐的言语和动作,营造出极富幽默感的表演,如《绣襦记·教歌》《春草闯堂》《遇皇后·打龙袍》《打城隍》等折子戏。第四类是“技艺”,这类作品主要凸显演员在唱、念、做、打方面的技巧,以此吸引观众的注意,如《闹天宫》《玉堂春·苏三起解》《血手印》等名段。南戏和传奇在结构上通常会将这些“戏点”或“卖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丰富的戏剧效果[3]。那么,从时间维度审视,当舞台时间减缓甚至停滞时,这通常预示着“戏点”的来临;从空间维度审视,当舞台空间保持固定不变,或与现实空间匹配,乃至有所延展,往往也是“戏点”之所在。相反,当舞台时间快速流逝,且空间频繁切换时,通常不是“戏点”。在一般性叙事中,时间通常被压缩,空间频繁变化,而“戏点”之所在,空间不变,时间变慢或停止。尽管中国古人对于何为“戏点”或“卖点”,及其在舞台上对时间和空间的巧妙运用,并未形成明确的理论认识,然而,从现存的众多折子戏中依旧能感受到古人对舞台时空观念的把握非常极致。如今的部分观众群体,往往将戏曲视为“拖沓”,但实际上,戏曲的情节开展极为迅捷,时空的转换也极为流畅。其所谓的“拖沓”,通常是表现在一些“戏点”上,在这些部分,剧情几乎停滞。随着文化环境的变迁,这部分观众已无法像过往观众那样去品味这些“戏点”,尤其是对戏曲中较为亢长的抒情性唱段,因此产生了“拖沓”的感觉。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墨色的浓淡变化与布局的虚实关系,书法家亦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说。在探讨戏曲舞台上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时,通常引用此说法,即戏曲舞台的时、空表现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戏曲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再现时空环境,通过唱、念、做、打等表演手段,创造出特定情境,实现舞台时间和空间的灵活处理。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变化均围绕“戏点”展开,旨在更好地展现剧情之精彩之处。舞台上叙述故事时,时间会被简化,场景空间也频繁变换,但在关键剧情节点出现时,舞台形式往往趋于固定不变,时间的流逝也变得缓慢。戏曲舞台对于时间、空间的处理均是围绕“戏点”展开的。
四、结束语
戏曲舞台作为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对戏曲美学特征的深入探究。戏曲舞台形式的演变并非孤立存在,其背后的民族性、审美意识、艺术特征是维系其生命存在的基础,是戏曲艺术持续发展的关键。戏曲舞台的时空观念,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时空观念并列研究,从而创作出更符合戏曲审美法则的视觉语汇,运用于当下戏曲舞台设计的实践创作中。怎样更好地借鉴中国传统绘画的表达方式来表现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的戏曲舞台形式的设计理念中,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阿甲.戏曲表演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2]范钧宏.戏曲编剧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J].文艺研究,2006,(05):86-94.
作者简介:崔婉星(1990-),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讲师,从事舞台美术及服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