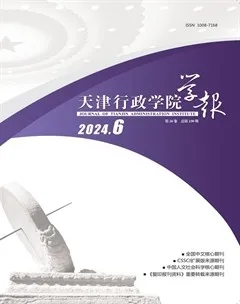整合与介入:“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逻辑
摘 要:
“矛盾不上交”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来并长期推广的基层治理模式,已然成为卓具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技术。“矛盾不上交”之所以具有治理效能,在于其具有“整合式治理”和“介入式治理”两种特征。从整合式治理的角度看,基层社会从结构维度实现了主体之间的关系整合、主体之间的能力整合、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制度整合,从机制维度体现了协商治理的运作过程。整合式治理在学理上体现了“复杂性管理”的逻辑。从介入式治理的角度看,当基层群众力量难以解决特定矛盾时,国家力量的介入能够在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协同中实现矛盾的在地化解,这也体现了国家能力的价值。总体来看,“矛盾不上交”与关系维度的国家治理相契合,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构建稳定的秩序,体现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整合式治理;介入式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4)06-0037-10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社会的稳定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探索并实践科学有效的基层治理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治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中,发端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是卓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1](p.54)。由此,“枫桥经验”从地方性经验上升为总体性经验。“枫桥经验”以“矛盾不上交”为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技术。
学术界对“枫桥经验”进行了大量的学理化阐释,总体形成了四条研究路径。一是“枫桥经验”的重要意义。学者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生动诠释了“中国之治”的领导核心、人民主体、治理方法和文化基因,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创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理念、新价值、新方法和新领域[2]。二是“枫桥经验”的构成要素。学者认为,“枫桥经验”的构成包括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结合、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谐[3]。三是“枫桥经验”的发展路径。作为新时代的治理方法,“枫桥经验”要以现代治理扬弃与超越传统管理,在党的领导下与人民群众一起治理[4]。四是“枫桥经验”的法治化问题。学者指出,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化,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形势、新要求、新目标,把“枫桥经验”的核心要素纳入国家法治范畴,转换为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5]。
整体审视,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枫桥经验”的价值、机制、法治化等问题,为理解其运行的方式、方法和效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随着“枫桥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各地也开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设计实现“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模式,在特定的工作机制和治理技术中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然而,价值阐释和机制描述只是描述在地化解矛盾的过程,并没有从治理理论的角度系统回答基层为什么能够实现“矛盾不上交”。所以,“矛盾不上交”背后所蕴含的基层治理逻辑还需要进一步提炼,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的实践中抽象出基层有效治理的总体原则。基层社会的何种治理模式能够实现“矛盾不上交”?其所体现出的理论逻辑是什么?“矛盾不上交”又体现了何种整体性价值?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规范层面提出“矛盾不上交”中所蕴含的“整合式治理”和“介入式治理”两种模式,并基于此总结“矛盾不上交”的价值旨归,以廓清“矛盾不上交”的治理全貌,为理解基层治理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二、整合式治理:社会力量统合中的有效治理
治理模式的转变需要同社会的基本特征相适应。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治理问题的涌现性、复杂性显著增强,加之人民群众的身份、利益不断走向多元,社会矛盾纠纷因此而呈现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诉求复杂化等特点[6]。对此,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必然要同其多元性、复杂性相适应。基于“矛盾不上交”的运作机制,文章提出“整合式治理”的概念,这也是基层社会有效实现“矛盾不上交”的第一种治理逻辑。
(一)整合式治理的内涵与构成
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历程表明,原有的基层社会以国家权力为主,处于高度统一的状态。然而,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这种高度统一的状态开始向高度分化转变。基层社会成为一个颇为松散和开放的场域,存在着大量相互隔离、缺乏合作的分散化要素[7]。因此,实现“整合”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目标。按照《辞海》的解释,“整”的意思是“从攴从束从正,正亦声。攴是敲打,束是约束,使之归于正。合起来表示整齐”。“合”则很好解释,即“一起,共同”[8]。从字面意思上看,“整合”的基本概念就是将不同的要素协调成有秩序的、相互配合的整体。在西方的治理文献中,整合被置于网络的社会资本中加以分析,其要素构成包括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实现整合的主要方式包括社会规范、价值、集体想象等[9]。鉴于此,我们可以将整合式治理的概念界定为,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特定的规范形成有机整体,以完成某种治理目标的治理模式。由此,整合式治理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结构”与“机制”两个维度。其中,结构维度强调了静态层面的关系;机制维度强调了完成治理目标的动态过程。
结构维度的整合式治理由三个要素构成:主体之间的关系整合、主体之间的能力整合、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制度整合。第一,主体之间的关系整合需要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不仅包括矛盾双方,也包含基层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及各类行业性、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和调解组织等。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实践表明,主体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能够形成合力,因为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衔接不畅往往会导致调解的失效。所以,关系之间的整合首先要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并明确不同主体在矛盾化解中的职责和功能,使之形成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第二,主体之间的能力整合旨在强调第三方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随着矛盾纠纷的日益多样化,以专业性的调解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方的作用愈发凸显,这也体现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的基本逻辑。不过,调解主体的能力会被矛盾的特征影响:当调解目标为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结束敌对关系时,具有权威的第三方更有利于冲突的化解;当调解目标为修补并长期维系双方关系时,无权威的第三方将发挥更好的调解作用[6]。因此,能力的整合须以矛盾议题为基本参照,只有能力与议题相适配,才能形成“1+1>2”的良好效果。第三,制度整合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有机配合,既要在矛盾化解中尊重法律的权威,也要充分发挥情感纽带、道德纽带在修复人际关系之间的作用。“矛盾不上交”是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模式,自治体现了社会力量的作用,法治体现了矛盾化解中的规范性原则,德治则体现了通过情感关怀、心理慰藉等方式与社会成员建立起非正式关系,并达到非强制性劝说的目的[10]。
机制维度的整合式治理体现于协商治理的运作过程之中,即通过协商的程序来实现各方面的整合,进而达成矛盾化解的治理目标。协商是贯穿于“矛盾不上交”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治理程序中多元主体走向协同合作的重要联系机制[9]。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在遵循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的伦理学基础上,不同主体之间能够超越极端个人利己主义,在协商中共同解决公共问题,并从中激发和培育社区公共性、增强社会包容性、推进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11]。这种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观念,即“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2](p.269)。协商不仅是人民民主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模式。以协商的方式实现治理,既能体现民主的基本原则,也能体现生活的共同经验,且与人民群众的交往习惯以及情感预期相契合,还能使协商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在共识中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例如,北京市某社区构建了一个能动员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共同参与的议事协商体系,引导群众参与协商,让协商成为凝聚共识、化解矛盾的重要机制;合肥某社区以民情气象站、同“欣”圆桌会等协商治理品牌为载体助力不同类型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矛盾不上交”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法,需要灵活性和规范性的共同支撑,以保障协商能够在制度化的运作中解决不同类型的矛盾问题。因此,基层协商治理要在议题甄选、主体选择、协商规范、结果落实方面保障协商能够在合理的范围、科学的程序中运行,进而最大程度提升协商的效率和效能。
(二)整合式治理中的复杂性管理逻辑
复杂社会对治理的挑战在于多元主体的在场和多元议题的涌现,为了回应社会的复杂性,复杂性理论与公共行政走向融合,成为理解公共治理的重要视角。在“矛盾不上交”中呈现的整合式治理模式,正契合了复杂性理论中“复杂性管理”的路径,故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从概念上看,“复杂性管理”就是一个系统通过各种手段来应对其所面对的复杂情况,进而实现系统对环绕其周遭的复杂性的有效控制,其核心目的是保证系统稳定[13]。将复杂性管理引入社会治理领域,就是治理系统如何通过优化重组来提升处理社会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从矛盾纠纷的角度看,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矛盾的类型、数量与日俱增,这些矛盾无法通过单一的标准和原则来处理;二是单一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能力,使其难以独立应对基层社会各类复杂问题。故而,复杂性理论融入公共行政所形成的一项基本治理原则就是打破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14](p.23),转而引入社会力量来应对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场景中的治理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整合式治理中的复杂性管理逻辑。
第一,社会力量的整合有效分担了基层治理的成本,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不断引入提升了基层矛盾化解的效率。“枫桥经验”初创之时就塑造了“放手发动群众”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力量走进了治理场域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其专业的服务,有的放矢地协助国家解决各类问题。基层社区的各类组织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整合关系,契合了复杂性管理中“放大”(amplification)与“衰减”(attenuation)的机制[15](pp.21-29):一方面,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放大”了治理的能力,克服了单一主体处理问题的弱点;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议题的优先性排序,能够协调不同的力量解决不同的问题、突破重点问题,使复杂多元的治理议题“衰减”至治理能力范围之内。例如,安徽省蛟塘镇着力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平台,依托镇村综治中心创新建立“化解网格”,以“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为基础,引入多个行业部门参与,邀请社会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和法律顾问作为力量补充,整合各方资源,汇聚多方力量,“一站式”受理群众诉求。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引入极大提升了矛盾化解的效率。随着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在优化条块矛盾处理能力、理顺纵向政府间关系、形塑组织治理流程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撑,是推进治理创新、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在基层矛盾化解方面,数字技术能够更为精准地实现议题预警识别和需求发现定位,同时能更加敏捷地匹配政府风险治理资源,数字技术通过更加主动发现各种矛盾风险源,来提升处置各种可能矛盾风险的效率,并打破矛盾调解的时空限制,从而努力达到消未起之疾、治未病之疾的治理效果[16]。
第二,不同运作机制和模式的灵活实践契合了基层社区的在地特征,保证了治理结构、方法同基层社会的适配性。“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核心原则,但整齐划一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不同场域的特征,各地的“枫桥经验”并非都复刻了枫桥的模式,而是在“矛盾不上交”总体原则下的灵活实践。各地的“矛盾不上交”实践基本上都和在地特征相结合,通过盘活本地的特殊资源来实现有效治理。例如,在民族地区,“双语调解”是“矛盾不上交”的运作特色,贵州省三都县就探索形成了“双语”普法调解、“异地”联动联调、“绣娘”互助调解、“水书先生”传统调解等符合少数民族生活工作习俗的多元解纷模式。总体来看,复杂性管理至少需要关注如下维度的问题:一是变化的动态性和时间维度;二是适应性过程;三是变化既是偶然的,也有其路径依赖[9]。所以,“矛盾不上交”的创新实践既遵从时间维度的变化,也基于不同地域加以灵活变通。首先,在时间维度,“矛盾不上交”充分契合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演化过程,基于社会发展不断整合新主体、新资源、新技术,以不断回应变化社会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其次,在空间维度,一些地方能够充分依托在地的文化特征以及治理资源创新“矛盾不上交”的实践形式,在特定治理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将治理的目标、方法、原则融入公众熟悉的文化形式来弥合人的认知与治理内容之间的沟壑,进而营造出一个具有心理认同和价值共识基础的治理共同体[17]。
总体来看,复杂社会的治理不能依靠单一主体抑或单一资源的力量,而是多元主体协同的结果。“矛盾不上交”正是在不同主体的力量整合与资源整合中实现了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以主体联结的复杂性有效应对了治理议题的复杂性,回应了治理过程中的专业化要求、精细化要求以及适应性要求。
三、介入式治理:国家力量回应中的有效治理
有效的国家治理既不能单凭国家的力量,也不能完全依赖社会,而是要依靠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合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表明,只有国家与社会合理分工、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有效治理。虽然基层自治能够通过群众的力量化解矛盾,但在一些棘手问题上,单纯的社会力量依然独木难支,故而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来帮助基层化解矛盾。所以,现实的“矛盾不上交”并不是将所有的矛盾都甩给基层,而是只将基层自身能够化解的矛盾交给基层,基层难以自主解决的问题,仍然需要上诉至治理体系当中,依靠国家力量解决。鉴于此,文章提出“介入式治理”的概念,将其作为分析基层社会之所以能实现“矛盾不上交”的第二种治理逻辑。
(一)介入式治理的内涵与机制
中国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模式。第一,国家尊重并引导社会的有序发育,将社会力量纳入国家治理,社会力量同国家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关系。第二,为了保障治理的正确方向,弥补社会力量的不足,国家依然在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所以,国家介入社会是一种同社会力量互补的机制以及对社会治理的矫正机制,即当社会自身难以实现治理抑或社会治理方向存在偏差的时候,国家力量需要主动干预,以保障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按照西方的治理逻辑,“强社会”往往会对国家行为造成掣肘,国家难以在社会场景中有效贯彻其意志。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国家—社会关系能够使国家保持自主性,以有效解决社会中的各类问题、保证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只有实现国家自主性与其他治理主体自主性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政治体系得到有效运转,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18]。在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介入式治理”:当社会自身难以系统解决其问题时,就需要依靠特定的机制使国家介入社会,使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协同解决相应问题。“国家介入社会”由两种机制构成:一是以国家主动回应为特征的群众路线机制;二是社会主动上诉国家的社会协商机制。
群众路线机制体现为国家主动深入社会提取信息的过程,是国家主动发现问题并协助社会解决问题的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群众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善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19](p.352)群众路线机制之所以适用于中国国家治理,主要有如下两方面原因。第一,中国国家治理存在着深刻的复杂性,社会问题往往处于潜伏的状态。国家既难以将视野拓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难以发掘社会角落中隐藏的问题。所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国家需要通过主动深入社会来挖掘社会中潜在的问题,打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壁垒,使国家能够感知到社会发展的整体情况,将目光聚焦于社会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并从源头挖掘处理社会矛盾,把社会中的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第二,社会治理虽然依靠社会,但是社会自身的治理能力往往受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故而,基层治理是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的结合[20]。在群众路线中,国家可以主动将人民群众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纳入国家视野,通过与社会力量进行协同来化解复杂的社会问题。
社会协商机制体现为人民群众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将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上诉到治理体系之中,进而在同国家的协商之中达成共识。社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要体现为官民之间的协商,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有效处治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手段[21](pp.46-47)。基层治理中存在着许多需要上级党委政府协调的矛盾冲突,而基层干群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需要依靠上级党委政府协调。在社会协商机制中,基层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矛盾“上交”到上一级的党委和政府,在上一级党委和政府的协调中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化解矛盾。在现实治理实践中,社会协商已经形成了多渠道、多载体的运作模式,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也使得社会协商从物理空间走进了网络空间。例如,河北省定州市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为抓手,建立健全集投诉、办理、查询、跟踪、监督、评价于一体的网上枫桥服务中心。据统计,仅2023年,该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便接听群众来电11万个左右,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762件,矛盾化解率达到98%,“有事找政府,就拨12345”成为该市广大群众的共识。简言之,社会协商体现了国家回应社会的“柔性治理”模式,即通过权力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对话机制,达成妥协、谅解、让步等,由此以非暴力的方式或者非刚性的方式彻底解决问题[21](p.51)。社会协商的价值就在于其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而不是在刚性的回应中激发矛盾,这种机制防止了矛盾冲突的进一步向上传导,尽可能地将风险控制在特定范围之内。
(二)介入式治理的国家能力价值
介入式治理以国家为主体,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回应。国家能够精准了解社会以及妥善处理好各类社会问题,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国家能力。以“矛盾不上交”透视国家能力,总体可以把握中国的国家自主性和信息能力建设问题。
从“矛盾不上交”的运作机制看,国家能够以群众路线的方式主动深入社会、回应社会,体现了国家不受社会裹挟的行动能力,因此体现了中国的国家自主性。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但是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国家自主性统合在中国的政党自主性之中,这使得国家的总体性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各项政策安排,都能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18]。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自主性始终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以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为行动目标,充分彰显了国家对社会的治理能力。结合“矛盾不上交”的运作机制,中国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如下两个突出特征。第一,国家对社会的回应具有选择性。“矛盾不上交”中可以上交的矛盾属于人民群众自身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对于人民群众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国家并不加以干涉。例如,河北省某市在践行“矛盾不上交”时,在基层干部、网格长等群策群力下,将日常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小事”全部化解在网格。这种选择性回应不仅有利于节省国家治理社会的成本,防止过多社会问题给国家带来的超负荷运转,同时有利于规避社会对国家的钳制,因为“过度强调社会重要性而一味满足社会要求的决策便可能是人类的灾难”[22](p.48)。第二,国家自主性受到社会自治的限制。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国家与社会形成合力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如果国家自主性压倒社会自身的能力,那么社会不仅会失去活力,国家也会在庞大的治理成本中消耗自身能力。所以,只有国家自主性和社会的自治能力相配合,形成国家自主性和社会自治的合理分工,才能达致治理的帕累托优化。
“矛盾不上交”通过链接国家与社会,有效提升了国家对社会的感知能力,使国家能够迅速了解社会中的各类问题,进而增强国家的信息能力。国家信息能力被认为是国家的“视力”,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辨识其治下公民及其活动状况的能力,关涉国家“看到”并“看懂”的社会广度与深度,关乎秩序维护、服务供给等治理议题[23]。由于技术以及能力的限制,古代国家很难获得透明的和确定的社会地图,只能满足于模糊的治理[24]。现代国家拥有现代信息技术和高超的统计手段,对社会基本态势的感知和了解已然超越了传统国家,因此,现代社会的治理精度、准度都远超传统国家。然而,中国国家治理具有庞大的规模和深刻的复杂性,国家的信息能力往往因受制于规模问题而难以实现良好的社会清晰性。故而,国家的“视力”需要以社会的“视力”作为补充。国家难以扫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社会中的人却能够将街角社会尽收眼底,这就是国家通过社会的可见性来提升自身可见性的过程。从“矛盾不上交”的运作看,改革开放初期,枫桥区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动干部群众及时发现、处理、制止各种治安问题。辽宁沈阳牡丹社区的“三零”工作法,通过构建民情问题清单来标注风险,有效消除了社会治理的盲区。可见,矛盾的发现就是依靠社会的“视力”发现社会问题,并在国家与社会的连结中将社会所发现的问题传导给国家,使国家能够感知到社会每个单元和细胞中的问题,把握社会的整体态势和明示与潜伏的风险点,进而定义政策的注意力和治理议题的优先级。换言之,国家只有充分了解社会中的信息,社会事实才能够从模糊走向清晰,国家治理才能够从模糊决策转向基于社会事实的“循证决策”。一方面,将社会问题的事后处理扩展为社会问题的源头治理,构建矛盾风险从预防到处置的全链条机制;另一方面,在完备信息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处理工具,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精细化程度和有效性。
整体审视,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分工是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提升国家能力的必由之路。基层治理不能忽视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有效介入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国家能够解决社会自身无法应对的问题,而社会本身也可以拓展国家的视野,帮助国家把握社会的基本脉搏、感知社会中的新问题。正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之中,社会矛盾能被有效地化解在基层,而不会进一步向上传导。
四、从关系中的治理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矛盾不上交”的价值旨归
“矛盾不上交”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与实践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出鲜明的治理价值。在整合式治理和介入式治理中,“矛盾不上交”形成了一种“关系中的治理”模式:一方面,矛盾纠纷的化解有效协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家和社会的分工合作中塑造了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特定关系的调整实现了良好的秩序,这样一种“关系中的治理”,也同样体现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蕴,这也构成了“矛盾不上交”所蕴含的整体性价值旨归。
(一)“矛盾不上交”所蕴含的关系中的治理
从公共生活的原初状态来看,政治无非由两种关系构成: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此,政治秩序的调整本质上是对这两种关系的调整。在现代民主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转向了平等,人与制度的关系则由民主程序形塑。在整合式治理和介入式治理的有机融合中,“矛盾不上交”首先调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源整合与国家介入中,人与人之间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协调中走向和谐,这为构造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社会基础。无论是哪一阶段的历史,都不存在建立于混乱社会秩序之上的政治秩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是社会稳定。换言之,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复杂适应性系统首先要维持稳定和秩序。稳定是指社会关系结构的相对恒定、社会运行秩序的有条不紊、社会运作规则的相对适宜、社会主体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相对满足[25]。其最为基本的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一最基本社会关系的稳定。“矛盾不上交”正是将治理的注意力集中于基本社会关系之上,通过整合式治理和介入式治理及时地发掘与处理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阻止社会矛盾的扩散与传导,并在重新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为社会生活重新注入和谐的因素。以小见大,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处理好以自身为原点的关系问题,就会为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基本的前提。
“矛盾不上交”同时以社会矛盾为枢纽,在整合式治理与介入式治理的运作中有效调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整合社会力量与调动国家力量构建国家与社会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塑造平衡的国家—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不断演进,社会不断地从国家中分化出来,传统的人与制度的基本关系演化为整体性的国家—社会关系。而社会是否具有活力是影响国家治理整体效能的重要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激活社会机体的活力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体现了“强国家—强社会”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蕴含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内在逻辑,旨在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25]。从“矛盾不上交”的起源来看,党和国家放弃了传统的大包大揽的治理模式,以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赋权于社会。随着“矛盾不上交”不断走向成熟,政府、社会组织与群众等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更加顺畅。整合式治理和介入式治理不仅链接了各类社会资源,使其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也通过国家的介入构建起了多元共治的格局。“矛盾不上交”在充分激活社会活力的同时补充国家的力量,使国家与社会能够在协商的民主机制中形成共识,打破了国家控制社会以及社会裹挟国家的畸形关系,构建了国家与社会科学分工、共同合作的良好格局。
总地来看,“矛盾不上交”的运作是通过调整基本社会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体现了活力和秩序的基本关系。其中,国家通过激发社会多元主体的活力来调整不同的关系,同时在关系的有效调整中塑造公共生活的和谐秩序,这即是“寓活力于秩序之中,建秩序于活力之上,实现社会有序运行与社会活力迸发相统一、相协调”[26]。
(二)从关系中的治理到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国家的治理格局本身是一个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抑或说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矛盾不上交”所体现的关系不仅存在于横向维度,而且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纵向维度,在这个意义上,“矛盾不上交”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共同体意蕴,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这既是一种机制性的表达,也是一种价值性的话语。在机制性表达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一方面强调了多元主体静态的关系结构与这一关系结构的动态行动过程,另一方面强调了这种关系结构的可持续性。因为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野下,弱关系可以演变为强关系,“参与”“协商”“合作”等行为也可以从动员转变为自觉[27]。“人人”既可以指代具象的、活生生的个体,也可以指代抽象的治理主体。“人人”作为一种复数的表达形式,只有在“有责”“尽责”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享有”的治理目标。换言之,“人人”强调了多元主体对治理成本的分担,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责”则是通过主体积极承担责任的方式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的执行力[28]。基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维度把握关系中的治理所蕴含的共同体意涵。第一,“人人”表达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是责任分配和实践的过程,连接了治理的起点和终点,多元主体通过履责行动来体现治理的动态性。第二,“人人”体现了多元主体作为治理过程参与者的自主性,同时体现出对不同治理主体权利和能力的尊重,包含了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权利十分重要,只有将不同主体的权利和责任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有效治理。另一方面,只有将不同主体之间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治理能力的最大化,提升整体的治理效能。
从价值性表达的角度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要聚焦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共同体”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虽然强调个体的权利和价值,但是个体毕竟生存于公共生活之中,不能脱离集体而存在,碎片化的生活只能给社会带来悲剧。故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这是社会得以可能的基础[29](pp.26-27)。从“矛盾不上交”的运作看,矛盾需要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参与协商才能得以解决,而矛盾的解决本身也是一个在调整社会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中修复共同体的过程。只有共同体的网络越织越密,社会才能愈发和谐,社会的发展才得以可能。其次,“共同体”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关系去理解人。那么,由关系塑造的共同体就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0](p.199)。由此,“矛盾不上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矛盾,使人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重新调整对他者、对社会的认知,同时还在于在民主的程序中彰显其自身的主体性,进而发展自身。
质言之,“矛盾不上交”内蕴的关系中的治理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体现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一方面,其整合了静态的治理网络结构和动态的治理行动过程,另一方面,其能够通过“共同体”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框架下,“矛盾不上交”才能塑造其整体的价值目标,稳定其运作的基本模式与基本方向,进而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不断制度化和规范化中持续发展和创新。
五、总结与讨论
文章从规范层面重新审视了“矛盾不上交”中所蕴含的基层治理逻辑,提出了“矛盾不上交”中所包含的整合式治理与介入式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其中,整合式治理在结构层面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在机制层面通过协商治理的方式凝聚共识。该治理模式在主体连结、资源连结中提升了基层社会的整体治理能力,适应了复杂社会的治理需求。介入式治理强调了国家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旨在说明基层治理本身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分工合作的过程。在国家的有效介入中,社会能够在国家力量的加持下解决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国家也可以在社会的协同中提升自身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优势互补。二者的结合提供了以“关系”来透视治理的视角。立足于“矛盾不上交”的运作和效果,关系中的治理既通过“关系”来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也在治理中重新调整了人与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整体来看,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体现了“矛盾不上交”的宏观实践过程,也突显了“矛盾不上交”的整体性价值旨归。
作为新时代实现社会稳定的抓手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动力,“矛盾不上交”在走出枫桥之后与不同地方特色相结合,衍生出了不同的模式、机制、路径,但本质上都没有脱离其价值内核,也没有脱离其内在蕴含的治理逻辑。这表明,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探索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既要立足于地方的基本情况设计不同的实践机制,也要牢固坚守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从各地实践的“枫桥经验”中不难看出,各地的“枫桥经验”实践整合了各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条件等地方性内容,但始终坚持着“矛盾不上交”的总体原则,贯穿了“矛盾不上交”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整体来看,中国的基层治理之所以产生真实的治理效能,主要是因为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能够坚守现代治理的价值,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需求,符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基层治理定然会在时代的发展中生长出新的治理模式和方法,在理论上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话语提供新的素材,在实践上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新的思路。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促进“矛盾不上交”有效运作的不同条件,进一步拓展“矛盾不上交”的应用性,夯实“矛盾不上交”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卢芳霞.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内涵与世界意义——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0).
[3]张文显.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命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6).
[4]宋世明,黄振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J].管理世界,2023,(1).
[5]李林.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J].法学杂志,2019,(1).
[6]郝雅立,宋沂霏.双网互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T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4,(2).
[7]陈秀红.整合、服务与赋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三种实践取向[J].学习与实践,2023,(8).
[8]辞海大全(网络版)[DB/OL].https://www.cihaidaquan.com/zidian,2024-07-20.
[9]Wong Villanueva J L,et al.Cross-Border Integration,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A Systems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Good” Governance in Cross-Border Regions[J].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2022,(5).
[10]吴同,胡洁人.柔性治理:基层权力的非正式关系运作及其实现机制——以S市信访社工实践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11]陈秀红.从“嵌入”到“整合”:基层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5).
[1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3]张贤明,张力伟.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J].理论探讨,2020,(2).
[14]Teisman G,Van Buuren A,Gerrits L.Managing Complex Governance Systems:Dynamics,Self-Organization and Coevolution in Public Investments[M].New York:Routledge,2009.
[15]Beer S.Diagnosing the System for Organizations[M].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1969.
[16]任勇.重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数字治理面向[J].探索与争鸣,2023,(8).
[17]李风雷,张力伟.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责任政治逻辑——基于“许家冲经验”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2,(3).
[18]刘伟,何頔.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学习与实践,2023,(9).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0]陈军亚,张振宇.“共同缔造”:基层治理创新中的群众路线[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
[21]周友苏,等.社会协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2]杨光斌.使民主归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3]吕俊延,刘燚飞.国家的“视力”:技术革命与国家信息能力建构[J].政治学研究,2023,(5).
[24]韩志明.国家治理的信息叙事:清晰性、清晰化与清晰度[J].学术月刊,2019,(9).
[25]杨开峰,仇纳青,郭一帆.“三治融合”: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4,(1).
[26]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N].人民日报,2023-02-27.
[27]李慧凤,孙莎莎.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J].治理研究,2022,(1).
[28]张贤明,张力伟.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逻辑、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J].理论月刊,2021,(1).
[29][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贾双跃]
Integra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Logic of “Resolving Problem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Zhang Liwei, Wu Na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Resolving problem at the community level” is a model of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explor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mod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overnance techniqu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Resolving problem at the community level” is pretty effective because its features of integration-type governance and intervention-typ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type governance, the society achieved relationship integration and capacities integration among diverse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integration among resolving social problems systems in the structure dimension. Integration-type governance reveals the logic of complexity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vention-type governance, the state is capable of intervening the special problem that citizens cannot resolve. The state capacity is reflected from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In a word, “resolving problem at the community level” fits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relation dimension. This shows the value of a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which everyone fulfill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shares in the benefits by adjust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Key words:
“resolving problem at the community level”, “Fengqiao” model, integration-type governance, intervention-type governance,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4-08-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研究”(21&ZD157)。
作者简介:
张力伟(1992—),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 楠(1997—),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