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文本与社会思潮:《甘蔗》封面之百年演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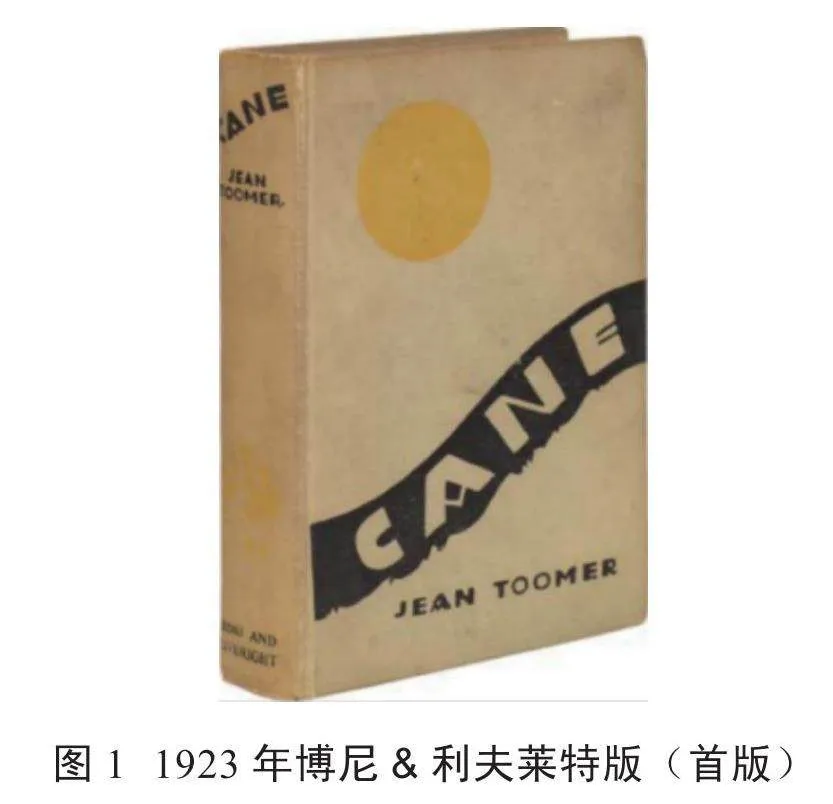
[摘 要] 对吉恩·图默(Jean Toomer)的《甘蔗》进行个案考察,聚焦封面、文本与社会思潮三者的互动,旨在为编辑学与文学研究开辟出一块跨学科的天地。研究表明,封面与文本共存共生,既是文本的视觉概要,也体现了封面设计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回应。同时,《甘蔗》的封面变化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迁,从对种族主义“曲线救国”式的暗讽到对隔离制度的迎头痛击,再到对种族关系的重审和黑人女性的关注,描绘出一部独特的《甘蔗》演变史。
[关键词] 文本 封面 社会思潮 《甘蔗》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4) 06-0118-08
Cover, Text and Social Trends: A Century of Evolution in the Cover Design of Cane
Cao Jinrong Xu De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Jean Toomer’ s Cane to explore the interplay among cover, text, and social trend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editorial studies and literary analysis. Cover and text coexist symbiotically, wherein cover functioning as both a visual synopsis of the text and a reflection of the designers’ interpretation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work. Moreover, the cover design of Cane reflects the shifts in societal focuses: from the subtle sarcasm of racism to overt challenges to segregation, and subsequently to the reevaluation of racial dynamics and an increased focus on Black women’ s status. This evolving cover design thus encapsulates the uniqu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is work.
[Key words] Text Cover Social trend Can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长久以来,以文本为中心乃是文学研究之“正道”。封面、插图、献词、前言、后记、注释等围绕在文本周边的“类文本”(paratext)[1]并不被文学批评家重视。然而,一部作品得以出版,并非作家一人之功劳,若没有类文本及其背后的编辑、封面设计等“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再优秀的作品也无法进入生产、传播环节,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文本与类文本是“一对冤家,相互依赖、共存共生”[2]。鉴于此,本文对美国作家吉恩·图默(Jean Toomer)的成名作《甘蔗》(Cane)进行个案考察,重点论证封面、文本、社会思潮三者的互动,旨在将被忽略的类文本及其背后的“无名英雄”纳入文学批评框架,尝试为编辑学与文学研究开辟出一块跨学科的天地。
《甘蔗》体裁混杂,含11篇小说、16首诗歌、1篇散文和1篇短剧。全书分三部分:第一、三部分描写美国南部的黑人农民;第二部分描写美国北部的城市黑人。《甘蔗》可谓“叫好不叫座”的典范,学术界对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在《甘蔗》首版的序言中赞誉其为“南方文学的先驱”[3],伯纳德·贝尔(Bernard Bell)认为《甘蔗》拉开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序幕[4]。可惜的是,这些学术认可并未能转化为市场销量。资料显示,该书首版销量仅为429册,盈利85.2美元[5]。时至今日,《甘蔗》在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的销量平平,这说明外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度并不高。而在我国,尽管非裔美国文学的研究正逐渐受到重视,但由于《甘蔗》尚未有中译本,因此其读者群体也十分有限。
令人费解的是,这部在市场上“乏人问津”的作品却获得了出版界的认可和推崇。自1923年首版以来,其再版次数超过40次[6]。最近一次再版是在2024年4月23日,启蒙经典出版社(Start Classics)为纪念世界读书日再次推出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持久魅力。如此高的再版频率远超同样诞生于吉姆·克劳(Jim Crow)时期的文学经典,如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土生子》(Native Son)和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等。《甘蔗》究竟为何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答案在于其复杂性与多面性。“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对《甘蔗》最恰当的描述。这种多面性在《甘蔗》的封面设计中得到了直观体现。40多个版本的封面设计各具特色,鲜有雷同,这正是因为《甘蔗》体裁杂糅、主题流动,如同一个多棱镜,从不同角度都能折射出不同的光彩,为封面设计者提供了极大的创作空间。在这个“读图时代”,封面作为作品的“视觉概要”,通过文字与图像的组合向读者传达文本主旨[7]。同时,封面设计还深受政治氛围、文化传统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不同版本的《甘蔗》封面不仅是设计者对作品本身的诠释,更是对不同时代社会思潮的反映。
1 20世纪初期:对种族主义的暗讽
1923年,《甘蔗》由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Boni & Liveright)首次出版。这家出版社以大胆前卫著称,出版过一系列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等,印证了学者对图默“前卫的实践者”[8]的评价。在《甘蔗》的首版的封面上,一轮红日位于左上角,下方则是一条蜿蜒上升的黑色小河。《甘蔗》中的甘蔗、蜂巢、收割者、棉花的象征意义均有学者讨论[9],却唯独忽略了太阳与河流,这无疑是一大缺漏。为此,本文将结合文本内容,详细解读太阳与河流在作品中的象征意义,进而揭示设计者将这两者置于封面之上的深层原因。
《甘蔗》中,太阳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共出现28次,分布在11个篇章中,可谓贯穿全书。《甘蔗》中的夕阳是阴暗恐怖事件的序幕。首先,夕阳是性侵的开始。《卡琳萨》(Karintha)描绘了年轻女孩卡琳萨在性侵面前的无力与绝望。文中“当太阳逐渐下沉”共重复6次,这不仅是日落这一自然景象,而且是黑暗势力逐渐笼罩的象征,预示着男性暴力与狂欢的即将上演,卡琳萨则在这样的阴影下被无情地拖入深渊。其次,夕阳是私刑的预告。《佐治亚州的黄昏》(Georgia Dusk)的开篇为:“慵懒的天空,不屑追逐夕阳,金色余晖未及延续,它为了夜间的烧烤,顺从地沉入夜色。”[10]这里的“烧烤”(barbecue)并不是一种烹饪方式,而是吉姆·克劳时期针对有色人种实施的火刑,透露出历史的阴霾与沉痛。此类私刑在平等司法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的私刑》(Lynching in America)中有着详细的记录。据统计,1877年至1950年间,美国南方12个州发生了超过4400起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恐怖私刑[11]。《甘蔗》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对黑人充满敌意的时代。图默在作品中生动描述了黑人汤姆因谋杀白人而被处以火刑的场景,围观者对这场“烧烤”的欢呼声更是凸显了种族主义者在黑暗掩护下的恶意与残忍。综上,《甘蔗》中的太阳象征着随黑暗而来的罪恶—性侵与私刑。前者是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压迫与侵害,后者则是白人对黑人的种族迫害与歧视。
太阳的形状也具有特殊寓意,圆形的太阳代表了整本书的设计。《甘蔗》在排版时,图默曾特意嘱咐编辑在每部分的第一页加一段圆弧,三段圆弧刚好合成一个完整的圆,突出圆形的设计。图默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
从三个角度来看,《甘蔗》的设计都是圆形。美学上,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到简单。地区上,从南方到北方,再回到南方……精神实体上,从《伯娜与保罗》(觉醒)开始,进入《卡布尼斯》,出现在《卡琳萨》等,进入《剧院》和《包厢》,在《收获之歌》中结束(停顿)[12]。
图默通过三个角度—艺术风格、故事背景和精神实体,构建了一个圆形结构。从艺术风格看,作品首尾两部分采用简洁的词汇和句法,中间部分则转向丰富词汇和复杂句式,形成了“简单→复杂→简单”的循环。从故事背景来看,第一、三部分聚焦于南方,而第二部分则移至北方,构建了“南方→北方→南方”的框架。然而,最引人深思的是精神实体层面的圆形。《伯娜与保罗》(Bona and Paul)是起点,揭示了白人姑娘与黑人小伙之间因种族差异而未能实现的爱情,映射出20世纪初美国社会对跨种族婚姻的歧视和黑人男性的自卑。随后的《卡布尼斯》(Kabnis)通过两位混血人物的命运对比,展现了黑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挣扎与选择,象征着从自卑到自我认知的过渡。最后,《收获之歌》(Harvest Song)以黑人农民在田间劳作的场景作为终结,强调了族群归属感和身份自豪。整体来看,这些作品呈现了一个从自卑到自我认同,最终融入黑人种族共同体的完整精神循环。
另一重要意象河流也有两层寓意。首先,河流象征着奴隶贩卖的“中间航道”。封面上,一条小河由左下角蜿蜒向右,形成一个上指的箭头,寓意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白色大写字母CANE犹如一艘艘将黑人运至美洲的船只。黑人如同牲口般被锁在船舱中,每日都有大量无辜的生命消逝,他们的黑色尸体被船员无情地抛入河底。这一历史悲剧在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作品《宠儿》(Beloved)的献词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六千万,甚至更多。”这一数字是保守估计,它代表了死于“中间航道”的黑人的最低数量。其次,河流是自由与奴役的分界线。在《罗伯特》(Rhobert)、《艾维》(Avey)、《卡布尼斯》(Kabnis)等篇章中均提及灵歌《深深的河流》(Deep River):“深深的河流,我的家在约旦那边,深深的河流,主啊;我想穿过河流,到达营地。”[13]“约旦”(Jordan)指俄亥俄河,是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线。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哈克和逃奴吉姆为逃到自由州,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目的地就是俄亥俄河口。图默续写了这首灵歌:“白人之地。黑人歌唱。焚烧,孕育黑色之子,直到不幸之河带来安息、甜美荣耀,到达营地。”[14]“不幸之河”象征着危机四伏的逃亡之路,无数黑奴在逃亡过程中不幸丧生,但他们的死亡被视为一种“安息”与“甜美荣耀”。相对于为奴的煎熬,死亡更像是一种解脱,这些葬身河流的黑色身躯,正是黑人反抗精神的生动体现。
《甘蔗》首版时,美国处于种族隔离时期。封面设计者巧妙地将政治隐喻和作者意图藏匿于太阳与河流的意象之中。这样的象征手法将《甘蔗》置于文学与历史的交汇点上,含蓄地揭露了种族主义的罪恶,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首版封面设计简洁,大量留白,予人无限想象空间,这种隐晦的设计与《甘蔗》的艺术风格颇为契合。正如非裔美国女作家津齐·克莱蒙斯(Zinzi Clemmons)所言:“这本书只适合先锋派和有质疑精神的人,对普通读者来说,它太困惑难解了。”[15]也许,这就是《甘蔗》的艺术性和销量不成正比的原因。
2 20世纪中后期:对隔离制度的痛击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日益高涨,一种名为“新奴隶叙事”的文学类别应运而生。该文学类别的发起者为非裔美国作家,他们以黑奴为主人公,在新世纪背景下重新书写了奴隶制的历史记忆,激发了公众对非裔美国人悲惨命运的思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甘蔗》得以再版,其影响力与意义也得到了强化和拓展。
1969年与1975年,《甘蔗》分别由哈珀&罗(Harper & Row)与利夫莱特(Liveright)[16]两家出版社再版(见图2)。这两版的封面都突出了“种族”主题,与同时代涌现的新奴隶叙事作品相呼应。例如,《快乐》(Jubilee)的封面以黑人女奴的头像作为前景,背景则是奔跑的白人士兵;《德萨·露丝》(Dessa Rose)的封面则描绘了两个黑人女奴正在收棉花的场景。严格来说,《甘蔗》并不能算作新奴隶叙事,因为尽管作品涉及种族,但它并未以蓄奴制作为故事背景,也不符合新奴隶叙事的叙事模式。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新奴隶叙事文学风潮对《甘蔗》的封面设计产生了显著影响。原本设计中对种族歧视的“曲线救国”式的暗讽,在新版的封面设计中变得更加直白和强烈,直接抨击了种族不平等的现象。
哈珀&罗版的封面右边为人面侧影,侧影的眼睛处是三名劳作的黑人。利夫莱特版封面右上方沿用了首版封面的红日,左下方是正在犁地的黑人男子,不远处有一个身着红裙的黑人妇女。两版封面的风格及构图截然不同,但有两处相同点。
首先,两版封面均使用黑人农民的劳作场景。该场景使黑奴与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农民形象高度重合起来。隔离制度将种族歧视合法化,以高压政策压缩非白人的生存空间。南方黑人多被迫成为佃农,尽管他们辛勤劳动,但往往食不果腹,生活困苦。“农场主规定种什么作物,如何种植,在哪加工,在哪销售。他(黑人)只希望能够在年底偿清债务。”[17]北方黑人则多从事重体力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且报酬低,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异化。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言:“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8]有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黑人农民均背对或侧对读者,与读者无眼神交流。根据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和西奥·范·利文(Theo van Leeuwen)的分类,这种姿态属于“供给(offer)”,即他们只负责提供信息,无意与任何人交流[19]。此时,黑人农民化身“他者”,就像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品,一层透明的玻璃将“他者”与“我们”隔开。这种拒绝交流的姿态好似在黑白之间立起了一道无形壁垒,这是对隔离制度的无声控诉,同时说明封面设计者对种族融合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其次,两版封面均采用了学者背书的方式。哈珀&罗版封面下方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非裔美国文学专家罗伯特·A.伯恩(Robert A. Bone)对《甘蔗》的评价:“与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和拉尔夫·埃利森的《隐形人》比肩。”这一评价无疑是对图默作品的极高赞誉。而利夫莱特版封面则在红日左侧标注“新引言由达尔文·T.特纳(Darwin T. Turner)所著”。特纳为爱荷华大学非裔美国研究中心主席,他在为1975年版《甘蔗》撰写引言后,又于1980年编著图默作品集《任性和追求:吉恩·图默作品集》(The Wayward and the Seeking: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Jean Toomer),进一步肯定了《甘蔗》的文学价值。两位学者的背书为《甘蔗》的文学价值提供了有力保证,同时也起到了广告宣传的作用。此外,两版封面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同时受到白人学者伯恩与黑人学者特纳的认可,充分说明《甘蔗》具有跨越种族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反映了超越肤色界限、摒弃种族仇恨是黑人与白人的共同愿望。
这两版封面反映了设计者在民权运动这个特殊时期对《甘蔗》做出的回应和思考。透过黑人农民的劳作场景,两版封面传递出被边缘、被隔离群体的恶劣生存环境,对“隔离但平等”提出了质问。图默笔下挣扎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黑人不仅引起黑人学者的共鸣,也让白人学者动容,侧面说明种族隔离触碰了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
3 21世纪初期:对种族关系的重审与对黑人女性的关注
进入21世纪,《甘蔗》一书重获出版社的广泛关注。自2010年至今的14年间,《甘蔗》再版将近40次。克莱蒙斯认为:“后种族的破灭和首位非裔总统的失败(不平等加剧、非裔美国人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使《甘蔗》再次获得了重视。”[20] 2008年,随着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上任,众多主流媒体纷纷宣称美国已经步入了所谓的“后种族时代”(post-racial era)—一个不再以种族差异为基础来界定个体身份和社会价值观的时代[21]。据盖洛普(Gallup)统计,奥巴马上任初期,对种族关系持乐观态度的美国民众比例升至67% [22]。然而,奥巴马的当选更像是一剂麻醉剂,它暂时麻痹了人们对种族问题的敏感神经,却未能治愈真正的社会创伤。黑人群体很快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种族紧张关系。2020年5月,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暴力执法死亡的事件更是成为了美国种族关系的转折点。随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席卷全美,引发了全球对种族问题的深刻反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甘蔗》多次再版,其封面展现出对种族关系的重新审视,尤其是对黑人族群中更为弱势的一方—黑人女性的关注。
2011年诺顿版的封面使用了图默的肖像,是典型的自传类作品封面。有学者认为《甘蔗》的第三部分是图默的“半自传”,主人公卡布尼斯与图默一样,都是黑白混血,长期处于黑白的尴尬夹缝[23]。此肖像采用俯视的拍摄视角,图默视线低垂,双手置于膝盖,显得非常局促,郁郁不得志。图默生活的年代,美国大部分州遵循“一滴血原则”(one-drop rule):只要有一丝黑人血统,便被归为黑人。图默的种族观与“一滴血原则”产生了正面冲突。1930年,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发出邀请,欲将《甘蔗》中的诗歌收入《美国黑人诗歌集》(The Book of American Negro Poetry)。图默在回信中婉拒:“我的诗歌不是黑人诗歌,也不是白人诗歌……它们源于美国的种族融合,这是一种新型种族,我将之称为美国种族。”[24]图默消解了“非白即黑”的种族对立,其种族观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种族隔离时期,这种种族观无疑十分前卫,甚至离经叛道。很快,质疑纷沓而至。有人认为这是他出于对种族歧视的恐惧而想出的托辞[25],还有人斥责图默利用黑人身份为自己的作品造势[26]。图默在指责声中远离哈莱姆文学界,65岁郁郁而终,生前仅发表《甘蔗》一部作品。透过封面上的图默肖像,我们仿佛看到他为种族身份所困的一生。直至今日,“肤色界限”(color line)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图默于百年前提出的黑白融合的新型种族终究只存于想象。
2021年柳莺版封面再现了百年前白人对黑人执行私刑的场景。封面中央是几圈光晕,如同黑夜中的篝火。一名黑人仰面呼喊,双臂被擒,强制拖拽,与《燃血的月亮》(Burning Moon)中描述的火刑情景完全一致。封面右上角是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对《甘蔗》的评价:“这本书应存于所有读者、所有作家的桌面上和脑海里。”安吉罗的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这部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读者应该去购买这本书,作家能从这本书中获得灵感;其二,这部作品中描写的黑人受尽压迫,甚至被残忍谋杀的历史不该被忘却。安吉罗的评价直指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的历史健忘症。虽已过去百年,被迫害的历史依然如影子般跟随黑人,但大部分白人却选择了忘却。2021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调查报告证明了这一点:75%的黑人认为提高对种族主义历史的关注度具有积极意义,而白人中持相同意见的仅占46% [27]。柳莺版封面带领读者穿越时空,回到种族隔离时期,将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
2011年利夫莱特版的封面将关注点转向了更为边缘的群体—黑人女性。封面右下方为“新后记由鲁道夫·P.伯德(Rudolph P. Byrd)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所著”。伯德和盖茨在后记中肯定了图默的文学天赋,特别提及他对黑人女性作家的影响,包括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等[28]。封面左上方是沃克对《甘蔗》的评价:“(《甘蔗》)在我心中产生了惊涛骇浪的回响。我狂热地爱着它;没有它,就没有我。”斜体字“我狂热地爱着它”属于前景化手法,突出了沃克对《甘蔗》的热爱。设计者选用沃克的评论,不仅因为她是黑人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还因为她是“妇女主义”(womanism)的提出者。沃克在《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中将妇女主义定义为“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29]。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30]沿用并丰富了该词的内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妇女主义的专著,将少数族裔女性由边缘拉到中心,使妇女主义一词拥有了消除种族、性别、阶级三重压迫的意义。沃克、伯德和盖茨的背书起到了广告宣传作用,也暗示了黑人女性是《甘蔗》的主题。封面左下角的男性黑影手持尖刀,双臂高举,仿佛在怒吼;右上角的女性黑影悬于半空,背对男性,双臂舒张,五指张开,仿佛风中柳叶随风飘摇。读者看到此封面,可能会误以为这部作品描写了一场骇人惊闻的谋杀。虽然《甘蔗》中大部分黑人男性的出场确实伴随性欲与暴力,可是图默并没有将全部女性都描写成受害者。相反,这些女性独立坚强,具有抗争精神,如大胆追求爱情的博娜与艾斯特、身体健壮堪比男子的卡玛、独自抚养混血儿子的坚强母亲贝姬等。可惜的是,这版封面仅突出了黑人女性作为父权社会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忽略了图默笔下女性的多面性。
2019年企鹅版的关注点也是黑人女性,强调了女性的无声状态。封面上,一位黑人女子侧过身,她眼睛盯着读者,该眼神属“要求”(demand)[31],表示她想对读者倾诉。但是,一根甘蔗苗遮住了她的嘴巴,将她与读者隔开,一个渴望交流却无法交流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甘蔗》中,图默常用自由间接引语展示男性角色的内心独白,因此读者得以“听到”男性的声音。相反,女性角色几乎没有内心独白,她们的所思所想偶尔经叙述者之口告知读者。正如梅根·阿波特(Megan Abbott)所言:“她们是近乎无声的容器,叙述在她们的意识周围打转,却从未直接进入其中。”[32] 21世纪,黑人女性依然受到种族、性别、阶层的三重压迫。与20世纪不同的是,显性迫害变成了隐性迫害。它们更加隐蔽,渗透在教育、职业、家庭等各个角落,使黑人女性丧失了言说苦难的权利,沦为“失语者”。
21世纪,《甘蔗》再版封面体现了“后种族”时期下设计者对种族关系的重审,抒发了种族融合的乌托邦之梦,但也提醒美国人种族历史不能忘却。同时,部分封面也给予了黑人女性一定的关注,突出了黑人女性所受的显性和隐性迫害。
4 结 语
再版是书籍的重生,每次重生都可能带着不同的“面孔”。《甘蔗》封面的百年演变史正是不同时代封面设计者对这部作品深刻回应和思考的具象化表达。20世纪初期,设计者巧妙地以“曲线救国”的手法,含蓄地批判了种族隔离的罪恶;20世纪中后期,设计者采用通俗直白的封面迎头痛击种族隔离;21世纪,除了对种族问题的持续关注,关注点还转移到黑人女性身上。因此,当我们凝视封面,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小说的封面,而是一个时代的关注焦点。遗憾的是,文学批评家往往将眼光局限于作家与文本,忽略了作家背后的无名英雄,也忽略了类文本与文本的交流互动。本文旨在将学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类文本及其背后的无名英雄身上,将研究视角拓展至编辑学与文学的跨学科领域,荡起一片跨学科的涟漪。
注 释
[1]法国文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类文本:阐释的门槛》(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中首次提出类文本这一概念,指围绕在文本周边的、使文本得以成为书本的各种要素。
[2] 许德金.类文本叙事:范畴、类型与批评框架 [J]. 江西社会科学,2010(2):29-36
[3] Frank W. Appendix II:1923 Foreword by Waldo Frank[M]//Toomer J. Cane. New York:Penguin Books,2019:168-170
[4] Bell B. A key to the poems in Cane [J]. CLA Journal,1971,14(3):251-258
[5][25][26] Larson C R. Invisible Darkness:Jean Toomer & Nella Larsen[M]. Iowa: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3:27,203,170
[6] 截至2024年5月2日,在美国亚马逊平台上可搜到42个版本的《甘蔗》。其中,1923年至1999年之间仅有3个版本,分别为1923年、1969年和1975年版。2000年至今共有39个版本,其中有27个由独立出版社出版。
[7] 吴平.《骆驼祥子》译本封面的多模态符际翻译研究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50(2):144-153
[8] Rusch F L. Form,function,and creative tension in Cane:Jean Toomer and the need for the avant-garde [J]. Melus,1992,17(4):15-28
[9] Foley B. Jean Toomer’ s Sparta [J]. American Literature,1995,67(4):747-775
[10][13][14] Toomer J. Cane [M]. New York:Penguin Books,2019:48,175,125
[11]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Lynching in America: confronting the legacy of racial terror [EB/OL].[2024-01-27].https://eji.org/wp-content/uploads/2005/11/lynching-in-america-3d-ed-110121.pdf
[12][24] Rusch F L. A Jean Toomer Reader:Selected Unpublished Writing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26,106
[15][20] Clemmons Z. Foreword [M]//Toomer J. Cane. New York:Penguin Books,2019:7-10
[16] 因陷入财务危机,Boni & Liveright曾多次关闭又重开,并将公司名改为Boni或Liveright。
[17] Sargent L T. African Americans and Utopia:visions of a better life [J]. Utopian Studies,2020,31(1):25-96
[18] History Editors. “I have a dream” speech [EB/OL]. [2024-01-27].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civil-rights-movement/i-have-a-dream-speech
[19][31] 在《阅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一书中,克雷斯和利文将图片中人物的眼神分为“供给”和“要求”两类。其中,“要求”型眼神指图片中人物直视观众,这种直接的目光交流仿佛在寻求观众的注意力和情感回应。而“供给”型眼神则表现为图片中人物朝向画面中的另一人物或物体,与观众没有直接的视线接触。
[21] Schorr D. A new, “post-racial” political era in America [EB/OL]. [2024-01-27].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8489466
[22]Saad L. U.S. Perceptions of white-black relations sink to new low [EB/OL].[2024-05-02].https://news.gallup.com/poll/318851/perceptions-white-black-relations-sink-new-low.aspx
[23] Goede W J. Jean Toomer’s Ralph Kabnis:portrait of the negro artist as a young man [J]. Phylon(1960—),1969,30(1):73-85
[27] Infield T. Deep divisions in views of America’ s racial history [EB/OL].[2024-05-02].https://www.pewtrusts.org/zh/trust/archive/fall-2021deep-divisions-in-views-of-americas-racial-history
[28] Byrd R P,Gates H L. Afterword [M]//Toomer J. Cane. New York/London:Liveright,2011:124-175
[29] Walker A. In Search of Our Mother’ s Gardens: Womanist Prose [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1
[30] 本名为葛劳瑞亚·晋·沃特金(Gloria Jean Watkins)。其笔名bell hooks的首字母故意使用小写,表达了对主流文化的反叛态度。
[32] Abbott M. “Dorris dances...John dreams”:free indirect discourse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in Cane [J]. Sounding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1997,80(4):455-474
(收稿日期:2022-05-31;修回日期:2024-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