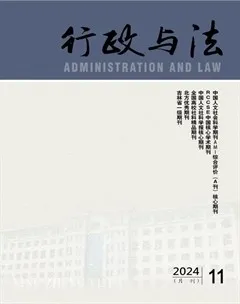地方政府编外用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优化
摘 要: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不断扩大,“职责—编制”矛盾日益突出。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编外用人的行动策略来充实基层治理力量,保障地方干事创业的资源需求,以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这使得编外人员成为了政府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力资源。但是,编外用人并非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产物,其生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通过梳理我国地方政府编外用人的历史演变过程,发现政府编外用人行动经历了中国古代胥吏制度、近现代临时工制度、计划外用工、劳务派遣等发展阶段。尽管所处历史方位、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等都有所差异,但政府编外用人在招录方式、角色定位、薪酬待遇、身份转换与晋升通道等方面存在较强的延续性或相似性。这种延续性相似性生发于中央一统与地方自主始终共存、正式与非正式并行不悖,并受到东方思维中“二元合一”的逻辑惯性深刻影响。新时代优化地方政府编外用人需要坚持差异化、法治化和专业化原则,重点优化编外人员培训开发、薪酬保障和组织激励机制。
关 键 词:编外用人;编外人员;编制;薪酬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4)11-0051-1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雇用了大量的编外人员,他们广泛分布在行政管理、综合执法、专业技术和后勤保障等岗位中,从事着辅助性、可替代性和临时性的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工作,对政府治理效果和社会治理效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政府职责范围的不断扩大,编外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出现逐步膨胀的趋势,在一些政府部门中,编外人员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编内人员。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要“严格控制编外聘用人员,从严规范适用岗位、职责权限和各项管理制度”。可以说,编外人员已经成为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和地方治理人事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和关键要素。
政府编外用人现象并非现代政府发展的产物,也非当代中国的独有现象,其生成和发展逻辑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尽管现代中国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社会和大众不可能短时间内丢掉所有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2]中国治国理政的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并深刻影响了现代的政府用工制度。[3]政府编外用人的行动选择对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深入了解政府编外用人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更加清晰且深刻地把握当下的政府编外用人行为。基于此,笔者深入探究古今政府编外用人行动以及编外人员长期存在的历史逻辑,以期对优化当代编外人员管理和规范政府编外用人行为提供思路与启发。
二、历史变迁:从古至今编外用人现象梳理
尽管编制和编制管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明确提出的,但从其外延角度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类“编外人员”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官制发展的历程中早已出现。在传统封建官制中,基层官府的“胥”和“吏”是作为区别于“官”的群体存在的,协助地方官治理一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加剧了官与胥吏在录用、俸禄、流动和晋升等方面的差异性,明清时期的胥吏专政又强化了胥吏“位卑权重”的特征。随后的民国时期,政府“编外用人”现象也得到了延续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发展,突出表现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临时工、计划外用工和市场经济时期的服务外包、劳务派遣。
(一)中国古代胥吏共存共治
我国幅员辽阔,为了应对超大政府规模之困,实现中央对各个地方的有效管理和掌控,在地方上形成了胥吏共存共治的局面。同时,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一种说法,其含义是指县级以上主要是皇权控制的官治系统,县级以下则是由地方宗族长老或者乡绅控制的地方自治系统。所以,地方官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地方的治理,往往也会使用大量的胥吏,这些胥吏多为当地人,熟谙当地情况,具有较好的地方性知识,能够更好地协助处理地方事务。
胥吏共存共治的现象出现于秦汉,伴随着郡县制而产生。郡县制之下,郡县完全受中央和皇帝的控制,是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行政单位,皇帝任免郡县的主要官吏,包括郡守、郡尉、郡监(监御史),县(道)的县令、尉、丞。相对于自身的辖区范围来说,这些地方官员是力不从心的,因此他们都会组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团队”,包括公差、衙役等。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出现了“官吏分途”人事改革特征,“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官品分化趋势明朗,胥吏日趋卑下。[4]官与吏在职业发展、职位等级、激励保障等组织制度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沟壑。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众多的社会精英通过科举制这一选官途径得以任用,其直接后果是胥吏晋升的通道越来越窄,虽然胥吏仍可为官,但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胥吏不再拥有晋升高位的资格,而只能处于官僚结构的底层。同时,国家开始严格规范胥吏的选拔任用,并确定了一些具体的选拔标准和方式。例如宋朝前期实行的“拣选制”和宋朝后期的“保引考试制”,但纵使如此,“官吏分途”给胥吏群体带来的消极影响已深入中国官僚体制深处。到了明清时期,胥吏政治逐步发展成为胥吏专政。科举制度的“异化”发展导致了此时期选拔的官员的知识结构不甚合理,由于他们不谙国家治理,因此官府的运转,尤其是地方层级上越来越依赖于胥吏群体。虽然其身份转换仍旧受到限制,但由于其掌握基层情况且具备一定的能力,加之官场对于胥吏群体的依赖,胥吏已然成为了真正的“掌权者”,成为和皇权共天下的力量。从积极意义的层面上来讲,胥吏群体承担了大量基层工作,他们和民众直接接触,传递了来自“皇权”的旨意,并将其具体施加于民众,有力地保证了古代中国官制体系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在“皇权不下县”的时代,胥吏的存在维持了正常的政治和社会间关系。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到清代时胥吏制度弊端已经十分严重,形成了“胥吏专政”“皇权与胥吏共天下”的局面。
胥吏制度并不是封建国家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一种正式化的用人制度,而是封建政治制度在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现实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形成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带有“约定俗成”色彩的封建官僚制度的辅助制度和支持制度。胥吏作为官僚集团的外围群体,不受封建官制的限制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事实上又与地方官员建立了宾主关系。尽管言轻身微,却直接参与各种基层事务的处理工作。即使在封建社会后期胥吏广受诟病,但政府和社会的运转仍旧无法脱离胥吏群体。可以说,胥吏辅助地方官吏实施地方管理,正式官僚与非正式官僚的共同存在使得一个规模相对不大的官僚机构能够对庞大的中华帝国实施有效治理。[5]
(二)民国时期政府编外用人正式化
清朝覆亡,民国继之。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吸收古代中国官吏制度和西方公务员制度的经验,创立了选任官员的考铨制度。作为“五权分立”体系其中之一,考铨制度通过考试,按照资历或实绩核定官职的授予或升迁。具体而言,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公务员的选拔,一律实行公开竞争考试,非经考试及格不得任用。考试分为普通考试、高等考试、特种考试。此外,民国政府还规定了公职人员任用制度、考绩制度、进修制度、俸给制度和服务制度,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分类、任用、俸禄、休假、保障及惩戒等内容有着详细的规定,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政府公职人员管理制度体系。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地方行政采取省、道、县三级政权的管理体制并着手制定了上述文官管理法规。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公务员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以“公务员”的名称代替“官吏”的旧称谓。
民国时期不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公务员管理系统,而且改革了中国古代的胥吏制度。民国政府规定“一等县设四科,二等县三科,三等县二科。二等县将以上第三、四科合并;三等县将以上第一、二科合并,第三、四科合并。”各科设科长一人,由县长呈请民政厅委任;科员二到四人,科员由县长委任。[6]对此《县政府办事通则》补充规定,各科科员总数一等县不得超过10人,二等县不得超过8人,三等县不得超过6人。然而,在正式的编制之外,封建时代的胥吏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和延续下来。这些旧朝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冗杂的“非正式人员”仍然饱受诟病。对于这部分群体的管理,民国时期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变革,其基本思路是以正式的编制管理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文官任用法草案》《文官考试法草案》《典试委员会编制法草案》《官吏服务令》等。尽管文官仍存在高级与低级、特殊与普通之分,但是胥吏借此机会改变了自身以往单纯执行具体行政事务的地位,不仅获得了文官的身份,也获得了相应的地位、收入和法律保障等。
(三)计划经济时期的临时用工和计划外用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临时工”群体广泛存在于政府、企事业单位中。其中,政府机关的临时工即和现在的“编外人员”相类似,主要是指协助政府开展公共事务服务管理而没有正式编制的人员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公共秩序类、行政执法类、党群工作类。[7]“临时工”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区别于当时的长期固定工而言的一种用工形式,是计划经济模式在用工制度和劳动关系中的反映。该群体的出现本质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用工制度无法满足当时用工单位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开展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确立了“国家包揽,行政隶属,身份差别,终身固定,全面依附”的固定工制度,在政、军、教界实施“包下来”政策。但是,这种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积极性不够、效率不高、活力不足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上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就出现了大量的临时工,用以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发展生产。[8]自此,临时工“蜂拥式”发展,在“大跃进”时期激增到2000万职工中有大约50%都是临时工。[9]基于此,在上世纪60年代遭遇严重困难时期中央开始上收劳动计划权限,控制地方自主用工形式的发展,大规模裁撤临时工和合同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初见成效,招聘临时工的现象又变得多了起来。1971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常年性的生产、工作岗位,应该使用固定工,不得再招临时工。”并且如上这些生产、工作岗位已经使用临时工,并且确实有必要继续使用的,可以改为固定工。[10]1979年4月,国务院以〔1979〕108号文件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当年要在已经清理压缩的基础上,再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200多万人。1982年8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人事部联合发文《关于继续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通知》,指出1982年全国预计清退计划外用工200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20万人。同时,强调要严格劳动计划管理,完善定员定额工作。1986年8月,劳动人事部、国家计委下发《关于严格控制计划外用工的通知》,重申要强化劳动力管理,立即停止增加计划外用工。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分割严重的背景下,当时清退压缩临时工和计划外用工的主体和重点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和国有企业中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同时,由于“国家劳动计划指标不能满足用工单位需求”等实际情况,临时工缩减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关于这一问题,当时的基本解决思路有二:一是将计划外用工纳入“计划内”,二是通过市场调节机制之下的“劳动合同”制度迫使临时工“自然消亡”。由于第二种解决思路的试点工作推进相对较为顺利,中央政府便决定拓展范围,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1994年后,国家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订)》等法律法规,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来完善对劳动关系的调整。由此,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劳动合同制为核心的劳动法体系。[11]
(四)市场经济时期的劳务派遣
1995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劳动法》从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劳动安全卫生、禁止使用童工、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和惩处等方面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进行了明确规定。《劳动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开始推行应用劳动合同制度,通过引入合同管理来规范和约束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的行为,进而保障双方的权益。受此影响,1996年,辽宁省劳动厅向劳动部请示“关于临时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问题,同年10月9日,劳动部办公厅作出复函,明确指出“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已经不复存在了,用人单位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可以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所区别”。同年11月,劳动部办公厅对于临时工相关问题的请示作出复函,再次申明不再保留“临时工”的提法,于是临时工这一称呼便不再使用。同时进一步指出,用人单位如果在一些临时性岗位上用工,不仅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还要依法为其缴纳各种社会保险,使他们享受到相关的合法的福利待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的工勤人员也要按照《劳动法》及其配套规章的有关规定实行劳动合同制。2006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95条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政府在编制限额和工资经费限额内可以采用合同的、聘任的方式聘任公务员。
政府机关单位既不允许随便招收编制以外人员,也不能随意突破既定编制额外扩编,因此,地方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经由劳务派遣公司招聘相关工作人员。2014年3月1日起实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对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合同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第二章“用工范围和用工比例”第三条规定: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此规定的目的在于规范劳务派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机关派遣人员代表机关的利益和形象,辅助机关正式人员开展工作或者直接负责一些原本需要机关人员来完成的工作,待遇和机关工作人员基本等同,另外还有一定的补助。机关事业单位引入市场化用人方式,通过劳动派遣补充政府人力,既有助于解决机关事业单位用人受编制和指标限制的难题,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招聘、遣散员工等问题给政府带来的负担。
三、路径依赖:政府编外用人的古今延续性与相似性
疏理从古至今政府编外用人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虽然编外人员身处不同性质的社会政权环境之中,但政府编外用人行为有着很强的传承性和延续性,重点体现在编外人员招录方式、角色定位、薪酬待遇、晋升通道与身份转换等方面的相似性上。
(一)招录方式的相似性
在招聘和任用方面,中国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类编外人员,诸如胥吏群体、临时工、劳务派遣人员等,和当下的编外人员在招录方式上有较大的相似性。考选招录是从古至今编外用人都有采用的方式之一。胥吏的考选招录方式自唐以来便已经开始实行,并在宋代有所发展。到了明代,要求凡充吏者“皆从藩府或巡按御史考选差拔”[12],清代在招募衙门书吏时更注重通过考试选拔的方式进行统一招录。可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从体制外引入相关人员的方式方法越来越趋于规范化和公开化。至民国时期,采用公开考选、评定成绩的办法将旧社会胥吏、差役等群体纳入政府部门之中更成为了一种主流的趋势。目前,对于非编人员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坚持了“逢进必考”的原则,采用统一报名、统一考试、统一聘用的办法。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一些招录任用方式如承袭式招录、保引式招录、捐纳式招录等,与当今政府编外用人行为差异较大,已无较多参考价值。考选方式作为规范招录的代表得以保存下来,而承袭、保引、捐纳等“灵活”方式只会带来更多的编外用人弊端。基于此,当下编外人员招录要崇尚规范化,力除随意化,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编外人员招录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角色定位的相似性
历史上的“类编外人员”主要指在官府中工作的胥吏群体,他们是“庶人之在官者”,往往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抄写、批勘、收发、传送公文,或管钱粮、牢狱、徭役、文书等,突出表现出具体性、事务性和辅助性特征。以清代胥吏群体为例,胥吏群体中出现了一批擅长记账筹划、训练有素的师爷,他们代替了地方官员去催征田赋、计算各种附加税额、统计应上缴朝廷及地方政府留成的税款分配等。胥吏代替或辅助正式官僚完成一些工作。如今,政府部门中的一些编外人员实际上承担了正式编制人员的工作,除了领导、重大决策以外,与正式编制人员的工作内容无较大差别。地方政府运行中普遍存在的“混编混岗”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同时,编外人员不仅从事辅助性工作,很多时候甚至承担起地方治理“主力军”角色。[13]可以说,古今编外人员都扮演着具体事务执行者和正式官僚辅助者的角色。
(三)薪酬待遇的相似性
非编制人员待遇相对较低。古代胥吏群体“薪资刻薄”,他们虽然在官府部门工作,承担着复杂的事务性工作,但是朝廷在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和定位上,仍将他们视为服役者。因而提供给他们的薪资普遍过低,更没有完善的薪酬保障制度机制。为了能够满足自身需求,胥吏所获更多的是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在当下,低薪是编外人员的重要特征之一。编外人员的工资低于正式职工的收入水平,大多数情况下只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尽管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有时多与正式编制人员相同,甚至岗位互相交叉重叠,但收入水平完全不同。一般编外人员群体中人事代理的工资待遇较好,但仍比正式职工差,劳务派遣的工资收入最低,而且还和工作单位没有劳动关系。可以说,薪资待遇较低是从古至今编制外人员的共同特征。
(四)晋升通道与身份转换的相似性
历史和当下的编外人员在职位晋升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胥吏群体“不入流品”,他们鲜有晋升通道。通过《唐律疏议》记载的“杂任,谓在官供事,无流外品”可以发现,在唐代,胥吏群体所处政治地位较低,仕途不畅。到了宋代,胥吏群体出职为官的可能性更小,这源于该群体身份转变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及至明代,胥吏转官的通道更加滞塞,吏员被视为“杂流出身”,终生只能担任“佐贰、幕职、监当、库之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14]。可以看出,为吏者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选任为官的资格,他们只能等待举荐的时机,晋升通道毫无畅达可言。到了清代,由于胥吏群体数量的空前庞大,吏员身份转换的压力也空前加大。计划经济时期用人单位在提拔用人时,只会从正式工里挑选,而不会考虑临时工。临时工群体面临着和胥吏群体同样的晋升困境。在当下,编外人员想要进入体制内,同样面临一定的困难。当然也有小部分编外人员通过持续学习和不断努力,成功改变自身身份,成为一名正式编制人员,获得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是2018年以来,一些地方相继取消了编外人员担任部门内设机构领导岗位的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编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容易使他们产生被排除在外甚至区别对待的思想顾虑甚至萌生辞去工作的想法,进而影响到组织的稳定性。
四、逻辑动因:政府编外用人的思维惯性与制度因素
政府编外用人的行动选择受到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多因素影响。其中一些内在的、稳定的因素,即使历史变迁,仍然稳定地发挥作用。研究发现,中央一统与地方自主始终共存、正式与非正式机制并行不悖深刻影响了政府编外用人的这种延续性。更进一步,东方思维中“二元合一”的逻辑惯性又是这种深刻影响背后的内在原因。
西方逻辑思维方式中多强调“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而中国社会之下的思维方式多是一种既承认“二元对立”,又看到“二元合一”的现实状况。“二元合一”的中国思维在看到矛盾之对立性的同时,更加强调矛盾相互转化和走向平衡的特点。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中存在着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存并相互转化的联系,这一联系居于国家治理逻辑的核心地位,并且正式与非正式共生并存、互为依赖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调节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基本矛盾。[15]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严格的、规范的制度使得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获得更强的稳定性和可信性,弹性的、灵活的规则使得地方获得一定的灵活、可控空间,可以说,这种 “不变”与“变”的统一维持着国家统一和稳定运行。这便是一种“二元互动”“二元合一”中国思维方式的体现。
从表面上看,编外用人是突破编制管理刚性约束的一种政府行为,编外用人和严格的编制管理并不可能同时存在于政府用人管理过程中,二者具有不可兼容的矛盾性。然而,在我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中,为了缓解正式编制人员不足的矛盾,顺利完成上级任务,在“三定”原则和编制相关政策的约束之下,结合自身财政实力,会主动采用市场化方式雇用一些编外人员,协助编内人员完成上级政府任务。编外用人没有增加编制数量,符合编制“只减不增”的政策要求,同时在政府自身财政实力和政策自主允许范围之内,达到了充实内部人力资源的目的。可以说,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编外用人是地方政府缓和“人—职”“人—事”矛盾的策略性选择,在矛盾之中,政府通过发挥自主性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因此,编外用人的长期存在正体现了矛盾统一的中国思维。
(一)中央一统与地方自主始终共存
周雪光认为中国政体内部始终存在着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基本矛盾,集中体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具体来看,中央管辖权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而地方治理权多表现为各行其是、灵活执行等。这一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并且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平衡,既遵循中央权威要求又灵活变通,中央一统与地方自主同生共存,正是这一基本矛盾之下的产物。而基层政府编外用人行动受到一直以来中央一统和地方自主性长期存在的深刻影响。
中央一统体制依托于正式制度和科层组织。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在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中指出,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正式制度的正式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再到细则和合约,其正式程度逐渐降低。[16]以正式规则和正式制度为基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官僚制理论。韦伯官僚制理论之下的科层组织具有专门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技术化和公私分明等主要特征。[17]但是严格的或者纯粹的理性科层制度是应然的和理想化的,作为实然的科层制可以趋于这个目标而趋于自我规制和自我完备。具体来看,我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科层组织体系,政府组织又通过种种正式制度规定了职位间的权威关系、等级结构、严令密法。不论是科层组织还是正式制度均强调一种权威性、稳定性、统一性和规范化,当然这些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和强化政策执行的“不折不扣”。但是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地方情况千差万别,一统体制下的决策过程难以应对这种变化和差异,并且过度的制度约束也会造成体制缺乏活力。因此,解决问题、应对危机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压力促使这一体制不断地将问题和解决方案下放到基层社会;与此同时,正式制度威严稳定,不得触动,只能默许其与实际政策运行过程松散关联,即官僚体制向下延伸止于县府,官府正式制度与民间社会之间松紧强弱因地而异,这一结构特点提供了巨大的灵活空间,也推动正式制度走向仪式化,使得地方自主、灵活变通成为可能。[18]可以说,这种灵活变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基本矛盾。
中央一统之下,仍存在着逐级代理制度。地方政府作为地方“代理人”时常处于资源不足的状况,在维护中央权威前提下,地方代理人会主动采用变通的方式来改变自身处境。近些年来,政府机构和人员规模膨胀的弊端日益显现,政府通过禁止随意扩编、压缩正式编制数量、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等方式缩小政府机构和人员规模,以减少政府财政压力,提高政府运转效率。但是与此同时,社会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政府职责也日益多样化,不断增加的政府事务,要求相应的人力等资源支持,解决编制与职责之间的矛盾成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在正式制度框架内,即上级政府准许和自身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采取这种灵活、可控的用人方式以缓解政府组织对辅助、临时性岗位人员的需求。
(二)正式与非正式并行不悖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制度是如何思维的》一书中对制度的产生和影响进行了深刻诠释,她认为制度在赋予人们“身份”的同时,塑造了社会群体的记忆和遗忘功能,还可以对事物加以分类。[19]具体可以理解为,制度是通过规范和权威的一种方式,给予人们一种稳定的“身份”,让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来规范自身的行动选择。在“不逾矩”的同时,制度产生的稳定性和凝固性将一些事物放入不同的类别并赋予道德和政治的内容,加上价值判断。基于此,国家通过建构制度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注意力,利用信息和规则来代替个人思维。
在国家治理中,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叉并行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缓和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中央通过建构严格的正式制度体系,树立国家权威,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而同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允许一些领域的灵活性并且根据事项的差异以及变化,非正式的制度空间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中央通过这种允许正式和非正式、权威和灵活的同时存在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进而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当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内在的紧张。非正式制度的过度使用或者运行过程中的“异化”,会衍生出更多的负效应,例如“地方化”倾向、地方性知识的权力扭曲,威胁到中央的一统体制;正式制度的过度使用或者运行过程中的“极化”,会导致组织的僵化和效率低下,影响组织的整体稳定性。故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处于不断地动态调整过程中。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包括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非正式制度是在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长期演化而来的。在用人方面,长期存在非正式制度,例如地方性知识、忠实人际关系、官本位思想等。[20]中华帝国的治理核心不仅在于庞大的官僚结构中存在的正式权威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存在于各个层级的官僚胥吏的非正式行动以及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历史上的胥吏到近现代的临时工、计划外用工,再到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各种形式的编外人员,都是在正式官僚制度和人事制度之外的一种灵活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具体来看,在政府机构和人员管理方面,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体系并实行严格的编制管理,但是在政府中除了编内人员外,还长期稳定存在着没有编制却参与政府管理的编外人员群体,并且编外人员日益发展成为基层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编内人员与编外人员共存于政府组织之中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可以同生共存的制度路径启发,也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共生并存的具体表现方面之一。
五、优化策略:政府编外用人的基本原则与机制建设
从政府组织运行和发展现实来看,编外人员是政府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编外人员“一刀切”或者完全杜绝政府编外用人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此,从组织理性视角出发,规范政府编外用人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在差别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指导之下,通过规范编外人员管理来规避编外人员对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带来的诸多负效应,进而更好地发挥编外人员对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的正向功能。
(一)政府编外用人的基本原则
⒈差别化原则。由于编外人员和体制内人员在承担职能、福利待遇、奖惩晋升和后续发展等多方面的根本性差异,试图将两类群体进行统一化管理,即以同一套管理标准和规章制度对两类群体加以同等标准约束的管理模式,往往在现实中会产生新的诸多问题。因此,对于编外人员的管理,应首先坚持和正式编制人员的差别化管理原则。一是确立编外人员的“权责清单”,对比当前地方政府权责清单的相关要求,建立编外人员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编外人员必须承担哪些责任、必须做哪些事情,明确其“职责边界”。二是按照差别化管理的原则,确立编外人员待遇和奖惩方面的基本标准,应首先承认编外人员和编内人员待遇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现行编外人员工资待遇的问题,适当提高过低的工资收入,使其待遇与职责基本匹配起来。三是在差异化管理原则的指导下,确立编外人员职业发展和能力提升的管理办法。
⒉法治化原则。编外人员这一群体在政府中大量、广泛存在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基层政府通过合同制、聘任制等多种形式雇用了大量的编外人员,尤其是公安、城管、街道办、县直等部门。近年来基层编外人员数量膨胀明显,规模不断扩大。在一些地区或部门,编外人员数量甚至超过了正式编制人员。然而,对于该群体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的相关制度建设依然阙如。这其中尤其以法治化管理的滞后性表现最为突出。虽然只是一种体制之外的用工模式,但面对数量庞大的政府编外群体,只有对其实施法治化管理才能促使编外用工走上良好的发展道路。应坚持法治化的管理思维,将编外人员管理纳入法治化发展的轨道,完善编外人员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可以由国务院牵头制定行政法规,或者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等制定部门规章,将编外人员纳入规范管理之中。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着手出台法治化标准下的编外用人管理细则,不断提升相关规定的法律位阶,以使编外人员管理迈入法治轨道。
⒊专业化原则。对于编外人员的管理是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作,以现阶段地方政府承担的实际职能来看,各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处于“超负荷运作”的状态。将编外用人管理横加于政府之上无疑会平添许多负担,况且政府部门管理编外用人的经验相比于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第三方”仍旧显得“专业不足”。这种情况下,坚持专业化管理原则,让“专业的机构从事专业的行为”,把编外人员管理外包给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三部门”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目前许多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已经接手编外用人的招录等工作,他们提供劳务派遣解决方案,组织人员承接政府事业单位行政文秘、信息管理、物业后勤、呼叫坐席等辅助性岗位的工作职能,这无疑是专业化管理道路上的有益尝试。
(二)规范编外人员管理的机制建设
⒈编外人员培训开发机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曾指出,教育影响生产率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技术发展的动态和不确定环境中,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可以更快地汲取新信息,更为有效地采取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技术等。[21]所以,对现代经济社会而言,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增加劳动力和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而在组织管理中,提高劳动力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培训。培训不仅是着眼于现在的一件事情,更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超前投入。由于编外人员参与政府工作岗位和内容日益广泛,编外人员素质对于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执行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政府理应强化对编外人员这一群体的培训,从而提高该群体的整体素质能力。一是强化政府对编外人员培训的重视程度,在制度、政策和经费等方面予以支持。尤其是基层政府,要改变编外人员培训可有可无的观念,转变对编外人员培训的态度,充分认识到编外人员培训对提高基层政府组织绩效和优化群众服务的重要价值。二是明确编外人员的培训目标和培训计划,搭建培训与激励间的联系。政府对于编外人员的培训,应该与职位工作相关,注重现状和需求,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设计学习内容和标准,通过组织面向需求的培训内容来弥补编外人员技术或者能力的不足。培训计划应该是双向互动的结果,应结合编外人员的实际需求和岗位的客观需求,强化培训的供需匹配和精准化。三是优化培训内容,丰富培训方式。从内容上看,加强对编外人员道德、价值层面的培训,深化其对于公权力、组织忠诚和责任的认识。注重对编外人员处理政府事项的业务能力培训,提升编外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培训方式来看,除了可以采用案例研究、讲座报告、角色扮演、小组研讨、实地调研等多种培训形式外,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现代化和智能化方式应用于政府编外人员培训工作中。
⒉编外人员薪酬保障机制。随着组织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薪酬制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绩效表现。编外人员薪酬影响着编外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组织绩效的实现。因此,应强化对编外人员的薪酬管理。一是从薪酬激励的视角来看,政府应对编外人员的薪酬体系进行调整,形成薪酬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基层工作者薪酬待遇稳步增长。应建立基层编外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将基层编外人员的薪酬与考核绩效挂钩,工作绩效好,有相应的补贴和奖励,工作绩效差,也要给予相应的惩罚。由于我国公安系统较早地使用编外人员,警务辅助人员的数量也较为庞大,对于这一群体的管理制度建设相对完善,公安系统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的相关顶层设计和具体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以河南省辅警改革为例,河南省率先在省级层面联合多部门出台了《河南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层级和薪酬管理办法》,通过设定辅警的七个层级以及薪级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组成的薪酬体系,将层级与薪酬制度整合,完善辅警薪酬结构,提高辅警的整体薪酬待遇,实现薪酬动态调整,更好地发挥了薪酬激励的作用。并且通过实行层级升降制度和退出制度,实现辅警队伍的优胜劣汰,增强辅警队伍的整体能力素质。[22]二是从组织公平的视角来看,政府应关注到基层编外人员的福利问题,彻底解除基层编外人员只有“死工资”却无法享受福利的限制,建立起编外人员福利补贴机制,规范基层津、补贴发放,发挥“正激励”的作用。例如,西方许多国家将组织成员的薪酬与职务、责任、功绩等挂钩,美国的公共部门会给予工作优秀的组织成员一定的奖金,具体金额由部门负责人视情况而定,但一般不低于一个月的工资标准。[23]
⒊编外人员组织激励机制。编外人员作为政府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样应该是政府组织激励的对象之一。政府应针对编外人员的需求,采取多样的激励措施,建构起完善的激励保障体系,从而提高编外群体的组织绩效。编外人员激励机制应涵盖薪酬激励机制、培训激励机制、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奖励激励机制、机会激励机制、情感激励机制、环境激励机制等内容,从组织到个体、从工作到心理,搭建起全方位的基层编外人员激励机制体系,达到适才适用,人尽其才。除了激励机制以外,还应该建立竞争机制、监督问责机制、更新机制等配套机制,避免激励的极端化,形成合力,真正发挥编外人员服务基层的最大积极性和主动性。一要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举。物质是组织成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支撑和来源。物质激励可以通过薪酬、补贴、保险、奖金、福利等方式实现。多种实践表明,合理的精神激励对员工行动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组织关怀、情感激励、尊重等方式来对编外人员实施精神激励,弱化政府中由于编制给编外人员带来的身份差异,增强其组织归属感,进而提高其绩效。二要坚持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互促。正激励的方式主要有奖励、表扬、加薪、委以重要的工作等等,而负激励主要通过奖惩分明、考核问责机制等予以实现。通过建立组织惩罚机制来抑制政府工作人员的自利倾向之下的“谋利”行为,起到规制和约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EB/OL].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
[2]燕继荣.中国治理:东方大国的复兴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8.
[3]杨志云,陈小华.编制管理软约束抑或体制灵活性:基于四个城市辅警扩张的实证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9(2):88-99+127-128.
[4]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J].社会,2016(1):1-33.
[5](法)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徐建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83-84.
[6]吴树滋.赵汉俊.县政大全(第二编)上册[M].台北:世界书局,1930:71-73.
[7]钟玉明.协管员壮大之谜[J].瞭望,2007(34):12-14.
[8]彭茂安,刘辅臣. 劳动工资计划体制改革问题讲稿[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2:89.
[9]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81+396.
[10]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35+172.
[11]张学兵.计划外用工:当代中国史上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J].中共党史研究,2014(1):57-68.
[12]宁欣.中华文化通志·选举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05+275.
[13]叶贵仁.双层治理结构:地方治理中的统筹编制[J].行政论坛,2024(2):56-63.
[14]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93.
[15]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J].开放时代,2014(4):108-132+8.
[16](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64.
[1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8+309.
[18]周雪光.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J].清华社会科学,2019(1):7-42.
[19](英)玛丽·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M].张晨曲,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86-141.
[20]包艳.从“背离”到“互构”:制度实践的行动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96.
[21]张志超,雷晓康,吴晓忠,等.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304.
[22]河南出台辅警改革两个《办法》薪酬管理、奖励等重点全部明确[EB/OL].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henan.gov.cn/2020/04-07/1313775.html.
[23]徐刚.“体制化”漠视:基层政府人员薪酬极化的组织行为分析——以广州市P区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5(4):10-20+153-154.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Optimization
of Non-staff Employ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Tian Xiujuan, Wang Sheng
Abstract:As the focus of social governance continues to shift, the scope of responsibil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responsibility and establish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local government generally adopts the action strategy of non-staff employment to enrich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force and ensure the resource needs of local governance, so as to achieve good social governance effects. Non-staff personnel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group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But the phenomenon of non-staff employment is not a product of modern government development, it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basis.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on-staff employ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non-staff employment in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Xuli” in ancient China, the system of temporary workers in modern times, the planning of external workers, labor dispatch and so on. Although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economic level, political system,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are different, the action of non-staff employment has continuity or similarity in recruitment methods, role positioning, salary treatment,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channels. This kind of continuity or similarity is born of the coexistence of central unity and local autonomy, the coexistenc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and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ogic inertia of“unity of opposites” in eastern thinking. So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non-staff employ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tion, leg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and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salary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 mechanism of non-staff personnel.
Key words: non-staff employment; non-staff personnel; establishment; salary guarantee mechanism
(责任编辑:刘剑明 助理编辑:刘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