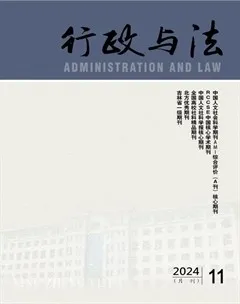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建构与实现机制


摘 要:“共富工坊”建设是浙江省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创造性举措,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当前,在“共富工坊”典型经验的复制推广中面临着如何在实践运行中实现最大功效问题,而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合作网络与实现机制的建构。以浙江省S村“共富工坊”的实践探索为例,通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共富工坊”参与主体互动均衡样态进行分析,凝练总结“共富工坊”建设与发展的三大基础机制,即政治赋能主动作为的村级组织统筹机制、利益共融的规范化收益分配机制与共治驱动的多元主体行动共治运行机制。值得注意的是,镇村级组织往往成为“共富工坊”合作网络构建的核心行动者并在整个“共富工坊”参与主体之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是动态的,受到国家经济形势、制度变迁与各方参与主体之间分化程度的高度影响,并对“共富工坊”“转译”带来了较大影响。为此,“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建设与发展应聚合吸纳多元主体以增强合作网络资源交流,以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激发网络行动者的“转译”动力,以完善共建共享共富机制增强合作网络的稳定性。
关 键 词:“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共富共同体;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4)11-0116-13
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如何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是学界与实务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过程中,“共富工坊”①应需而生,在降低企业用工用地成本,解决留守老人、妇女、残疾人和低收入农户群体就业困难等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一批典型经验》,“共富工坊”列在首位。尽管“共富工坊”的典型经验复制推广的意义重大,但要在实践运行中发挥最大功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合作网络与实现机制的建构。“共富工坊”有多种类型②,其建构的主体也各不相同,不但涉及政府、企业、村级组织、合作社、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种养殖大户及普通群众等各类组织与个人,而且也涉及农村闲置土地房屋、车间厂房、乡村民宿、景点景区等。[1]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好三个问题:各方主体加入“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动机是什么?合作网络中的各个主体利益诉求如何回应?“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高效运行需要怎样的机制?基于此,笔者试图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微观视角对浙江S村“共富工坊”如何构建联结各方主体与资源的合作网络进行分析,探究其发展规律与运行机理,进而论述“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建构的实现机制,从而为浙江乃至全国开展“共富工坊”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参考。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共富工坊”参与主体互动均衡样态的理论分析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诠释
行动者网络理论最早见诸于1986年法国科学哲学家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发表的《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后经法国社会学家约翰·劳(John Law)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进行继承与发展,行动者网络理论趋于完善。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Actor或Actant)、转译(Translation)与网络(Network)是三个核心概念。[2]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组织、个人等)与非行动者(市场、政策、技术、观念等),两者在网络中平等且利益相互关联。[3]转译是行动者构建网络的路径和过程,也是整个理论的核心。为确保转译的针对性和高效性,核心行动者需要被明确,一方面需要核心行动者接收并表达出其他行动者的问题与利益,另一方面核心行动者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手段将不同行动者的问题与诉求处理成为行动者共同的东西,成为不同主体实现目标的强制通行点(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见图1),进而推进行动者网络不断变化发展,同时各方着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伴之前进。
作为行动者网络的核心,米歇尔·卡龙对转译的步骤进行了论述,其包涵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Profit sharing)、征召(Enrollment)、动员(Mobilization)四个环节。[4]问题呈现是指在该阶段核心行动者提出某个问题或议题,将其作为行动者实现各自目标所必须经过的点;利益赋予是核心行动者为解决或明确各行动者的利益与路径而采取的手段;征召是其他行动者基于利益赋予而成为行动者联盟成员;动员是核心行动者通过对其他行动者进行职责确定并分配相应的任务,通过各种策略来达成共同合作。[5]至此,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完成一个网络的构建。当然在网络形成并运行中,行动者对某些关键问题产生认同与行动上的差异将会影响网络稳定性,这就是异议,也是转译过程的重要概念。[6]
(二)分析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共富工坊”参与主体互动均衡样态分析
显然,行动者网络理论核心关注点在于转译中异质行动者互相展开行动协作和利益博弈,进而发现网络结构的动因和机制。[7]“共富工坊”主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企业拥有资金优势与市场实力,但在城市用工用地困难且成本较高,尤其是临时性、季节性用工更难。二是农村闲置着大量的土地、房屋、山林等资源,同时农村富余劳动力或低收入群体面临着临时就业渠道短缺、议价能力不足、报酬兑现无法保障等难题。从中不难看出,双方在资源要素上具有互补需求,在利益追求上具有共同的目标,同样也存在着可能被对方侵害利益的风险。在这样的状态下,急需一个核心行动者来完成对双方问题与利益目标的表达转换,同时通过对双方资源的联通与运用,消除双方的问题和风险。镇村级组织①作为实体化载体,不但能充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价值,而且也能够体现人民群众需求,能够推进农村资源的整合利用与促进“集体行为”②。可见,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共富工坊”如何构建各方主体共赢路径与实践机制提供了理论启示。
⒈合作网络结构的基础:异质行动主体共同参与。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网络构建非单个个体能够完成,必然涉及多方主体的参与和互动,并且包含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前者包含组织、个人等,后者包含市场、政策、技术、观念等。“共富工坊”各方主体与行动者在主体结构上相契合。一是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在“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关系中,村级组织、企业、农户都是平等的行动主体,不存在支配者或绝对控制。在“共富工坊”合作主体中,企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一般具备优势资金与市场实力,村级组织、低收入群体、农村富余劳动力一般具备廉价的土地资源要素或劳动力要素,双方可相互达成优势互补,能够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二是参与主体利益相关性。行动者网络强制通行点的形成是基于行动者最后达成利益追求的共同性。在“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建构过程中,双方基于各自要素资源优势,通过合作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企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主体依赖于村级组织富余劳动力、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廉价土地或劳动力,而村级组织、富余劳动力、低收入群体则依赖于企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提供的资金与市场实力,通过合作网络来实现双方利益的相互依存与共融。三是参与主体有序性。在“共富工坊”建设与发展中,无论“共富工坊”参与主体彼此达成的直接合作,还是通过镇村级组织等中间组织形成的间接合作,都是具有一定的生产分配规则,其目的在于维护并促进双方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些规则可表现为多种形式,既可以是书面协议,也可以是口头约定或非正式的信誉担保,其最终目的在于确保双方行为与权责具有依据性。
⒉合作网络结构的重要动力:镇村级组织的引领。从宏观角度来看,“共富工坊”参与主体的互动关系可以看作是外部资源与农村资源之间的交换过程。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必须需要“转译”,需要一个中介者来完成双方协调合作。镇村级组织作为“共富工坊”的重要中介组织,内生于本地且具有较强的政治权威性资源,不但拥有与其他各参与主体博弈的资源与能力,而且也可动员与组织其他参与主体,可以成为“转译”中的核心行动者。镇村级组织通过“转译”,联结企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人类行动者与市场、政策、技术、观念等非人类行动者,形成互相协作相互影响的动态行动者网络。可见,镇村级组织引领合作网络建构的过程将极大地避免或消除各方参与主体可能发生的恶性竞争或利益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合作共赢。
⒊建构利益共同体: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转译”。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转译”是整个网络形成的关键,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将行动者不同事务转换成共性事务。也就是说,镇村级组织作为“共富工坊”网络构建的核心行动者在整个“共富工坊”参与主体之间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实现各方主体间的信息传导。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镇村级组织在各个参与行动主体之间所形成的信任与认可规则,最终指向是达到各方之间的共融与互生,进而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户等人类行动者与市场、政策、技术、观念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共富工坊”合作网络,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二、案例呈现:浙江省S村“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建构
S村是浙江省临海市江南街道辖下的行政村,位于江南街道最南端,村域面积5.58平方公里,村民326户,总人口1008人。①之所以将S村“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建构作为案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S村“共富工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S村“共富工坊”是台州市级示范“共富工坊”,目前运行效果较好。②S村“共富工坊”不但集多种类型“共富工坊”于一体,而且也与其他共富共同体合作叠加,具体涉及街道内外多个主体,包括镇村级组织、企业、村民(富裕劳动者或低收入群体)、合作社及金融机构、强村公司、新型经营主体等相关主体,整个网络有序高效,具有很强的样本价值。二是S村“共富工坊”的案例资料获取性较强。笔者所在的团队于2023年9月对S村“共富工坊”进行了田园调研,选取镇政府工作人员、“共富工坊”负责人、合伙人、村干部、村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主体进行深度访谈,同时也从本地政府部门的文本资料与网络新闻媒体等渠道获取相应的信息,形成信息数据相互印证,进一步确保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为此,笔者将基于田园调查与案例数据资料,呈现S村“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建构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总结其运行机理。
(一)问题的呈现:确定合作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在问题呈现阶段,镇村级党组织凭借自身政治身份与资源优势获得自己作为网络的核心行动者,进而将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加以确认并使其成为其他行动者的共性问题,并引导吸纳更多的行动者加入其中,促使各个主体行动者在实现各自利益与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强制通行点(见图2)。
在S村“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构建中,涉及多个行动主体,每个行动者都存在不同的问题或困境,主要有:⑴镇村级组织。其主要面临着如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尤其是如何有效地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或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与收入提升问题。⑵各类企业。企业城市用工用地难且成本较高,在农村则面临用工用地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更高成本。⑶村中富余劳动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多为一些农村的老人、妇女、残疾人、农村学生,其中也包含着较多的低收入群体。富余劳动力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因自身的各种原因而无法离村就业,平日的收入低且收入渠道有限,急需工作来提高工资性收入。⑷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规模小,农产品销售渠道少,经常被压价而获得低利润,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⑸种养殖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问题比较相似,农产品销售渠道有限,无法获得好价格,抗风险能力弱。⑹政府各部门。包括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政府部门,面临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缺乏抓手平台、扶助资金无法提高绩效性、如何更好地服务“三农”缺乏有效路径等问题。⑺金融机构。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服务“三农”能力不强、渠道有限、业务品种比较单一,这是金融机构加入“共富工坊”的重要原因。⑻快递公司。近年来我国的快递行业发展迅速且竞争激烈,面临市场拓展慢,业务易下滑不稳定、价格恶性竞争、服务质量不稳定等问题。⑼强村公司①。拥有的农村土地、房屋、山林闲置资源较多,缺乏稳定可靠的合作对象,提高村民收入缺乏途径。[8]⑽浙江农科院。投入生产一线的机械设备产品、服务的使用情况不明,缺乏信息有效沟通渠道,顾客需求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与服务易滞后。
(二)利益赋予:行动者的利益呈现
利益赋予是集聚与稳定其他行动者的“策略”与手段,旨在让行动者相信加入行动者网络经过强制通行点可满足自身的需求与实现自身的利益,进而为整个行动者网络提供动力支持。[9]在S村“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建构中,利益赋予是国家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政策方针、发展规划与决策以及各类资源赋予核心行动者的镇村级组织,将S村“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建设与发展交予所有的行动者。
在S村的“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中,异质行动者都可预期自己的利益:⑴镇村级组织。通过合作网络的有效运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推进,有效破解“三农”问题,扩“中”提“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⑵各类企业。依靠自身的资金优势与市场实力,通过合作网络来解决用工用地难,尤其是临时用工难以解决的问题,获取更大利润。⑶村中富余劳动力者。其被赋予的利益是将自身富余的劳动力通过就业工作转换成现金收入,提高收入水平。⑷农民专业合作社。其被赋予的利益是获得更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及时掌握市场信息以调整生产种植,降低成本与风险。⑸种养殖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似,其被赋予的利益是获得较好的售出价格,及时获得市场信息与生产信息,降低生产成本和风险。⑹政府各部门。其被赋予的利益是找到工作路径,主动履职与服务,有效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⑺金融机构。其被赋予的利益是业务品种创新,优化信贷结构,拓展服务“三农”与共同富裕的职能。⑻快递公司。拓展业务并提高总收益,稳定合作关系,避免陷入价格战,不断提高快递服务质量,提高品牌影响力。⑼强村公司。将农村土地、房屋、山林闲置资源变现,获取稳定可靠的合作渠道,提高村民收入。⑽浙江农科院。一线实地观察,比较相关机械产品与服务的使用情况、反馈意见及数据的收集,获取改进与优化产品性能的一线数据。
(三)征召:行动者的加入
征召是“共富工坊”合作网络构建中的重要环节。具体到S村“共富工坊”合作网络,是指作为核心行动者的镇村级组织通过利益赋予并由其他行动者参与主体接受后,运用多种的征召策略与措施来促进其他参与主体加入S村“共富工坊”的建设发展,同时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角色与相应的任务。经过这个阶段,S村“共富工坊”各方参与主体的自身利益与合作网络的成效之间产生了紧密联系。
在“共富工坊”合作网络构建中,上级政府通过战略指引与制度供给来完成对地方政府与各行动者主体的征召。如临海市党委政府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和《关于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共富工坊”建设的指导意见》(浙组通〔2022〕32号),加快推进“共富工坊”2.0建设,先后制定出台了《临海市“共富工坊”建设实施方案》《基层党组织引领“共富工坊”建设指引手册》(以下简称《指引手册》)、《临海市“共富工坊”扶助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扶助办法》),用以指导“共富工坊”建设与发展,尤其是进一步推进了全市不同类型“共富工坊”的建设与S村“共富工坊”的建设。同时,市发改、经信、财政、商务、市场监管等有关单位、镇级党委政府、村“两委”响应政府号召,制定出一系列扶助政策与措施,促进各行动者主体认可并接受核心行动者的利益赋予与路径安排,从而成为联盟成员。比如,当地物流企业响应市场征召,与S村“共富工坊”商谈,为“共富工坊”提供快递服务优惠至5~8折,物流费率平均降低30%,每年可节约500万元左右;再如,当地镇级党委政府响应征召而设立镇级“共富工坊”服务中心,主要由街道工办、应急办、金融、群团等镇级部门组成,常态化服务保障“共富工坊”的运行与参与主体的权益。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各行动者主体间也进行相互征召。比如,当地街道党委政府接受企业的征召,按照“共富工坊”参与企业或其他主体对“共富工坊”的合作要求,全面整合辖区内的村级经济合作社,形成镇级经联社(镇级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盘活各村闲置土地、房屋、山林等资源,从而为“共富工坊”相关主体提供支持保障。
(四)动员:共富联盟的最终形成
在这个阶段,核心行动者最大的任务是将所有行动者联合组织起来,使其自身拥有的资源优势与所处的角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构建整个行动者网络中形成稳定高效的利益联盟。[10]具体到“共富工坊”合作网络构建中,作为该核心行动者的镇村级组织已成为整个合作网络联盟的代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对其他“共富工坊”参与主体的管理权,对于整个“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的高效稳定、持续运行负有责任和义务。
在S村“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构建过程中,首先,S村村“两委”主动争取街道党委政府的行政支持。为进一步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与农业资源优势,扩大就业范围,S村向镇党委政府申报“最美时光in上江”共富工坊建设项目,当时街道办事处正在大力推进“江南·溪望谷”农旅融合项目,接到申请后,经实地调查研究决定,将“最美时光in上江”共富工坊作为“江南·溪望谷”旅游专线的重要节点。为此,在整个“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建设中,街道党委政府成为坚定支持者,继而镇村两级组织共同发力,“最美时光in上江”共富工坊实现了快速建设与发展。
其次,镇村级组织动员市场力量开展数字共富赋能。镇村级组织对接市社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市社发集团)关于“共富工坊”的数字化需求,市社发集团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市场主体信息库、“共富工坊”经纪人等为主体内容,构建“共富工坊”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在数字智管过程中,重点在“共富工坊”的参与主体需求、资金情况、订单情况、安全生产监控、问题反馈以及“共富工坊”评级、政策补贴等方面进行数据化,解决“共富工坊”合作网络运行中出现的企业、农户及其他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
最后,镇村两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动员作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考核方式来完成对下级党组织的动员。比如,临海市相继制定出台了《指引手册》《扶助办法》等文件,S村“共富工坊”所在的镇村党组织以此为依据促进基层党组织推进“共富工坊”的建设与发展。另一种是以党建引领方式来完成对参与主体的动员。比如,街道电子商务协会党支部充分利用电商直播资源,结合本地的实际需求,聘请专业直播导师入住“共富工坊”,联合MCN机构创设“陪跑培训室”“共享直播间”,最终形成“共富工坊”电商直播间20个,创立本土电商品牌34家,动员返乡人员从事电商100余人。2023年,线上销售额达3000余万元,有力推进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与品牌建设,直接或间接带富农户5000余人。
三、何以可能:“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建构的实现机制
(一)政治赋能:主动作为的村级组织统筹机制
村级组织是我国最基层的力量,服务“三农”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其重要的职责与使命。[11]村级组织生长于本地,不但拥有国家赋予的以集体土地资产为核心的经济资源,而且还拥有村民认可的具有权威性的政治治理资源,以及包含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与村民自治为内核的制度性资源优势,共同形成了村级组织统筹作用得以发挥的充分条件。[12]
首先,党组织发挥战略部署作用,引领“共富工坊”发展。一是村级党组织统筹规划“共富工坊”的整体发展目标,具体运营与具体环节则由“共富工坊”负责人处理,实行原则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最终确保“共富工坊”的宏观发展方向不走偏,共同富裕有保障。二是基层党组织统筹工作机制。构建镇级党委、村党组织与“共富工坊”党小组三级联动工作机制,统筹生产联动、工作联商与活动联办,从而推进“共富工坊”市场主体和党建资源的互嵌与共融。三是统筹安排指导帮扶机制。统筹安排“三级包联”帮扶机制,即每家“共富工坊”统筹配置“一名镇(街)领导+一名驻村干部+一名村社干部”,统筹安排农村第一书记、“三师”助企员、科技特派员等,形成服务“共富工坊”的力量。
其次,村集体运用好制度统筹优势,稳定农村资源开发。“共富工坊”的着眼点在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村资源如何使用都会带来相关制度的变革变迁,而制度变迁都将产生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13]为防止“共富工坊”发展过程中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等问题,镇村级组织运用好区内农村资源与制度统筹是相当重要的。一是组建强村公司统筹对接全域农村资源。“牵线搭桥”各村社,促进低效用土地的整合与农村闲置房屋、土地、山林的盘活。二是统筹全域“共富工坊”的点位布局与差异化发展。重点是立足于所在村的产业、土地、用工等实际,统筹对接企业要求与村社资源,避免各地“共富工坊”的无序竞争,以及促进以“坊”带“线”、以“线”带“片”的“共富工坊”示范片区建设。三是村级组织统筹本村土地资源整合。要充分利用制度统筹功能,积极推进本村土地流转,尤其是结合村民对于土地的不同需求,以土地置换方式及政策来保护村民权益,从而实现本村土地资源的整合,为本村或区域内的“共富工坊”建设准备土地资源要素。
(二)利益共融:规范化的收益分配机制
在“共富工坊”的发展过程中,“共富工坊”的负责人与经纪人往往会为快速扩大“共富工坊”规模、提高自身收益而采取提高场地租费、土地价格、服务费或者增收其他名目的费用,或者相关参与主体因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反复进出合作网络,这对于“共富工坊”合作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来说是不利的。究其原因,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则体系,而核心行动者的镇村级组织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有两种路径:
一方面,构建“共富工坊”行动者的利益共融收益分配模式。例如,S村“共富工坊”设置利润分配的标准线为400万订单,若超过这个订单额的,超出部分所获得利润的50%奖励给“共富工坊”职业经理人,超出部分所获利润的30%作为分红分配给村委会,超出部分所获利润的20%作为风险基金进行提存。“共富工坊”风险基金的提存,主要是用于“共富工坊”的全年经费或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意外事件所带来的支出,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稳定性与持久性。
另一方面,构建“私域利益”与“公域利益”融为一体的收益分配机制。[14]一是通过场地建设、资金贷款、税收优惠、保险保障等方面的支持来增加“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稳定性,并保障各方参与主体实现各自利益和目标的基础性条件。二是各参与主体凭借自己的资源带入经过“转译”而实现自身的利益。显然,要通过不断强化“共富工坊”合作网络高效运行来深化两者的融合,增加两者各自效益的产出,尽管不同类型的“共富工坊”的融合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以两者相融合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机制是一致的。
(三)共治驱动:多元主体的行动共治运行机制
“共富工坊”的各方主体是因各自利益与目标而构建,“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稳定与高效运行离不开各方参与主体在行动上的协调共治。
首先,形塑“共富工坊”的合作模式。在乡村振兴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基层党组织不但在整合协调各方资源与统筹实施行动方案等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而且要引导与推动镇村级组织向上级政府部门争取财政、税收、政策优惠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基层党组织也要有效沟通市场主体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共建“共富工坊”并形成共富共同体。镇村(社区)或相关主体在制定好“共富工坊”建设发展方案以后,通过利益共融的收益分配机制来选聘“共富工坊”管理人员,或者“共富工坊”核心行动者作为工坊的负责人来协调开发“共富工坊”。
其次,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统合作用。基层党组织不但具备政治功能,而且也拥有组织功能。通过“共富工坊”建设,充分落实党组织总揽全局与协调各方的作用。基层党组织利用政治资源倾斜、党员带头示范、情感感召动员、利益联结等方式促进村社内外各方主体积极参与“共富工坊”建设发展的价值共识,结对共同推进“共富工坊”行动共治的实践,吸纳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协作,打造并形成情感与利益双层属性的共富共同体,将党组织、企业、农户等主体紧密连接,形成合力,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统合协调作用发挥得更好。
最后,构建行动共治共富机制。“共富工坊”合作网络构建是一项涉及多方主体的系统性工程。如果仅仅以镇村级组织或政府部门来包揽承担整个建设与发展,“共富工坊”的共富能力将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其生命力也将无法持续。在“共富工坊”的合作过程中,党建引领凝聚乡村共富共同体共识,发挥镇村级组织的政治统筹、制度统筹功能,转变镇村级政治资源为共富治理效能,沟通导入市场力量共建“共富工坊”场域。要利用镇村级组织掌握的各类资源优势引导和动员其他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富,进而激发“共富工坊”多方主体的协同治理效应,构建出党建引领村社、企业、村民及各类组织、个人共同参与的“共富工坊”共治共富机制。
四、结论与启示
笔者基于对S村的田园调查,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构建及实现机制,尤其是在“共富工坊”各方主体进行转译的具体过程中,归纳总结出“共富工坊”建设与发展的三大基础机制,即主动作为的村级组织统筹机制、规范化的收益分配机制与多元主体的行动共治运行机制。在这三大基础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共富工坊”建设与发展的稳定性与高效性得以保持,进而有效促进乡村振兴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S村“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建构的案例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开展“共富工坊”或乡村共富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参考与借鉴。然而,“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是动态的,也会受到国家经济形势、制度变迁与各方参与主体之间分化程度的影响,并对“共富工坊”“转译”带来较大影响。为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一是聚合吸纳多元主体,增强合作网络资源交流。“共富工坊”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它的类型是多元的,在实践中已呈现出一个“共富工坊”中包含多种类型和模式或叠加多个共富共同体,这意味着“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需要更多的资源导入,方能维持“共富工坊”的稳定性与高效性。为此,除镇村级组织、企业、村民等基本的参与主体之外,核心行动者还应重点将返乡大学生、新乡贤等群体,以及其他农村中介组织吸纳引入“共富工坊”合作网络,从而更加有效激活“共富工坊”的内生动力,促进相关主体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有效交换和配置,促进乡村内外资源助力于“共富工坊”的融合发展。
二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激发网络行动者的“转译”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不是简单的一产‘接二连三’,关键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要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15]“共富工坊”合作网络的核心行动者应时刻关注其他行动者因其异质性所带来的利益需求与主体角色的变化,要时刻关注“共富工坊”发展中的实际情况,要严格遵守所有合作网络参与主体平等性原则,通过有效沟通协调并适当调整合作网络“转译”中的强制通行点,进而实现利益联结机制在模式上的创新,满足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与目标诉求,保障合作网络的稳定与高效运行。
三是完善共建共享共富机制,进入“共富工坊”发展新阶段。镇村级组织在“共富工坊”合作网络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要不断促进合作网络主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意识,依托利益联结机制,逐步建立持久稳定的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要充分认识并利用好“共富工坊”带来的资金、人才与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建立健全资源共享机制,不断完善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促进生产活动与农村社会生活相融合,逐渐形成村民的社会文化共识与身份认同,不断提升农民归属感与幸福感,真正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台州市共富工坊建设管理规定[N].台州日报,2023-12-06(06).
[2][9]Callon M.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6:19-34.
[3][7](法)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M].刘文旋,郑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89,185.
[4]Latour B,Sheridan A,Law J.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23.
[5]Hardy C A,Williams S P.E-government Policy and Practice: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Public E-procurement[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08,(25):155-180.
[6]Walder A G.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5,101(2):291.
[8]周爱飞,杨晓丽,叶芳,等.山区县域强村公司:从消薄消困到共创共富的重要力量[J].浙江经济,2022(3):56-57.
[10](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7.
[11]顾昕.共同富裕的社会治理之道——一个初步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23(1):45-67+227.
[12]高海,朱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特别性与规则完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8-68.
[13]郭晓鸣,张耀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领域拓展及动能强化[J].经济纵横,2022(4):87-95.
[14](德)克劳斯·施瓦布,(比)彼得·万哈姆.利益相关者[M].思齐,李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156.
[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00.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Cooperation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of S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
Xu Bobo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is a creative meas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Currently, in the re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typical experiences in the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there is a problem that how to achieve maximum effec-
tiveness in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the biggest difficulty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 This case study is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in S village,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equilibrium pattern of participa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by using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summarizes the three basic mechanism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namely the village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empowered by politics, the standardized pro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for interest integration, and the multi subject action and governance operation mechanism driven by governanc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own and village organizations often become the core 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participating subjects. However,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is dynamic and highly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among various participating entities. It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should aggregate and absorb multiple entities to enhance the exchange of cooperation network resources, innovate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 linkage to stimulate the translation motivation of network actors,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sharing, and prosperity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cooperation network; common prosperity community;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马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