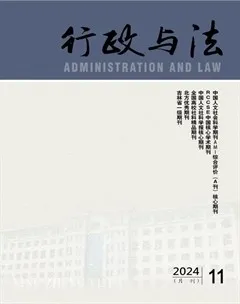新时代担当精神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探析
摘 要:担当精神是彰显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相统一的主体性精神,其作为人的本体逻辑规定,首要本质是蕴含实践导向的主动性精神,这种主动精神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存在、社会关系以及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统一。担当精神作为主体对自身存在的本体论觉解,为时代新人对公共生活的主动参与、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和民族使命的主动担当建立起“知行合一”的思想动力与价值旨趣。而且,担当精神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作为历史主动精神的底蕴特质为时代新人勇担历史重任提供了内生动力与实践指引。担当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这种蕴含主动性的实践精神不仅是历史主动精神一以贯之的底蕴标识与精髓特质,更是时代新人自觉投身民族复兴征程、推动历史性变革的精神基点。探赜新时代担当精神的内在机理,不仅能够实现对时代新人践行历史主动精神的规律性引导,更能推动时代新人本身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和具体实践中焕发敢于担当的勇气、磨练善于担当的志气、涵养甘于担当的骨气、熔铸乐于担当的底气,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注魂立心。
关 键 词:担当精神;思想淬炼;生活历练;实践煅造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4)11-0027-12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1]这一重要论述精准概括出担当精神的根本特质是“迎难而上、挺身而出”,不仅彰明了担当精神内含高度自觉的意志主动性,更将这种主动性呈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揭示担当精神的内在机理,关键在于探赜担当精神的内涵实质与生成机理,挖掘其更高远的内在超越性力量;在于将担当精神本身“当作实践去理解”[2],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挖掘其葆有的历史性、主动性、创造性。唯有如此,方能指引时代新人把握历史主动、牢铸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现实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构建。
一、担当精神的内涵实质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3]担当精神作为驱动人自由自觉建设精神文明家园的主动性精神,绝不是抽象思维在观念世界的逻辑演绎,而是具有根植广阔实践天地且反映人之本质、关系及其现实生活过程现实规定性在精神上的形态彰显。这一主动性现实性精神形态在唤醒自我意识的基础上,自觉将个体维度与社会维度连缀贯通起来,而后当代实践中获得了思想精神的现实性力量。
(一)担当精神是彰显主体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
人的存在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主体性过程。主体在从无到有的意义追寻中不断获得将自身的存在担当起来的主体性力量,在自觉担当中通达生命的终极意义。担当精神作为反思自身存在状态、追求生活意义的主体性精神,它的塑造过程不仅仅是单个主体的自我形塑,同时也是无数个体汇聚融合而成的历史合力对时代精神的意义塑造过程。时代精神是一种普遍的关于生活意义的自我意识,是关于自身情感、意志、理想的“自我意识”。[4]因此,作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精神必然要在主体的情感、意志以及追寻自身价值这三重逻辑的反思中,以主动性合力提振时代新人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
从反思自身情感的逻辑来看,担当精神是主体从无到有的意义追寻,是唤醒人的主体性存在的精神基点。人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现下的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前提,而过度依赖必然导致主体的异化存在,甚至是主体性的自我消解。马克思认为:“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5]主体对客体的意识过程,本身就是主体对自身本质的复归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主体的自我意识才能以对象化的形式为主体自身进行现实确证。现代人的意识、情感,甚至包括他们的思维本身,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异化控制。为此,从对象化关系即从“他者思维”的视角来看,担当精神能够以其内在的主动性力量克服那些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相适应的消极的、利己的意识蒙昧,并且自觉上升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的质的规定性,进而在文明的跃升中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与复归。在此意义上说,重新唤醒主体的担当精神本身就是对主体的自我唤醒。正因如此,担当精神才能作为主体克服资本主义物化统治的关键性力量,进而为时代新人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变革提供不竭动力。
从反思自身意志的逻辑来看,担当精神是主体超越自然属性的意义获得,是人积极占有自身本质的精神确证。黑格尔认为,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意识到自我存在也意味着自己为他人存在的维度。[6]担当精神绝不是自然属性意义上仅仅代表“物的尺度”的精神状态,而是主体以“人的尺度”在自由自觉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实现的意义获得。这种意义获得一方面以公共性为伦理规范,将主体的自我实现建立在公共关系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它又为主体的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客体视角和边界意识。因此,担当精神本身就蕴含主体与客体、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性维度,并且为主体担当精神的真正实现提供可能。
从追寻自身存在与价值的逻辑来看,担当精神是人类面向历史的意义主动,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彰显个体存在意义的精神追求。现代社会挣脱了神学的牢笼,将人的主体向度归还于人本身,然而它在揭开宗教信仰的神秘面纱之时也为现代人的虚无主义困境种下了无垠之根,失去了宗教庇护的现代人因信仰无处皈依而沉沦在无根的狂欢中。肆意的狂欢后是堕入“信仰危机”“意义失落”的存在主义焦虑的空虚状态,人们面向对死亡、绝对自由、孤独与无意义感的无力抵抗的恐惧,只能以消极的处世态度规避现代性风险、保障本己性安全,主体性的复归方兴未艾又再度丧失。从重建主体性的逻辑上讲,担当精神正是避免现代人陷入主观消极情绪、自觉面向历史主动的密匙。人在担当中重新找回存在的意义、找回迷失的信仰,从而消解“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无意义感,对主体存在实现新的超越。在此意义上说,担当精神的生成过程是个体重拾主体性、走向自由的过程,是通达个体对存在意义与生命价值的可能寻向和精神追求,是自觉将个体意义追寻与人类自由解放的历史趋势联结一致的意义主动。
(二)担当精神是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相统一的德性伦理精神
人在将主体内在的自我意识外化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德性伦理的维度来对精神本身加以规范。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曾就人的存在与道德的关系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存在的外在性是道德自身”[7]。如果说道德价值是人之存在的外在性显现,那么担当精神的外化过程就是个体在传扬民族道德与美德中获得社会价值的过程。这一逻辑结论中内在蕴含着双重意蕴。
一方面,担当精神是主体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至善的规范伦理精神。人的主体性是在承担客体性责任中彰显的,主体在其中存有某种责任伦理境遇。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同盟基础上的团结是一种社会联系,它把所有人都组织了起来:每个人都要对其他人负责。”[8]主体生活不是离群索居的单人生活,而是与人现实地产生联系的社会化生活。因此,主体对生活方式、生活意义的追问必然要从求真的向度延伸为至善向度。就其根本而言,追求精神在旨趣上的至善需要“保证同主体间共有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当中的生活历史发生关联”[9]。以此观之,追寻至善的主体必然要将担当共同道德观念视为获得社会价值的伦理方式,实现“个体主体—他者主体”的思维转向,在担当社会责任、恪守民族道德中切近至善境界。另一方面,担当精神是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美德伦理精神。冯友兰曾将自觉到人的主体性存在并努力将“小我”融入“大我”概括为美德之高阶境界。担当是主体在普遍一致的价值共识中获得称赞认同的过程,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10]担当精神相较于履行义务的被动性客观责任而言展现了强烈的主动性色彩,是在规范伦理原则的基础上自觉将“涉己”与“涉他”的品德联结起来并加以平衡的伦理精神。在民族共同体中,主体以确定性的价值共识为美德追求,在“自我-他人”的关系平衡中实现小我与大我的共生,在传承民族美德中为延续民族生命而笃行伦理担当,在个人生命与民族生命的统一中敞开个体的社会性价值意蕴。简言之,个体基于自我发展的愿望将承袭民族道德与美德传统作为获取社会性价值的途径,于是民族生命以个体对真善美的民族伦理精神恪守传扬为纽带,与个体生命紧密维系起来。在此意义上说,担当精神作为内含主动性的伦理精神实现了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的统一。
(三)担当精神是为时代发展提供内生动力的实践精神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1]当今中国的一切伟大实践都凝练在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中,担当精神只有扎根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才能获得时代的具体的规定性,获得区别于一般精神的强大实践导向和力量源泉。
首先,担当精神内在透溢的奉献意识为投身伟大实践提供了思想自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12]这需要秉承担当精神自觉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笃行奉献。当今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进拓深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也是中国力量在世界文明格局的交错变化中挺膺担当的时代。无论是面向世界格局深层变革的百年未有之变局,还是走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都迫切需要担当精神来为人提供精神力量和实践力量的支撑。基于此,新时代新征程的担当精神一方面要强调个人要勇于担当责任,从兼顾他人到无私奉献,最后上升至舍己为公的高尚境界,自觉将个人利益融入民族利益中,以自觉奉献促身体力行;另一方面还要拓宽世界性的视野眼光,将个人、民族、国家的存在嵌入世界历史格局中,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中确证个人与国家相连缀的担当精神。其次,担当精神精准阐扬的责任意识为接续历史使命提供意志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景光明辽阔,但前路不会平坦。我们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13]随着社会改革进入纵深化,新时代的中国会遭遇更大阻力,在艰难困苦面前,唯有以挺膺担当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实践汇注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才能功不唐捐、玉汝于成,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铸入实践的动力源泉。以此观之,挺立担当精神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伟大实践精神的时代性、实践性、主体性力量,应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匹夫精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攻坚精神、“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实干精神融合贯注于新时代担当精神的体系中,自觉挺立担当历史使命的责任意识。再次,担当精神蕴含的敢为人先的创新思维为弘扬中华文化存续信心之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4]担当精神不是在各个时代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连续性并且能够在不同时代的传承赓续中焕发生机与生命力的精神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底蕴深厚、内涵隽永的魂脉为内在支撑,既为担当精神的连续性发展厚植了文化滋养,又在新时代新征程为担当精神丰富了新的时代内涵。正因如此,确立敢为人先的创新思维在当今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这份坚毅担当的勇气为推陈出新注入信心,以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且屹立永驻,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永续发展存续信心与勇气。最后,担当精神象征指涉的人类情怀为敞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世界图景提供价值归依。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全人类的未来前途,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呼吁各国摒弃丛林法则的传统思维,用互利互惠取代零和博弈、以合作共赢消弭霸权扩张。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入到世界文明层级深刻演变的人类历史格局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构想,为全人类文明发展和文明跃升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智慧和突出的原创性贡献。[15]这些举措反复确证着弘扬着“大道不孤,命运与共”的道义担当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敞开世界图景、指引高远的前途命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价值归依与思想自觉。
二、新时代担当精神的生成机理
担当精神始源于人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追寻,在对“时代新人”的自我觉解中产生。个体自我意识蕴含着社会自我意识,在其现实性上,担当精神外化表现为主体意识的社会化,在肯认“个人梦”的公共生活向度中生发,为时代新人承担社会责任提供认识论前提。随着担当的“对象”由一般性社会责任跃升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担当精神也随之获得了更高远的历史性意义。最终,担当精神以时代生活为鲜活载体,以强大的实践导向指引时代新人在“个人梦”铸融于“中国梦”的过程中获致精神主动,从而通达知行合一的理想状态。
(一)担当精神始源于对时代新人的主体性觉解
时代新人是新时代担当精神主体具体化的形象呈现,发挥时代新人的主体性作用是体悟“个人梦”从而自觉担当“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由此,新时代 担当精神的生成逻辑始于时代新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主体性觉解。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横渠语录》)担当精神对其他一般性精神的超越性体现于高远的精神旨趣,它不仅内在指向个体自由的主体性关怀,还外在关涉了一种觉解人与人现实关系的他者向度,在精神内省外化的运动过程中彰显着丰富的对象性思维。基于此,担当精神在时代新人内省的过程中呈现出“内外互嵌”的精神张力。内省是主体参照社会现实确准内在状态,在反思中修正自身的行为。其中,担当精神既作为“外在的客观性理想图景”推动主体向内自省,又作为“内生的主体性精神动力”推动主体向外对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由此,在担当精神的动力内核中便生发出由内推与外延融通作用、相互嵌入的合力,在主体性觉解中彰显出巨大张力。时代新人通过内省的方式将社会理想图景存续内化,回落于内心世界对存在意义的精神整合,以内外互嵌的合力推动主体觉解。
担当精神在时代新人自我调整意志动机的过程中趋近理想状态。担当的初始状态是良知,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其概括为“约拿情结”,即“人在真理、正义、是非感、责任感的基础上建立起良知”[16]。担当精神从良知上升为道德意志需要时代新人审视外部环境,发挥意志的调控功能增强社会责任担当的意愿、强化对民族使命担当的情感认同。质言之,主体意志调控8cc45083de42deae0f65f5ffc29db4d3的过程就是担当精神德性意蕴的内演过程,担当精神须在其德性意蕴的敞开中切近理想状态。
担当精神在时代新人的自律担当中获得内在超越性。一方面担当精神植根于现实且需要他律向度,另一方面又能以自律之法凌空超拔,在现实的批判中锲入理想的精神境界。时代新人在他律的基础上确准社会意志,通过内省、反求诸己、批判性反思、良知与意志调控的环节内化为意愿。自律则是对先前环节的深化,表现为内化并自觉以“担当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为准则进行自我约制。时代新人的自律担当既寻得了主体性复归,又触及了自由意志的维度,彰显了担当精神在主体信仰高度的境界追寻。
(二)担当精神生发于个人对公共生活向度的肯认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认为:“个人主体是在公共生活中心的个人生活、文化和人格的问题。”[17]担当精神不同于一般精神的特殊规定性恰恰在于对象性,这似乎表明担当精神只有在人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方可彰显其内在的规定性。因此,其生成必将涵涉公共向度并且在社会生活中确证精神存在的合法性。新时代担当精神何以在公共生活向度中生发且构成意义?质言之,需要经历“主体接受—肯定—认同”三个阶段的心理整合过程。
首先,从主体认知的意义上说,时代新人接受且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生发担当精神的基础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共相文化f6c81f093683dedcd6c38f4026b27749传统判断社会公民行为是否存有道德价值的核心标准。其中公民层面的价值观提供品德支撑,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展现社会生活的理想愿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描绘国家使命的时代蓝图。内化价值观意味着认同国家所提出的道德修养与思想品格要求。其次,个体主体在与他者主体的交往中实现“共生主体间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公共性”[18],亦构成了个人生活的公共向度。“个人梦”是对意义感、幸福感与人生理想等多方面价值追求的凝练,人为了获得价值必然要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敞开公共关怀。主体的亲社会行为表明:个体必将经历社会化过程,且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作为责任主体,对其他成员和共同体需承担责任与义务。此为生发担当精神的核心阶段。最后,时代新人在确证其公共向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产生安全感与信任,由此产生了担当的意识,而意识转化为精神则需要时代新人对“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的根本认同。这其中,社会共同体蕴含的共同文化底蕴为个人提供本源性的认同资源。时代新人在析理个人梦与中国梦内在关联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从而生发对国家社会的担当精神。由此,“他的自我意识就生长起来,从而他的道德力量也随之生长起来”[19],此为担当精神生发的终极阶段。
(三)担当精神深化于责任义务向民族使命的延伸
担当精神原初是连缀个体生命与社会价值的一般主体性精神,伴随着担当精神在历史逻辑中敞开,将个人梦置于民族复兴的语境中,从民族梦、中国梦的意义上论及价值实现,其独特的历史性意蕴也随之彰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第八章·泰伯篇》)民族使命是民族意志的具体化呈现,它以民族精神为纽带支撑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同样为使命担当献身。“所有人都完全平等,拥有同一种内在精神。教育、财富或外貌或许有异,但本质与为理念献身的能力绝无分别。”[20]社会责任唯有上升至民族使命的崇高境界,才能赋予担当精神更高远的存在意义,才能连结历史、现实与未来,使一般性的责任意识深化为特殊性的民族精神。时代新人以肯认公共向度为前提,形成了将社会作为对象的责任意识。毫无疑问,每一个时代社会发展的主题都与某一国家民族正在奋斗的事业和理想息息相关。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民族复兴语境中,时代新人需要自觉将个人梦与民族梦连缀起来,将二者的高度一致性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来理解,置于我们正在奋斗的事业中来揭示,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来完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指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的使命、现实的使命、时代的使命,还贯通历史与现实将建党以来的全部实践布控入民族复兴的棋局中,使民族使命成为“共有的文化所证实的价值承诺”[22]。从文化认同到使命承诺,时代新人把原本隐而不彰的公共责任意识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烙印,建立起自身与共同体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确证了主动担当建设大任的主动性精神力量。
(四)担当精神挺立于时代新人的知行合一
精神家园的建设是个体自我意识与社会自我意识相互“认同”与“认可”的双向生成过程。[23]在此意义上说,实现担当精神的终极价值需要获得社会自我意识对个体自我意识的认可,需要通过实践将主体意识对象化、外化、现实化。随着主体精神转化为客体性精神,评价标准获得了具体的现实规定性。因此,达成社会价值理想与个人价值期待的内在统一,需要不断将主体精神切近客观标准并修正主体行为,从而获得社会意识的“认同”。然而人“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24]因此,对担当精神的解读要从实践的维度出发,以时代性的社会意识为基准,推动担当精神立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对时代新人的实践要求,为新时代挺立担当精神提供了理论遵循。这些要求具有高度的继承性和突出的连续性,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又能够立足当下中华民族发展的现代性使命切实地根据世界格局、时代主题和民族事业不断丰富、发展与完善,是一个传承赓续、推陈出新、因势而新的内在统一体。“坚持原则,不逾底线”是坚守担当精神的底线思维,时代新人在划清担当界限的同时更要明晰“应该担当什么”,在科学认知中确准担当精神的原则与底线。“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是挺立担当精神的意志标准,不仅要培养敢于担当的勇气,更要在磨砺意志中砥进担当的志气。“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是厚植担当精神的信仰情怀,时代新人要做到立场明确、忠诚担当,在坚定理想信念中铸牢勇毅担当的信仰。“注重实际,增强本领”是践行担当精神的手段支撑。[25]“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晋·傅玄《杂诗》)时代新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笃实地提升综合素养,在实践生活中历练担当的本领。除此之外,还要拓宽视野眼光,将自身的存在与全部人类历史和宏大时代紧密联系起来,在全人类自由发展的高度上挺立自身作为主体的存在根基和价值旨趣。简言之,新时代的担当精神经由主体觉解、确准社会属性、认同民族使命的内生过程,最终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将精神动力外化为实践力量,挺立担当精神在新时代的特殊性存在意义。
三、新时代培育担当精神的现实路径
揭示担当精神内在机理的价值旨归在于以生成逻辑作用于对时代新人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感意识、责任意志、民族气节、行为实践的培育逻辑。培根铸魂的教育工作应从思想淬炼、生活历练、民族精神赓续、实践锻造四个维度展开,指引时代新人在反思、内省与自律中焕发敢于担当的勇气,在获得目的性的生存方式中磨砺善于担当的志气,在民族精神的感性化浸润中涵养担当的骨气,在立足新时代新天地的实践锻造中熔铸乐于担当的底气,从而以主动性精神和实践性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推动伟大实践。
(一)在思想淬炼中焕发担当的勇气
在对担当精神的本体论追问中,勇气确证了主体存在的本性,勇气的焕发是对存在的自我肯定,是一种克服了否定的肯定。时代新人获致勇气必然要经历思想的淬炼过程,在自我反思、意志调控与自律的思想内化逻辑中克服具有否定性的消极情绪,以积极的主动性焕发敢于担当的勇气。
首先,思想淬炼需要遵循“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规律逻辑,担当精神首先应当是从现实世界中生发的对感性直观的真5af88f0c7c4460a901ec1dc705260c24bede2f587702ad6ccd7e0af0024b8434实反映。具体时代具体社会的评价标准就是担当精神发展的客观依据。时代新人应当将自我存在与社会存在统一起来并结合公共评价标准进行自我审思,即从了解世情与国情,爱祖国、爱社会、爱人民,以及使命意识、创新思维、奉献精神和拼搏精神等更为宏大开阔的视野来审思担当精神。在客观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批判,为反思提供思想前提,进而在扬弃中通达担当自明的状态,使“理想之我”与“现实之我”趋向一致。其次,个人的能动意志是促进精神从对外部世界直观映射的基础上施加主观目的、尺度、意图的内在驱动力。时代新人应当以担当意志为动力,不仅要从内生性的角度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驱动意志,同时也要坚持以外生性的时代使命不断强化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甘于担当的强大意志。要以民族复兴为历史使命增强担当的信念,基于特殊具体的目标使命来反馈在意识思想中,进而积极调控担当情感和担当意志,根据外部要求设立并调整阶段性目标使其不断趋进,以情感的主动性推动自身理想人格的完满。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的主流观念形态,既是党和国家根据当前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思想要求,又是符合人民精神发展需要和思想观念运动规律的价值引领。因此,时代新人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和价值遵循,从国家战略发展和人民精神文明需要的双重向度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成为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习,以此激发对担当精神历史与时代双重向度的使命追求,在思想境界的跃升中引致自律向度,通达担当精神的理想状态。
(二)在生活历练中磨砺担当的志气
生活世界是公共生活的世界,人们以语言等符号化方式在群体间搭建意义、凝聚认同。担当精神的合法性确证需要生活的向度,需要在以生活世界为依托进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高扬担当的现实关怀和崇高精神。因此,培育担当精神要善于运用公共生活、道德生活、日常生活等在场形式不断强化时代新人对“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认同,以认同促生担当的主动性,催生时代新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勉励他们以坚定的历史自信迎击挑战、锻造自身,从而在生活的历练中磨砺时代新人善于担当的志气。
善于担当的志气来源于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与本领自信。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拥有绵延赓续、自强不息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决定了它能否具备坚定不移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从历史与文化层面建立起来的自信是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的,越是在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中,越能够生发出自信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此观之,践行担当精神,需要时代新人自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明理增信,以深厚的学养和历史文化底蕴为理论根基,在领悟原理中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强化政治担当,从而在复杂局势中探究根本,预见事物发展大势走向,精准把脉时代症候,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获得担当之“智”。不仅如此,时代新人还需以强健体魄为力行支撑,以优雅圆融为美德情怀,以“事必躬亲”的实践态度为行为准则,勤学苦练,锻炼担当的本领,增强善于担当的本领自信,在日常向度中以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使命担当的理想信念,以善于担当之志在“攻坚克难、固本开新”的使命担当中践行人生理想。
(三)在民族精神赓续中涵养担当的骨气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一个民族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精神是整个国家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更是影响涵育这个民族的新人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重要基石。基于此,新时代培育担当精神要尤为重视历史教育,需要植根深厚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历史的本质、立场、观点、方法的揭示弘扬民族精神,进而在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中激发时代新人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这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切中担当精神符号化教育的特殊规律,将鲜活的历史事件注入感性化叙事体系,进而将“讲故事”这一感性传播形式作为构建意义、象征担当精神符号的主要手段,运用历史教育与仪式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能否创设富有感染力的叙事环境从而在感性化的氛围浸染中传扬民族精神,是“讲故事”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运用诸如沉浸式体验、3D虚拟展览、云叙事等多重科技手段,为时代新人搭建铭记历史的叙事平台,通过营造历史与现实联动的空间将身体置于内嵌式和激活式的在场状态。叙事是特殊的教学手段,教育者须在构筑环境的理路中将叙事传播过程视为整体性文化互动,进而在讲述历史故事中积极调动参与者的感官、情绪与身体,通过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的多维度深度互动激发时代新人的身体在场状态,营造出由个体、社会、时代、历史多重要素作用整合下的文化环境。在具有时空流动性的叙事传播环境中,担当精神在要素互动中获得了历史深刻性与时代先进性意蕴,从而在“讲故事”的叙事传播中被理解、浸润与传承。
(四)在实践锻造中熔铸担当的底气
归根到底,一切价值和真理都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无论是从观念论的视角去探究担当精神作为主体性精神的思辨逻辑,还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挖掘担当精神对人的关怀与效用,最终都要进入实践论的视野,在实践的广阔天地中获得精神的现实规定性。以此观之,对于精神的自我省思、价值认同、精神浸润的意识环节唯有在实践论中才能焕发思想张力,担当精神中蕴含的主动性意志亦只有历经主体实践的锻造才能外化为现实力量。
毫无疑问,社会实践是时代新人施展抱负、践履理想的根本途径。人是怎样的人,这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当今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最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时代新人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最核心最伟大的具体实践中勇毅担当,为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踔厉奋发。一切实践都要以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为根本原则,因此时代新人要始终以切实反映和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践标准,坚持心系党和人民,胸怀国之大者,勇于自我革命,立志建功立业,在切近理想见之于现实的实践图景中笃行不怠。不仅如此,时代新人还要敢于直面社会复杂多元的文化现象,将担当精神置于多重思潮激荡的思想争鸣中,在对消极社会思潮的认知与阻击中净化行为动机,避免堕入功利主义的陷阱,既要心怀“功成不必有我”的豁达坦然,又要肩任“功成必定有我”的当仁不让,乐于承责、坚守初心,堪当国之重任;要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担当、去奋斗、去绽放青春之花;去扎根基层实践,投身于支教、支农、扶贫等各种基层劳动;要在深刻的劳动实践中躬行担当,“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26],从而根本切近国情、社情、民情,在真正的现实经历中运用担当之智、焕发担当之勇、磨砺担当之志、抒发担当之情,将担当意志深刻转化为笃行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
[2][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3,18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00.
[4]孙正聿.属人的世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1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4.
[6](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1-84.
[7]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Trans.A.Lingis.Pittsburgh:Duquense University Press,1969:302.
[8][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0,28.
[1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7.
[1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2.
[13]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
[14]中共中央党校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12.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
[16](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55-60.
[17](法)阿兰·图雷纳.现代性批判[M].巴黎:Fayard出版社,1992:335.
[18]冯建军.从主体间性、他者性到公共性——兼论教育中的主体间关系[J].南京社会科学,2016(9):123-130.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9.
[20](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9.
[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
[22](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53.
[23]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0.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05.
[25]任仲文.新时代 新征程 新奋斗[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171.
[26]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42.
Analysis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Realistic Path
of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Era
Gong Yifei
Abstract: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is the subjective spirit that manifests the unity of individual life and national life.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human ontology, its primary essence is the practice-oriented initiative spirit, which realizes the internal unity of human’s subjective existence, social relations and living mode. As the subject’s ont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existence,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establishes the ideological motivation and value interest o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for the new people’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life, active commitment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tive commitment to national mission. Moreover, in the grand narrativ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as a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provide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new era to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has a clear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this practical spirit containing initiative is not only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but also the spiritual basis of the new era to consciously participate in the journe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promote historic change. An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era can not only achieve regular guidance for the new era to practice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but also promote the courage of the new era themselves in the great journe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concrete practice, hone the ambition of being good at taking responsibility, cultivate the backbone of being will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develop the confidence of being will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build the spiritual hom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tempered thought; life experience; practical calcination
(责任编辑:刘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