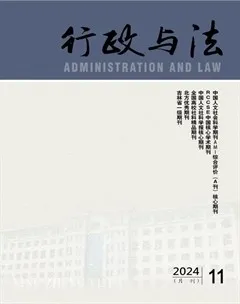社区“微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
摘 要:社区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各种新型社区应运而生。征地拆迁安置社区因其形成的特殊性,其治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创新治理机制。“微治理”通过微单元下沉细化、微服务精准设置、微管理有机结合和微诉求顺畅表达,提升了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微治理”中逐步形成。“微治理”实践的有效展开源于党政力量协同推动、治理主体多维赋权、利益关联与约束监督及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互构。当前,由于社区治理行政化突出、基层治理主体权责不匹配、治理资源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微治理”实践仍面临社区居委会能力不强、治理资源缺乏统筹、居民参与度不高等困境,需要从厘清政府和社区的治理职能、健全社区监督工作机制、完善社区工作人员激励机制、推进志愿组织规范化建设和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等方面深化社区“微治理”长效机制建设。
关 键 词:“微治理”;党建引领;多维赋权;激励机制;规范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4)11-0001-13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征地拆迁安置社区不断增多,这类社区的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一些社区的治理方式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诱发了社区内的矛盾纠纷,影响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实现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已成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社区“微治理”是近年来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成果,学界对其缘起、实践及机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赵丽江等认为,社区“微治理”是立足于居民需求,通过创新单项制度、实施单个项目的方式来实现社区善治的社区治理模式。[1]宁华宗认为,“微治理”是应对当前社会分化、群体异质化、个性发展日益突出的社会现实,最大程度地满足多元利益需求,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积极参与而建立的差异化治理和精细化治理。[2]在社区“微治理”实践与机制方面,学界的关注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侧重研究城市社区“微治理”实践与机制。尹浩以赋权为视角,认为在城市社区“微治理”中,以项目为载体的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社团的成长提供了合法性环境;以社区公益组织为载体的社区赋权,培养了社区公共精神;增能技术是使社区赋权与制度赋权具有相应全面可操作性的催化剂,使居民的参与更加有效。[3]董幼鸿、宫紫星以闵行七宝老街“微治理”为例,探讨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认为通过深化精细化管理意识,提高了多主体参与积极性,健全了精细化管理a76f7c3ff9a435f5cea4c126a65a6f98ed53b8d5a0190d68926a4d647c9de2f4机制,提升了智能化水平。[4]二是侧重研究农村社区“微治理”。余练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认为“微治理”不同于抓“中心工作”的运动式治理,也不同于抓“主要工作”的一般制度化治理,湖北省秭归县通过“幸福村落建设”,治理主体构建了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日常化的和解决细小琐碎事务的治理体系,解决了项目落地、环境整治、内部纠纷和农民组织化问题,而低成本的组织动员、组织而非个人的集体协调机制和熟人社会内部的奖惩机制是这一治理模式的重要条件。[5]郭晗潇以农居庭院美化项目的推进过程为例,研究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认为村两委通过探寻国家发展战略与村民观念的契合点,探寻具体工作方式与文化本土性的契合点,探寻工作目标与村民利益的契合点,从而达到利益均衡,实现了合作共赢。[6]三是关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微治理”。包先康认为,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介入农村社区“微问题”的解决、“微事情”的处理和“微心愿”的满足,促进农村社区“微治理”。[7]梁贤艳、江立华基于襄阳古城15个社区的调查,认为通过建立以“政策倡导机制、技术服务机制、组织培育机制、资源整合机制、能力提升机制”为内容的“治理孵化器”运行机制,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可以充当“治理孵化器”,承接政府购买的“微治理”孵化服务,从而使“微治理”运转起来。[8]总体而言,学界对“微治理”的研究时间不长,议题不广,成果不多,无论是理论探讨、实践总结还是机制分析均远远落后于丰富的实践,因此,需要对当下“微治理”的实践样态与运行机制进行更多总结、分析并提出优化路径。本文以Y市X社区的“微治理”为例,分析“微治理”的实践样态、运行机制和优化路径,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提供可参考的经验和思路。①
二、社区“微治理”的实践探索
X社区是四川省Y市的一个征地拆迁安置社区,包括3个小区,人口近8000人。社区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有社区服务(社区居委会、社区综治中心)、医疗与社会福利服务(卫生服务站、康复医院、老年公寓、日间照料中心)、文化体育服务(健身广场、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商业服务(农贸市场、星光夜市、便民跳蚤市场)及教育服务(幼儿园)等。近年来,X社区通过创新“微治理”实践,在社区服务和管理上不断提档升级,社区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微单元下沉细化
X社区成立于2008年,基础设施老化,生活环境较差,居民抱怨多。2021年上半年,在社区两委带领下,X社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整治前,社区两委进行了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对社区环境的评价、所在小区是否进行垃圾分类、小区周围的环境问题有哪些、对环境卫生整治有什么建议等。之后,社区召开会议商讨环境治理的措施和方法,通过原村民小组的微信群传达会议精神,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环境整治,并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在环境整治的同时,为社区增添了运动健身器材,修好了各小区门口的路灯和监控,社区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为巩固环境整治成果及后续管理维护,社区实施微网实格,完善了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两委管理制度。微网实格由社区网格员串联其中,成为连接楼栋居民与社区两委的桥梁。早在2018年,X社区就推行网格化治理,网格员由政府统一招聘,然后分配给社区。政府招聘的网格员,其工作职责是人口管理、数据排查和居住证发放等。X社区分配有3位网格员,分别管理3个小区,他们定期对所管辖小区进行走访,及时更新居住人口信息。由于管辖范围过大,小区内的一些细小事务,如设施损坏、旧家具乱丢、下水道堵塞等往往上报、处置不及时。为此,社区在现有网格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下沉治理单元,在楼栋设置微网格,由老党员、原小组长义务担任微网格员,并在工作上与网格员密切配合,织密了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
(二)微服务精准设置
社区治理要应对的主要是内生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微治理”有效运行的关键就在于其聚焦居民日常生活中小微型事务的治理。[9]X社区地处青城山景区,经济比较发达。由于是安置社区,除了本地居民外,社区内还有大量外地租客(成都主城来的养老人员、务工的农民工以及成都东软学院的学生),人员复杂,流通性大,社区经费紧张,导致社区内现有的公共服务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针对以上情况,X社区通过优化便民服务中心功能,成立志愿者组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丰富社区服务内容和形式。
X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是X社区2021年孵化的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社区与社会组织协商,选择本社区所需要的服务内容、服务时间和服务要求,定制服务组合套餐。“便民跳蚤市场”是其组织开展的社会服务项目之一,包括磨刀、配钥匙、修伞、缝补、修鞋和理发等,这些项目每次都能吸引大量居民积极参与,并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这些小微服务看似微不足道,却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很好地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将惠民、利民、便民的公共服务引进社区,送到居民家门口,解决了居民关心的小事,居民足不出社区便可方便快捷地享受服务。
与此同时,便民服务中心也会联手社区志愿者巡逻队给独居在家的高龄老人送温暖。截止2022年底,X社区60岁及以上老人有1748人,占社区户籍人口的21.9%;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有501人,占老年人口的28.7%。由于X社区的住房分配采用抽签方式,原来具有熟人社会性质的村小组被打乱,邻居关系薄弱,加上中年子女奔波在外挣钱养家,照顾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的老人逐渐变成难题。针对这种情况,便民服务中心和社区志愿者巡逻队定期开展上门送温暖活动,根据社区微网格员收集的老年人信息,有针对性地给老人送温暖,如定期上门聊天、节假日送米面油、组织老年人参加或观看文艺表演等。
此外,X社区还通过便民服务中心为社区的儿童提供寒暑假服务。社区通过连线搭桥当地的幼儿园,充分利用返乡大学生和社区下沉党员等资源,开展儿童唱歌跳舞、书画比赛、耕读田野等活动,丰富儿童寒暑假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长的负担。
(三)微管理有机结合
X社区居民多,结构复杂,社区内不仅安置了多个村庄的征地拆迁农民,还有许多外地购房者和租客,管理事务繁杂、难度大,需要从小事、身边事着手,将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在一起。
一方面,强化党员的先锋示范作用,引导社区居民、志愿组织共创社区美好未来。X社区根据本地实际,相继出台了社区党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的责任清单以及社区党委成员和社区党支部成员的任务清单,并在X社区的宣传栏上公示,最大程度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确保社区工作紧扣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此外,社区党委还加强对社区志愿组织的领导,激发社区志愿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督促其开展灵活多样的活动,形成区域化共创共建新格局。
另一方面,完善工作制度和学习制度,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X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置专门的公示栏,每天更新社区两委的工作日志。社区为所有工作人员安排固定的办公场所,社区两委每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社区党委书记传达学习上级文件政策,社区两委汇报社区一周的治理情况,大家一起探讨、总结这一阶段社区治理的总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畅所欲言,交流经验,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出谋划策。
此外,在社区党员带领下,社区志愿者收集社区居民的旧衣物、书籍、摆件、时钟、茶壶、洗衣机、豆浆机等闲置物品进行义卖,将义卖所得的钱一部分汇入社区的集体账户,另一部分则直接捐给社区慈善基金会,再由基金会工作人员将资金变现为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利用节假日把这些生活物质送到社区困难的居民家中。这种爱心传递活动,不仅使社区居民的闲置物品得到重新利用,拓展了社区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还加强了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的日常联系,增强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微诉求顺畅表达
需求表达是有效治理的基础。在X社区,通过搭建联动平台,居民能快速、便捷、顺畅地表达日常生活中的诉求,为社区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提供了基础。
一方面,搭建微网实格平台,便于了解居民的日常需求。X社区在三个网格下划分微网格,微网格按楼栋设立,每个微网格员管理3—4栋楼,约300人,微网格员除由15个居民组长担任外,其他由所属区域的党员或者声望较高的居民担任。微网格员属于志愿者,没有报酬。微网格员主要就楼栋内的公共事务了解居民的诉求,然后汇总给专职网格员,由专职网格员上报网格长,网格长汇总来自所有网格的居民诉求后,在社区层面开展协商,与居民一起商讨治理举措。
另一方面,运用青城山镇“码上办”网络平台,提升政府和社区回应居民诉求的及时性和精准性。“码上办”是政府和社区联合创立的线上意见征询平台,在X社区服务中心张贴组织结构框架图、“码上办”二维码以及社区两委成员名单和联系方式。社区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进入诉求与意见表达通道页面,反映社区生活中的日常问题。社区服务中心接到居民诉求后,将工作分解给工作人员及时回应,或联系政府相关部门协商处理。
三、社区“微治理”实践的运行机制
在征地拆迁安置社区,高密度的居住空间和复杂化的群体结构,不仅给基层政府和社区带来巨大的治理压力,也对社区治理过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X社区,“微治理”的实施,最初是为了弥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治理短板。由于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微治理”得以推广并将其适用范围从疫情防控扩展至社区治理各领域。目前,X社区“微治理”已从应急状态下的治理模式转变为常态化的社区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党政力量协同推动、治理主体多维赋权、利益关联与约束监督及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良性互构。
(一)党政力量协同推动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和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治理结构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典型特征。在社区治理形势复杂及治理任务日益繁重的背景下,“微治理”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党政力量的引领和推动。
首先是社区党组织引领。在“微治理”实践中,社区党组织将组织体系贯穿于治理全过程,并借由社区联合大党委-社区党委-党支部等架构对社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嵌入式覆盖,织密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X社区有党员156人,社区党委下设三个党支部,对应划分的三个大网格,在37个微网格中,绝大多数微网格员由党员担任,社区党组织通过发挥他们在微网格中的作用,将党的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成为社区“微治理”有效运行的组织基础。
其次是政府有力支持。在社区转型背景下,传统的社区治理已无法满足转型中的社区治理要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社区内各种矛盾的叠加,仅仅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能够快速有效地调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并可依据社区公共事务的紧急程度和共识强度来判断行政权力介入的程度,如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实践活动、老年人的定期体检等,它们均需要政府制定方案,提供资金和人力资源并组织落实。
(二)治理主体多维赋权
社区治理离不开居民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而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需要建立在多维赋权的基础上。赋权就是政府向社区和社会下放权力,激励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赋权包括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个人层面的赋权,是个人主动借助外在权力提升自身的技能和能力,从而不断提高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的效能感和荣誉感;组织层面的赋权,是社会组织通过权力的赋予,增强组织发展的合法性,扩大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和参与权。从个体内在增权和外部推动增权来看,个体内在增权是社区居民注重自我效能的提高和自我发展的意识觉醒;外部推动增权则通过外部力量的推动,增强社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社区赋权的关键是社区公共精神的培养和社区内不同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意识的增强。相比于传统村落,社区是一个具有明晰界限的公共场域,在某种程度上已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以S小区为例,每栋楼有8个住户,8个住户并排而住,每个住户占据一至三层楼,打开门就能接触到前后排大约20多户人家,且小区居民大多是原来同村或同组的,居民之间比较熟悉。然而,一旦涉及社区公共事务,居民往往面面相觑,闭口不谈。因此,为了培育社区公共精神,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X社区把自治权力下沉到楼栋,并通过完善社区微网实格治理结构框架图,缩短组织与居民的距离,居民的诉求能够快速上传,也能够及时得到回应;同时,居民也能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一起协商解决身边的小事。
与此同时,社区还通过技术的嵌入支撑赋权。技术赋权侧重个体行动者内生力的发展和参与意识的培育,意在挖掘社区潜在的资源,促进社区居民利益需求的自愿表达。“增能技术主要用于挖掘潜在的社区资源,促进需求群体自我分析与主动表达,使社区服务更加符合居民需求,减少制度赋权与社区赋权执行的阻力。”[10]如X社区的日常问题“码上办”,老年养老的“康养青城山”,这些二维码连同微网实格宣传海报张贴于社区各处,以便社区居民能及时反映问题。此外,镇政府同X社区和康复中心打造了“关爱之眼”。“关爱之眼”源于疫情防控,安装摄像头是为了实时了解那些在家隔离的人群,现在则是为了守护8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社区通过“关爱之眼”了解高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情况,社区网格员和老人子女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看独居老人的居家情况,防止高龄独居老人在家中遭遇跌倒、昏厥等危险状况后长时间无人发现的情况。
(三)利益关联与约束监督
利益是人类理性行动的驱动力。在X社区,居民除本地人外,还有外地租客,他们生活习惯有差异,利益诉求复杂多样,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时有发生。即使是本地居民,风俗习惯相同,共享地方性规范,也会因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与邻居产生矛盾。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利益关联度高,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就强,居民就会更加注重合作交流,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反之,利益关联度低,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存在猜疑,对社区参与持消极态度。传统的社区治理,由于社区管辖的范围较为宽泛,居民有利益诉求也只是向社区干部反映,希望社区解决。“微治理”则把治理单元下沉到楼栋,设置微网格员作为连接居民与社区两委的桥梁,通过微网格员及时收集居民的日常诉求,聚焦在微网格中解决生活中的微小事件。如小区内的噪音扰民、车辆停放,楼栋前后的空地种植蔬菜,住房改造搭建,小区内流浪狗、流浪猫管理等。在治理过程中,对于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利益关联度高,紧迫性强的诉求,通过社区和楼栋共同解决;对于利益关联度低,紧迫性不强的诉求,则通过楼栋、网格组织大家协商处理。正是在这些小微事件的治理过程中,居民的集体感和参与感增强了,“微治理”才有了扎实的社会基础。
社区日常约束与监督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居民监督。X社区利用社区居民内部“熟人关系”纽带和联结作用,让社区中有声望的人担任微网格员。在实践中,这些微网格员在严于律己、接受居民监督的同时,发挥熟人关系的纽带作用,对居民的行为进行提醒和约束。二是社区两委、物业公司、其他社会组织除受相关规定的约束外,依据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人和事进行监督。如社区两委指导、监督物业公司的小区管理,物业公司对业主不当行为的提醒,等等。正是因为不同主体在治理过程中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提供了“微治理”有效运行的机制保障。
(四)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良性互构
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脱嵌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难题。社区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协调公共利益,回应居民诉求,维护社区秩序。然而,社区治理实践中常常出现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错位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事务与自治事务交叉不清,治理目标与居民需求存在差距;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治理过程变成“干部干、群众看”[11]等。在社区“微治理”中,治理事务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普惠性强,有助于校正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的错位,使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形成良性互构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在X社区,“微治理”目标与行动实现了有机统一。一方面,“微治理”目标确定后,相关主体就组织落实,务求实效,并且随着“微治理”的深入推进,治理目标进一步细化,通过各种形式的微组织,分阶段完成“微治理”的小目标,最后汇聚成总目标。另一方面,一些热心且有公益心的积极分子,在社区组织动员下,成为社区治理中的“半正式人员”。由于他们能感同身受社区治理的微小事务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和积极性高,并且通过他们的动员与示范,吸引更多居民参与身边的治理事项,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形成了良性互构。
四、社区“微治理”实践的优化路径
“微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提升了社区治理的回应性,提高了社区治理绩效,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微治理”中逐步形成。当前,由于社区治理行政化突出、基层治理主体权责不匹配、治理资源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微治理”实践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如社区居委会能力不强、治理资源缺乏统筹、居民参与度不高等,需要从职责体系、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规范化建设和动员机制等方面深化社区“微治理”长效机制建设。
(一)厘清政府与社区的治理职责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人口密集,需求众多。按事务的性质,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可划分为排他性和非排他性。排他性的公共事务属于特定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包括房屋维修、设施维护、场所使用、收益分配等;非排他性的公共事务包括环境、卫生、治安、文化等,涉及社区居民共有的需求。由于社区中人际交往、公共生活较为频繁,居民之间的利益关联度较高。社区自治是国家对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社区居民之间自愿形成的集体选择,需要发挥居民在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上的积极作用。政府行政权与社区自治权的界线划分一直是社区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应对复杂多样的居民需求,实现社区高效有序的治理,需要合理厘清政府与社区的治理职责。
一方面,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责范围。“资源的稀缺性和能力的有限性、居民的异质性和需求的多样性、行政对自治空间可能的挤压或路径依赖,决定了城市社区微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行使力度应以居民的积极性或动力为限,即居民能够自治的则由居民自我治理,居民不能够自治和自治有难度的政府则予以不同力度的支持。”[12]在社区治理中,政府应着重提供非排他性公共服务,排他性公共服务主要由市场和社会供给。在供给非排他性公共服务中,政府需要考虑需求在居民中的紧迫程度和共识强度。需求的紧迫程度有高有低,共识强度有强有弱,政府应根据需求的紧迫程度和共识的强度来确定是否介入、如何介入及介入强度。对于需求紧迫程度高、共识强度强的公共事务,政府应及时介入、强力介入;而对于其他事务,政府主要发挥牵头和引导作用,调动社区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以形成合作治理局面。另一方面,要明确社区自治的服务内容。社区自治要回应的是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这个回应机制应该快速、便捷、高效,为此,社区自治主要应立足社区自身能力,通过挖掘社区自身资源来解决社区问题。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居民发挥主动性,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多方式的自治解决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如下水道堵塞、楼道清洁、车辆停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需政府行政权力介入,应该由社区通过自治的方式去解决。
(二)健全社区监督委员会工作机制
民主监督是基层自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社区“微治理”的有效运行,需要以健全监督机制为保障,尤其如X社区这类征地拆迁安置社区,其保留有一定的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如何发展和管理、收益如何使用和分配,是群众关心的社区重大事项,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
从实践来看,社区监督委员会还需在以下几方面完善工作机制:第一,优化运行机制。社区监督委员会是基层自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细化监督委员会的具体职责,为其履行监督职责和参与治理提供制度依据与保障;同时,明确社区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流程,包括议事规则、决策程序、信息报告和沟通机制等方面的内容,提升监督委员会的运行效率。[13]第二,重视监督过程。如对社区的资金流动、人员调整、集体决策要进行监督,保障社区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合理,做到人员调整公正,决策过程透明。换言之,就是要借用社区监督委员会的力量把社区两委的权力关在笼子里,督促社区两委成员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保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区有效治理。第三,加强队伍建设。有效的监督需要监督人员具备一定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来支撑。在X社区,监委会发挥的作用还有限,主要源于监委会成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业务能力不足。因此,社区在完善监委会成员选举程序的同时,要鼓励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参与社区监委会选举,将返乡大学生、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年人吸纳到监督委员会,同时加强业务培训和日常业务指导,提高社区监督委员会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三)完善社区工作人员激励机制
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微治理”的重要力量,优化社区“微治理”组织体系,需要将更多优秀人才吸引到社区工作人员队伍中来。当前,社区工作人员以新生代社工为主,由于工作压力大、事务多而工资相对微薄,他们普遍表露出诉苦、抱怨、不满情绪,导致人员流动频繁,社区“微治理”的骨干力量遭到削弱,亟需从拓宽优秀社区工作人员发展前景、提高社区工作人员收入水平及加强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完善社区工作人员激励机制。
首先,拓宽发展出路,打通优秀社区工作人员的上升通道。一方面,继续完善社区工作人员晋升通道。当前体制背景下,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职业晋升存在明显的体制“天花板”,他们的身份是“半正式人员”,性质上属于聘用人员,进入体制内流动的渠道非常狭窄,需要扩大他们职业发展的机会和渠道,比如通过“制造流动”,将一部分工作表现优异、干事能力强的社区工作人员从普通社区调到重要社区、明星社区,甚至开放街道内设部门的中层领导岗位,来激励优秀社区工作人员。[14]另一方面,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让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认同感,对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规划,在工作能力上不断提升。
其次,适当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近年来,不少地方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但他们在主观上仍有不满,这种不满主要源于“相对剥夺感”和“付出回报失衡”。“存在相对剥夺感是因为许多社工认为他们的工作负荷并不低于公务员,但经济待遇悬殊,认为不公平。认为付出回报失衡是因为一些社工认为其收入与工作投入不匹配,特别是连续遭遇重大行政任务需要长期加班时,失衡感会加剧。”[15]因此,要尽可能在现有物资待遇的基础上,增加工作业绩奖励。工作业绩奖励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多在物质奖励上下功夫;经济条件一般的地区,可在精神奖励上多想办法。
再次,加强保障制度建设,减少社区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结构合理的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应该是老中青相结合。年龄稍大的社区干部,对社区情况熟悉,群众工作经验丰富;年轻的社区干部,文化水平较高,信息化能力强。调研发现,年龄稍大的社区干部都害怕换届选举,因为担心选不上。X社区的主任解释说:“这是因为虽然文件上说男性60岁退休,但现在有些社区50岁多一点就不让继续干了。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不像政府工作人员有相对丰厚的社保,之前有位干了30多年的老书记,退下来之后生活过得很不好,这没办法不让我们担忧。”为此,需要进一步充实体制保障措施,如可以按社区工作人员的岗位和工作年限设定社保缴纳水平,确保长期在社区治理一线的工作人员没有后顾之忧。
(四)推进志愿组织规范化建设
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2016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办等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城乡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要开展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鼓励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社区服务。社区志愿组织是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也是社区自治的表现形式之一,其鲜明特点是无偿性和服务性,既可以是社区居民自发形成,也可以是当地公益机构支持形成,核心是志愿者积极奉献、不求回报。社区志愿组织一般包括社区志愿服务队和专业志愿服务队。社区志愿服务队着力于调处社区日常纠纷、清扫社区环境卫生等,专业志愿服务队涉及某些专门的领域,如法律援助、儿童教育、社区养老等。在社区“微治理”中,社区志愿组织既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还活跃社区的文化氛围,为文明社区建设添砖加瓦。然而,由于社区志愿组织大多是由本地居民的志愿者组成,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性不强,组织多但比较松散,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建设。
一方面,制定标准化的章程,为社区志愿组织的运行提供制度基础。社区志愿组织是志愿者自发形成的组织,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没有标准化的章程,社区志愿组织将难以长久运行,即使短期内服务效果不受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其志愿服务的动力、效率将降低,影响将减弱。另一方面,要提升志愿者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志愿者要有甘于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善于团队合作、与人沟通,同时,志愿者还要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在进行一些具有专业性服务时,如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人群的特殊服务,要遵守相关规定,按规范流程操作,展现出一定的专业化素养和服务水平。
(五)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
“微治理”的目标是要达成一种良好的公共秩序,这一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居民的广泛参与,尤其在外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需依靠社区内部力量。调研发现,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与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密切相关,通过拓展居民需求满足的渠道、构建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及发挥积极分子的动员示范作用,能有效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首先,拓展居民生活需求满足渠道。近年来,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科技应用普惠化,社区中的基础设施日趋智能化、人性化,如高龄老人家门口的“关爱之眼”、智能健身器材、日间照料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社区治理智慧化,大大提升了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与此同时,社区治理还需因地制宜,在满足社区治理整体需求的同时,还应考虑居民的个体需求。以小区的绿化地为例,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应允许居民在自家门口的公共绿地种植花草,既可以丰富居民的闲暇生活,也可以推进花园小区建设。另外,在规划“微治理”项目时,应多关注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尽可能全方位地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社区生活和谐稳定,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增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才会提升。
其次,构建社区居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社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社区居民之间存在疏离感,即使最初的安置以村落为单元,由于住房买卖,人员流动,小区中的居民缺乏有机关联的纽带,加上居住较为封闭,文化观念差异,小区成为单纯的物理空间,居民之间联系不多。在X社区,最初的居民大多是以前X村的村民,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习俗,较为密切的社会交往,但由于住房买卖和外地租客的进入,目前社区人员复杂,对社区缺乏认同,对社区治理关注不多。因此,需要发挥微网格员的沟通、协调作用,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同时,通过举办一些居民喜爱的活动,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期间,小区内部举办坝坝宴、楼栋之间举办联谊活动等,居民通过参与各类活动消除相互间的疏离屏障,建立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居民相互熟悉、对社区有认同感,居民就有意愿关心、参与社区事务,社区既是居民的生活共同体,也是治理共同体,社区“微治理”就有厚实的群众基础。
再次,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动员和保护。在社区治理中,要实现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需要一个持续激励和动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将社区中的积极分子首先动员起来,通过他们的有效参与,有助于带动更多的普通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担任党小组长、居民小组长、楼栋长、巡逻员、微网格员等,他们具有“半体制性”身份,在社区组织和居民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二是作为社会组织负责人,如舞蹈队、乐器小组、老年帮帮团等,他们主要协助社区组织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和助人为乐活动。积极分子是社区组织与普通居民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力量,通过他们的宣传发动、率先垂范等,能带动普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但是,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积极分子会面临动力消解问题,提升城市社区的治理效果,还需要从构建保护积极分子的舆论氛围、组织网络和完善对社区内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行为制裁机制,增强法律与制度执行力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对积极分子的动员、吸纳和保护,让积极分子在工作中既有获得感又有荣誉感,提高积极分子自身参与和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可持续性。[16]
【参考文献】
[1]赵丽江,尼加提·艾买提,陈海林.城市老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平衡研究——基于武汉市L街道的实证分析[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4):51-58.
[2]宁华宗.微治理: 社区“开放空间”治理的实践与反思[J].学习与实践,2014(12):88-96.
[3][10]尹浩.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多维赋权机制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6(5):100-106.
[4]董幼鸿,宫紫星.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以闵行七宝老街“微治理”为例[J].党政论坛,2020(8):55-58.
[5]余练.农村基层微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其运行机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1-19.
[6]郭晗潇.探寻契合点:乡村微治理的实践策略——以横村农居庭院美化项目的推进过程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06-119.
[7]包先康.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21(6):51-59.
[8]梁贤艳,江立华.划界与跨界:城市社区“微治理”中的政府职能边界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20(5):106-113.
[9][15]王德福.中国式社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85,250-251.
[11]欧阳静,王骏.基层治理中的“干部干、群众看”[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71-80.
[12]谢正富.治理孵化器:社会工作视角下“微治理”实现机制探索——基于襄阳古城15个社区的调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1):77-85.
[13]徐超,周彩,吴一平.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能否改善村庄治理绩效——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3(11):164-184.
[14]杨华.“制造流动”:乡镇干部人事激励的一个新解释框架[J].探索,2020(4):37-50+2.
[16]罗兴佐,何晓龙.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分子动员与保护[J].行政与法,2023(9):97-105.
Practice Explor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Community
“Micro Governance”
Luo Xingzuo, Tang Huizhen
Abstract: Community i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re are arious new types of community emerged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faces more challenges and requires innov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due to 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resettlement community. Through the micro-unit sinks and refines, precise setting of microservices,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icro management and micro-appeal smooth expression, micro governance have improve responsiven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chieved refinement and precision in governance, a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s gradually formed where everyone has a responsibility, everyone fulfills their duties and everyone enjoys in “micro governanc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micro governance practice stems from the leadership and promotio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forces, multi dimensional empowerment governance subjects, interest linkage and constraint supervision and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objectives and governance action. In currently, due to the prominent administrative natur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ismatch of responsibilitie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entities and the impact of limited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the practice of micro governance still fac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unity neighborhood committee lacks strong capabilities , lack of coordinated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low resident participation, need to clarify the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establish a sound working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community workers,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and stimulate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and other aspects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s for community micro governance.
Key words: “micro governanc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 ; multidimensional empowerment; excitation mechanism;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刘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