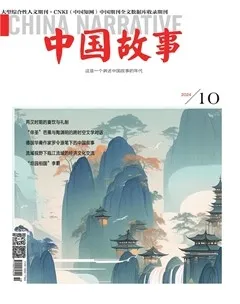论元末明初诗人刘永之的涉道诗
【导读】元朝末年,时局动荡,刘永之隐居山林,交友唱和,创作出大量的涉道诗,反映了刘永之个人的道教情结,揭示出元代道教与文坛的密切联系。通过对刘永之涉道诗的分析,分析元末明初士、道交友的特点,展现元末明初儒道互补的士人文化情怀。
涉道诗即有关道教的诗歌,是随着道教发展而来的诗歌题材。元代是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据《元史》记载:“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士人与道士多有交往,道教对文学的影响随之增强。刘永之,字仲修,自号山阴道士,生卒年不详,清江(今江西临江)人,其弟子章喆、何光编修其诗文有《刘仲修诗文集》八卷。当前较为全面收录其诗歌的是《全元诗》(第六十册)共计319首。在刘永之的诗歌中,涉道诗20余首,通观其涉道诗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登临游观类,登临道教圣地,抒发古今感慨;二是题画赠答类,评析自然山水画作,赠与道士共赏;三是酬唱感怀类,与道士集会酬唱,怀念士道情谊;四是闲适隐逸类,将隐逸之情融于道教山水。元末明初战乱加剧,促使脱胎于求仙问道的道教,开始关注现实的世积乱离,这拓展了刘永之诗歌创作的思想深度,从而使得刘永之的涉道诗呈现出富有时代价值的独特色彩。
一、登临游观——抒古今悲情
随着元代道教的兴盛,统治者大肆兴建道观道宫,道观建筑群是集风景园林、道教思想和交游玩乐为一体的审美景观,是继山水园林后,士人出游赏玩的绝佳之地,刘永之在吟咏之中,夹杂个人对于历史事实的看法,作《游承天宫》:
石桥流水隔飞尘,古木苍苍绕涧滨。
灵壝旧栖逃汉史,白云曾识避秦人。
冠裳千载遗琼笥,环佩三秋集羽轮。
翠壁丹崖如夙契,欲持名姓纪嶙峋。
承天宫,位于山东省蒙山之上,主祀为东岳泰山神。诗歌风格清奇,道教色彩浓厚。首联从宫祠周围的环境写起,水流造景是道教重要的风水设置,水流和古木环绕宫祠,一个“隔”字,将尘世和仙境分开,营造出幽深寂静的自然环境。颔联将宫观环境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避秦人”运用典故,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写有“避秦时乱”与世隔绝的村民。结合道教发展历程来看,因朝代更迭,战火中的民众向道教寻求庇护,而道教也为了吸纳教徒,拯救了民众,正是下层民众心中的“桃花源”。兴盛于魏晋求仙问道的道教,转向关注民政疾苦,正是道家教义的转变,使得元明之际的诗人,将桃花源与神仙道观结合起来,这也是元代涉道诗的特色之一。颈联对仗工整,实写道观收藏的书籍丰富,虚写仙子们驾车游仙。尾联诗人直抒胸臆,翠壁丹崖,赞颂山川美景,赞叹之余,抒发个人“成仙得道”的主观愿望。诗歌相较于前代涉道诗,极具代表性地将代表隐逸的桃花源与道教道观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战乱视角下,诗歌创作的主旨深化。
刘永之的山水道观诗不仅关乎元末明初的社会战乱,而且反思由古至今的历史发展变化。《题烟云台》:
祠宫俨肃穆,灵贶赫然敷。藻井乘珠实,素壁绘金图。涧长三花树,林栖九子乌。遥峰隐残照,丹霞晚渐舒。眇然登云驾,谁谓古今殊。
诗歌先叙述登台所见,再描绘远眺所看,从宫殿起笔,由晚霞落笔,前景是庄严肃穆的宫殿,背景是晚霞铺满远山,远景是自然风景,近景是宫殿的装饰和摆设,由近及远,由小到大,诗句将这幅画面层层展开,营构出庄严肃穆的宫祠环境。“遥峰隐残照,丹霞晚渐舒”点明宫祠坐落于深山密林之中,其中“隐”使得宫祠带有神秘的色彩,夹杂着作者对于仙境的无限想象。诗人最后直接抒发感慨,“眇然登云驾,谁谓古今殊”。登楼怀远,登高怀古,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抒情模式,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即所谓‘伤高怀远几时穷’是也。此后词章中写凭高眺远、忧从中来,几成窠臼。‘囊括古来众作,团词以蔽,不外乎登高望远,每足使有愁者添愁而无愁者生愁。’”而本诗打破登楼远眺的崇高感和历史的纵深感,消解诗人登楼沉思的古今之叹、家国之悲,对中国古代诗歌所营造的意境进行解构,究其原因,诗人所登的是道教圣地,老庄思想所倡导的是“大象无形”,历史循环往复,朝代更迭,从古今对照poB4thw5O5DJAW+4UBu4ymazHFYV/MF6qpyTpRTxswQ=的角度看,刘永之的感慨是对“有”的超越,从而达到“无”的境界,换一种角度,透过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历史来看,则是对“有”的升华,历史几经沧桑变化,总是带来相似的历史结局,诗人所信赖的、依靠的,都化作空无,诗歌便蒙上历史巨变下的悲伤韵味,诗人妄想通过道教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超脱。
二、题画赠答——感自然山水
元代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题画之风,题画诗是诗画艺术结合的完美表现。刘永之“工书法,篆楷行草,皆有师承”,刘永之与友人交往密切,互相赠答题诗,刘永之所作题画诗有40首左右,约占其诗歌创作的八分之一,其中与道教相关的题画诗有5首,由此可见,刘永之交友范围广,诗歌与书法皆善。刘永之题道士画作赠予道士的诗《题方方壶画仁智图为道士主默渊赋》:
玉检神仙记,琼台羽士家。
轩窗明日月,冠佩剪云霞。
白鹤窥残奕,青童扫落花。
忆曾访丹术,枫径驻轻车。
诗歌运用“玉检”“琼台”“白鹤”“丹术”描绘出一幅道士修仙图,首联将“记”和“家”两个动词后置,与“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形式相似、押相同韵,点明道士所居住的地方,颔联中承接上句的神仙色彩,“日月”“云霞”两个自然意象呼应,给诗歌笼罩一层朦胧感,颈联画风突转,“残奕”“落花”即象征着元代末年的世积乱离现实,将思绪从神仙密境拉回到人间的末世苦难,此句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境类似,借自然事物的凋落,衬托朝代更替的哀伤氛围,尾联诗人思绪再次回转,回忆曾经求仙问道的快乐场景,“枫径驻轻车”句既有“停车坐爱枫林晚”之景象,又兼“舟遥遥以轻飏”之情,枫林漫天,驻车遥望。纵观全诗,起承转合,神仙道教和现实的社会动乱相对照,这种独特的融合是对元代道教盛行、元末明初战乱之时代风貌的独特呈现。
此外,刘永之在题画赠答诗中表达了更加直接的游仙思想,《方壸画轩岐论道图为道士何仲旭赋》:
彩笔发神秘,仙山开画图。灵文隐玉笈,石扇启金枢。寤寐轩岐术,结交苏董徒。羽服系萝带,笻杖悬药壸。行当谢尘服,从子昆仑墟。
作者起笔从整体的层面评价“轩岐论道图”,其中“开”字形象地写出画作具有气势磅礴的特色,“神秘”为画作本身的意境在作者情感上的主观投射,揭示出“轩岐论道图”的传神色彩。“玉笈”“金枢”是道教作品的代名词,“寤寐”则说明画中人物对于道教的痴迷程度之深,作者通过对画中景物的具体描写,营造出飘然的意境,画中道士衣带飘飘,悬壶拄杖,书籍叠落,诗歌由画中道士联想到道士生活,谈论方术,遍交友朋,共同论道,落笔处变为作者本身的情感抒发,超脱人世,游历仙境。本诗由画入诗,由诗见画,具体的意境之外有着细致的物象临摹,而在具体物象之上,又能阐发个人联想,情与景共具。
三、酬唱感怀——叙深厚情谊
元末明初的战乱社会中,刘永之用诗歌表达自己的痛苦哀思,并希望借道教的超脱精神,使痛苦得到缓解,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士人的儒家用世精神与封建君主专制产生了矛盾,具体表现在刘永之的涉道诗极力营造两个世界,一个是无忧无虑的神仙秘境,另一个是悲情凄苦的人间世界,读者在其中遍历自由的仙境与残酷的现实。在西峰山上的一次文、道集会,友人分韵得字,提笔作诗,记叙交友之乐事,而在刘永之此后的生命中,写下七八首怀念此次聚会的诗作,或是怀念此次聚会,或是怀念西峰道士,总体来看,透过本次集会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元末明初士、道交友活动之多样,感情之深厚。《至正壬寅二月廿一日雍虞岂临江宋理道士刘旻李文同登西峰之烟云台以登高望远为韵各赋四首(其一)》:
仙山百余仞,振衣聊共登。阳林映昭晰,阴壑泻璁琤。灵泓蟠玉虬,丹荑冒翠藤。霏霏縠雾敛,冉冉卿云升。栖遁皆真侣,摛掞画高朋。虽非幔亭会,终使逸情增。
诗歌以抒情为主,极力描绘仙山美景以及士人与道士同游之乐,“霏霏”与“冉冉”两个叠词营造出云雾缭绕的仙境,此地的道士则是值得深交的朋友,与道士聚会使得自己思绪更加开阔,诗人四首其四最后感慨“谁言薄当世,暂䜣尘事远”。从战乱视角来看,刘永之的涉道诗,有着真切的情感内蕴和历史的厚重感,现实社会的苦楚无法排解,诗人便转而寻找道士仙山,得以短暂疏离伤痛,刘永之在《和胡参谋书怀韵简彭书记》中,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词赋哀时切,诗书易俗难。颇闻边报早,聊足慰辛酸。”由此可见诗人对现实政治情况的关切,刘永之的涉道诗清楚地认识到神灵仙境的虚构性,他在《寄西峰道士七首(其六)》中指出:“瑶擅丹柰景阑干,不比人间荔子丹。”对社会的关切意识加深了诗人诗歌创作的现实深度。
诗人的怀旧之作更显情深意切和悲悯情怀。《重过西峰兴怀旧游》:
游云薄层霄,飘飘从所适。偶与长风会,高举翔八极。既无聚散情,宁存去留迹。神宇属再经,经术记已历。溜溜出谷泉,礧礧当涧石。皋兰秀初春,风条鸣终夕。临觞缺佳偶,抚枕虚瑶席。芳词故在庋,青徽讵云匿。向思托柔翰,方期重来觌。
诗歌情感真挚,笔致空灵,首句“游云”是道教意象的典型代表,“飘飘”亦是一种人生状态,是作者自身孤身一人漂泊在外的主观形象的意象化表达,而游云飘飘有所适,但作者此时旧地重游,却无所适,从意象的使用和意境的营造两个方面凸显诗人孤苦寂寞的游子心理。“偶与长风会”则是失意作者试图通过往日的聚会场景,消解此时的孤单情境,“宁存去留迹”,紧接着诗人的情感流转,悲苦情绪无法排解,甘愿留有悲苦心绪。“神宇”“经术”是道教术语,作者故地重游,昔日在广阔自由的天空下谈论经术的场景历历在目。此四句诗以作者情感为脉络,着重书写妄想割弃孤苦情景,却不得已陷入苦闷愁绪的矛盾心境。作者将写作的视角从自己凄苦的主观心境,转移到自然界中的山山水水,拟声词“溜溜”用来形容泉水的走势,凸显自然山水的活泼可爱,“礧礧当涧石”此句则是化用杜甫《白沙渡》的诗句:“水清石礧礧,沙白滩漫漫。”山谷中泉水涓涓细流,而泉水边的幽幽兰草,增添山中景物的自然灵气。面对如此山水幽兰、虫鸣鸟叫,诗人悲苦心境还是无法排解,反而将怀念旧游的情绪表达得更为直接。“临觞缺佳偶,抚枕虚瑶席”,诗人春日旧地重游的感觉也被形象地表现了出来。“芳词”本为美好的词,代指山谷美景以及诗人自身无人欣赏的情形。诗人在最后将思念的愁苦,再次寄托给游云,期待着与好友再次相遇。诗歌虽是以“游”为主题,却以“情”为主线,由“游云”想到自身处境的孤苦无依,试图通过自然美景排解孤苦无依的情绪,无法排解之时,诗人直抒胸臆,情感一泻而下,再次将相思托付给“游云”,可谓是情感一波三折,意象前后呼应,着重突出了刘永之对西峰士人、道士集会游观的怀念之情。
四、闲适隐逸——记自在生活
刘永之辞官归隐之后,隐居山林,登临吟啸,闲居赋诗,诗人借道教山水来表达隐居的愿望,是对元代隐逸之风的继承和发展。“所谓‘隐逸’,‘隐’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逸’则是一种生活形态和精神境界。隐者要有‘逸’的精神境界。”在刘永之的涉道诗中,“逸”的精神境界与道教结合在一起,在日常生活的典雅书写中,透露出对于道教的诠释。《云鹤巢》:
厌彼鸡鹜群,爱此青田鹤。结构象□巢,幽栖在林壑。孤骞白云杪,遐瞰紫烟中。山影摇松月,涧声鸣竹风。不为好爵縻,独秉冲霄志。即有万里翔,聊闻九皋唳。少君沧海上,一札传仙书。明当跨霜翮,游戏昆仑墟。
诗歌借物咏志,“鹤”意象脱胎于神仙道教,象征人、仙、道的三者结合,通过对青田鹤独立世外的赞美,表达了对于尘世繁杂的厌恶,首句便以“鸡聚群”和“鹤孤飞”作对比,此句是化用李白《鸣皋歌送岑徵君》“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衬托出仙鹤遗世独立的高傲身姿与高洁品质,“少君沧海上,一札传仙书”点明青田鹤连接仙山与尘世的独特作用,此时的仙鹤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代表着诗人想要超脱世外的主观心愿,而诗歌的最后,诗人更是将这种思想直接表露,“明当跨霜翮,游戏昆仑墟”表达想要生出双翅,遨游于昆仑之巅的愿望,而此时的昆仑山是兼具隐逸色彩和道教求仙旨意的“桃花源”,寄托着诗人对于世俗的厌恶和高洁人格的向往。刘永之诗作《野老看云图》:
文湍激幽涧,白云流远山。偃仰长松下,延眺一怡颜。清风拂素服,瑶花落树间。拾薪青烟际,煮苓供晚餐。耽此丘中赏,竟日未言还。
潺潺流水,悠悠浮云,松下独卧,风吹花落,画中之景,画外之人,交相叠映。诗歌开篇,由近及远展现视角的变化,近观流水深涧,远眺白云高山,而后引出观看的人物——独卧青松之下的老翁。景物在前,人物紧随其后的叙事视角,呈现出“景在人前,人藏景后”的视觉层次,视觉层次可以由画中人物与景物延伸到诗人与画,画中人物在欣赏美景,画外作者在观赏画中人物欣赏美景,看与被看视角是艺术欣赏的盛行模式,本诗的视觉变化描绘的正是这种模式。“清风”“素服”“瑶花”等意象的运用,以“拂”“落”两个动词连接,衬托出老翁仙风道骨的人物形象。诗到此处,已经完整描述画的内容和意境。中国山水画强调的人在画中游的动态美与中国诗歌重视的意境美,深度融合在了一起。诗歌最后两句则是诗人的联想和议论,山中老翁或许在捡柴烧饭,由缥缈仙境到人间冷暖的转变,也是由画到现实的延伸,诗人最后的感慨和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本首诗中刘永之着力塑造老翁仙风道骨的形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山野生活的向往。
总体看来,刘永之的涉道诗带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表达了诗人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反映了时代环境中个人生存的焦虑以及历史沉浮中的国家兴亡,作者借由道教思想将社会现实进行再创作,表现出带有时代性的社会情感。刘永之的涉道诗侧重选取带有浓重道教色彩的意象,营构精巧自然的道教仙境,从而抒发作者的情感,在诗歌的最后往往夹杂着作者的议论,构成圆融的诗歌抒情模式。
五、结语
刘永之身处元末明初的社会乱世中,通过与道士交往交流,获得精神上的超脱。刘永之在涉道诗中营构了一个精巧神秘的神仙境地,而在诗歌的末尾又将世间的悲苦与之相对应,完成诗人忧国忧民的情绪表达。内心极度苦闷的士人与道士,试图以游观、集会、题画、赠诗等士人艺术活动与现实的苦难对话,使得涉道诗增添现实情怀和悲世情怀。从战乱视角看刘永之的涉道诗,挖掘士、道交友中深藏的诗人情感,可窥见元末明初诗人儒道互补的文化心态。
参考文献
[1]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杨镰. 全元诗[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杨士奇. 东里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5] 查洪德. 元代诗学通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 宋濂. 宋濂全集[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7] 诸葛忆兵. 论宋代科举考场外的诗歌创作活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