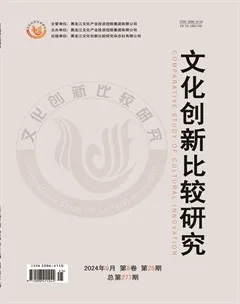红色文化空间建构及其优化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红色文化一直高度重视,提出“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红色资源,增强红色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作为承载红色记忆、建构族群身份、形塑家国认同的重要媒介,红色文化空间不仅承担着文物展览、爱国教育等社会功能,还彰显着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价值。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以史料呈现为主的“物质性”生产的传统红色文化空间建构,越来越难以吸引受众,抵达他们心里。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为了更好地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该文立足文化记忆视角,探讨红色文化空间建构的优化路径。研究认为,通过氛围铺垫、细节叠加、具身实践等情境生产,将“死”的记忆转变为“活”的记忆,成为未来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红色文化;文化空间;文化记忆;记忆空间;空间建构;空间优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9(a)-0090-05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Red Cultural Space
TAO Rong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nheriting the red culture, enhancing the "expressive, communicative, and influential" power of red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carrying red memories, constructing ethnic identity, and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red cultural space not only undertakes social functions such as cultural relics exhibitions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consolidating national spirit. With the advent of digit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cultural spaces still relies mainly on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material" produc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ttract audiences and reach their psychology. How to optimize the status of red cultural space, through contextual production such as atmosphere paving, detail stacking, and embodied practice, to transform "dead" memories into "living" memor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Key words: Red culture;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memory; Memory space; Space construction; Space optimization
红色文化空间是重塑红色文化的记忆之场,建构身份认同的媒介场域,不仅承担着文物展览、爱国教育、旅游经济、公共文化需求一系列社会功能,还彰显着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价值。
一直以来,红色文化空间以“物质性”作为最主要的建构形态。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媒介变革带来的信息接收主体变迁,人们以参观者的身份进入红色文化的空间场域,被动地“观看”历史,巨大的时空差异无法让人们感同身受地进入历史现场。优化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和非“物质性”的生产情境是改变红色文化空间建构现状的另一种路径和策略。
本文借鉴人类学的文化空间形态特征,结合民俗学对文化空间的属性定位,立足文化空间理论,通过探讨文化空间的时空结构和文化关系,探寻红色文化空间建构的时代意义与价值传承。
1 红色空间及其文化意义
1.1 空间与红色空间
1.1.1 空间与空间转向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带来传统认知时空转型和信仰迷失,加之各种思潮涌动,价值混乱,网络民族主义、虚无主义的盛行,促使社会学家们开始进行反思。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等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时间”范式中调转开来,使空间从历史(人物、事件)及社会(生产、交往)关系的载体或容器概念中挣脱,指出“空间……是以人类主体的存在为中心来加以组建的人与事物之间的前理论的关系状态”[1]。空间从最初的自然科学研究,开始了文化上的转向。空间不仅意味地方、地点,被应用于地理学中,重要的是被应用于文化领域中,进一步赋予了文化建构的意涵,空间的文化承载功能被发掘[2]。
1.1.2 文化空间与记忆之场
空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向,促使不同学科对空间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和延伸,空间作为一种意义与文化生产的意义被凸显。文化空间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人类学范畴的“文化空间”强调人类口语和非物质遗产的形态。民俗学的文化空间,除了自然属性外,侧重留存人类日常行为和文化传统的文化属性。即文化空间是由人、地和信息组合而成的实践产物,是公共生活形式和文化权力运作的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性文化空间,是该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观念、文化传统和生活样态等要素综合作用的动态场所[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文化空间回到了其本原意义,指一个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4]。
一直以来,文化记忆纵横交织在时间领域和空间领域。时间的流逝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何超越流逝的时间,铭记历史,留住记忆。如何用空间承载文化、征服时间、表达永恒,是文化空间的核心宗旨所在。这个具有时间性的空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观和时间观,既要有文化内涵,又具有纪念性。所谓纪念性,是“由人们为了其外在需求而拥有可显现其内在生命、行动、社会性概念象征/符号所延伸而来的”。在拉丁文中纪念物最初意为“可被提醒的东西”[5],例如国家设立的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等。在这个场域内,遗留下有形的、物化的、可触的实体性存在,如遗物、遗迹、文献资料等。在这些具有文化价值的纪念性空间场域里,人们可以共享记忆,重塑想象的共同体。
1.2 红色空间的文化意义
红色文化是在反抗外族入侵,争取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特殊历史时期,体现出来的浴血奋战、顽强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历史记忆。红色文化空间就是承载这些革命精神和记忆的物质载体,既包括有形的遗迹、遗址、遗物,也包括无形的精神遗产的动态开放空间。
红色空间勾连现代与历史,作用于现实与过去。通过场景化营造一种特殊的仪式,建构一个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的仪式空间。保罗·康纳顿在讨论社会如何记忆时指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 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如渡江战役纪念馆的烈士名录厅四周摒弃了传统的人物图片和事迹展示,打造了四面汉白玉的墓碑墙,墓碑上刻满了8 000多名烈士名单, 长廊的尽头是个汉白玉的棺椁雕塑,上面覆盖着党旗,旁边摆放着人们祭奠的簇簇菊花[6]。烈士纪念馆用墓碑和棺椁的符号,构建了一个肃穆而圣洁的空间,置身其中,之前模糊的、抽象的、遥远的无名烈士变得清晰、具体、可触摸。这种仪式操演,让人们了解历史、感悟当下,从而唤醒记忆。
红色空间不仅是人们缅怀历史、共享记忆的仪式空间,更是凝聚共识、建构认同的媒介场域。记忆研究学者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最终转变为共同体的记忆遗产[7]。如通过历史会议现场的修复和还原,重塑记忆共享的媒介场:人们在中共一大旧址重温入党誓词;在中共七大会址还原地遥想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在遵义历史步道,重走“长征路”,感悟长途跋涉的艰难;在井冈山,品尝“红军餐”“忆苦饭”感受战争的困境,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2 物质性生产:红色文化空间的建构现状
传播的物质性是媒介学家研究的核心,正如德布雷所言,“思想只有通过物质化才能存在,只有通过流露才能持久”[8]。无形的、抽象的精神正是通过物质性的实体才得以具象化。“物质性”这一概念事实上体现在具体社会建构活动过程中人类意图所遭遇的一种隶属于物本身的“固着性”(fixedness),这种固着性可以超越(至少阶段性地超越) 建构活动中的社会情境,从而对建构活动的结果产生影响[9]。
有形的物质性实体是红色文化空间建设的基石。作为承载这些革命精神遗产的特殊空间,红色文化空间以人为核心,围绕着历史事件、红色遗物等呈现历史,而正是通过这些物质化的载体——遗迹、遗址、遗物,红色思想才能被呈现、被铭记、被传承。
2.1 史料物品: 红色文化的展览呈现
在研究文化如何被表征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文物提供了过去与现在最为坚固且稳定的联系[10],揭示了历史文物的文化链接和情感链接作用。因此,红色文化的空间建设,最初主要以红色文物的保存和展览为主。作为历史的一手资料,这些红色文物真实地呈现着过去,引导着人们在参观的过程中认识历史、了解历史。
历史旧址和纪念馆是红色文物陈列最集中的文化空间。中共一大石库门旧址,保留了当年“一大”召开时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以及当年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请愿书和场景照片。为了更真实地呈现历史,“一大”纪念馆还原会议现场,塑造了“一大”代表蜡像,使观众更加切身感受一个政党的百年变迁。此外,很多战争实物,如四渡赤水时红军搭浮桥用的门板、渡江战役时运粮用的“独轮车”、一套满是弹孔的军装等也被保留着,透过这些,人们可以更加真实感知战争的腥风血雨和先辈们的英勇顽强。
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故居里的遗物大多为原物,如韶山毛泽东故居中学习用的方桌、板凳,休息的木床,农活使用的水车、水桶等,人们凝望着这些伟人使用过的物件,追忆伟人的心路历程;在延安的三孔土窑洞,注视着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走向时用过的砚台,憧憬“新民主主义”的未来。故居的室内陈设也尽量保持旧貌,如淮安周恩来故居,陈设简朴,床上铺着打着补丁的旧被褥,书房保留着陈旧的书桌,这些激起人们想象总理生活、学习的情景,思考这里如何萌生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伟大豪情。
2.2 建筑材料:红色历史的表层意象
有形的物质性展览只是表层次的信息生产,革命文物的陈列只是将“死”的历史冰冷地呈现,对于历史的铭记和传承而言,这种单一的史料呈现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发掘出它们的历史价值,激活“死”的历史,焕发出人性的温度,让陌生的过去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除了史料物品的呈现,作为红色历史表层意象的实体性体现,建筑材料的运用,是红色文化空间物质性生产的另一个体现。
建筑材料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故居的修旧如旧和纪念馆的符号化表达。淮安周恩来故居,最大程度地保留室内的陈设和室外的环境:青砖、灰瓦、木结构平房。灰色的外墙,保留明清时期典型的苏北城镇民居建筑风格原貌,裸露的泥土体现着故居古老质朴,内墙上也布满了雨水冲刷形成的霉点,一些地方裸露着的青砖,砖缝处由于阴湿生出点点苔藓,触摸着雨水冲刷过的斑驳的墙壁时,瞬间感觉穿越历史,回到了那个满目疮痍的峥嵘岁月,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
与旧居旧址的原状陈列不同,作为现代建筑的纪念馆,缺乏故居的天然历史感,只能通过赋予“符号活动”意义,将与其有关的文化形式编入符号世界,通过符号来认识世界[11]。体现在设计上,主要通过图形和符号来挖掘文化的象征意义。
遍布全国的红色纪念馆,叙事底色都是“红”色的。浴血的抗争史不断地被强化,红色成为一种符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里。在革命圣地井冈山,铸有象征点燃胜利燎原的星星之火的火炬符号,诉说着红色精神生生不息的动因。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斜三角形设计,似渡船也似丰碑。与地面的49°倾斜,隐喻1949年战役的胜利。纪念馆前方,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谭震林(从左至右)的雕像远眺巢湖,仍能感受到他们当年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才伟略。纪念馆内部,深色大理石仿古瓷砖,体现着厚重和久远,营造出与过去神韵相通的历史感。室内物品陈列主要以玻璃展台为主,透明的材质将遗物与参观者隔绝开,彰显了遗物的距离感和神圣感。人们无法触摸到实物,只能静静地观赏。
3 情境创设:红色文化空间的嵌入优化
除了物质性的营造,红色文化的纪念属性还需要通过空间策略来建构。在数字化时代,这种空间策略集中体现为技术化的情境创设,通过建构场景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所谓情境,情境主义学者乔恩·巴威斯认为“情境是在各种各样的时空场点上具有性质和处于关系的个体”[12]。其后,基于符号互动视角,戈夫曼进一步指出人的行为需要情境。环境、事件和人物关系构成情境三要素,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力越强,就越能构成情景交融的整体,人物的行动与相互关系的推进才越有动力[13]。
因此,如何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全方位感官系统,通过氛围铺垫、细节叠加、共鸣跨越的情境创设方式,来实现触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记忆、塑造认同的功能,是红色文化空间建构的优化路径和策略。
3.1 氛围铺垫:基于历史再现的观察设置
氛围铺垫主要是指利用环境铺垫,奠定情感基调。红色文化的氛围铺垫主要是通过历史再现进行设置的,历史再现为人们提供观察,并在此基础上引发思考。具体而言,氛围营造将人们引入特定的历史情境,烘托环境,渲染气氛,有利于故事的展开,为后面突出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出场,以及参观者情感的爆发作铺垫,即“运用隐喻、暗示、联想等环境手段来引导人们的思考,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从而表达出空间的纪念性”[14]。通过空间陈设,营造氛围感,建构人们的想象和思考。情境不仅能够调动观众的情感,使其置身于场景之中,还能勾连记忆和想象,回味和放大感受到的情感[15]。
红色文化的空间建构,主要通过现场重返、打造特定时空、还原真实历史来实现。依据真实历史生产的影像用图像和声音打造虚拟时空,主要体现为历史遗址复原。例如,韶山毛泽东故居修旧如旧,用旧物来复原当年场景,典型土木结构的南方农宅,泥砖墙、青瓦顶,门口还有毛泽东幼年时游泳的池塘,不禁让人遥想其“浪遏飞舟”的英勇气魄,思考“红太阳如何从这里升起”。此外,还有重大会址还原、站前作战指挥所复原等。例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方指挥所旧址,保留了“秦砖、汉瓦、马头墙”徽派建筑风格,砖木结构,青砖铺地,真实地再现了战争时期艰苦的环境。通过这些历史的再现和氛围的铺垫,让人们重返历史现场,亲身感知环境的艰辛,体悟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
3.2 细节叠加:依据典型事件的问题探索
“信仰”“使命”“担当”这些宏大词汇,在战争年代是具体真实的,然而,100多年过去了,如今开始变得虚无模糊。如何和当下的人们解释这些概念,如何具象化这些词语,氛围铺垫只是情感生发的基础,细节的呈现和叠加才能使人们真正进入那段尘封的历史,激发他们的情感,拨动他们的心弦。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着毛泽东用过的煤油灯,“一根灯芯”的故事,书写了伟人的节俭质朴,“八角楼上的灯光”是毛泽东在夜以继日地思考“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中共一大会址,石库门旧址陈列着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用过的打字机,言说着白色恐怖时期,李大钊将性命置之度外、心怀天下的使命与担当;渡江战役纪念馆里的“渡江第一船”上悬挂的破的帆,诉说着当年渡江战役的惨烈和战士们的英勇……一点一滴的细节呈现,一层一层的情感叠加,使先烈们勤俭节约、克己奉公、视死如归的形象更加真实,更加动人。
通过细节层层叠加,“进入”历史情境,就典型事件设置问题。例如,是什么激发着他们在生死未卜的状态下毅然决然的抉择?支撑这些行为的力量是什么?信仰的力量为何如此巨大?带着这些问题去寻找答案,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探索欲,帮助人们更进一步了解革命先辈,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动因,破除信仰虚无的思潮,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3.3 共鸣跨越:融入具身实践的时空感悟
氛围铺垫是唤醒记忆的环境基础,细节叠加是打动人心的关键一步,当下的红色文化空间建设,更多地运用VR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实现了真实的具身实践,互动式的体验,打破了时空,触动了人们心弦,实现情感上的共鸣,强化了家国认同。
“VR等虚拟现实技术的核心是在沉浸互动和想象的加持下,人类综合感知器官得以延伸,影像内容在生产上从传统观看模式转向体验感知。”[16]具体体现为,历史背景加3D动态模拟还原周围环境、人物、声音,甚至体感等更直观的体验方式来感受历史上的奇迹战役[17]。例如,VR重走长征路系列,VR巧渡金沙江、过雪山草地、飞夺泸定桥等模拟体验,人们戴上VR眼镜,仿佛成为红军的一员,匍匐在铁索桥上,脚下是咆哮的滔滔江水,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向前,在九死一生的战斗中体会战争的残酷和先烈的英勇。震慑人心的视觉、听觉,真实的“触碰”体验:“扶起”战友,“抓起”沙袋,射击时手柄的震动感。此外,人们还可以与革命人物进行对话,通过互动式的交流,提高参与感。历史现场1∶1还原,逼真的环境,多维的感知,人们具身沉浸在实践中认识历史,更容易理解革命先烈们当年的选择。
情境和互动是人们情感维系的基础。红色文化的空间建构,首先,通过文物陈列回到历史现场,营造历史氛围感,创设情境;其次,叠加一系列的历史细节,启发人们思考探索,激起人们内心的情感;最后,嵌入VR等技术,构建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使人们沉浸在同一个时空下,具身体验峥嵘岁月,通过“体验—促发”行为,拨动人们的心弦,实现情感上的共鸣,获取身份认同,最终找到文化归属感。
4 结束语
文化的传承强调延续性和持久性,偏重时间维度。红色文化空间建构,本质上是如何用空间解释时间,将时间维度的红色历史嵌入实体性的物理空间,纵向地描述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曲折过程,将具体事件放置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考察和判断,探求红色精神的内在动因。
红色文化空间是缅怀历史的记忆载体,是民族情感的滋养空间,其蕴含的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正是通过这些实体性存在和文化空间,主体才可以跨越现实时空、寻踪人类文脉、追溯族群历史、建构集体记忆、增强家国认同感。
因此,XZ1rkDLbhiXZo0N6AN2k9g==只有将红色文化空间建设好,让人们了解,我们的国家遭遇了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屈辱和奋战,未来要往何处去,才能深刻地理解为什么红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才能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红色精神代代传承。在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和国内风险时,才能不负使命,担起时代的重任,坚定不移地为了实现中国梦而不断奋斗。
参考文献
[1] 彭松林.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对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启示[J].图书馆建设,2021(1):105-113.
[2]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 李孟舜.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构建与创设路径[J].中州学刊,2022(7):166-172.
[4]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81-88.
[5] 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学术月刊,2012,44(7):134-137.
[6]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 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9]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1(7):104-112,121.
[10]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3-37.
[12]乔恩·巴威斯,约翰·佩里.情境与态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郑向荣.从“奇观”到“情境”:旅行真人秀节目的突围与升级[J].中国电视,2015(9):52-57.
[14]田云庆.室外环境设计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1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79-280.
[16]郭春宁,富晓星.全景共情机制:虚拟现实在空间叙事与文化记忆中的应用[J].天津社会科学,2022(2):122-126.
[17]陶荣婷.智媒时代红色记忆传承的挑战及其消解[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5):7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