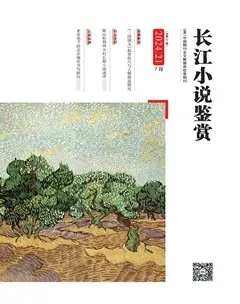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规训与惩罚”
[摘 要] 作为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安妮·塞克斯顿对十七则格林童话进行了重写,其中对《十二个跳舞的公主》的改写揭示了以男性为中心构建的权力关系对女性施加的规训与惩罚。诗歌中的女性被商品化,成为可以被男性交换的资本,其行为一旦偏离父权社会制定的常规,惩罚就会成为必然。塞克斯顿创造性地颠覆了这一传统童话故事的乐观结局,生动描绘了女性在受制度规训和惩戒后主体性消解,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命运的悲剧性结局,从而对女性生命价值及生存困境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安妮·塞克斯顿 女性主义 规训权力 《十二个跳舞的公主》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1-0113-04
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年)是美国著名的自白派诗人,也是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其代表作《变形》(Transformations,1971年)是自白派诗歌和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文本,该作品源于对格林童话原著的重构与阐释。塞克斯顿在保留原童话故事基础情节的同时,通过现代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再审视与解读。其中,改编后的《十二个跳舞的公主》(The Twelve Dancing Princesses)故事原本描述了一位老兵揭开了十二位公主的舞鞋磨损之谜,并最终与其中一位公主结婚的故事。然而,塞克斯顿对这一传统的幸福结局进行了颠覆,从女性视角批判了男性主导的婚姻与行为规约,细腻地刻画了女性在丧失个体主体性之后,自我价值感的流失和对命运的无力反抗,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制约。在女权运动席卷全美之前,塞克斯顿等女性诗人通过其诗作实践了性别诗学(poetics of gender),“向读者传达了一种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女性特有的令人窒息的压抑感”[1],并通过文学主题的美学呼吁女性解放。
格林童话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众多学者从中汲取灵感,对其进行了重新诠释与改写。英国著名小说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于1979年出版的《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和丽兹·洛克海德(Liz Lochhead)的《格林姐妹》(The Grimm Sisters)等作品,都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格林童话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与反思,从而颠覆了男性主导的文学叙事传统[2]。安妮·塞克斯顿的《变形》也属于为女性发声的标志性著作,国内学者对其采取的女性主义解读视角亦有着丰富多样的见解。学者郭一[3]、洪雪花、马全振[4]等人针对塞克斯顿的女性主义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从《变形》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入手,利用凝视与反凝视理论分析了女性如何变成被观看的对象、成为他者的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对《十二个跳舞的公主》的研究,解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中,女性是如何被规训与惩罚,以及在违背了父权社会规定的常规后,所承受的惩戒。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女性在拥有自我主体性时的生命价值,以及在主体性被消解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一、凝视、规训与惩罚
安妮·塞克斯顿对《十二个跳舞的公主》的改写与格林原版童话在开篇部分呈现出相似的情景,描绘了国王的十二位公主如同被囚禁般的生活状态。原文描述如下:“一位国王拥有十二位女儿,所有女儿皆美貌绝伦,她们共同居住在一间宛如女生宿舍的房间内,床铺并排而置。夜幕降临,国王便会将房门紧锁,并加上门闩。”[5]在此情境下,十二位公主被迫共居一室,夜间所有出口均被严密封锁,无从逃脱。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规训权力以“匿名的权力手段”[6]运作,使得这间房间既是公主们的寝室,同时也扮演着监狱的角色,执行着监视与禁锢的功能。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公主们的身体与精神均受到束缚,即女性在夜间不得外出。
福柯将现代社会比作一座“全景敞视”的监狱,其核心为中央监控点,权力在此全方位渗透,通过肉体上的监视与规训,生产出主体同一化的灵魂。他指出:“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6]在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规训下,十二位公主并未公开反抗夜间的禁锢,反而表现出对这种制度的表面顺从。她们选择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悄悄离开,并在秘密被揭露时试图掩盖真相,这正是外在顺从的表现。然而,福柯曾言:“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7]尽管受到规训,十二位公主仍坚持反抗。在国王发现舞鞋破损的线索并展开调查后,她们依然每晚外出。大公主通过迷晕调查者,将男性从观察者、主体转变为被观察者、客体。男性调查者无法得知公主们的去向,而公主们却能目睹骑士在迷药作用下沉睡的窘态。长期以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置于“第二性”的地位[8],将女性的特质定义为“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9]。塞克斯顿通过反凝视策略,颠覆了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关系,揭示了女性对构建这种权力关系的规训的反抗。
然而,大公主对老兵的反凝视只是对传统女性角色不从属规训的一种挑战,而老兵对十二位公主的夜间外出和舞蹈的全过程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监视,显现出一种真正的权力不平衡。当老兵披上隐身衣,他转变成了一个全知的观察者,目睹了公主们进入秘密通道、银色树叶、钻石镶嵌的书本、饰有红宝石的杯子,以及她们的舞蹈全景。尽管老兵曾三次暴露破绽,他还是得以隐形不被发现,而公主们则成了被监视的对象,缺乏观察者的权利。福柯将凝视视作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观察者处于不可见的黑暗中,监控着被观察者,而后者则暴露在视觉可及的场域中[10]。老兵受命监视十二位公主,并以隐身衣遮蔽,彰显了其作为权力行使者的地位,而在其凝视下的公主们则屈居于被统治的地位。这一权力关系映射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老兵作为男性监视者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女性的秘密则无所遁形。
男性的凝视不仅限于老兵对十二位公主的监控,还延伸至婚姻领域。在原版格林童话和安妮·塞克斯顿改编的《十二个跳舞的公主》中,国王都将女儿的婚姻看作是男性间可以交易的物品,只要骑士揭开了国王想要知道的关于公主舞鞋的秘密,不论个人条件如何,都能任意挑选心仪的公主。就这样,女性的身体被转化为男性交换中的物品。如同商品无法自行表明其价值一样,女性缺乏自我定义的能力,其价值完全由男性所界定[11]。在婚姻议题上,公主们作为女性的意愿并未被国王所考虑,她们的主体地位被剥夺,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塞克斯顿颠覆了原有童话中幸福美满的结局,描述大公主和老兵并非“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是“公主们像婴儿被迫远离奶嘴一样从夜生活中被撕扯开”“在婚礼上,她们低垂着眼眸,如同磨损的运动衫一般无力”[5]。塞克斯顿的这一叙述揭示了女性在丧失主体性后不得不服从命运的无奈,以及在男性中心话语权力构建中所占据的次要和不幸的位置。她讽刺了父权社会编织的所谓美好结局仅存在于童话之中,批判了父权制下婚姻的本质[4]。
大公主与老兵的婚姻关系不仅反映出男权社会将女性视为可交易的商品,女性成为被观看和被客体化的对象,还暗含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与惩罚。老兵选择大公主为妻的理由是“他已年迈,因此选择了大公主”[5],将婚姻视为一种奖励而非基于爱情的联姻。除此之外,大公主的婚姻还带有警示作用。通往外界的密道在大公主的床下,由大公主敲响才会打开;是大公主拿盛装迷药的酒,负责迷晕监视者;同时也是大公主在路途中安抚小公主不安的情绪,使出游正常进行。大公主不仅是夜间出游跳舞计划中的指挥者,也是用酒迷晕骑士与老兵的主导者。作为最具有反抗男权社会下制定的常规精神的大公主,因超越了传统女性的规范,而被选中成为老兵的配偶。“惩罚不是朝着终结和否定的轨道滑行,而是沿着调教、驯化和干预的方向前进。”[12]因此,大公主作为最具反抗性的人物,其遭受的惩罚具有强烈的警示性。惩罚和警告都是在婚礼这一公共场合进行,让所有的公主都成了观看者。塞克斯顿改写了传统的童话结局,描绘了公主们“如同被撕裂般的痛苦”“眼神如同破旧运动衫般下垂”[5],揭示了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并非奖赏,而是男权社会施加的规训与惩罚。
二、生存困境与生命价值
塞克斯顿在其著作《变形》中对女性生命价值及其生存境遇进行了深入探讨。格林童话集中大量故事巧妙地融入社会现实与文化构建,其中不乏对女性进行父权规训的描写:女性的人生价值与生活质量往往被男性所左右。无论是被困于水晶棺的白雪公主、陷入沉睡的睡美人,还是被禁闭于森林高塔的长发姑娘,她们共同的命运都是被动地等待王子的拯救,以此来摆脱困境,寻求幸福,实现生命的深远意义与价值[13]。身为自白诗派的杰出代表,塞克斯顿以其坦诚和大胆的自我情感与生活经验表达而闻名。她的诗歌创作时期恰逢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因此其作品不仅展现了她对女性处境的关切,还深刻反思了女性生命的价值观。她对《十二个跳舞的公2ce6b28a06ff9c726021ea8b0765b53eceeb1501f5d4e10c78c57828395b4365主》的改写在保留了原格林童话的核心内容的同时,引入了自身的观点,特别是在作品开头与结尾部分,分别映照了当代女性的生活境遇与生存价值。
女性追求自由的过程不被理解,成为社会中的“他者”是当下女性面临的一大困境。诗歌伊始即提问:“如果你从午夜舞动至拂晓,又有谁能够理解?”作者随即给出了答案,是“逃逸的男孩、瘫痪者的配偶、独行的杀人犯、健忘病患、深夜沉醉的天才诗人、失眠者及埋头苦守夜晚的护理人员”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5]。这些夜间的理解者,拥有着社会大众所未知的个人故事,他们独特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使他们成了社会的“他者”,生活在常规行为规范之外,因此他们能够共情那十二位公主整夜的舞蹈之乐。十二位公主之所以选择在夜间出游跳舞,与她们在白天要遵守公主礼仪规范,受到规训无法随心所欲,自我主体性消解有关。如同那位夜晚呈现真实自我的天才诗人一般,白日里的他们只能隐藏自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在评析童话时指出:“女人把社会价值观内在化以后,她自己就成为囚禁自我的监狱。”[14]无论是对任何男性的爱恋,无论是过往的配偶还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女性在父权文化的社会体系中始终难以自由表达自己、追寻自我的独立,因此女性始终是处在从属地位的“他者”[13]。
女性生命的价值在于通过自我身份的构建得以实现,然而,婚姻与父权制度往往成为限制女性自由的枷锁,导致其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夜间,十二位公主的秘密出游,她们穿越银叶树与钻石树,与英俊的王子共舞,品尝着盛满红宝石的酒杯中的美酒[4]。这些美好的元素——银、钻石、王子与红宝石——象征着女性在挑战男权社会规范、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她们自我主体建构与自我价值实现的体现。然而,国王与常人一样,无法理解公主们的行为,为了揭露她们的秘密并规范她们的行为,国王发布悬赏,甚至以女儿的婚姻作为奖励。
在诗歌的结尾,塞克斯顿写道:“他赢了/舞鞋不会再跳舞了”[5],这不仅意味着老兵完成了任务,更暗示着国王在这场男性与女性、父亲与女儿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十二位公主被永久剥夺了跳舞的权利,大公主被迫嫁给老兵,其余公主则被迫观看婚礼以作警示。女性被迫接受规训,放弃自我主体的构建,再次完全受制于男性。改写后的《十二个跳舞的公主》以这样的结局告终:“现在逃跑的人再也不逃跑了/她们的头发再也不会被钻石缠绕/她们的鞋子也不会再跳破大笑/床再也不会掉进炼狱/随后让她们用路西法舞步爬出去。”[5]故事的结局是十二位公主不再跳舞,跌入炼狱后,再也无法通过跳舞爬出来。福柯指出,现代规训制度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它“压抑自然、压抑本能、压抑阶级、压抑个人”[7]。十二位公主在秘密被老兵发现后,开始受到规训制度的强制制约,被迫压抑自然、压抑本能的快乐、压抑个人,主体性被消解,成为被迫接受命运的木偶人。塞克斯顿通过改写原童话中的幸福结局,反映了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作为觉醒的女性,诗人清楚地认识到,丧失了自我价值的女性也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她要改写结局,引发社会深思,呼吁尊重女性的主体性而非他者形象。
女性生命价值的缺失及其生存困境,不仅体现于其自我主体性的消解,沦为被支配与被审视的对象,更深层次地关联到不平等且缺乏沟通的父女关系。以国王与十二位公主的关系为例,国王作为父亲,每晚将女儿们严密禁锢于房间之内,当发现她们的舞鞋每日破损时,并未选择与女儿们进行对话以了解真相,而是利用王权,公开悬赏以揭露女儿们的秘密,并随意决定她们的婚姻。这种充满霸权、阶级、禁闭与监视色彩的父女关系,使得女性的处境尤为艰难。父亲对女儿的控制欲导致女性失去自主权,沦为父权制度下的附庸,成为父亲满足窥探欲望的工具。简·品彻(Jane Pilcher)与伊美达· 维勒汉(ImeIda Whelehan)对“父权制”(Patriarchy)给出了经典定义:“‘父权制’(Patriarchy)的本意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部落等)由男性首领所统治。家长通常是社会中的长者,拥有对社会其他成员(包括年轻男人、所有的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利。”塞克斯顿笔下公主们在秘密被揭露后的悲惨结局,揭示了在压抑的父权制度下,无声且不平等的暴力迫使女性无法自主掌握个人喜好与命运,只能被动接受父亲的安排,从而凸显了女性自我价值的缺失及其面临的生存困境。
三、结语
安妮·塞克斯顿对《十二个跳舞的公主》的改编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父权制度下的压迫与困境。通过描绘十二位公主在夜晚遭受父亲的禁闭、老兵对她们的全景式监视,以及国王与老兵随意安排她们的婚姻,塞克斯顿展现了女性如何被父权制度规训,沦为被观察的对象和商品。在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婚姻不再是格林童话中的美好结局,而是转变为一种规训与惩罚的手段。
塞克斯顿对女性生命价值与生存困境的深刻思考亦体现在此作品中。首先,女性的生存困境体现在她们追求自由与快乐的行为被视为异常。十二位公主夜间的舞蹈活动违反了父权制度为女性设定的道德准则,她们的行为被视为异类,不被社会接受,一旦被揭露,便面临规训与惩罚。其次,女性生命价值的缺失表现为自我主体性的消解。十二位公主被剥夺了持续跳舞的权利,她们的自我身份构建与认同感受到破坏,沦为父权制度下的附庸,其行为受到严格的监控。最后,在父权制的影响下,十二位公主与国王之间的父女关系表现为一种充满暴力与霸权的权力关系,而非被关爱与呵护。女性被禁闭、监视,并被随意婚配,失去了对自我生命的掌控权。
塞克斯顿的描写揭示了女性在父权制度下的压迫、自我主体性的被迫解体,以及成为被支配的客体形象。女性的自我价值感受到缺失,婚姻在男权社会中成为对女性的约束,而非童话中的救赎。这一现象对当代女性呼吁两性平等、改善父女关系、追求自我主体性的构建与身份认同,实现自我价值与自我拯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唐根金等,20世纪美国诗歌大观[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2] 何宁.论丽兹·洛克海德诗歌中的女性声音[J].外国文学,2022(4).
[3] 郭一.改写童话:翻转的风月宝鉴——安妮·塞克斯顿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赏析[J].名作欣赏,2015(4).
[4] 洪雪花,马全振.凝视与反凝视——安妮·塞克斯顿诗歌的女性主义解读[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5] Anne Sexton. The Complete Poems[M]. Boston.Mariner Books,1999.
[6]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7] 包亚明.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特约编辑 范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