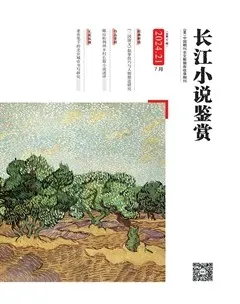真实之血
[摘 要] 作为台湾“新新电影”时期大放异彩的导演之一,张作骥在《醉·生梦死》中延续了对无处归属的台湾底层青年的关注,通过对老鼠、硕哥、哥哥等人生活状态的表达,描绘他眼中的现实。结合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三界学说”和“客体小a”概念,分析导演如何建立起人物的自我认同感、影片片名四字成语和妈妈以及三个男性角色之间的能指关系,并阐释在精神分析视域下角色如何在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中穿越,对了解其如何在影像中建造“另一种真实”世界,能够有所帮助。
[关键词] 拉康 精神分析 张作骥 《醉·生梦死》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1-0089-04
法国学者雅克·拉康引用符号学理论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镜像阶段”理论和“三界学说”。拉康认为人在“镜子阶段”不断以一种“误认”的方式构建自我(想象界),最终进入“大他者”代表的语言符号秩序(象征界)之中并获得主体性。而这种公约是不完全、不彻底的,俄狄浦斯阶段所压抑的乱伦欲望成为原初缺失,“实在界”的原乐(死亡)作为一种匮乏刺激着“主体”在现实世界寻找欲望的客体以寻求短暂满足,而这一具体的人或物始终无法填满这一匮乏,在梦想成真的场景中透露出危险的瘢痕。
《醉·生梦死》在第52届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获得10项提名,并最终赢得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剪辑四项大奖。导演张作骥在访谈中说到,影片所处理的是关于“母爱”的话题。张作骥“喜欢拍男性”,而电Eg8C6SUYJwsUb0JbQ3z4Dw==影也可以看作围绕着三个失去了母亲的男人展开:硕哥、哥哥和老鼠,在对影片的分析中常常将他们与片名中三种状态生、梦、死对应。加之不同的动物能指,我们得到了硕哥—蛆虫—生,哥哥—蚂蚁—梦和老鼠—老鼠—死的联系,而统领“生梦死”的“醉”则和母亲,以及老鼠执意养在家中的吴郭鱼对应。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分析导演如何在影像层面完成人物和其动物能指间的映照关系,并将生、梦、死与拉康三界理论中的“符号界”“想象界”“象征界”联系起来,说明硕哥、哥哥和老鼠三人并不单纯对应于生、梦、死的三种状态,而是穿梭于这三重境界之间。最后,尝试分析三人由于失去了母亲而共享的动力学机制,并说明电影中的世界如何在导演的表现中走向“客体小a”的位置,来到博洛米结的中心。
一、破镜之后:凝视、窗与镜头、银幕
“‘镜子阶段’标志着儿童心智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1],它意味着自我经由认同过程的形成。1950年之后,拉康把“镜子阶段”的概念扩展为一种主体性的永久结构,即想象界秩序的范式。“理想自我”在生命的全部过程中充当对于未来整体性的某种许诺,并把自我维持在预期之中。张作骥作为“眷村弟子”,创作上自然关注那些同样散布在台湾的外省族群,文化上的认同“迥异于台湾本土人的家庭观念以及对个体身份的自觉”[2]。作为台湾后新电影时代重要的导演之一,他在影像美学上继承了台湾新电影时期的写实主义风格,描摹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表现边缘青年的焦虑和迷失,却也有意识地解构侯孝贤式的传统父权家庭,父亲形象或是缺席,或在极端弑父行为下崩塌[3]。“镜子”被打破了,完整的自我也就被揭示为一场神话。放弃在现代化都市中追逐化约身份的努力之后,电影中拒绝被框定、被映照、被秩序召唤的角色却并未获得自由和解脱,他们把自己放逐在高楼之外,徘徊于肮脏黑暗的巷子里,“悲剧性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体会着自我作贱与肉体毁灭的快感和宿命”[4],最终在虫鼠身上看到了自己。
《醉·生梦死》无疑是以老鼠为叙事中心的影片,我们却找不到一个老鼠照镜子的镜头。即使老鼠用摄像机记录“恋爱心得”,导演也将之处理成了他手拿相机背对电视屏幕的样子,于是当他面对镜头时,影像在他的身后,而当他转过头看画面时,也只能看到自己的背影。老式电视里被扭曲的、模糊的、看不到面容的屏幕无法完成镜子的功能。在影片开头,老鼠透过窗户看着一只老鼠濒死挣扎,它毛发残缺,满身油污,却获得了主人公长久的注视,通过视线和名字,导演建立起了两者的对应关系。
《醉·生梦死》有一个一分钟左右的长镜头:白场,老鼠从画面深处走来定为近景,直视镜头,落下一滴眼泪,又慢慢低头、黑场。此处我们先不做“打破第四堵墙”和它代表的间离效果的解读,导演所做的是无比直接地向观众展示老鼠的凝视动作,视线的另一端不是空间层面上、银幕另一端的电影观众,而是时间进程中的整部影片。他长久地、偏执地观察老鼠、虫蚁、鱼,与它们对话,用手机、相机拍摄它们,拍摄远离现代都市的边缘空间,用视线(镜头)捕捉能够自我投射的空间。他劝说老鼠放弃生命(自己失去了生的力量)、希望吴郭鱼老老实实待在缸里(妈妈不要在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意外死掉),即在用这些永远不会做出回应的生物们代替那个过于疼痛、充斥着焦虑、悔恨和迷惘的真相。“幻象域的惰性出场,悬置了阐释的运动”[5],老鼠因为母亲去世、哥哥离开放弃了好学生、好儿子身份(象征界),又无法面对自己间接导致的母亲的死亡(实在界),于是终日游荡在菜市场、小巷和客厅之间(电影中老鼠没有自己的房间),困囿于凝视动作和它运作出的想象界之中,此间母亲的生死不定,像幽灵般回返。
二、摇摆的主体:“生”“梦”“死”与三界理论
上述的“镜子阶段”与想象界的概念紧密相连,老鼠在理想自我破碎之后依托动物能指,以凝视、阐说重建的想象界呈现为《醉·生梦死》这电影。除想象界外,拉康三界理论中还区分了象征界与实在界。他结合索绪尔的语言学重新阐释了俄狄浦斯情结,婴儿只有放弃“想象的阳具”,转而认可只有父亲的阳具能够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才能在符号秩序中获得位置,作为“缺失的主体”登录象征界。拉康认为,符号秩序即语法,象征界在某种意义上划出了人类的界限,或者运用合法的说辞表达自己的欲望,于是我们也被迫服从这一律法。“‘实在界’是拉康最困难但同时也是最有趣的概念之一”,处在世界发源的、前象征的位置,因为在象征秩序之前,也就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是“某种受到压抑并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运作的东西,它以需要的形式闯入我们的象征性现实”“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未经分化的块状物,我们必须经由象征化的过程,从实在界区分出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6]。实在界与弗洛伊德的“创伤”概念联系在一起,即与孩子观察或幻想出来的父母性交场景有关,它是一段无法象征化的记忆,是无法被语言转化的剩余。与实在界相遇,只有回到母亲的腹中,回到被分娩之前与母体合二为一状态,因而这个相遇本质是不可能的,它意味着原乐的获得,也就是死亡。硕哥和生、哥哥和梦、老鼠和死的对应强调了人物的主要属性,而“在匮乏与剩余意义间摇摆不定,乃主体性固有之维度”[7],所有角色实质上无法只安居于实在界、想象界或象征界这三种的状态的某一状态中,而是永远被原初的缺失驱动着,追逐现身于符号界的某物,却始终无法真正实现欲望。
硕哥与象征秩序联系非常明显,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金钱和女人是费勒斯中心主义下男性权利地位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志,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他西装和精致发型的背后,是已经去世却被说成是在美国需要自己资助的母亲和追求俊俏外形进行的整容手术,实在界隐隐现身,精心营造的现实便崩塌为谎言。哥哥的屋子里贴满讲述爱情故事的海报,他工作的电影公司也表现为一条贴满了爱情电影海报、灯光昏暗的走廊,仿佛想象界的实体。但这样的爱情从影片开头老鼠讲过的因爱自杀开始就是不可信的,令他打破符号秩序、逃离母亲令人窒息的忧愁和关爱、远走美国所追寻的欲望幻想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老鼠代表的是死,实在界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周围:阿努比斯纹身、母亲的尸体、随身携带的小刀……未被压抑和转化的死亡驱力化作这些惹人厌恶、引起恐惧的污秽、斑痕。
也就是说,尽管三个角色因为自己的人格特点格外符合“三界”中的某些特征,我们却不能满足于他们和生、梦、死的一一对应。影片开头,老鼠的镜头从城市中发现刚回家的哥哥,随即开始了一段主要人物的日常状态描述:哥哥脱下外衣在房中开始健身,硕哥则穿上衣服准备出门“上班”,临走时听到哥哥房间里传来他用英文打电话的声音。画面一切换,老鼠也坐在菜摊前面吆喝着——仿佛三个人都或多或少和正常运转的世界有关,并非隔绝于符号界之外。不同于希区柯克依靠镜头前推以暴露画面中的异质性斑点,三人所竭力隐藏的实在界因素首先是以声音形式出现,即对白中的“你哥听说在美国想不开是不是”“等我出国以后,我妈出事”“一直到我们的女儿出生,我才知道,他竟然把我们的钱,通通拿去给他女朋友治病”,使本就破碎的叙事片段更加捉摸不定,而后从一小时十八分左右开始,又在影像中密集被表现出破碎:糟糕的性爱、表姐拿着开瓶器向硕哥的复仇,以及妈妈的尸体。这些段落的表现手法也十分相似:画面中先是狭窄的门将其框定为有限的面积,接着是摇晃的长镜头特写和疼痛的叫喊、诘问和呕吐的声音,主人公的正脸并未出现——它们因为作为人物的某种“前史”而必须被呈现,却无法被呈现。结尾仿佛是开头的一次复现,老鼠拎着刚买的猪头遇到哑女和硕哥,一转身前者却消失不见,镜头继续跟着后者前行,走回那条幽暗的小巷——实在界的血色之后,又辅以想象界梦般的暖意。
三、醉客逆旅:三界的中心,客体小a或“醉”的世界
客体小a是理解拉康理论的核心概念,它作为缺失(实在界)呼唤欲望(想象界)在现实生活中(象征界)不断寻找能够使之暂时得到满足的对象,因而处在博洛米结的中心——在三大秩序的交接之处。在《醉·生梦死》中,我们能找到“烈酒—母亲”与“爱情对象—丧母的儿子”两段相继的欲望客体-成因关系:对于母亲来说,淡蓝色的酒是她暂时逃离心碎的通路,是欲望客体在现实世界的表现方式,而它由于无法被符号界化约,最终也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母亲的出场总是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南管戏曲,就像《后窗》中打断斯图尔特和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吊嗓子女高音,作为一种幻听语音象征着无法摆脱的母性超我,象征着父性权威衰亡后充满控制力的母爱。当哥哥与母亲爆发争吵,质问她的担忧到底来自何处时,母亲训导被揭露为对其身份的不理解、不认同。哥哥最后不断念叨着“我永远是你的儿子、我永远是你的儿子”。导演在这里试图展现的母爱意味着超我和本我本质的相连,符号界与实在界在母亲身上重叠为一体两面,母亲是承担了训诫功能的继任父位,也是无法逃脱、不可割舍的原初之乐。老鼠对哑女的追求来自填补母亲丧失的遗憾:老鼠和母亲、哑女对称的共舞片段中,同样的近景、手持镜头和环绕运动,只是后者发生于昏暗灯光下的朦胧环境,显得暧昧不明;母亲裙子上的宝蓝色延宕到哑女身上,也延宕到表姐漂染的头发上——哑女和表姐只是两个失去母亲的男人寻找的欲望客体。现实领域缺失的小客体,支撑着现实:母亲的不在场“推动片中的所有人去建构、重组他们彼此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母亲成为角色确定自身的客体小a。
沿着导演在片名中利用一点隔出、强调的“醉”字,继续分析其背后的精神分析意涵,除去母亲和醉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醉”同样是影片中其他角色的精神状态,他们和母亲一样用酒逃离失败的现实世界和无法挽回的丧失,而不论醉酒后的他们如何说笑或狂欢,画面中始终无法忽视的是蓝色的酒液和骷髅头形状的杯子——不可化约的实在界之现身。这一否认的、逃避的、恍惚的姿态,给予角色们充分的空间根由自身的缺失设置意义,同时为之支撑起现实的框架,成为他们另一层面的客体小a。
学者杨小滨曾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的古典诗学相结合,认为侯孝贤电影中的自然或乡土能够作为使角色与之认同的理想自我,即将外在自然作为自身的镜像。在张作骥这里,那个宁静超脱的前现代世界业已崩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代表的那种投身自然怀抱的慰藉不复存在,人物无法在高楼、市场、舞厅,所有这些现代社会和其遗址构成的外在世界中窥见自身。也许我们可以在此延续杨小滨的观点,给“醉”字赋予最后一层含义:无法支撑镜像投射的外在世界离开了想象界范围而来到博洛米结的中心,作为以老鼠、硕哥和哥哥为代表的台湾底层青年们所感知的、携带着自我毁灭的欲望追逐的现实,交织着生、梦、死三界,成为“醉”的世界,它被符号允诺的幸福生活神话抛弃或放逐,时而给予稍纵即逝的幻象,却始终笼罩着痛苦和焦虑的底色。张作骥持续了整部电影的非线性剪辑、手持摄影就是试图描绘这一“醉眼”中的世界,在这里,时间似乎循环往复,人物在相似的场景中游荡。
四、结语
齐泽克的电影机器理论揭示了完满叙事表面下暗藏的危险深渊,“对意识形态操控反戈一击,将幽暗的影院变为精神分析的现场”,呼吁观众从虚构的影像中发现“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张作骥则展现了那些与黑暗迎面相撞后的青年的世界,“从一种历史性、带有伤痛的意识转变为一种对现实的当下的关注”。一代人书写一代人的成长,新新电影一代的张作骥与侯孝贤的前现代怀旧、杨德昌的现代性审视或蔡明亮的后现代挣扎都不相同,他所创建的,是交杂着规则、欲望和死亡的醉生梦死的世界,父(母)的幽灵无法安葬,欲望携带沉痛创伤投向无辜的他者,故事没有结局,在时空的迷宫里徘徊,爆发于一场血色的死亡。
参考文献
[1] Jacques Lacan.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go[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53(34).
[2] 于丽娜.边缘身份·青春成长·内心素描——张作骥电影的作者特征[J].当代电影,2012(4).
[3] 孙力珍.父权的式微与认同的焦虑——论张作骥电影中“真实台湾”的在地性探析[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4] 李道新.父权的衰微与身份的找寻2008年台湾电影的“成长论述”及其精神文化特质[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2).
[5] 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6] 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7] 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特约编辑 范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