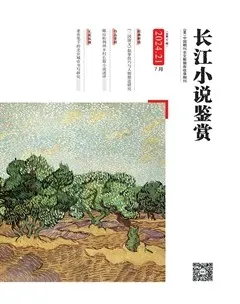沈从文《边城》中的宗教情怀
[摘 要]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小说以诗意的情绪、宗教般的虔诚,描写了湘西边境茶峒小城少女翠翠和外祖父相依为命的纯朴宁静生活,以及这份纯朴宁静生活中无可奈何的忧伤与悲哀。小说字里行间浸透着佛家的通透与悲悯,寄托着沈从文独特的宗教情怀,其宗教情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山水坐忘中蕴含的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人生“偶然”与“必然”交织的宿命关照,生死齐一的归宿意识。小说中处处流露出的佛理禅意,也给洋溢了淡淡诗意理想的湘西世界涂抹上了一层流星闪电般美丽的宗教圣境。
[关键词] 沈从文 边城 宗教情怀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1-0073-04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创作于1934年,小说通过描写湘西边城少女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俩美丽、朦胧而令人哀愁的爱情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自然和谐、诗意纯美的湘西生命世界。在小说中,忠厚朴实的外祖父、清纯灵动的翠翠、秀拔出群的傩送、慷慨豪爽的天保……与温柔亘古的河流、清远幽静的山林、绿色逼人的翠竹和白日里喧嚣夜里静谧的渡船一起,构成一幅像诗像画更像音乐的优美图画。
《边城》中的一切人、景、物都像珍珠那样纯净自然、晶莹剔透,人在自然山水中行走过活,自然与人水乳交融在一起,是人装点了自然,亦是自然美化了人。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只能在一种无法逃遁的人生的“偶然”与“必然”交织的宿命寂照里淡定成永远的记忆。小说中的男主人傩送和天保,一个出走,一个身亡,一个顺乎自然人情的爱情故事不得不以宿命性悲剧告终。最后,伴随着翠翠外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平静的去了,曾经暗恋翠翠母亲的杨马兵代替外祖父陪伴着孤独的翠翠。边城中的人事更迭,边城中人的生与死,如山间的清风、江流中的绿水、水边的白塔一样自然平常,他们异常朴素通透的生死观与自然界的时序流转泯然一体。独特的宗教视角,使小说氤氲着一层如电光火石般美丽忧愁的宗教情怀。
一、山水的坐忘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佛家的坐忘,是一种自在、自然、自适的生命状态,坐不是忘,是不执,是破除执碍,是自然的人化,人化的自然,是自然与人的浑然一体,水乳交融[1]。
坐忘中的自然是诗性的自然,坐忘中的山水是灵性的山水,坐忘其实是人与自然山水的物我两忘,浑然一体。小说《边城》处处展示的就是这种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优美境界。故事的发生地,茶峒小城依水而生、依山而建,与自然山水泯然一体。“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周围环境极其和谐,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边城人生活的环境完全是依据自然走势,滨水临崖而筑,且与湘西的山、水完美融合于一体,丝毫不显得突兀,也不存在人为刻意地改造、装饰,全是一派自然谐调,但却令人眼目为之一亮,倍感自然舒适,独具自然天成之美。
同时,居住在这一派自然天成境界中的人也都是自然化的人,带有人类之初才有的纯然之气。小说主人公翠翠和傩送、天保兄弟是作为自然之子贯穿小说始终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巧,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不仅天生具有一种自然之美,且举止行为也处处流露出自然之女的天真无邪,毫无人为社会的心机。当翠翠撑完渡船,站在小山头玩耍时,她也会自然地“且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自然之女翠翠就是如此自然任性地一天天、一年年游玩成长于山水之间。而男主人公傩送和天保也是一派淳朴的自然之子模样,“两个年轻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小说中这些人物从外表举止到内在精神都流溢着一股山水的淳朴自然健康之气,毫无忸怩做作之态,自在,清透。边城的山山水水让他们如珍珠般晶莹剔透,他们又给自然山水涂抹上了别样的灵气,自然与人浑然一体[2]。
边城世界中的自然也是人化的自然,独具人的灵性情感。文中的一滴水、一朵花、一片云、一只鸟、一阵风、一只狗都包含了人的情感意绪。伴着翠翠的黄狗,会随着翠翠的情绪波动而独具人的灵性情感,当祖父撑渡船靠岸时,黄狗会非常尽责地“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为尽职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靠岸。”黄狗对于主人不仅是忠诚尽职,主动努力地为主人分担职责,同时黄狗也是翠翠最亲密的伙伴,它会陪伴翠翠一起上街,一起玩耍,一起忧愁,一起发脾气。当祖父讲城中久远的战争故事时,黄狗也会安静地“张着耳朵”,陪翠翠一起听;当翠翠和初次见面的傩送置气时,黄狗会“警告水中人似的,汪汪地叫了几声”,当傩送拿起手中白鸭吓唬黄狗,“黄狗为了自己不被欺还想追过去。”当爷爷要还回过渡人给的钱,翠翠帮忙拦阻,与过渡人有所拉扯时,“黄狗为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见一致,也便在翠翠身边汪汪汪地吠着。”小说中的黄狗俨然已成为相依为命的祖父和翠翠家的一份子,积极地融入并且参与祖孙俩每个平凡宁静生活的瞬间,和主人公共同劳动尽责,与祖孙俩同欢乐、共悲喜,具有人的灵性情感。
总之,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世界是一个诗意化的境界,天、地、山水与人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沈从文曾写道:“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山花,翠竹,流水,微风,黄昏,雾霭,杜鹃以及自然精髓化成的水目含睇,手足微动,如花笑靥,撸歌互答……一切都在一片浑然中被一片神秘的光彩所笼罩,幻化成一个灵魂的寄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在这个自然灵性的世界,人忘却了自己,山水忘却了自身,人已不是单个的人,自然已不是那个纯然的自然,自然与人和谐的浑化为生命的一体,同哀乐共寂寞,在山水与人的无痕的沉淀与涅槃中超脱出一种神性所在的妙境、生命所暂居的安适寄所[3]。
二、宿命的寂照
佛家提倡对世间万物静观寂照,于静观寂照中明了世间的无常与恒常,从而领悟存在的根本、人生的偶然与必然,寻找生命的真谛与灵魂的归宿。对于《边城》中蕴含的人事哀乐、爱情命运,作者并没有加以道德理性的衡量与纯粹因果轮回的评判。但文中人物的人生命运、爱情悲剧却似乎被笼罩在一种无可逃脱无法说清的定数里聚合浮沉,如沈从文在《水云》中所强调的,“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4]。”
无疑,《边城》中人人都是善良朴素的,都是怀了对人生平凡的期许,他们一天天宁静地把日子过活,他们心心相印且没有任何勾心斗角。但正是因为命运无常,因为一份偶然中蕴含的必然,宽厚淳朴的祖父虽然极早就看到翠翠正走着和她死去的母亲一样的老路,祖父既没有抱怨已然逝去的翠翠的母亲,也没有人为地强行去改变翠翠的命运轨迹,“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眉毛长,眼睛大,皮肤红红的。也乖得使人怜爱……但一点不幸来了,她认识了那个兵。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祖父看看那种情景,明白了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五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的一切全像她的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外祖父从一开始就知道翠翠从性格、情感、到人生轨迹整个都是重复着她母亲的老路,包括最后的悲剧性命运,但是外祖父从一开始都没有人为过度地去阻拦,去人为改变些什么。虽然他内心深处也为自己疼爱至极的孙女忧心,但他始终认为,翠翠母亲的命运,包括翠翠的命运,全由“天”负责,是命运的安排,自己只有顺应命运。这里固然有湘西传统农业社会固有的宿命意识,其实从某种角度也体现了湘西人无意识中参透佛理的通达情怀[5]。
正因平凡生活中处处的不凑巧,一份偶然与必然交织的宿命,善良朴素的小女子翠翠与同样善良朴素的傩送之间的爱情也注定是隔膜的、不确定的,要无望地等待茫然的未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中翠翠的爱情悲剧并不具有戏剧性,也没有任何冲突,却尚未明明白白开始就在一次次误会叠加中戛然而止:爷爷对翠翠与傩送之间情感的误会,“但老船夫却做错了一件事情,把昨晚唱歌人‘张冠李戴’了。”加之爷爷的木讷和犹疑,源于没有“碾房”的自卑与善良人的自尊,“他明白翠翠不讨厌那个二老,却不明白那小伙子二老怎么样。”[2]翠翠对二老的误会,“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大老的殒命,二老对外祖父的误会,“虽老船夫言辞之间,无一句话不在说明‘这事有边’,但那畏畏缩缩的说明,极不得体,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这件事曲解了。”船总顺顺对爷爷的误会,“二老父子方面皆明白他的意思,但那个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两人便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包括最后二老的出走,一连串生活中无可解释、无法解释的偶然误会,导致翠翠爱情的必然悲剧,让人可把握又无可把握。于是,翠翠与二老的爱情悲剧就在一种宿命里无可逃脱,正如同翠翠母亲命运一样。尽管翠翠、祖父、顺顺、傩送与天保之间有一连串的误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互相抱怨,甚至是怨天尤人,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朴素的观点:“若论当地风气,这些事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二老当真喜欢翠翠,翠翠又爱二老,他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但不知怎么的,老船夫的关心处,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皆有一点误会了。”
“世界虽极广大,人可总像近于一种宿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经验到他的过去相熟的事情。”对于这一连串的误会,一连串的命运轮回,边城人是忍耐与顺天应命的,爷爷也是宽容的。当他意识到翠翠将要遭遇到同母亲一样无可逃脱的命运时,他是知天认命的,“一切皆是命。”将一切聚合哀乐交给“天”,边城人内心深处是这样朴素地渗透着佛家的随缘自适与静默达观,因而即使是人生的残缺与悲剧,我们也似乎体味不出特别的悲痛,只是让人心里生出一阵阵悸动的美丽。沈从文所做的,就是将这种“生命的偶然与必然”赋予一种忧愁的美丽,使一切爱憎和哀乐尽可能化解并掩映于“偶然的跳脱生机中”“美丽使人愁”或许正因为这份经历过佛家静照洗涤的忧愁的衬托,美丽本身才更能触动人心。
三、生死的淡然
“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是故说名轮转生死”,佛曰:“缘起则生,缘落则灭。”佛家的生死离合,是自然的,是静默的,也是达观的,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也处处渗透着佛家通透自然的生死观。
面对生死聚合,《边城》中的人们绝不喧哗闹腾,饰粉添彩,也绝不龇牙咧目,悲哭怒嚎。生就如翠翠一样,像河边翠竹风里、雨里、阳光里长大,像山光晨黛,水长水短般自自然然、活活泼泼;死时就如同面对一片云彩的消逝,一朵花的凋零般自然,边城人的爱恨生死都渗透着佛家的自然平常。当祖父得知翠翠母亲殉情后,祖父没有哭天恸地,甚至也没有对猝然逝去女儿的一丝丝怨尤,“事情也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祖父把对翠翠母亲逝去的悲哀深深消解于如水流般的平常日子中。祖父朴素地认为:“日头,雨水,走长路,挑分量沉重的担子,大吃大喝,挨饿受寒,自己分上的皆拿过了,不久就会躺在这冰凉土地上喂蛆吃。”人生于自然,当也归于自然,这与自然界的花鸟虫兽并无区别,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最普通的道理,也是佛家生死观的精髓之处,全部平常地渗透于边城人每个晨钟暮鼓的寻常日子里[6]。
小说中不光是祖父的生死观渗透着朴素的佛道禅理,边城中的男男女女对于人事的悲欢离合、生死聚灭的理解,莫不渗透着这份朴素的认知。文中大老的突然殒命,一个暴风雨之夜,随着屋后的白塔坍塌,祖父也在雷雨将息时于睡梦中猝然离去,一切都平静而自然,简简单单的两块木板决定了一个人的死。不管什么原因,逝去的已然逝去,活着的人也没有任何怨尤。“日子平平地过了一个月,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一切的生死聚合,平常的一个又一个日子是最好的良药。但是,生者都还当一如既往地把日子平常过下去,船总顺顺对着河畔风雨里依然摆渡的孤独的翠翠说:“翠翠,爷爷死了我知道了,老年人是必须死的,不要发愁,一切有我。”那自来填充祖父位置,和翠翠做伴的杨马兵对翠翠说:“听我说,爷爷的心事我全都知道,一切有我;我会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我会安排,什么事都会。”与翠翠相依为命的外祖父去世了,全茶峒的人都来帮忙,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帮翠翠安排好外祖父的后事。而先前和外祖父因儿孙情感有着难以说清误会的船总顺顺,早将那些无需说清,从来也不会造成边城人冷漠隔膜的误会全然忘却了,立马过来帮忙,带领大家帮助翠翠料理外祖父的丧事,对于孤苦无依的翠翠,更是充满关切地请翠翠到家里去住。此时,曾经暗恋过翠翠母亲的杨马兵自然地代替外祖父的位置,陪伴着翠翠。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边城》人一种彻底的善良,一种别样的生命观,一种渗透着佛家悲悯通透的生命哲学观[7]。
正是在这样一份清静自然的宗教情怀烛照下,《边城》人的生命在这世上便如流星闪电般美丽,不粘着,不纠缠。爱与死不分离,因爱而思索死,在生中窥见美,唯其如此,生才不显得负累,死亦不意味着恐惧。“生命永生”也不再是一个神话,一个虚妄的乌托邦,不再是一串注定要失落破碎的梦幻。《边城》的人正是以他们虔诚、善良、平常,获得自身的永恒。
四、结语
正如沈从文反复强调的“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沈从文在小说《边城》中以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诗意的语言、哀伤的笔调,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世界,寄托着他对故乡湘西的深沉眷念,对田园牧歌世界的无限想象,对健康优美生命形式与传统道德重建的无尽期待,以构筑他理想的人性人生的“美好世界”。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黔小景[J].北斗,1931(3).
[2] 沈从文.边城·湘行散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M].山西:北岳出版社,2002.
[4] 沈从文.水云[J].文学评论,1934(4).
[5] 沈从文.湘行散记[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6] 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7] 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特约编辑 范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