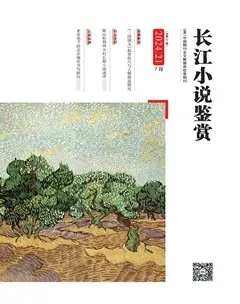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视域下的郁达夫小说研究
[摘 要]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女性解放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可规避且受到学者广泛探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为女性解放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作家郁达夫始终将抨击封建主义、揭露社会黑暗为己任,在其诸多小说著作中利用独特方式关注并呈现中国女性命运,描绘不同时期的中国女性形象变化过程。基于此,本文以郁达夫小说集《春风沉醉的晚上》入手,在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视域下针对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展开深入探讨,以此来揭示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女性观 郁达夫 女性形象 两性关系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21-0045-04
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女性观与方法论,不仅针对不同时期女性家庭地位、历史地位、社会地位予以阐述,还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到的压迫的本质、根源等进行阐述。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提倡构建平等、互爱的两性关系,从根本上转变数千年男尊女卑的观念,为女性解放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其小说集中从不同历史角度揭露女性受压迫现状的问题。但从既往文学研究中可以看出,文坛有关郁达夫小说的研究多集中在“性苦闷”等研究上,针对郁达夫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视域下深入探究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对于拓展郁达夫小说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本研究还可以为新时代女性解放提供有益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主张以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出发点,从发展角度来看女性与两性性别问题[1]。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提倡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女性及两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人类历史立场上,就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进行讨论,阐明了“私有制是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并指出要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消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观念。第二,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所强调的就是女性独立与女性解放问题。认为在男女交往中,女性首先应享有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利,随后才应该尽到作为女性的义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更加强调女性的个体、个性解放,只有实现女性个性解放才能实现女性真正解放。同时,马克思的女性观也指出,妇女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潮流,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女性会获得解放且终将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实现共产主义后才能使两性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爱关系,从而使男女之间的关系实现真正的和谐,促使女性获得彻底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视域下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1.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奴”类女性
1.1父权压制下的逆来顺受的家庭奴仆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认为,在一个家庭中,男性(丈夫)这一角色的属性就是可赡养家庭成员,同时也是具有良好经济来源的人,所以促使“丈夫”这一家庭角色能够凌驾于法律规定之外。所以,相应的也就导致在整个家庭中,男性(丈夫)通常可以将其归属于资产阶级中,但是女性(妻子)则隶属于无产阶级[2]。为此,在父权社会下女性毫无地位可言。而郁达夫小说集《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所构建的“贤妻良母”女性形象便是父权压制下的产物。
一方面,基于父权压制,郁达夫小说中女性只能依附丈夫生存,是逆来顺受无个人意识的扮演者“贤妻”角色。《茑萝行》中“我”的妻子,在“我”的长期凌辱下,最终不得不成为一位对家人忠诚不二、逆来顺受的“贤妻”[3]。“我”对她的冷淡是对一种传统的、由父母决定婚姻的反抗,而她只是用一双眼泪汪汪的眼睛,静静地望着“我”。“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妻子发泄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压迫和屈辱,而她只是在憎恨中一次又一次地宽恕“我”。可见,在郁达夫小说中女性不但要经受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要经受男主角的暴力,其对来自父权的压迫毫无抵抗意识,只会顺从、容忍,会乐意扮演“贤妻”角色。
另一方面,父权压迫下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不仅需要扮演“贤妻”角色,更重要的是要扮演“良母”角色,女性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将女性与孩子紧紧绑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认为自然生产是制约女性地位的重要因素。在封建社会中正是由于女性具备生育能力,促使人们将女性与孩子牢牢拴在一起。基于此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女性不得不扮演“良母”角色。郁达夫小说《茑萝行》中,“我”对这个新生的婴儿并没有太多的感觉,而“我”这个做父亲的甚至对这个婴儿充满仇恨,“我”看着新生儿对妻子说道:“你看看他哭泣时额头上的青筋,难道不是他神经质的证据吗?” “我”甚至认为孩子患有神经质,基于此种认知孩子的抚育重任则落到妻子身上。此外,郁达夫小说《茫茫夜》等作品中均塑造了女性的“良母”形象。
总的来看,郁达夫在小说中将美丽温顺的传统女性的屈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奴”性柔弱和顺服的表现。
1.2专制制度下人格缺失的底层劳动奴仆
恩格斯对专制制度下的女性地位进行阐述,位于底层的劳动女仆通常都会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也正是通过此种方式才能促使男性拥有并长期巩固个人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制度,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无条件的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3]。在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下,女性成为社会最底层,《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便描绘了侍女等女性形象,此类女性在专制制度下无话语权和独立人格,只能仅仅依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生存,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对女性的压迫。
一方面,郁达夫通过对底层女性的刻画,将在封建独裁统治下处于下层的女性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揭露了女性在社会底层的悲哀与无助。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此类主人公厌恶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苦苦追求并寻找自我实现价值的途径。在生活不尽如人意情况下,底层女奴则成为主人公“零余者”的消遣对象。小说集《春风沉醉的晚上》《祈愿》中主人公便是“零余者”,作为留日归国学生,在归国前一心想要打破社会腐败风气,“戒酒戒烟戒女色”,但当主人公抵达上海后,自身感受到孤寂,非但未实现戒烟戒酒,还出现了性欲伸张,当性欲无法得到满足时,主人公在“鹿和班”邂逅海棠。郁达夫笔下的海棠相貌平庸、性格愚钝,忠厚老实的性格让主人公动了一丁点怜悯之情,但当海棠悲伤时,主人公却劝说海棠:“明朝我帮你去贴一张广告,替你找一些有钱的老爷吧。”可见,虽然主人公与海棠在一起,但仍一味地要海棠接客。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并未将海棠视为独立个体,仅将其视为性交易对象,从侧面反映出男性在封建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底层女性尤其是行首仅仅只是男性的性欲发泄对象。而面对此种压迫,郁达夫小说中的此类女性只能遵循封建制度,并不敢奋起反抗。
另一方面,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同样塑造了典型的社会底层妇女形象——侍女。如果将郁达夫所写的行首形象视为没有话语权和独立人格的女人,则其所撰写的侍女形象则可视为无鲜明的性格特征。《银灰色的死》中郁达夫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的酒馆侍女形象,她言语不多且同男主人公交往时如同朋友一般,是主人公的倾诉对象。在《沉沦》中酒楼侍女则是作为主人公的性欲对象,当主人公迷迷糊糊被酒馆侍女拉到酒楼中时,主人公的心思便离不开那位酒馆侍女。在《逃走》中婢女莲英同样是主人公的欲望对象。在此类作品中,“她”是一个沉默的、没有发言权的、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只有依附于主角而生存,可以被视为一种“性符号”的女性形象。
综合来看,在郁达夫笔下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人格缺失的“行首、侍女”,其本质上均是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逆来顺受的奴仆,是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奴”类女性。
2.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思想夹杂的女性
2.1个人意识觉醒但留有封建残余思想
20世纪初期,中国正处于战乱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出现巨大变迁,处于这一时期的女性思想方式发生转变,个体意识逐渐觉醒,但仍然无法摆脱传统封建残余思想的桎梏[4]。
其一,在社会变革的早期,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但其仍缺乏突破封建观念束缚的勇气,最后不得不向封建社会与思想妥协。《过去》中的女性“老三”便是此种形象,老三曾暗恋李先生,但李先生当时心中只有老二,老三忌惮世俗眼光,最终压抑情感远嫁他人。而在老三丈夫去世后,老三再次遇见令其心动的李先生,但由于已经结过婚,受到“守妇道”这一观念的束缚,老三再次选择放弃。经历一系列变故后,老三不断压制自己对李先生的情感,最终到情感熄灭。由此可见,在《过去》中,老三受到来自封建传统道德规范的限制,尽管她已经拥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并试图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但其仍然没有勇气打破传统封建伦理限制,直至最后她不得不为了守“妇道”而放弃幸福。
其二,社会转型初期,郁达夫笔下女性自我意识增强且反抗旧伦理纲常,但对于传统封建思想仍存在依赖性。《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便塑造了如此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郑秀岳是一名个人意识极强但具有较强依赖性的女性。当好友不在身边时,郑秀岳首次失去心灵寄托,当李文卿喜新厌旧时郑秀岳再次失去精神寄托,而当吴一粟失业且重病缠身后,郑秀岳又一次失去心灵依托。事实上,郁达夫笔下的郑秀岳一生都在寻找“火一样的爱”,但其并未对此做出努力,一味地将心灵、情感寄托于他人,此类女性虽然在思想和行动上具有自由性,但仍然存在对男性和封建伦理纲常的依赖,其最终结局必然同“奴”类女性一样走向灭亡。
2.2个人意识增强在黑暗中奋起反抗
郁达夫的作品中也有一种女性,她们处于迷茫和困境之中,通常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属于伦理纲常中视为“丑陋”的一类女性,具有性格乖张、崇拜和追求强权等特点,通常用婚姻的背叛和个人的享乐来对抗旧社会的忠贞观、取代旧社会女性的博爱精神。
其一,以婚姻的背叛反抗旧社会忠贞观。郁达夫小说集《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河》中所塑造的小妾形象便是如此。《秋河》中吕督军的小妾是个人意识极强的女学生,她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压迫采取反抗态度。小妾本就是吕督军“半买半抢”来的,虽然享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但其在精神层面尤为空虚,其所旺盛的性欲被压制。与此同时,其与吕督军之间并无情感,在与吕督军发生性关系时只是履行应尽义务。她无法忍受没有感情的婚姻,进而选择奋起反抗。起初是被仇恨蒙蔽双眼大范围接触男性,将男性视为“肉做的机器”,最终由吕督军留学归来的儿子唤醒心底的欲望,开始与其欢愉。此类女性形象可以被视作“无羞耻心的妇人”,从本质上来看,此类女性本身就是受害者,男主人公压抑其内心最真实的欲望与性需求,其所奋起反抗的对象不仅是男主人公,更是对社会制度的反抗,但此种反抗方法仍然是错误的。
其二,以个人享乐来取代旧社会女性的博爱精神。郁达夫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里李文卿就是这种类型的人物,其是一个完全奉行金钱万能主义,追求肉体享乐可以获取精神上满足一次又一次超越道德底线的“女金刚”。在李文卿看来,传统美德毫无价值,金钱才是万能的。可以说,郁达夫笔下的李文卿是“虚荣拜金”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既具有前卫大胆的恋爱观念,又一味地追求肉体享乐,甚至勾引自己的父亲、老师与其发生性关系。此类女性虽然打破了传统道德束缚,但抛弃了原有价值观。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郁达夫笔下的女性“行为放荡”“性格丑陋”,但是,其思维和行动是自由的和积极的,与“奴”类女性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区别,其个性更为清晰且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尽管此类的女性最终结局仍是悲惨的,但至少此类女性拥有独立意志。
3.社会公共领域的“新时代”女性
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曾指出女性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在社会变革与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影响与重要作用[5]。郁达夫的小说紧紧围绕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主题,以新时期女性形象的书写,展示新时期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水平。
第一,在战争与压迫面前,郁达夫所塑造的这一类型的女性并不像郑秀岳或李文卿那样肮脏,相反,她们依然保持着纯真,憧憬着美好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追求着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陈二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陈二妹性格乖巧,魅力十足。小说中的“我”由于住房价格的上升被迫住进了贫民区,最后在一家烟厂遇到了陈二妹。陈二妹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还得忍受着上司的骚扰,即便是这样她也没有忘记把自己攒下来的钱和“我”分享。“我”把辛辛苦苦得来的面包和香蕉分给了她,她还在担忧“我”是不是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的,而当“我”解释后她又害羞地看着“我”并向“我”道歉。可见,郁达夫笔下的陈二妹虽然受到工厂主压迫,但其并未像同一时期其他女性那般被世俗污染,仍不忘初心。
第二,在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同时,正确思考女性解放问题。《她是一个弱女子》里的冯世芬就是一个具有理智和意志的女人,她敢于打破传统习俗,通过自己的奋斗争取到新时代女性应有的权利。在这种传统的教育下,冯世芬长大后成了一个懂得尊重长辈、懂礼貌的好姑娘。然而,这个看上去很保守的女人却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抵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并积极投身革命建设中。与此同时,在小说中冯世芬逐渐把“革命”的自觉转化为现实,她通过写信与二舅陈应环谈革命,力求做一个“新世纪革命”的人。最终,她放弃封建意识形态奋起抗争,敢于打破封建主义的囚笼,为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与二舅私奔并进入工厂打工,最终获得经济独立。
与郑秀岳、李文卿等女性类似,陈二妹、冯世芬等同样受到时代和制度压迫,也曾陷入迷茫,但其并未追求暂时的享乐,而是不断发展自身,丰富思想境界,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经济独立、婚姻自主”的新时代女性,其始终能够保持澄澈的内心,在压迫中不断觉醒,进而实现全面发展[6]。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郁达夫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郁达夫小说作品各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觉醒存在显著的发展特点,即由逆来顺受的受专制压迫的女性到转型初期新老思想交错的女性,再到经济独立、乐观坚强的“新时代”的女性。可以看出,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其对封建独裁统治下的非人本性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对自身的境遇进行正确抗争,其不再是追求一时之快、个性丑恶的“女性”形象,而是积极投入到社会的建设和革命的建设中去,勇于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并未得到彻底的解放。可以说,郁达夫作品中的“反抗者”和“顺从者”的命运都是悲剧的,同时,郁达夫笔下小说也反映了封建父权、私有财产和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暗示了女性解放之路的艰辛和曲折。
参考文献
[1] 谭婷婷.压迫与解放: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研究[D].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24.
[2] 刘艳萍.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视域下的郁达夫小说研究[D].西华大学,2018.
[3] 郑依晴.析《茑萝行》的反讽性[J].文学教育(下),2012(2).
[4] 陈娅.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J].西部学刊,2023(3).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郑琪,吴立红.论新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观[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3).
(特约编辑 杨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