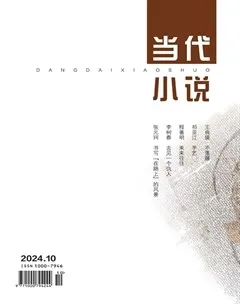妮子是一匹驴(短篇小说)
1
老莫决定去老花家看驴。响水村的老花要卖驴,便宜,只要五百,集市上一头成年驴卖到两千块。老莫觉得,老花的驴卖那么便宜,肯定是他的驴有问题。第一可能是有病。无论人还是驴,有了病就不值钱,就像那年莫大夯花两千块钱买了个四川媳妇,结果那女人有痨病,总咳血,不到一年就死了。第二呢,驴是好驴,但不好调教,只吃料不干活,白搭草料和工夫,买了只能杀了吃肉。无论什么原因,老莫都决定去一探究竟,来回几步路的事儿,买不成也不搭什么。
驴身架不大不小,不长不短,是人们说的巧个儿。就是有点瘦,肚皮上方的肋条清晰可辨,像蒙了层皮的搓板,看着硌眼。老莫心想,真杀了,肉也见不得有几斤。老莫买驴,不为让它干活,更不会杀了吃肉,杀生造孽,天理不容。老莫想买驴,是觉得家里空荡荡的,里外就他一个喘气的,总该多个活物,买头驴养着,就像添口人。老莫养过一条叫老黑的狗,陪伴了他两年。那狗忠诚,不仅能看家护院,还会讨好人,摇着尾巴跟在他屁股后边转,不时觍着脸讨好地看着主人,眼睛里柔情似水。老莫待见它,待它像自己的孩子。后来老黑让偷狗贼偷了,老莫心疼了好多天,便不再养狗。狗太贪吃,不然不会吞了下了毒的肉包子,结果成了人家包子里的馅儿。
“说实话,这驴有点小毛病,不咋吃东西,估计也不是啥大病,就像人,厌食。但我忙得很,没工夫调理它,便宜点卖了,省心。”老花翻翻眼皮接着说,“不然,五百块连个驴头也买不到。”老花见老莫像个老实巴交的人,觉得没必要隐瞒他,爱买不买,实在没人买就卖到张屠夫那里,价格也差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能送点驴杂碎给他。所以呢,对待老莫的态度不冷不热,笑脸都不舍得给一个。
老莫不再想老黑的事,倒背着手围着驴看了几圈,又掰开嘴看了看牙口,不动声色,心里却上下左右盘算事儿。
“不用看,不到三年的驴,正是好时候,如果好好调理,上上膘,是个干大活的料,拉车耙地,怎么使唤都行。”老花说着掀了掀驴尾巴,“看看,还是头草驴,养好了,说不准能下个驴驹子呢,那你可就赚大发了。”见老莫像个行家,盯着驴犹豫不定的样子,老花不失时机送上话。买卖成不成,全仗一张嘴。
老莫松开驴的嘴,琢磨着老花的话,并不搭腔。抬眼看时,那驴正眼巴巴地看着他,大眼睛里水汪汪的,似乎蓄满了泪。老莫心抖了一下,盯着驴眼不知所措——驴的两只眼睛上套着宽大的白圈圈,似用白油漆专门涂上去的,使那驴眼陡增些精神和神秘。那一刹那,老莫似被一块石头击中,心脏突突地骤痛几下。
老莫极力掩盖了情绪,沉下脸淡淡地对老花说:“不用你说,这驴一看就有病,且病得不轻,看,快瘦成纸片片了,一阵风能刮上天,五百块……不值。”老莫头摇得像拨浪鼓。老花尴尬了一下,似笑非笑说:“好好的谁会卖?这么便宜,买头猪差不多也上千块呢……那您能出多少?”
老莫略一思忖,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百啊?太少了点。”老花连连摆手,“少了点,加一百吧。”老莫寻思一下,再次伸出手指,是五根。“加五十,不卖就走人。”
老花不说话,思忖片刻,使劲跺一下脚。
牵了驴走到门口,老莫问:“叫什么名字?”
“我?”
老莫拍拍驴的头说:“它,这匹驴。”
“一头驴,有什么名字?还一匹?”老花觉得老莫跟这头驴一样,有病,蠢蛋一个!
“马是匹,驴比马都强,更应该是匹。”老莫拍拍驴的脊背接着说,“驴是大牲畜,小狗小猫都有个名儿,它该有名字。”
2
兽医董良围着驴看了两圈,拍拍肚子,还掰开嘴看了一番。他不关心牙口,看的是舌头。看罢,董良的脸沉了一下,却淡淡说:“应该没什么大毛病,肚子里有虫吧?看瘦成什么样了,吃下点东西不够养虫子的。”董良开了几服药,说:“先灌几服药看看,没事儿就养着,有事儿再过来吧。”
灌了几服草药,驴的胃口好多了,精神也见长。老莫抚摸着驴的头说:“那个老花虐待你,听说娶了个小媳妇,贪恋床上那点鸟事儿,哪有工夫伺候你?早给你看医生也不至于瘦成这样。”老莫拍拍驴的头接着说:“也好,让我捡个便宜,以后你就跟我过了。对了,说给你起个名儿呢,叫个啥呢?”老莫看着驴,驴也看着老莫,眼睛里似乎充满期待。此时,老莫又盯着它的白眼圈看,还伸手摸了摸。驴眨了几下眼,蹭得老莫心里痒痒的,老伴的模样蓦地在他面前晃动起来……
那时他们都还年轻。有一次县里的剧团来村上演戏,唱了一出《铡美案》。回到家他意犹未尽,问媳妇:“妮子,我要是画上老包的脸好看不?”媳妇说:“你的脸黑得也差不了多少,画上看看就知道了。”媳妇在墙上刮了石灰末用水调了,用一只秃毛笔在他脸上涂起来。画完拿镜子给他照,他一看,竟然只画了两个白眼圈。他哈哈笑着拍打着媳妇的屁股说:“臭妮子,这是包公吗?分明是个丑角儿。”
媳妇笑弯了腰,咯咯咯咯,上气不接下气。
老莫出神地看着驴的白眼圈念叨:“妮子,妮子。”驴听到老莫的话,竟然仰脖子叫了一声,然后不住地点头。老莫愣在那里,他的惊奇和喜悦同时爆发出来,他张开手臂紧紧抱住驴头,瞬间泪如雨下。
老莫没养过大牲畜,为此他专门求教了年轻时当过饲养员的六爷。按照六爷的指引,老莫专门去集市买了豆饼,把干草切得精细,拌上碎饼渣给妮子吃。妮子胃口一天比一天好,精神也日渐提振。老莫知道,牲口跟人一样,再好的东西吃得时间长了也会生腻,所以老莫间或给妮子喂一些玉米饼子和鲜嫩的草叶青菜。妮子的食量不断增加,脊背和屁股厚实起来,皮毛渐渐放出油亮的光。
老莫的几亩地都流转给别人去种了,没有什么活计可做,但老莫闲不住,每天都会牵着妮子到处走走。多是去村南的山坡上转,让妮子晒晒太阳,吃些鲜活的青草树叶。有时也去集市上走一遭,买些生活必需的物品,也让妮子见识见识各色男女和热闹街景。妮子很兴奋,眼睛亮得放光,蹄子踏出的节奏像一首欢快的歌。
每逢初一十五,老莫会带妮子来到山前老伴的坟前,摆一点山里摘的果子,再烧一刀纸。烧着纸,老莫慢声细语,跟坟里人说悄悄话,说着说着还滴几滴老泪出来。妮子有时默默站在一边,有时卧在坟前,似一尊不会动的雕像。它似乎知道土包里面埋的是谁,长长的脸上挂着凄然,眼睛也红红的。平时,老莫叫它妮子,它频频点头摆尾,还抬起蹄子刨几下地。在坟前,老莫对着那块小小的土包叫妮子时,它却无动于衷,站在一边低着头,它知道那不是叫它。
原先,老莫出门是牵着妮子的,后来,缰绳被解掉了,他在前边走,妮子在后面默默跟着。就这样,一人一驴,一前一后,走在村街上,走在山坡上,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像一幅移动的水墨画。有人看见便觉得奇怪,瞪着迷惑的眼睛,转念一想,又觉得温暖,感动。
3
老伴走了两年多了。她肚子里长了瘤子,疼起来像刀割,捂着肚子呼天号地。去医院一查,肠癌晚期。老伴临走时,拉着老莫的手一腔的不舍。老莫心疼得几次昏厥,守在老伴床前,茶饭不思,人瘦得像根柴棒。他握紧老伴的手说:“妮子,你走了,我也不想活了,没了你,再活着还有啥意思?让我陪你一起走了吧。”老伴心疼,想哭,可眼泪流干了,也哭不出声。
两口子只生了一个闺女。老莫是单传,老伴一直为没给老莫生个儿子耿耿于怀。但老莫并不介意,说生儿生女都是天意,天意不能违,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好在闺女优秀,考上大学又读了博士,后来去了国外搞科研,找了个男人,据说是个大企业家,有花不完的钱。老伴走时,闺女竟没能赶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老莫不怪她,在外国呢,隔着千山万水。再说,疫情铺天盖地来了,国外可比国内厉害多了,每天上万人感染那个病毒,没那么容易回来。
老伴走后,老莫的天塌了一半,整个人像被抽了筋,软塌塌没了支撑。后来总算熬过来了,人没跟老伴去,精神头却被抽走大半,恹恹的样子令人生怜。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走了,天南海北的,剩下的多是老头老太太和孩子,整个村子也像老莫一般恹恹的了无生气。老莫始终没从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走出来,人变得孤僻冷漠,很少跟人来往。有人说,老莫的魂让老婆带走了。他知道,这样苟活于世也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事,老天就是让他遭这个罪。但他确信,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追随老伴而去,命数已由天定,谁也抗不过命。他一日日熬着,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只等着那一天到来。闺女好几次要接老莫去国外,老莫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说过不惯外国的日子,守着老伴心里踏实。都说老莫这人太倔,也蠢,放着天堂的好日子不过,非在地狱里受苦。
那天,响水村的老杜来这边走亲戚,吃过酒饭,一堆老头在村街上围着他问东问西。老杜做着小生意,贩卖些瓜果梨枣,去的地方多,见多识广,又一张好嘴,爱说话。老莫也凑过去,便听到了响水村老花要卖驴的事儿。老杜说:“那个老花一肚子花花肠子贼心眼儿,死了老婆娶个小媳妇,又弄了头驴驹儿想养两年卖个大价钱,却不上心养,舍不得给驴吃好料,每天扔把干草给它,结果给养病了,不死不活的。现在急着出手,省得死在他手里,也不知哪个瞎眼的会上他的当。”老莫听后也不说话,低着头回家去了。
第二天老莫便去了响水村。
4
老莫的肚子隐隐地痛。他没在意,以为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老莫吃饭不讲究,特别是老伴走后,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大多是凑合,干的凉的,糙的馊的,都能下口。他觉得自己一辈子胃硬,咽下块石头也能化了。他忍着痛给妮子拌好料,倒进食槽里。妮子舔舔老莫的手,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老莫站一边看,就像看着老伴在桌前吃饭。老伴总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细嚼慢咽的,好像在绣花,一针扯着一针,不慌不忙。喝口粥吧,也不像那些糙女人,张开嗓子呼噜呼噜喝,她是一小口一小口抿,像大家闺秀。闺女上中学时就说过,俺娘吃饭也是那么文雅,秀气。“大家闺秀”就是闺女说的。
肚子突然很剧烈地痛起来,就像一只手在扯他的肠子,冷汗大滴大滴落下来。他忽然明白,是上天在召他呢,这个痛法跟老伴去世前一个样子呢。快三年了,让她等太久了。疼痛愈来愈烈,他终是忍不住,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脸色煞白。妮子停止了咀嚼,睁大眼睛看着他,两条腿不安地踢踏着地面,发出“嗒嗒”的声响。
不行!我不能死在家里,屋里死过人会让人觉得晦气,以后都不好住人了,老伴当时也是有所顾忌,最后死在医院里。当时他想把老伴接回家,可她死活不肯,说死在家里屋子就污了。这老房子是留给闺女唯一的东西,他知道,闺女不会瞧得上这老屋,可这是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她想怎么处置随她愿。
村东的莫老三,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儿子几年前犯事逃了,再没回头。莫老三去年死了老伴,一个人过不下去,一根绳把自己吊在了屋梁上。村里人联系不上他儿子,就把莫老三烧了,草草发了丧,连个哭丧的都没有。屋子里吊死过人,村里没有人向他那屋多看一眼,路过都绕开走。几间老屋空一年了,儿子没音信,连亲戚都不来看一眼,院里长满了草,屋子眼看要塌了。老莫哀叹一声想,村里老人,走一个少一个,早晚就空了。到那时,这莫家庄就没了。莫家庄有多大?几十户人家,东一户西一户,远处看,像随手撒下的一把芝麻。在地图上连个小黑点都没有,没了也就没了呗,没啥稀罕的。
老莫强忍疼痛,牵过妮子套在那辆排车上。他带好东西锁了大门,躺在车上说:“妮子,走,去坟地。”
妮子叫了两声,抬起蹄子一路小跑奔山坡而去。
墓地没有人迹,只有风儿轻轻掠过,时而有几只雀儿啼鸣。停在老伴墓前,老莫似乎听到老伴给他打招呼:老头子,你来了,你让我等了好久,好久……这块墓地是当年老伴选定的,老伴指着那棵柿子树说:“以后我死了就埋在这里,有树遮阴,柿子红了还能看光景,喜庆。”他说:“妮子好眼光,这里风水好,我死了也埋这里,活着在一屋,死了一座坟。”
又一阵剧痛袭来。老莫抱着肚子坐起来,他想下车给妮子松套。老莫说:“好妮子,我不能再陪你了,我就在这里陪着她去。你呢,回村里,会有好心人收养你,因为你是个……好妮子,大家肯定稀罕你。”说着,他挣着身子要下车去给妮子解套。又一阵更剧烈的疼痛袭来,他忍不住哀号一声昏死过去。
5
一片白光,一种生疏的气味,他觉得该是到了老伴的那个世界。
慢慢睁开眼睛,老莫渐渐清醒过来。他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飘过来,俯在他身边说:“终于醒了,我去叫医生。”
“我,这是在哪里?”
“医院,你刚做完手术,手术很成功。别说话,你需要静养。”
医生看了下病人的情况,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叮嘱护士几句就走了。
他慢慢恢复了记忆,问护士:“我的东西呢?一个布包。”护士说:“给您收着呢,放心吧,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那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差不多有五千,准备给自己办后事的,麻烦你替我交医院的费用吧。我知道可能远远不够,现在动动刀得上万块,我家里还有我闺女留给我的银行卡,我出院后就取出钱来,一定还上,我不会赖账……护士,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胃穿孔,幸亏送来及时,不然可就没命了。您刚做了手术,少说话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对了,您的家人呢,谁送您来医院的?”
“谁?”他闭上眼睛想……突然睁大眼睛问:“妮子,妮子呢?”
“谁是妮子?您女儿吗?没见着啊。”
“妮子……是匹驴。”
“哦……”护士捂着嘴笑了,“原来是那头驴呀!听说了,是一头驴拉着车送您来的,可没见到赶车的人。听保安说,驴拉着车,车上躺着人,停在医院门口,堵住后面一大溜汽车,怎么轰都不走,还嗷嗷叫。后来一看车上躺着个昏迷的人,保安赶紧把驴车牵到急诊室,这才救了您一命。我就不明白了,赶车的把您送到医院,人怎么就没影了呢?”
“没有人赶车,妮子自己来的。”
“怎么会呢,驴认得来医院的路吗?”护士觉得不可思议,惊异地瞪大眼睛,“这也太怪异太离奇了吧!”
“它认得路,之前我赶着它不止一次来医院送病人,都是乡里乡亲,雇不起车,我这驴车方便,也不收钱。”老莫说着,忽然坐起身眼睛向窗外看去,“妮子呢?它在哪里?”
护士扶他躺下说:“保安把它赶到了车棚里,那个放自行车的棚子拐角上有个空地儿,太阳晒不着,下雨淋不着,还有人天天给它送吃喝,您就放心吧。这可是头传奇英雄驴,大家都会善待它,您说对吧?”
老莫突然想起那个在心头盘旋很久的问题。“姑娘,你说为什么马是一匹马,驴却是一头驴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约定俗成吧。对了,我帮您查查。”护士打开手机刷了几个来回,“找到了,我给您念念吧。古时候,匹是一个计量单位,用于计量布帛,四丈为一匹,后来才用于计量马。孔子曾解释说,在阳光下,马的影子有一匹那么长,长达四丈,故此称为马匹。还有古人解释说,良马和君子都要由具备慧眼之人‘相’过之后才能确定,可见良马必须与君子匹敌,故称马匹。”
老莫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认为驴与马也能匹敌。”
小护士转动着大眼珠,好像在想一个难解的问题。“大伯,您为什么叫它妮子呢?它是个女的吗?”
“嗯,是的。不为什么,就是觉着好听。”
“嗯嗯,妮子,好听!”
6
医院里突然来了很多背照相机的人,像记者。有一个还扛着摄像机,应该是电视台的。还有一些举着手机搞直播的,男男女女,对着手机手舞足蹈咋咋呼呼。他们围着车棚,对着妮子上下左右拍照片,闪光灯一闪一闪,妮子被逼到墙角,不安地看着那些人,眼睛里充满疑惑和恐惧。那个护士把老莫和妮子的事写成小作文发到网上,没想到引起了轰动。
一个长得十分端正的男人找到老莫,说要买老莫的驴。男人说:“这头驴不得了了,不仅比人有灵性,有道德,还充满正能量。我要把它打造成明星,为我们企业代言,我们生产的保健品就能销往全世界!这头驴便是世界级的明星。”男人说完伸出一个手指给老莫看。老莫摇摇头不说话。男人想了想,一拍腿随即把双手食指交叉起来说:“十万行不?”老莫又摇头,然后一字一顿说:“一、百、万,也不卖!”
妮子瘦成跟刚来老莫家时那样了,肚子塌瘪,肋条一根根撑着,似要凸出来。小长脸儿像用刀斧削过,缩成窄细的一条。老莫能下床后,第一时间便来到楼下的车棚。
“也别怪人家没好好伺候你,毕竟不是在咱家,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看看,瘦成什么样了。妮子,我知道委屈你了,走,咱回家。”
颠了一路,老莫顾不得刀口隐隐作痛,动手给妮子拌料,细碎的干草掺上豆饼,特意加了点盐,最后还磕上两个鸡蛋。妮子舔舔老莫的手,表达它的感激,低头吃了几口却住了嘴,抬头哀哀地看着老莫。老莫说:“妮子啊,你救我一命,自己却受了委屈,看瘦成这样,真难为你了。咱现在回家了,你该好好吃饭,补补身子啊,怎么停嘴了,傻傻地看着我干啥?”老莫转念又想,这一路上妮子无精打采,走路腿老打晃,几次差点儿歪倒,莫非又犯病了,肚子里的虫又都活过来了?这该死的虫子,就像那些世上祸害人的坏蛋,像韭菜一样割一茬生一茬,非得下猛药才能死绝。
董良有些吃惊,问:“那头驴还活着?”
“一直活得好好的,就是这两天受了点委屈,不怎么吃东西了,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再给包两服药吧,猛一点,打虫子。”
“老叔啊,这……”作为兽医,董良像做了什么亏心的事,表情挺复杂,“叔,我给您说实话吧,这驴有病,绝症,治不好的。当初看您那么喜欢它的样子,不忍心跟您说实话,没想到它能活这么久,真难为您这么伺候它。”
老莫傻在那里,他不相信董良的话,这么好的妮子,怎么会得绝症呢?
董良见老莫动了感情,心似乎被扎了一下,一阵刺疼。这老莫,把头驴当人待呢。“老叔,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牲畜也一样。想开点,好好伺候它几天,顺其自然吧。”
邻家老皮过来问:“这几天你去了哪里?”
看老莫不愿说话的样子,老皮不再说什么,转头要走,却瞥见棚子里的驴正目光冷冷地对着他看。老皮心头一凛:这畜生,长了对什么眼啊!“老莫,你养了头啥驴嘛,看瘦成什么样了,纸糊的似的,一阵风能刮到天上去。看它那倒霉相,还盯着我瞅,瞅啥嘛,真是头蠢驴!”
“是一匹驴,它一点不蠢,比有些人强多了。”
老皮本想借驴骂老莫,不想反被老莫不动声色地骂了回来。老皮觉得无趣,扭头便走。走到门口,回头说了句:“看你那歪瓜裂枣的样子,倒养了个好闺女,家里有座金山呢。人啊,咋说呢?唉!”
老莫闻见老皮的话里泛着一股酸味儿。老皮是外姓,总觉得在村里被莫姓人欺负,为人小心谨慎,却一肚子弯弯绕,从不吃亏。这个人却好命,养一个闺女,嫁进县城,经常开着小轿车回来显摆。那时刻,老皮就倒背着手在村街上晃,遇到谁都笑着打招呼,还给人递烟,请人去家里喝茶。老莫骂他臭德性的同时,一种莫名的嫉妒也会漫上心头。
老莫不忍再多看妮子一眼,关上门在屋里闷着,饭不做,水也不喝。这一晚老莫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过往的许多事断断续续出现在眼前。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老莫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老伴,还有闺女,都笑吟吟地看着他。他伸手去抓,她们却倏忽不见了。
老莫一睁眼,天已大亮,阳光透过窗户铺开来,屋子里亮亮堂堂,暖气升腾。身上盖的那床被子上硕大的牡丹花被阳光暖活了,娇艳地开着,似有阵阵香气溢出来。这床被子是当年娶妮子时她娘家陪送的,一直放在柜子里,昨晚他睡觉时,突然想看看被子上那些鲜艳的花朵,就拿出来盖在身上。记得娶媳妇那晚,就在这床被窝里,他搂着她说:“看你小巧娇娇的样儿,盖着大花被子,真是个小花妮子,爱死个人哩。”媳妇说:“谁花?谁花?你才花,哼!不理你了。”说完,挣开了身子把后背对着他。他忙认错,说:“不花不花,是妮子,好妮子。”她娇嗔地一笑,说:“这还差不多。你以后在家里就叫我妮子吧,俺喜欢。”他说:“好!妮子,妮子,就妮子。”
“妮子,妮子。”老莫溜下床不住声地喊着妮子。往常,天一亮,妮子都会响亮地叫几声,还打几个喷嚏,那是喊他起床。
妮子没了。
老莫在院子里踅摸了一圈,没有妮子的影子。再看,院门竟然是开着的。昨晚是闩了院门的啊,这妮子,难道自己会开门?成精了不成?
白晃晃的村街上哪里有妮子的影子。老莫肚子上的刀口突然一阵疼痛,他不得不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妮子,你去哪了?难道你的大限已到,也跟我一样,不想死在家里?妮子啊,你个傻妮子!你究竟去了哪里?怎么不带我一块儿走啊!舍下我一个人在这……”老莫终是忍不住,张开嘴号啕大哭。村街上静悄悄的,只有一条老狗和一个小女孩站在一边看着他。小女孩走过来问:“爷爷,看你哭的,鼻涕都出来了,你家丢东西了吗?”老莫这才感觉到自己的失态,抹把眼泪说:“嗯嗯,爷爷丢了件顶顶重要的东西。”
女孩说:“爷爷,是不是你的妮子丢了,那匹驴?”
老莫惊在那里,他伸手揽过小女孩问:“你知道妮子?你看见它了吗?”
女孩点点头说:“看见了,它朝那边走了。”女孩伸出小手指点着村道远处,继续说,“它走着走着,突然长出一对翅膀,好大好大,然后……就飞走了。”
老莫一阵眩晕,喃喃道:“飞了,飞走了,它飞到哪去了呢?”
“那里。”女孩指着天上飘着的一片云朵说,“飞到云彩上面去了。”
那朵白云像一大团棉絮,雪白雪白,在天空上悬着,高处的太阳为它镶上一圈金边,闪闪发光。
老莫紧紧抱着小女孩,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