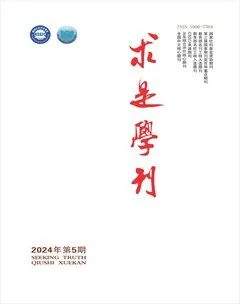“老去填词”在词史上的尊体价值及范式意义
关键词:朱彝尊;“老去填词”;尊体;词学史
词在唐五代定型初期多为宥觞或书写私人性的艳情内容,其中“思春”“伤春”主题较为典型,具有比较明显的青春文学倾向。早期词人绝少将词视为“立言”路径,因此,不少词家在词成后没有自觉的著作权意识,甚至在其仕途亨通之时,为了立一个忠直正派、洁身自好的形象,自毁词作,绝不允许因填词而污了门面、误了前程的情况出现。词史上如被称为“曲子相公”的和凝就是典型,与其同时代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①深为和凝惋惜,此后和凝悔其少作成为词学史津津乐道的典故。清代谭莹有论词绝句说,“香奁佳句少年时,度曲偏令异域知”②云云,仍对此调侃不已。这种情况一直延绵至宋代,陆游在其《长短句序》中自言道:“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①大才子柳永因填词触怒君上而断送了前程,虽然柳永面对如此遭遇表现出颇为不屑的态度,将错就错营造出一副白衣卿相的风范,但对于士子来说,终归起到了训诫警示的作用,令后人唏嘘不已。又如黄庭坚词好作艳语被释家弟子以堕入犁舌地狱而警告,黄氏以词是“空中语耳”来为自己辩解。②这些现象无不表明早期词家对于词体创作的基本态度,填词非但不能作为作者人品才情的代表,反而可能会招致非议。因此,不少词人到了中晚年便有悔其少作的心理。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就其身份而言,仍然无法与诗对等,这种情况随着元明两代词学的式微而并未得到改变。明清易代,给士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加之清初统治者的文字狱警慑、学术风气的转变等,为词体的复兴提供了条件。清词艳称“中兴”,其中推尊词体被认为是“清词中兴”的重要表征,但尊体并非词论中出现的附庸风雅地提高词体本源的论述,更重要的是词人对于词体的内在体认。清初两大文坛领袖王士禛与朱彝尊并称,王氏早年以填词为主,晚年却弃词就诗,朱彝尊恰恰相反,早年以诗为要务,晚年于词用力颇深,提出“老去填词”并明言疏离于词的艳情“传统”,在审美层面主张醇正典雅,以南宋姜张为尊,明显区别于唐五代北宋词活色生香的“天然本色”。相对于早期词人的“悔其少作”现象而言,“老去填词”提升了词体创作的品格,是词体创作的新范式,值得深入探讨。
一、朱彝尊“老去填词”说的提出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金风亭长、小长芦钓师等,浙江秀水人,明代大学士朱国祚之孙,由明入清,开创浙西词派,被誉为“一代词宗”③,同时又是著名的经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据考证有著录60余种。④清初与顾炎武、傅山等遗民学者鼓吹金石之学,访碑考古,提倡篆隶之学,擅书《曹全碑》,开一时访碑考古之风气,是金石学、碑学兴盛的重要人物。明清易代,朱彝尊家族经历了家国之变,颇为凋零,族亲中有数人因反清复明被戮,基于此,朱彝尊曾一度结交抗清人士,参与反清复明活动。⑤前半生漂泊流离,授徒游幕不歇,却贫寒困顿未曾离身一日,后迫于生计,应试康熙开设的博学鸿儒科,转而入仕清朝。李符《江湖载酒集序》载朱彝尊自36岁北上游大同始填词,⑥39岁词集《静志居琴趣》成书,44岁有《江湖载酒集》,词集名取自杜牧《遣怀》“落拓江湖载酒行”诗句,主要抒写其南北游幕期间的坎坷与蹉跎,遂有“老去填词”之慨。其《解佩令》为《江湖载酒集》自序,云: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⑦
这首词抒发了自己壮志消磨、飘零落拓的悲凉心绪。“十年磨剑”出自贾岛诗句,“五陵结客”用汉唐事典,说明自己在青壮年时期的勤勉、艰辛及结交豪杰的入世热情,最终成了“涕泪都飘尽”的徒劳。并明言自己“老去填词”并不囿于歌舞翠筵,而是为了寄托胸中的感慨。作者此时说自己“老去”,一方面结合当时朱彝尊的境况而言,他因生计窘迫,蹉跎坎坷,曾言“丈夫三十不自立,一身漂泊随秋蓬,虽未白头成老翁”①,早在其30岁客岭南时期就说自己是老翁了;另一方面,这里的“老”更多的是一种心境,人只有在岁月蹉跎、事事无成的境况下更容易产生对“老”的深刻体验和焦虑,所谓“料封侯、白头无分”,体现出一种垂老蹉跎的心理状态。李佳在《左庵词话》中说:“朱竹垞自题词集有云:‘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此语不啻为侬写照。”②
除了这首词,朱彝尊还在《三部乐·题曹侍郎〈寄愁集〉》一词中重申“老去填词”:
绣虎惊才,看老去填词,惜香还又。银筝低按,绝胜当年秦柳。也终是、家令情多,把晓鸿夜鹤,绿窗题就。且听班管,分付笛床歌袖。 霜华最怜镜里,况文园病渴,洛阳人瘦。禁他梁尘乍起,风吹红豆。惹新愁、旧愁都有。拼一饮、须倾一斗。兴复不浅,坐塞月、南楼如昼。③
这首词是为其友曹溶词集所题。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号秋岳,明朝进士,官御史,入清后历官户部侍郎,因此这里称其为曹侍郎。“绣虎”本是曹植的号,后世以绣虎之才盛赞才华横溢之人,加之其友人为曹姓,故相类比。“文园病渴”是指司马相如体弱有消渴之疾的典故,“洛阳人瘦”借用晏几道与张采萍曲折的情感故事,以此来暗示友人在词集中书写的人生境况与情感经历。朱彝尊与曹溶同为明遗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曹溶曾多次在经济上救助朱彝尊,朱彝尊追随曹溶从大同到岭南,终其一生保持着深厚的交情,可谓平生至交,当推曹氏为第一。④曹溶仕清后成为所谓的“贰臣”,内心的矛盾与苦楚多以词寄托,已然超出了“秦柳”词的表现范围。朱彝尊称其“老去填词”,可谓感慨良多。
从《江湖载酒集》结成到朱彝尊51岁举博学鸿儒科,间隔7年,这基本上就是朱彝尊政治心态发生转变的一个时间段。从反清到仕清,朱彝尊的人生志向迫于现实生活的困顿而最终妥协。他在仕清后作为康熙帝近臣兢兢业业,但内心始终悔意犹存。⑤朱彝尊《江湖载酒集》词集中又有《百字令·自题画像》一词,进一步摹写了其“老去填词”的形象,词上阕云:
菰芦深处,叹斯人枯槁,岂非穷士。剩有虚名身后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无闻,一丘欲卧,漂泊今如此。田园何在,白头乱发垂耳。⑥
这首词开篇就用了反问句式,自嘲“穷士”境况,年过40而一事无成,只能以“小技文章”成就虚名。这幅自画像摹画了朱彝尊窘迫而能自得其乐的文人形象,虽有牢骚但仍然不失文人风度。清人李调元在《雨村词话》中说:“余酷喜其(朱彝尊)自题画像百字令。”⑦清代词学家陈廷焯也评价这首词说:“感慨而不激烈。顾宁人自谓不如竹垞和厚,想见先生气量。”⑧朱彝尊“老去填词”的形象在后人心目中代表的是高洁萧放的文人风度。
二、“老去填词”创作范式的接受及经典化
清代词体创作繁盛的一大原因是清廷的文化高压政策造成文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失语和压抑,“老去填词”为仕途困顿不得志的文人群体在创作心理层面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成为他们纾解困顿压抑的人生选择,引起广泛共鸣。可以说,朱彝尊的“老去填词”演绎成了一种经典的词家情怀,开创了新的创作范式。
朱彝尊早年由于家贫而入赘冯家,①后历经清初战乱,流离失所,四处藏身,终于在中年后修建了自己的宅院,取名竹垞,倍感珍惜,特地作《百字令·索曹次岳画竹垞图》词,延请其书画好友曹岳为其作《竹垞图》。词上阕云:
杜陵老矣,共丹青曹霸,白头漂泊。花柳春残都未见,底事燕南栖托。略彴长堤,呕哑柔橹,只忆江榔乐。吾庐何处,斜阳芳草村落。②
这首词开头就说,“杜陵老矣,共丹青曹霸,白头漂泊”,可谓沉痛,将自己与曹岳比为杜甫与曹霸,曾经身处盛世的杜甫与曹霸如今垂垂老矣,却仍在漂泊。朱彝尊借此感慨自己多年漂泊,余生唯愿有竹垞小院,著书填词,透露出较为浓郁的归隐情志。结合朱彝尊仕清后两次被贬,最终归乡著书填词的结局,这首词大有“词谶”的意味。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后充日讲官,知起居注,成为康熙近臣。后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被再次罢免。③归乡两年后,朱彝尊将曹岳的《竹垞图》装潢成卷,将其索图词《百字令》书于卷首,并题跋说:“康熙甲寅春,客通潞,填《百字令》,索秋厓补图,二十一年矣。秋厓久逝,‘小楼’‘墙角’至今未添,而予衰愈甚。展对此图,不胜迟暮之慨。因付装池,并书前阕,以要和者。”④图一经传出,题咏者甚众,并且绝大多数以《百字令》行,作者从其同时代的词人如李良年等,直至沈曾植、朱祖谋一众晚近词人,绵延一二百年,数量多达百首。⑤这一事件对“老去填词”在后世的接受及经典化具有直接影响。李良年题词《百字令》有句曰:“史局谁长,酒仙臣是,晚遂归田策。白头题句,这回真个头白。”⑥朱彝尊当年题词索图时仅45岁,如今已是66岁,因此说“真个白头”。李沣词云:“白头解组,尽消闲幽舫,小长芦泊。十载东华成往迹,倦向软红尘托。”⑦徐釚题《百字令》有句云:“细按濒洲鱼笛谱,醉擘蛮笺十幅。”⑧题咏词基本结合朱彝尊原词书写的词意及思想情感倾向展开,对朱彝尊归田著书、老去填词作诗的行为给予美扬,并表达倾慕之情,这一方面出于对朱彝尊被罢免的同情,另一方面则缘于对朱彝尊在学术、文学等方面的崇高地位及其文人风度的推崇。
嘉庆元年秋,阮元主持重修竹垞曝书亭,倩画家周瓒、方薰摹图,并自题《百字令·和朱检讨自题原韵》词云①:
嘉庆元年,秋试毕,嘉兴得观曹秋厓竹垞图,属周君采岩摹写一帧,并录竹垞老人词跋及同时诸和作。即用《百字令》原韵题后,以要和者。十二月十二日书于小琅环仙馆。
先生归矣,记江南春雨,扁舟初泊。自种垞南千个竹,老让懒云闲托。茧线牵鱼,弓枝射鸭,足伴填词乐。画图长在,肯教踪迹零落。 今日水浅荷荒,岩低桂蠹,残址难斟酌。何处墙边楼影小,曾展秋窗风幕。2DCLS672MYzcybZZuMulsg==儒老乾坤,书悬日月,莫漫悲亭壑。重摹横卷,远山还染三角。
这里“自种垞南千个竹,老让懒云闲托。茧线牵鱼,弓枝射鸭,足伴填词乐”,摹画出朱彝尊老去填词的形象。当时题咏者还有王昶、钱楷、朱文藻、张若采、吴锡麒等30余人。晚清收藏家王秉恩先后得两幅《竹垞图》,并题词索和。③易顺鼎有《百字令·为息存题所藏竹垞图用原韵二首》,其一上阕云:
淡烟细雨,记小长庐下、孤篷曾泊。欲觅竹坨何处是,胜有丹青堪托。老去填词,空中传恨,底事伤哀乐。平生涕泪,披图犹似珠落。
“欲觅竹垞何处是,胜有丹青堪托”,便是指曹岳为朱彝尊作《竹垞图》之事,怀想朱彝尊“老去填词”的悲凉心绪,几欲落泪。朱祖谋亦有《念奴娇》词题之,词序说:“《竹垞图》有蓝谢青、曹秋厓二本,皆作于康熙甲寅,锡鬯客通路时也。王息存先后得之,索为小词,志合并之雅,用锡鬯原韵。”其中有词句云:“千首填词,十年磨剑,心决归耕乐。小楼添否,白头依旧牢落。”⑤这两首词在风格上也有意模拟朱词,应和“老去填词”之慨。
正是由于《竹垞图》在后世的流传及不断题咏,朱彝尊“老去填词”的形象不断地被摹画和渲染,使其这一形象逐渐经典化。如后世填词图的创作及题咏多有“老去填词”说。汪承庆(1827—1890)作《声声慢》词题蒋复敦《芬陀利室填词图》云:
青衫落拓,彩笔飘零,十年名艳词场。溪号罗敷,水天惯住鸳鸯。烟鬟画屏双笑,按参差、低度霓裳。思往事,只迦陵风格,一样清狂。 为问江湖倦旅,甚声偷字减,偏老柔乡。酒醒乌蓬,萧萧几树垂杨。樽前坠欢重觅,换天涯、无数苍凉。吟未歇,恐新愁、又萦寸肠。
词中“青衫落拓,彩笔飘零”“十年名艳词场”“江湖倦旅”“偏老柔乡”“换天涯、无数苍凉”等都是从朱词中化出,旨在表现蒋复敦“老去填词”的形象。又,薛肇基(1866—1955)有词《浣溪沙·题〈讱庵填词图〉兼送南归》其二云:“老去填词近玉田,燕钗蝉鬓几曾怜。竹坨身世觉犹贤。 漆室忧时歌倚柱,铜仙辞阙泪流铅。几番欲去总留连。”⑦上阕评价林葆恒“老去填词”的词风近南宋张炎,下阕用漆室少女的家国之忧、铜仙流泪的亡国之恨来说明其词的表达主题。
徐珂有《纯飞阁填词图》,题咏者颇多,如邵章《传言玉女·徐仲可(珂)纯飞馆填词图》词上阕云:“劫后年华,拂镜满头霜白。绮怀天远,忏三生此夕。池水弄影,渐老何郎词笔。瑶觞闲引,宝栏低拍。”①马叔伦《清平乐·题徐仲可丈纯飞馆填词图》有“五陵怀抱。诉与朱弦袅。……画里词人垂老”②之句。李详《题杭州徐仲可(珂)纯飞馆填词图》绝句说:“读当摇落变衰时,老去心情剧乱丝。敬是复堂佳弟子,箧中知有箧中词(君为谭复堂入室弟子)。”③可见徐珂是“老去填词”又一人。近人郭晋超曾绘《老去填词图》,海内名士题咏甚多。④夏仁虎亦有《老去填词图》。⑤填词图作为清以降特有的词学现象,具有丰富的词学史意义,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填词图的出现是词体创作经典化的重要标志,填词不仅仅是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更是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具有典型性、象征性的经典意象。
此外,朱彝尊《解佩令》一词是为自己的词集作序,以言明自己的创作宗旨及旨趣,后世词学家亦逐渐将“老去填词”作为填词的一种范式来总结评价词人的词体创作境况。如舒昌森为黄文琛《疏篁待月词》⑥题《摸鱼儿》词云:
憩方壶、偶嫌岑寂,无端游戏尘世。酸咸滋味都尝遍,运蹇性偏明慧。磨不死。希隐逸、怡情待月疏篁里。移宫换羽。问叔度家风,涪翁才调,几辈可怜子。 衔杯乐,抛去浮名俗累。休论萍梗遭际。新声同倚欣同调,谊重半生知己。愁莫洗。君不见、愁多别有埋愁地。韶华逝水。恁老去填词,空中传恨,醉墨清襟袂。
上阕感慨黄氏“酸咸滋味都尝遍”,运途坎坷却明心慧性,能以填词慰一己之怀。“叔度”指汉代士人黄宪,以才学操守为时人所敬重,乃至被比作颜回,“涪翁”是宋代词人黄庭坚,以此二人比拟黄氏的人品才学。结尾“恁老去填词,空中传恨,醉墨清襟袂”,点明其填词旨趣。王寿庭(1805—1860)《台城路·书孙月坡〈听舻词〉后》一词亦是为词集作序,上半阕云:
卅年消受双鬟拜,旗亭遍留佳句。草色鹦洲,萧声雀桁,都是曾销魂处。惊心战鼓。忽一片江山,尽成凄楚。老去填词,那堪风雨听柔舻。⑧
王寿庭官至苏藩署吏,后因太平军破城而殉难。这首序词低徊沉痛,词中概括了孙氏词集所叙写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社会境况,而这也是王寿庭自己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诉说因家国不安而产生的凄惋心境,“老去填词,那堪风雨听柔舻”,蕴含着深沉的焦虑与忧患之感。“老去填词”在填词图的题咏及词序中频频出现,已然成为带有批评理论色彩的词学概念。
随着“老去填词”的经典化,其又被借用于戏曲创作语境,如谭献《玉师堂后五种曲叙》说:“陈叔明先生(陈烺),骥德已老,鹤鸣在阴。……《玉师堂五种曲》,旗亭传唱,一片城孤;酒所旧闻,双泪河满。已而独居深念,老去填词。新酿初熟,浇块垒以一杯;旧事重提,数螺纹于五指。”⑨词曲学家吴梅《题〈秣陵春〉传奇》诗曰:“金华殿上题名日,白袷飘然一少年。老去填词多隐语,暮春野祭作神弦。”①亦将“老去填词”借用到戏曲创作语境中。又,蔡寄鸥(1890—1961)有《瀛台梦传奇续编》,第一出副末以【高阳台】开场,代作者言:“十年读书,十年磨剑。平生一事无成。老去填词,偏教浪得虚名。绿深门户啼鹃外,小窗间书架纵横。尽萧闲浴研临池,泼墨堆云……”②蔡寄鸥此曲针砭时弊,感慨非常,这里的“老去填词”特指自己身处乱世,年老以后以戏曲创作作为人生消遣的无奈。戏曲创作语境对“老去填词”的借用表明这一文学创作范式已经影响到其他文艺类别。
值得注意的是,自嘉道年间就出现了“老去填词”的文人闲章,如《梅里词辑》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薛廷文原辑,道光九年(1829)冯登府重编。浙江图书馆藏有冯氏《梅里词辑》稿本,除“登府私印”外,钤有“柳圩东畔渔师”“小长芦旧史冯氏手校”“老去填词”“竹坨乡亲”“小榜李亭”“西园小长芦之南曝书亭之北”诸印。不难看出,冯登府的这几方印多有瓣香朱彝尊的痕迹。沈景修(1835—1899),兼诗人与书法家身份,晚年喜好倚声,有“老去填词”文印。篆刻家赵之谦亦有“老去填词”印,印文深得浙派赵之谦之神韵。③而李叔同晚年自号息翁,也有“老去填词”印,边款“息翁夫子命刊,丙辰志页湖州”。④据郑逸梅《艺林旧事》载,近人周退密“擅填词,著有《石窗词》,我为他作序,其中多师友唱酬,夫妇涉胜,以及赏花题画之作。刻有‘老去填词’印,则是用小长芦钓师‘解珮令’句,也是很恰当的”⑤。作为文人闲章的镌刻内容,标志着“老去填词”已然成为文人群体的雅尚。
综上,“老去填词”自朱彝尊始,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开创了新的词体创作范式——在创作心理上倾向于老成、复杂,在表达上注重人生经历的丰富性及情感的深刻性,在风格上呈现出苍浑、沉郁的特征。“老去填词”成为一种具有丰富美学观照的人生意象,体现词人在历经坎坷和痛楚,经过反思、内省、参悟而完成的境界层面的跃升,达到老成与萧放境界,成为文人风雅情怀的典型之一。
三、“老去填词”与晚近词风的转变
从晚清到近代的近百年间,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内忧外患的社会形态使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激宕出新的词体创作风貌。咸丰元年(1851)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周曾锦在评价杜文澜词时将其与蒋春霖词同观,认为:“天挺二老于咸同之际,亦词界之中兴也。”⑦周氏谓“词界之中兴”不失为卓见。朱庸斋也说:“逮及清季,国运衰微,忧患相仍,诗风大变,声气所会,词学复盛,名家迭出。”⑧二者都指出了在社会动荡背景下词体创作出现的新气象。朱彝尊提出的“老去填词”在后世的接受和经典化、意象化,一方面是词体自身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境况、学风及审美祈尚有着密切关系。面对社会动荡,文人内心的不安、苦闷、压抑往往不便于明言,而词恰恰为其提供了纾解的通道。因此,晚近时期词人对“老去填词”的广泛接受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首先,“老去填词”作为晚近词人的群体选择,是尊体意识的体现,深化了词体表达的内涵。相对于早期大部分词作活色生香的青春文学倾向,“老去填词”则带有浓郁的人生反省意味,词体创作的严肃性增强,在表达意境上更为深沉。词学家蒋复敦在《芬陀利室词话》中自叙学词经历说:“嘉庆末,余年童稚,始识阳湖周保绪先生于田若谷邑宰署中,蒙以奇童见称。时习经史及帖括文字,间亦作诗,未尝问津于倚声之学。中年抑郁无憀,乃学填词。从王子久茂才处,借得先生存《审轩词》一卷读之,是真得意内言外之旨。”①蒋复敦中年开始学填词,并且追求意内言外之旨,显然与传统词作的青春、娱乐气息截然不同。张鸣珂《棠梦词》自序言:“仆少知奏赋,老去填词。怕听红萧,不歌金缕。孤花病蝶,兔管心灰;落叶哀蝉,螺钿尘满。乌丝尚在,翠墨依然。览此遗音,恍逢故我。谁能遣此,种江潭红豆之思;何处寻君,有风雨苍梧之感。旧日翩翩白袷,诵昨宵酒醒之词;此时渺渺黄墟,痛落日邻哀之笛。”②张鸣珂年少时用力于“奏赋”这样的实用文体,老去后始为词,而且无心于传统词学的倚红偎翠作风,只因自己此时已是“孤花病蝶,兔管心灰”,人生种种境况如过眼云烟,道出了“老去填词”的悲凉心绪。陈钟祥有《香草词》五卷,又有《鸿爪词》《哀丝豪竹词》《菊花词集》《集牡丹亭词》《香草词补遗》各一卷,词体创作可谓繁富,但其填词却是40岁之后才开始的,莫友芝说:“同岁息凡子,素擅诗笔,年余四十,始涉为词,即洞其奥。亦既更历世故,牵掣宦场,属时多事鞅掌,鲜有居息。”③陈栩《澹庐诗余序》对“老去填词”论述得更为贴切:
人在绮年,必多艳事,心有所思,情有所系,口之所不能言,意之所不能尽,则酝酿而成句,遂连缀而为词。既不必如诗之苦寻对偶,更不必如文之安排局势。是以天趣盎然,无待矫饰,流露性灵。……平心而论,则老去填词,决不能如少日之风华流丽,固无奈何事耳。……吾因而思人生于世,正如花木当春初花,则天然之美,自然流露,毫不假借于人工。而盆梅之屈曲,固无取也。及秋落木则枯秃无华,纵有丹黄霜叶点缀其间,恐不能回复如春日园林中繁香醉人之情味耳。
这里陈栩提出老去填词与年少时期是非常不同的,青春词如当春初花,有天然流丽之美,人到老年,就如树木到了秋冬季,即便仍然有斑斓霜叶的点缀,但却再也没有春天花木的芬芳氤氲,老去填词也必然如同这秋冬之树木另有姿态。这一观点总结了清以降词人老去填词的普遍况味,即老去填词在情感内容上多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苦楚、焦虑和无奈,以萧瑟、悲伤为主。
此外,不少词人早年即致力于填词,至中年后词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浙派末期中坚郭麟说:“余少喜为侧艳之辞,以《花间》为宗,然未暇工也。中年以往,忧患鲜欢,则益讨沿词家之源流,借以陶写厄塞,寄托清微,遂有会于南宋诸家之旨。”⑤坦言自己中年以后由于人生忧患少欢,填词风格由侧艳转为清微,注重寄托以写厄塞。又如常州词派词家兼词学家陈廷焯曾说:“余十七八岁,便嗜倚声。古人老去填词,余愧学之早矣。余初好为艳词,四五年来,屏削殆尽。是集所选,一以雅正为宗。纯正者十之四五,刚健者十之二三,工丽者十之一二,其一切淫词滥语,及应酬无聊之作,概不入选。”⑥首先,陈廷焯后悔自己学词太早了,因为“初好艳词”,没有领悟到“雅正”之宗。从他摈弃艳词追求雅正来看,正是推崇朱彝尊的词学主张所致,他曾说:“朱竹垞词,艳而不浮,疏而不流,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⑦后陈廷焯与庄域交往,入常州词派阵营,最终提出“沉郁顿挫”的词学宗旨。常州词派中坚周济说:“文人卑填词为小道……余少嗜此,中更三变。年逾五十32c92c882fa6ea9528b16470894138f8ac2b12293dffdf37375b29347c0eb20d,始识康庄。自悼冥行之艰,遂虑问津之误。不揣浅陋,为察察言,退苏进辛,纠缠姜、张,剟刺陈、史,芟夷卢、高,皆足骇世。”①从周济的这段言论可以看出,常州词派的词学主张是比较倾向于更为沉着有内涵之词风的。姚鹓雏有论词词《满江红》二首,其一上半阕云:“老去填词,原只是、空中传恨。试闲数、晚唐十国,溯源循本。兰畹金荃香草弱,阳春白雪莺簧嫩。问谁将、雅郑别风诗,漱芳润。”这里用“弱”和“嫩”来概括唐五代词。其二转而论清代词风说:“鹿潭起,重扬扢。逮彊村高密(郑文焯)敦盘相接。七宝楼台迷架构,十围大木森苍郁。比秦王扛鼎我何任,心先慑。”②从“弱”“嫩”到“七宝楼台迷架构,十围大木森苍郁。比秦王扛鼎我何任,心先慑”,可以想象其早期词体创作与晚近词风之大相径庭。张尔田说:“古丈(朱祖谋)晚年词,苍劲沉着,绝似少陵夔州后诗,此其所以为大家。”③因此,“老去填词”就词体创作而言具有明显的反省意味,也是晚近词人的普遍选择,不论是常州词派还是浙西词派后期词人都更为重视“老去填词”所达到的词笔随年健的境界。如果说从朱彝尊开始,“老去填词”是清词开拓的新的词体创作境界,那么到了晚近时期,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转变促进了这一范式的经典化,在词境上体现出更为老道成熟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出现是词体发展的自然规律,是时代风会契合于词人词心的结果。
其次,“老去填词”范式体现了学人之词的风范,提升了词体创作的品格。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词人的词体创作尤其注重音韵格律,所谓“守律严谨,自是学人本色”④。“老去填词”带有一种做“专门之事业”的创作态度。谭献曾描述王尚辰(1826—1902)填词情形,说:“谦斋老去填词,吟安一字,往往倚枕按拍,竟至彻晓。固知惟狂若嗣宗,乃为至慎。予自来合州,与谦斋交,改罢长吟,奚童相望,两人有同好也。”⑤王尚辰与徐子苓、朱景昭合称“合肥三怪”,老去填词,为一字而彻夜推敲,用力之勤可见一斑。谭献又评价许增说:“迈孙老去填词,传频伽、蒹塘本师衣盔。频年校刻《古今名家词集》,千金一冶而矜慎下笔,一字未安,不欲问世。”⑥清代是传统学术的大总结时代,也是各文艺类别广泛融合的时代。谢章铤说:“长短调并工者,难矣哉。国朝其惟竹垞、迦陵、容若乎。竹垞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⑦朱彝尊词以学胜,特指其词表现出来的学识涵养及高古宽博的审美情趣。晚近文人以追求诗、书、画、印“四全”为最高的文艺理想,嗜好金石碑版及古器物的收藏及鉴赏,深刻影响了词学审美祈尚。如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都嗜好金石碑版,况周颐曾受缪荃孙之邀,与李瑞清、程颂万等在南京淮舫唱和。程颂万赠诗况周颐云:
白袷残春建业城,共君金石论纵横。秦淮赁庑兼歌哭,老去填词易姓名。砚外转灯移水色,酒边欹枕听潮声。香楼旧址迷离外,不负看山读碣情。(况夔生近更名芸台,号阮庵,所居周氏河亭得小碣,有媚香楼三字。)⑧
清中晚期金石学兴盛,文人普遍嗜好金石,濡染甚广,所谓“共君金石论纵横”是当时文人的生活日常,况周颐中年以后嗜好金石碑版,以金石入词,词风为之一变。此次聚会是一次金石雅集,所谓“老去填词易姓名”“不负看山读碣情”。况周颐多以“沉着”“能成就”“密”“深静”论词,无一不透露出学人之词的老成境界,尤其是“重、拙、大”更是带有鲜明的金石气倾向。蔡嵩云曾指出:“何谓重、大、拙,则人难晓。如略示其端,此三字须分别看,重谓力量,大谓气概,拙谓古致。工夫火候到时,方有此境。以书喻之最易明,如汉魏六朝碑版,即重大拙三者俱备。”①因此,况周颐“老去填词”引领的是“重、拙、大”的新词风。又如缪荃孙(1844—1919),是晚近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和目录学家,有《碧香词》共计45首,曾在写给金武祥的一通书札中说道:“弟自选常州词,三年以来填词二三十阕,夔生、仲修以为可存。老去填词,亦属可哂。然每日阅数十首词,操笔即来,今日欲求深处,反觉思涩,能于涩中再入自然,当有进境。”②这里说的“自选常州词”,是指其编纂《国朝常州词录》之事,三年填词二三十阕已经占其词集一半,因此缪荃孙词体创作并不如诗歌创作一样自少及老,而是老去填词。他说自己填词追求意境上的深,但求深难免会思涩,其实不止思涩,下笔亦会走涩之一路,继而又希望能够于“涩中求自然”。作为金石学家的缪氏濡染金石碑版甚深,自然在审美上偏向于古拙之美,尤其是书学史上碑学大盛,碑学书法家多以涩笔追求篆隶书法的朴厚凝重风貌,直接影响到词学。晚清词学大兴“梦窗热”,一时间词人纷纷学习以艰涩难解见长的吴文英词,因此有尚“涩”之风。黎国廉字季裴,有《秣音集》,叶恭绰编《广箧中词》录其词,评价说:“季裴丈老去填词,刻意梦窗,功力深至。”③所谓“老去填词词意涩”,可见晚近时期的“梦窗热”及尚“涩”之风是词人们“老去填词”的一大祈尚。“老去填词”与传统词学的“要眇宜修”大相径庭,带有金石气的“重、拙、大”词风,尚“涩”“密”“沉着”等倾向可以说是学人之词在审美上规避甜俗、纤佻、浅滑进而转向老到、沉着的倾向所致。学者型词人的“老去填词”提升了词体在美学上的维度,并融合了书画印等艺术门类的审美趣味,形成了学人之词的独特趣味。
最后,从清初“老去填词”的首倡到晚近时期的经典化,“老去填词”的创作范式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朱彝尊经历了明清易代,半生飘零,感慨异常,弃诗为词,赋予“老去填词”丰富的内涵与意蕴。晚近时期整个社会政治内忧外患,动荡不安,民生困敝。很多士人面对这样的时局心态随之内敛,将无限悲悯与沉痛寓于词体中,聊以遣怀寄兴。较为典型的是蒋春霖,其“早岁工诗,中年乃专力填词。……所作词多抒仕途坎坷、穷愁潦倒之感,而其咏时之作,谭献乃称之为‘词史’”④。谭献又评曰:“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⑤褒扬其词反映家国之患,具有“诗史”特质,这一段评价被词学史广泛接受。⑥庚子事变,王鹏运与朱祖谋、刘福姚身陷危城,避祸四印斋,以填词纾解内心的愤懑与苦楚,有《庚子秋词》名动一时。此时王鹏运已是风烛残年,⑦其《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云:“华发对山青。客梦零星。岁寒濡呴慰劳生。断尽愁肠谁会得,哀雁声声。 心事共疏檠。歌断谁听。墨痕和泪渍清冰。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⑧沉痛悲凉,读之令人心灰。郭则沄认为,王鹏运《庚子秋词》中如《鹧鸪天》谓联军盘踞禁苑,叫嚣廛陌也;《谒金门》哀首祸亲贵也;《三字令》谓京僚疏请回銮,而订期屡展也。余作皆有所指等等。⑨虽然没有实证,但其所抒发的情志影射时局毋庸置疑。龙榆生说:“彊村先生四十始为词,时值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左袵沈陆之罹、忧生念乱之嗟,一于倚声发之。故先生之词托兴深微,篇中咸有事在。……咸同兵事,天挺蒋鹿潭以发抒离乱之忧,世以拟之杜陵‘诗史’,若先生所处时势之艰危,视鹿潭犹有过之。读先生之词,又岂仅黍离麦秀之感而已!”①叶嘉莹也说:“郑文焯(词)反映的是庚子之乱的流离,朱祖谋(词)反映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②吴梅在朱祖谋去世后有《水龙吟·古微丈挽词》云:
暮年萧瑟江关,举头惟见河山异。抗声殿角,回楂岭表,乱云如戏。海峤莺花,吴门鲑菜,忽忽弹指。记听枫旧馆,隐囊挥麈,知珍重林泉意。 还是悲歌无地,结沤盟、沧江鼎沸。东华待漏,中兴作颂,纷纷槐蚁。忍泪看天,十年栖息,天还沉醉。算平生孤愤,秋词半箧,付人间世。③
词开头以“暮年萧瑟江关,举头惟见河山异”点明朱祖谋老去填词以寄托山河之变的悲哀,接着概括朱祖谋从政经历。下阕写政局变动以及后人对其效忠清王朝的议论,最后悲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黯淡结局。“九一八事变”不久,逊帝溥仪逃至东北,郑孝胥、陈增寿等遗老前往追随,此时与其同声共气的朱祖谋进退两难,深感悲绝,留下遗词《鹧鸪天》云:“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姜被减奇温。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后牛衣怨亦恩。 泡露事,水云身,枉抛心力作词人。可哀惟有人间世,不结他生未了因。”④这首词隐晦地吐露了其家庭不和的苦楚和不能为家国尽忠的悲凉心境,也言明其以填词为事的无奈,所谓“进为国直臣,退为世词宗”⑤,是这一历史时期多数词家的选择。
近人陈作霖(1837—1920),有《可园词存》四卷,曾自序曰:“予六十以后,始学填词。家国伤心,寄情楚些。竟犯绮语之戒,发为凄惋之音。红豆相思,谁裁曲谱;青衫下泣,遂付琵琶。”⑥由于所处时代政治动荡,家国不宁,所以作者将内心的苦楚诉诸于词,这样的词更多地是寄托自己的家国之思。张伯驹为靳志《梦华集》作序说:“长安近日,局棋又新。大陆方起龙蛇,君子将成猿鹤。痛定思痛,言无可言……少年结客,驰驱锦绣之丛;老去填词,飘泊干戈之际。燕垒斜阳,谁怜王谢;兔园雪月,尽减邹枚。读君斯篇,生我离绪,能不下晋驼之泣,动越鸟之思乎?”⑦叙述了时局的动荡纷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志之士痛惜之余却无能为力,只能混迹于各种诗盟酒会聊以自遣。张伯驹感慨自己年少时是“驰驱锦绣之丛”,如今老去填词,身处“漂泊干戈之际”,历经沧桑,因而在读了靳氏的词集后更觉悲凉凄惋不能自已。姚鹓雏说自己原本“不谙倚声”,后“瞻念乡园,贼烽犹炽;伤时感事,辄托小词。文隋情生,音无繁缛,等之竹枝杨柳,信口可歌,固非嚼征含商、窈渺刻深之比也”⑧。因此,“老去填词”与晚近时期的家国之患直接相关,正是由于词体的内敛性特征,处于忧患焦虑中的文人才将词体作为其排解内心郁闷、隐喻时政的表达路径,“老去填词”成为这一时期词体创作的经典范式,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结语
朱彝尊历经家国之变,半生飘零,仕途迁蹇,以“老去填词”来纾解自己的失意困顿,开拓了词体创作的新范式,在后世被文人广泛接受,并逐渐经典化。从词学史上来说,相对于“悔其少作”的唐宋词人,清人“老去填词”是对词体在更深层面上的接受,打破了“青春词”的局限。在词体自产生至发展、成熟,进而成为一代之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身份问题一直是词学的首要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一部词学史就是一部尊体的历史。至晚近时期,由于内忧外患的时局环境,不少文人选择以“老去填词”自遣,“老去填词”是尊体意识的重要体现。“人书俱老”是唐代书法家孙过庭评价书法时提出来的,意为书法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学识的累积而呈现出一种老成的境界。词学家朱庸斋引用孙过庭的话,说:“‘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此孙过庭《书谱》论学书程序语,极精到。余谓学词亦如是。”①至此,词体创作与诗、书法等同有“老”之一境,表明晚近词风转向更为深沉的境地,体现了学人之词在审美上的新拓展,也标志着清代词学尊体事业的九转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