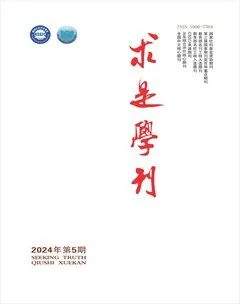阿多诺关于审美幻相的思考及其当代意义
关键词:幻相;艺术作品;审美;真理
按照阿多诺的看法,艺术作品包含了真理内容。如果艺术作品包含了真理内容,那么我们把握艺术作品就是要把握它的真理内容,而不是去拯救幻相。从常识的观点看,幻相并不是真理,充其量不过是伪装的真理。那么,阿多诺为什么强调审美的核心是拯救幻相呢?这不仅与阿多诺对于幻相的理解有关,而且与其对于艺术的精神、艺术作品的本质特点的认识有关。通过领会阿多诺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不仅可以深入理解阿多诺审美理论,提升审美能力,从而更好地领会艺术作品,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真理与幻相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
一、如何理解幻相
阿多诺对于幻相的理解主要吸收了康德的观念。按照康德的看法,理性有一种无法避免的倾向,即它试图通过概念的纯粹运用,进行一种系统的推理,从而去规定自在之物。在这里,理性“把我们的概念为了知性作某种连接的主观必要性,看作了对自在之物本身进行规定的客观必然性”①。本来人们在主观上把知性概念连接起来,是为了把这些概念构成一个体系,但是人们却误以为这种主观的连接是对自在之物本身进行了客观的规定。这是理性为了达到最终的真理而产生的一种错觉,是“对纯粹知性的扩展的错觉”。他所说的幻相也包含了这种“错觉”。理性把只能经验地使用的知性概念用到了没有经验根据的对象上,并错误地认为,它达到了真理。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这个意义上的幻相理解为先验幻相。在康德那里,认识所要把握的对象是现象,当认识超出现象领域的时候,理性就会走向幻相。阿多诺把艺术作品既看做是现象,又看做是幻相。对于阿多诺来说,艺术作品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幅画、一尊雕塑、一场戏剧等,不是某种客观的东西,而是与人相互作用中存在的东西。用阿多诺的话说,人要把这种物化的东西精神化。这种精神化的东西就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现象或“现相”。但是艺术作品是要达到超出现象的东西,是要达到绝对。于是艺术作品既是现象又是幻相。这就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现象与幻相是不同的。
由于艺术作品是精神化的东西,因此艺术作品是动态的,是一种精神活动。阿多诺甚至认为,艺术作品是一个过程。对于阿多诺来说,虽然艺术作品是人创造的,但是艺术作品的精神却独立于人。于是,艺术作品好像变成了某种独立自主的东西,某种自主的精神活动。也正因为如此,阿多诺把艺术作品理解为具有内在性意义的单子。阿多诺对于艺术作品的这样一种理解其实也扩展了传统的艺术概念。在传统上,人们把艺术作品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的意义类似于知性在现象领域所获得的知识。但是精神不满足于这一点,精神要努力达到真理,于是精神就超越了现象的范围。当艺术的精神超出现象的范围的时候,艺术的精神就走向了幻相。因此,艺术作品的幻相是与它的真理内容有关的。如果艺术作品是一个精神的过程,而这个精神过程要不断地追问绝对,那么这个艺术作品就会如同理性一样要走向一个总体。这就是说,艺术作品要变成一个意义的总体。但是,艺术作品恰恰与理性的科学体系不同,它要把握的是无法用概念表达的意义,它常常包含了许多歧义。所以,艺术作品不可能变成一个意义的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作品越是想成为一个意义的总体,这个意义的总体就越是分裂的。不仅如此,艺术作品是把客观化的东西精神化,比如,把一幅画、eU200wypcanljardENkeUuZZtgmY/CurpIAUohuAq5o=一尊雕塑精神化,而这些雕塑作品或者绘画作品恰恰是物化的东西,艺术作品的精神化总是受到物化的质料的束缚。艺术作品中总是存在着精神和质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于是,艺术作品要成为一种观念化的总体是不可能的,艺术作品必然会陷入一种幻相之中。阿多诺说:“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取决于它们能否成功地把与(艺术)概念不一致的东西、从概念上看偶然的东西吸收到其内在的必然性中。艺术作品的目的性要求无目的性。其结果是虚幻的东西渗透到它们自身的一致性中,幻相是它们的逻辑。”②
艺术作品的真理性是与它的幻相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一种现象,但是却又要超越现象而走向绝对(非同一的东西,只能借助于模仿来把握的东西)。当它努力走向绝对的时候,它认为它把握了绝对,达到了非同一的东西,但是其实它并没有达到。这就如同康德所说的,本来理性应该对于知性概念进行经验的使用,从而获得知识,但是理性却把知性的概念进行了先验的使用,并认为它像把握现象那样把握了绝对的东西。这样,他就陷入先验的幻相,这个先验幻相中包含了理性的一种错误意识。而艺术中的幻相也是如此。阿多诺说:“审美幻相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带有审美上的非一致性,这种非一致性是艺术所显现的样子和艺术的本来的样子之间的矛盾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要素通过展示出来的样子而提出了本质性内容的狂妄要求。”它显现出来的样子(在精神中显现出来的样子)好像达到了绝对,它完全直接把非同一的东西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展示出来了,好像真理在这里直接出现了。当我们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感到震惊,我好像直接把握了本质。但是,这个显现出来的样子和本来的样子是矛盾的。艺术作品的本来样子并不是如此。审美主体在这里以为自己达到了绝对,其实它并没有。所以阿多诺强调:“这些要素从否定的角度尊重这一要求,尽管它们自身展示出来的样子以肯定的方式表现出更多的东西的姿态,这是一种即使是彻底地不追求感染力的作品也无法摆脱的感染力。”①艺术作品好像以肯定的方式达到了某种更多的东西,即超出现象的东西,但是其实不是,艺术作品中的这些要素只是“从否定的角度”满足了这个狂妄的要求,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理性的狂妄要求。
从康德哲学中,我们知道,幻相是理性从内在的领域走向超越的领域而产生的。艺术中的幻相也是从内在性走向超越性的结果。知识的领域是我们可以用概念来把握的领域,而艺术是要把握超出概念的领域。这个超出概念的领域需要借助于模仿才能达到。艺术以吸收传统的模仿的方法来达到这个超出概念的领域。不过阿多诺对于超越性有着特殊的理解。对于他来说,超越的东西是内在的。他从一种内在超越的道路来达到超越性。在他那里有一种“内在性的辩证法”。而他所理解的这种“内在性”是与“被狭隘地关注的内在性”是不同的。“被狭隘地关注的内在性”是否定了超越的内在性。当我们从辩证的角度来理解内在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内在性中所包含了幻相。阿多诺说:“如果人们不那么严格地看待艺术作品的内在封闭性,那么正是在这些作品认为自己最不受幻相影响的地方,幻相压倒了它们。”②纯粹的内在封闭性不过是谎言,内在性中包含了超越性,因而包含了幻相。
二、幻相的危机
从前面关于审美幻相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艺术作品对象化为一种客观的东西的时候,这种客观的东西又要被摧毁。我们不能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对象化的、固化的东西,而要从动态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我们把它们精神化,从而达到真理的内容。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审美幻相就是在它从现象走向超越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要避免这种幻相,那么在我们的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把艺术作品变成纯粹的现象,或者把艺术作品变成纯粹的超越。把艺术作品变成纯粹的现象或者变成纯粹的超越的做法就会导致幻相的危机。当人们把艺术变成纯粹的现象的时候,艺术就缺乏超越的维度,而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要素。而艺术变成纯粹超越的东西的时候,艺术就与社会生活无关,变成纯粹的奇思妙想。艺术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取得一种“幻觉效果”。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们都缺乏对于内在和超越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正如康德对于认识中所出现的幻相表示不满一样,在艺术领域,人们对于幻相也会产生不满。康德致力于把现象和超越分离开来,把认识限制在现象的领域,从而消除审美幻相。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人们也同样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艺术能不能幸免于幻相?”③
如果艺术作品变成一种独立于经验领域,变成一种自在存在的东西,那么它就可以避免幻相。阿多诺认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部分就是要试图克服艺术作品中的幻相特征的努力。在这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在不强行确立其内在形式的情况下,在不假装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进入艺术的单子中”。好像艺术作品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不需要借助于“想象和虚构”而变成一个独立的单子,这个单子好像不是人造的,不是人为活动的结果。作品在这里取得了一种幻觉效果。所以阿多诺说,在这种审美构造中,“ 审美幻相被提升到了幻觉效果(phantasmagorie)的地步”。这种幻觉效果的作用是,本来艺术作品是人为的,但这种人为的东西好像是艺术作品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艾伦·坡的《皮姆历险记》也有这样的特点。这个历险记好像是讲皮姆本人的真实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经过坡的文字加工变成了小说。小说虽然是虚假的,但坡的小说是真实的。作者在这里玩弄真实和虚假,把虚假变成真实。阿多诺认为,艺术创作中的这些特点表明:“不断传播的实证主义精神如此这般地渗透到艺术之中,以至于艺术渴望成为事实,并对任何显示其被压缩了的直接性也是被中介过的情况感到羞耻。”①当艺术渴望成为一种事实的时候,艺术作品就是要客观化,实证化。好像它们是直接存在的事实而没有被精神所中介过。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幻相的危机。
幻觉效果的功能是让人产生一种艺术作品自在性的幻觉。阿多诺说:“在小说中,对另一个世界进行窥视的幻觉,被虚构的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所控制,这个幻觉既要有一个人为构造出来的世界的现实性,也需要像虚构小说那样的非真实性。”②阿多诺对于小说的这个描述,与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级真实是一致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超级真实是比真实更加高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矛盾消失了。鲍德里亚说:“非真不再是梦想或者幻觉的非真实,不再是彼岸或者此岸的非真实,而是真实与自身的奇妙相似性的非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不是真实,是被制造出来的真实。鲍德里亚在分析新小说的时候说:“新小说设想在真实的周围创造空无,铲除一切心理和主观性,让小说恢复纯粹的客观性。事实上这种客观性只不过是纯粹目光的客观性——这是终于摆脱了客体的客观性,它从此只是接替那种略过客体的目光。”③这种客观性是没有客体的客观性,只是确认目光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其实是人为构造起来的客观性,它是一种幻觉效果。当艺术作品取得一种幻觉效果的时候,艺术作品抹去了它的产生的痕迹,艺术作品变成了一个独立于人的虚构的领域。
与这种用幻觉效果取代幻相的做法不同,人们还会把某种现实的东西纳入艺术作品中,从而破除艺术作品的幻相特征。这种做法就是把艺术作品变成经验现实中的一个要素。我们可以说,这其实也是艺术中所出现的一种“实证主义倾向”。按照阿多诺的分析,20世纪初,在艺术中出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哈姆雷特穿西装,罗恩格林没有天鹅。”④这就是让艺术作品回归现实,变成一种事实性的东西,消除那些会引起人们想象的东西,消除那些让人们产生幻相的东西。这就是说,艺术作品要对抗它自身的“内在意像(imagerie0tD2KO+ePVa3TaJx+zMvG/S7vAYpjoHZWVJbl+LGOLE=)”。本来,按照阿多诺的看法,艺术是自律的,是与经验现实相对立的。但是,艺术要把现实的东西引入艺术中,从而破除艺术的之中“内在意像”。这种做法就是要消除艺术作品的超越性的维度。
当艺术作品试图克服幻觉效果的时候,艺术走向了新客观主义,走向了新小说。但是,无论在新小说,还是新客观主义中,它们都无法彻底摆脱幻相。然而,艺术作品又努力摆脱幻相。甚至一些包含了幻相的艺术作品也都被人们看作非幻相的艺术作品。本来表现主义反对复制外部现实,这就是要把幻觉要素加入艺术作品之中。但是,它在反对现实主义的时候把这种表现看作一种心理因素的表现,变成了心理图像,幻相的特点被否定了。艺术作品越来越变成一种艺术的事实。所以阿多诺说:“艺术正回归到纯粹事实的状态”。阿多诺认为,这是艺术的倒退。比如,杜尚的“泉”就是消解艺术的一种倾向。他说:“最近对科学的幼稚无知的模仿是这种倒退的最明显的症状。”他还进一步强调:“当前,许多音乐和绘画作品,尽管缺乏再现式的客观性和表现力,却完全可以被归入第二自然主义的概念之下。”在这种去幻相的努力中,有些艺术家采取了一种物理主义的态度,把音乐回归到纯粹的声音,甚至回归到可以用物理学的方法来加以计算的声音。在阿多诺看来,“这种方法绝望地压制审美幻相,而这个幻相就是艺术所确立起来东西的真理性”①。幻相的危机类似于哲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的危机。人们从一种实证主义的角度否定形而上学的东西。
其实艺术的这种趋势就是社会生活中的物化趋势在艺术中的反映。或者说,艺术被迫接受社会的物化趋势。阿多诺承认一切艺术都受到社会要素的影响。然而,虽然艺术作品中也会包含物化的趋势,但艺术是要批判这种物化趋势的。比如,它通过虚构的方法把这种物化发展到极端来讽喻这个物化的世界。可是,艺术的这种做法却决不能等同于把艺术变成现实中的一个既定的事实。阿多诺指出:“对灵韵的厌恶,是今天的任何艺术都无法逃脱的,也是与非人性的东西的爆发分不开的。”在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中,艺术也反对灵韵。当艺术作品厌恶灵韵的时候,当艺术把自己变成一种确定的现象的时候,甚至把想象也变成一种确定的现象的时候,艺术就失去了它超越社会的力量。阿多诺指出:“一旦艺术作品如此狂热地担心它的纯洁性,以至于对这种纯洁性产生了困惑,它开始向外翻转,关注那些不再是艺术的东西,比如画布和纯粹的色调,艺术作品就成了它自己的敌人,成为目的理性的直接和虚假的延续。”②工具理性的方法渗透到艺术之中,甚至创作者的心理状态也变成了一种心理图像,想象也变成了图像,所有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种事实。艺术不再是艺术,而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东西而已。
三、幻相与艺术中不可避免的矛盾
虽然现代艺术要消除幻相,但幻相又是它所无法消除的。于是现代艺术中出现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中所出现的这种特点恰恰显示了现代艺术的伟大之处。
在认识过程中,理性试图从主观上把概念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体系。艺术作品在追求真理内容的时候也试图达到这一点。它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备的统一体。但是,艺术不可能直接达到真理的内容,也不可能成为完备的统一体。阿多诺说:“没有一件作品是完备的统一体,每一件作品都装扮成为这样的统一体,从而与自己发生碰撞。”③这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二律背反的,却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统一体。艺术作品的幻相特征表明,艺术试图假装自己是这样一个统一体。在艺术作品的精神化过程中,艺术作品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内在的同一体,并把自己与现实对立起来。阿多诺把这个统一体中所出现的幻相说成是“内在的幻相”。但是,艺术作品在进行整合的时候必须把精神的他者带入艺术作品中,如果没有他者的要素,艺术作品也不需要进行整合。艺术所实现的整合恰恰表明,这种整合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要努力成为一个意义统一体。但是,这个意义统一体恰恰不是统一体。也正因为如此,阿多诺说:“艺术作品借助于它自身的意义关联而自封为自在的存在者。这种意义关联是艺术作品中的幻相的工具。”艺术作品把自己构建为一个虚假的意义统一体,而就在这种关联中幻相出现了。可是,如果诗歌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是骗局,如果这里不存在意义的统一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诗歌呢?难道我们就是要把自己陷入一种骗局之中,我们喜欢骗局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虽然诗歌不是意义的统一体,但这也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客观的意义。不过艺术作品中的客观意义、艺术所包含的真理内容不能肯定地出现。这种意义是作品中的“隐藏的本质”。它要通过否定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才能出现。所以,艺术作品不能出现统一的意义,而恰恰是在对于统一的意义的否定中走向客观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出,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意义是矛盾的意义,是意义的幻相。这种意义的幻相就是要告诉人们,他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所得到的意义是虚假的意义。但是,“意义的幻相不是意义的全部规定。”当我们取消了这种意义的时候,艺术作品中还有一个没有肯定地显示出来的意义,需要人们仔细地加以追问的意义。人们建构艺术作品,把艺术作品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就是要让艺术作品“说话”。但是,当艺术作品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从作品中阅读那些“话”。用阿多诺自己的话说,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沉默”来说话。我们要在作品有声的地方,找出其沉默的东西。这个沉默的东西在“说话”,并且这个沉默的“话语”才是客观内容。在这里,隐藏的本质不是肯定地存在的,但也不是不存在。所以,阿多诺说,这个本质是“怪物”。艺术作品就借助于这个本质来表达意义。阿多诺说:“当艺术把隐藏的本质——艺术要把这个本质置于现象之中——当作怪物来谴责的时候,这种否定同时也把一种不在场的、可能性的本质当作自己的手段;意义甚至存在于对意义的否定之中。”①在这里,这个隐藏的本质变成了否定表面意义的手段。其实,这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用语言描述某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是要从客观上达到事实(真理),但却并不能果真达到真理。语言中的事实并不是事实。于是,我们必须否定了语言,才能达到事实。我们需要描述事实,又需要否定这种描述,才能真正走向事实。艺术作品也是如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艺术作品的本质意义是借助于幻相来表现的,但它又不同于幻相。幻相是艺术作品在试图构建一个统一体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它假装自己达到了真理内容,但却不是真理内容。虽然它不是真理的内容,但它却是达到真理内容的手段。由于艺术作品的客观意义是与幻相联系在一起的,是否定性地出场的,所以阿多诺说:“一切意义都被赋予了悲伤,艺术越是悲伤,成功组合就越是意味深长。”对于这里的悲伤,他是这样解释的:“悲伤是一切形式之中异质东西的影子,而这种异质的东西是形式力图要加以消除的纯粹的定在。”异质的东西是与艺术的精神相对立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被压制的东西。在阿多诺看来,任何形式(幻相也是广泛意义上的形式)都包含了非形式的东西,都有内容沉淀于其中。这些内容对于艺术的形式来说是异质的东西,是艺术的形式要努力消除的纯粹定在。如果说形式是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特征的话,那么这种形式又压制其中的所应该包含的内容,于是这种内容就表现出一种被否定的意义,带有悲伤特点的意义。而这种带有悲伤特点的意义总是意味深长。于是,“从艺术作品中所无声地散发出来的是,它之所是,而又通过它——一个不确定的语法主体——之所不是,而得到宽慰。”②在这里,艺术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意义是通过否定的形式出现的,即这个意义不是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是它所不是的东西。艺术作品之所是,恰恰是它所不是的东西。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说过,艺术作品是现象,但又超出现象。
在康德看来,艺术作品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的特性。这就是说,它有一种内在的目的。这是因为,艺术作品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人把这个东西制造出来,肯定是有一种目的表达在艺术作品中的。按照康德的分析,在认识自然界的时候,我们试图把我们的知识变成一个系统,这是理性的调节性运用的一个结果,理性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自然界虽然不是果真有目的的,但它们似乎是有目的的,似乎是一个体系。而艺术作品恰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它具有内在的合目的性。自然界所无法达到的东西艺术却可以达到。但是,如果艺术作品是一个完备的系统,那么它就应该是自在的,是一个完全自主的系统,如果这个系统要依赖于这个系统之外的东西,那么这个系统就恰恰是不完备的。艺术作为一个系统恰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自主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不完备的。它越是要成为一个完备的统一体,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目的的东西,它就越是无法成为一个内在的统一体,它的内在性依赖于外部的东西。于是艺术作品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一种幻相。因此,阿多诺说:“由于这种统一体不存在,由于作为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否定了(艺术作品)自在存在(的特点)。”③艺术本来是要成为一种自在的东西的,但是它又是人为性的,它否定了它自身。这是艺术不可避免的幻相。
艺术的这种幻相特征在艺术的表演中表现得最突出。艺术作品所要体现的是绝对的东西,是必然的东西,但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是人工制品。人们在表演中无法达到必然的东西。为此,阿多诺说:“任何一种艺术作品的不可能性规定了杰作的最简单方面。”杰作就是要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或者说,艺术作品就必须朝着这个不可能的方向努力。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表演者所面临的是“作品内容和它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的不可调和性。作为内容,作品是要表现绝对的,是要达到真理的,但是作为现象,它却无法达到这一点。这类似于我们在艺术表演中常常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表演中究竟是表演者与角色一致起来,还是表演者与角色拉开差距?这表明,在艺术表演中,演员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与角色的要求完全一致起来。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在这里“表演所进行的恰当解释就是把作品作为问题来说明:这就要认识到一种不可调和的要求,即表演者在面对的作品内容和它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时所出现的不可调和的要求”。在面对着这个问题的时候,表演过程所采取的方法是,“作品的表演在把一件作品呈现为杰作的时候必须找到一个冷漠点,在这个点上不可能东西的可能性被隐藏起来了”。这里所说的不可能的东西是指达到真理这种情况,即达到艺术作品本质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表演的过程中演员要把这种不可能性隐藏起来,好像他可以达到本质。阿多诺说:“由于作品是二律背反的,完全恰当的表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表演都必须压制矛盾的元素。”艺术的表演把不可能性变成可能性,其实这就是一种幻相。按照阿多诺的标准,压制矛盾就是一种强制。如果暴力的强制被表现出来,那么艺术作品就没有美感了。因此,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表演不是要掩盖这个矛盾,而是要在无压制的情况下表现这个矛盾。但是,赤裸裸地表现矛盾也不行,艺术的表演还要不断地纠正这些矛盾。在阿多诺看来,如果艺术的表演达到这样一种水准,那么就是一种精湛的艺术表演。本来演员是无法达到与角色一致的,但表演者却掩盖了这个矛盾,好像他已经和角色完全一致了。其实,这是幻相。所以,阿多诺说:“那些被刻意构思为杰作的艺术作品都是幻相。”①杰作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接近艺术作品,忠实地表现艺术作品。而当它接近艺术作品的时候,就必然走向幻相,把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类似于艺术的魔术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这是一种被掩盖了的虚假,类似于幻相。杰作就是一种幻相。这种幻相与所欲求的事情是不同的。康德说:所欲求的事情就是能够做到的事情,就不是艺术。②
四、幻相与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要不断地压制艺术的幻相;另一方面,消除幻相的努力恰恰又把幻相再生产出来。
当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就被固化为某种东西了。但是,我们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不能把它当做某种固化的东西,而是要把它作为动态的东西。但艺术作品本身作为被固定下来的东西,作为现成存在的东西,只能假装自己是动态的东西,“假装它是变”。既然艺术作品本身是把自己“假装”成为变的,而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真正变成变动的东西。这就是要把它从人造物变成非人造物,即固化的艺术作品作为人造的东西,似乎还包含了非人造的东西。杰作其实就表现了艺术作品中的这种特点。这就是说,一种人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的东西,在艺术作品中被达到了。于是,人造的东西表现出非人造的特点。阿多诺概括说:“在杰作的悖谬中,在把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的悖谬中隐藏着绝对的审美悖谬:人造物如何作为非人造物出现?一个按照其概念不正确的东西为何也是正确的?只有在内容不同于幻相的情况下,这才是可能的。然而,艺术作品只有通过幻相,通过幻相的形式才有内容。”①这里的作品中人为的东西和非人为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把现象和超出现象的关系体现出来了。我们在现象中所把握到的不是真理内容,真理的内容超出了现象之外。现象所体现的是不正确的东西,但是这个不正确的东西中却又好像在告诉我们正确的东西,而这个正确的东西又不是现成存在的。
cMk8ZV4BGxH2xYhUMBhqsA==可是,在这里,我们又必须注意,当我们通过幻相走向真理内容的时候,这个真理内容很容易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为某种现成在手的东西。阿多诺指出,拯救幻相就是要拯救被精神所剔除出去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非精神的东西,就是要拯救艺术作品在被还原为质料的时候所剔除掉的东西。这里要拯救的是非精神的东西,是客观的东西,但这个客观的东西也不是质料性的东西,而是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性内容。这个要被拯救的东西既非精神,也非质料,但同时又与精神、质料有关。这个东西不是现成存在的。可是,在把这种真理内容拯救出来的时候,这个真理内容就好像变成了现成的东西。而这又是错误的。所以,阿多诺在这里指出:“通过幻相来进行救赎本身就是幻相,而艺术作品以其自身的幻相的形式接受了这种无力。”②在拯救幻相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了幻相之中。我们误以为真理内容被把握在手了。这是艺术作品所无能为力的。人们在拯救幻相的时候,是要把握真理内容的,但把握真理内容的努力本身也变成了幻相,而艺术作品对于这一点是无能为力的,它不可能把真理作为现成的东西呈现出来。
拯救幻相就是要把握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这个真理内容是与艺术的质料有关的,是精神的他者,但这个精神的他者在艺术作品中是被压制、被否定的。这是因为,艺术的真理性内容必须借助于质料才能得到把握,但艺术的真理性内容又不能被还原为质料。为此,阿多诺强调,幻相是艺术作品的质料的特征,即艺术作品中的质料既是质料,但又不是质料。或者说,这个质料必须在精神化中被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的幻相既伤害了质料,又试图撤回这种伤害。由于艺术的幻相既伤害质料,又要撤回伤害,于是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从它所呈现的样子来理解艺术作品。如果我们直接从艺术作品所呈现的样子来理解艺术作品,那么我们就忽视艺术的幻相对于质料所进行的伤害。我们就陷入了一种“逼真绘画技法的骗局”之中,我们就错误地以为,作品把真理内容直接呈现出来了,其实真理的内容是隐藏在作品中的,而不是直接呈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隐藏在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就被牺牲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和它想成为的样子之间是不同的,艺术作品想成为的样子是它要直接达到真理内容,但它实际的样子是达不到这一点的。而艺术的幻相就是要让人误以为,它实际的样子和它想成为的样子是一致的。这是艺术的理想,但是艺术作品却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如何拯救幻相呢?阿多诺所提出的方案是:“艺术作品应该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其实,阿多诺所提出的这个方法与康德关于先验幻相的观念是一致的。按照康德的思想,理性要对于分散的要素进行综合,从而达到一个完善的体系。这个体系也是自下而上地建构起来的。而幻相就是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建构艺术作品的时候,如果人们也是自下而上地组织艺术作品的元素,那么在这种组织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先天地保证艺术作品可以达到统一。为了达到这种统一,艺术作品在建构自身的时候就预先对于其自身的要素进行加工,并由此而把艺术作品预设为一个统一体。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幻觉,好像艺术作品果真达到了统一体。在这里,“弥散的异己的东西与预设的整体先天地和谐相处,而和谐本身却是被确立起来的”③。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幻相得到了拯救。
本来拯救幻相是要从精神化的角度理解艺术作品,让艺术超出感性的要素,但阿多诺在这里又反过来强调,拯救幻相所要达到的不是纯粹精神性的东西。它所要达到的既是精神性的又是感性的。这与《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对康德关于上帝的理解是一致的,即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又必须被设想为存在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显然,理念是被排除在感性的范围之外的,理念不可能以感性的形式出现,但在艺术中理念恰恰又以感性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用一个矛盾的说法来表达这一点,即它是“感性的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在阿多诺看来,艺术中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幻相是因为,当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的时候,精神就变成了子虚乌有的东西,于是,精神必须借助于感性的要素才能把自己显现为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精神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存在者”。而艺术就按照精神的这个要求,把精神果真变成了一个“存在者”。阿多诺说:“艺术在字面上采纳了精神要成为存在者这样一种要求,并把这个存在者放在眼前,通过这样的方法,艺术检验了精神的幻相性是它的独一无二的本质。”艺术把“非存在者”,把精神变成了存在者。艺术同时也检验了自己,它意识到,幻相性是它的独一无二的特性,即把非存在者变成了存在者这样一种特性。可是,当艺术把非存在者变成存在者的时候,它同时也就意识到,精神也不是纯粹的精神,精神中一定包含了精神的他者,否则精神就不能变成存在者。这时候艺术中的“精神不仅仅是幻相,而且是真理;不仅仅是自为存在者的骗局,而且是对一切虚假的自我存在的否定”①。精神本来是“非存在者”,但这个非存在者包含了客观的内容,如果精神纯粹是空洞的,那么精神也无法变成存在者,可当精神变成存在者的时候,精神又扭曲了这个客观内容,好像这个客观内容已经被它完全把握了。在这里,精神不仅要把自己变成存在者,而且要知道它是虚假的存在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作品是幻相,同时也分有了真理。我认为,这个虚假的存在者可以用来解释这个“感性的理念”。
艺术的幻相是无法取消的,艺术作品的知识就和纯粹理性批判所说的客观知识不同了。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客观知识是关于现象的知识,而艺术作品不是这样,艺术作品是幻相,这个知识具有超越性的特点。我们欣赏艺术作品不会满足于艺术作品所提供出来放在我们眼前的东西。但是,这个超出眼前的东西又不是主观的、虚构的、纯粹精神的。这表明,客观内容既内在于作品之中,而又超出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艺术作品是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同时又是本质的表现。于是,艺术作品作为现象又是本质的现象。艺术要把本质的东西(客体)显现出来。阿多诺说:“在艺术作品中,现象是本质的现象,它绝不是与本质毫不相干的;在艺术作品中,现象属于本质的那个方面。”②
五、拯救幻相的现实意蕴和理论意蕴
艺术作品是一种现象,但又是幻相。在表面上它是人为作品,是有内在目的的,是要达到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却不可能是完备的体系。当鉴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人必然要获得一种经验,即那个试图变成一个完备的意义体系的东西永远都不可能是完备的。它必然包含了自身的矛盾。这意味着,通过人为构成的体系不可能是完备的体系。而现实社会就是要构成一个合理化的体系。既然它也是一个人为构造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永远都无法摆脱它的内在矛盾。审美本身就是要人们获得这样一种经验,即人为构造的体系一定是包含了矛盾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把握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从这个合理化的体系中看到这个体系的矛盾。正如,艺术的真理是超出现象一样,如果我们要在现代社会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个幸福的生活不能在这个体系中存在,而必须超出这个体系。而艺术作品就是在现实的交换体系之外的,是对抗这个交换体系的。
因此,假如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中幸福生活是可能的,那么这个幸福生活必须是超出这个合理化的体系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合理化的体系是一个让人绝望的体系。人在这个体系中按照市场交换的原则进行生存竞争,在这里我们毫无幸福可言。但是,如果我们果真能够超越这个生存竞争的体系,那么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可能的。这个幸福生活就如同艺术作品所显示的那样,它使无法和解的东西得到了和解。但是,我们也不要误解了,错误地以为在审美的领域中和解已经实现了。艺术作品中所实现的和解是一种幻相,并不是真正的和解。它只是告诉我们那些无法和解的东西实现和解是可能的。这就好像是说,如果我们果真在审美领域中生存,那么我们也不会有幸福。要过上幸福的生活不是直接逃避到这个生活系统之外,好像这个艺术的世界是一种“世外桃源”,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我们的生活就一定是幸福的。人类社会不存在这样一种现成的幸福。但是,审美的体验告诉我们,这种幸福生活又是可能的。阿多诺提出的那种内在的超越其实就预示了这种幸福的可能性,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我们自身的不断努力摆脱生存强制,或者说,在生存强制中摆脱生存强制。如果艺术作品中消除了幻相,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艺术作品就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把艺术作品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者艺术作品虽然提供了超越的东西,但它提供的是一种幻觉效果。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借助于艺术作品讽喻这个世界,批判这个世界,但这种批判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超越东西的体验。艺术作品始终变成了交换体系中的一部分。在第二种情况下,艺术作品给我们提供的是幻觉效果,变成了一种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游戏,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虚构和想象。而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幻相提供了一种内在超越的道路。这个内在超越之路给我们思考当代文明的出路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维尔默才认为,阿多诺对于幻相的拯救是对和解范式的拯救。①
艺术以一种外在于生活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思维,从而促进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艺术作品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却是抗拒市场体系的。它既属于经验世界,又和这个经验世界相冲突。阿多诺说:“艺术作品与经验世界的区别,它们的幻相特征,是由经验世界构成的,又是与经验世界相对立的。”这是艺术所无法回避的矛盾,一方面它要把自己同化到这个世界中,另一方面它又要对抗这个世界。因此,阿多诺说:“在这个过程中,当它模仿现实时,它把自己同化为它所反抗的物化:今天,介入不可避免地成为审美上的让步。”②艺术作品既要对抗这个世界,又要把自己同化到这个物化的世界中。在这里,当艺术作品成为经验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又要超越经验世界,并成为幻相。艺术本来应该坚持自己的幻相特点,但却不得不做出让步,要“介入”这个世界中。当然,这个“介入”不是要把艺术作品变成政治艺术,变成道德训条。而这种“介入”也使艺术陷入幻相的危机之中。
在康德哲学中,现象和幻相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当(广义的)理性超越了现象领域的时候幻相才会出现。而艺术恰恰就是要超出现象而达到超越的东西。或者说,在这里,内在和超越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艺术所达到的超越东西又与康德实践理性中所说的超越东西不同的。按照康德的学说,艺术是把超越的领域和现象的领域沟通起来的桥梁。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中的现象和幻相是结合在一起的。从认识论上来说,幻相是理性超越了感性的范围而产生的,是不合法的越界。而在艺术领域,理性借助于直观的能力达到一个理性所不能达到的领域,因此必然会出现幻相。艺术中所出现的幻相是人类企图把握本质的一种努力。阿多诺关于艺术作品是现象又是幻相的说法继承了康德的审美学说,又扩展了康德的审美学说。
拯救幻相体现了阿多诺审美思想中唯物论倾向。这种唯物论的倾向又与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阿多诺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内容或本质都具有非同一东西的特点。艺术作品是要把握非同一的东西,这种非同一的东西就保留在精神之中,即艺术作品的精神是精神同时又不是精神。这是因为,精神与理性一样有一种统一性的追求。在建构统一体的时候,精神又压制和扭曲了非同一的东西,这种非同一的东西不能肯定地显示出来。于是,这个艺术作品的统一体就成为一种幻相。而艺术家们又不满足于这种幻相,他们试图消解这种幻相,从而把真理的内容直接显示出来。这就导致了一种幻相的危机。幻相的危机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艺术超越传统艺术的必然趋势。但是,幻相的危机会伴随着一种艺术物化的趋势。艺术陷入了“第二自然主义”的困境之中。面对着这样一种趋势,审美的核心就是要拯救幻相,就是把每一件艺术作品作为幻相来理解。因此,在面对达达主义、新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拯救幻相的角度去理解这些艺术作品。它们也是走向真理内容的一种努力,但它们的努力走偏了。这就如同阿多诺在哲学上所批评的现象学一样。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是一种具有实证主义趋势的思想流派。他把非同一的东西——“存在”作为某种可以直观的对象。而新现实主义也是要把“非同一的东西”作为对象来直观。
这就好比说,艺术家把真理直接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直观真理的内容。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这种观念论的思路:“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①好像谜底就直接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品就已经把握了真理。阿多诺批评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是把艺术之谜等同于画谜。对于阿多诺来说,让我们震惊的艺术作品是把被隐藏的本质、被扭曲的真理显示出来,显示出来的真理又是幻相。从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努力把本质变成现象,变成可以直接被把握的东西,但一旦艺术作品把本质变成现象的时候,本质又被扭曲了,于是本质又要反抗自己成为现象。这里始终存在着非同一性。我们必须在这种非同一性的视角中理解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和艺术作品的本质。或者说,我们必须始终从幻相的角度去理解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和本质。它看上去是直接显露出来了,但它显露出来的时候,它又被扭曲了。在这里,真理始终是一种幻相,但我们也不能对于这种幻相感到失望,因为这种幻相同时也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