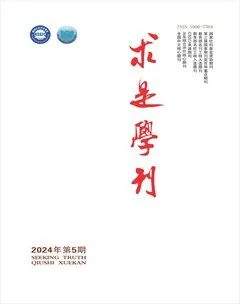“社会美育”: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第二原理
关键词:社会美育;蔡元培;美育思想;第二原理
最近几年,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社会美育”在学界显山露水,渐成气候。说它熟悉,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关于社会美育、学校美育、家庭美育的“三分法”,这是当时的美育教材依据实施美育的场域作出的最初分类。说它陌生,是说当今的“社会美育”阵仗之巨已超乎想象,已然成为涵盖社会结构方方面面的美学专用词,令人刮目相看。如今,“社会美育”不仅成为学术会议的热门话题、专业设置的显赫名目、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而且进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不过,虽然如此热闹繁华,但学界至今对于“社会美育”与其首倡者蔡元培先生的渊源关系似仍鲜有论证,故此予以深入的考察和探究成为必要。
一、专设机关:“社会美育”的确立
历来,人们提起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总会想起“以美育代宗教”说,此说已经成为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标识和徽号,但是其美育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美育”。蔡元培首次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一说是1917年4月8日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的同名演说词。从此次演说始,“以美育代宗教”成为蔡元培进行社会改良的利器,也成为融贯其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这次演说中对实施美育的机构设置和环境营造已提出了初步构想:
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以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赏览。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均以容多数人为快。①
在蔡元培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之际,新文化运动已在酝酿,此时他的构想还不乏乐观色彩,但时过境迁,风靡一时的文化运动过去,一切依然故我,世人仍陷于种种流弊而弃美育于不顾。蔡元培痛感当时文化运动虽已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在媒体上种种时髦的口号已屡见不鲜,但回眸看看美育,“除了小学校中机械性的图画、音乐以外,简截可说是没有”②。为此他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③。而他认为,疗救世俗的要义在于美育,特别是将美育普及到社会各方面:
有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有临时的展览会,有音乐会,有国立或公立的剧院,或演歌舞剧,或演科白剧……市中大道……小的市镇……大都会的公园……都是从美术家的意匠构成。所以不论那种人,都时时刻刻有接触美术的机会。④
此时蔡元培对机构设置和环境营造作为美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想法,也未提出明确的概念。对此进行专题讨论且明确提出“社会美育”的概念,则是《美育实施的方法》(1922年)一文,该文发表于以倡导美育为职志的《教育杂志》。在文章开头,蔡元培如是说:“十年来,渐渐的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⑤但很多具体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细化,而美育实施的方法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方面。
在该文中,蔡元培首先按照当时的教育状况将美育分为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三个方面:家庭美育包括胎教和婴儿养育,而幼稚园则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过渡阶段;学校美育包括中小学的普通教育和大学的专门教育;而“社会美育,从专设的机关起”⑥。这是蔡元培所有著述中最早明确使用“社会美育”概念之处。而其列举的“专设机关”包括美术馆、美术展览会、音乐会、剧院、影戏馆、历史博物馆、古物学陈列所、人类学博物馆、博物学陈列所与植物园、动物园;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普遍的设备,就是地方的美化,如道路、建筑、公园、名胜、古迹、公坟等。最后,蔡元培对上述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三个方面一言以蔽之:“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
后来相隔8年,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印《教育大辞书》(1930年)撰写“美育”词条,较前稍有变化,将以往诸种美育的次序改为学校、家庭、社会三大美育,但对“社会美育”的论述更加科学、合理,也更加详备、绵密:
社会之改良,以市乡为立足点。……设植物园,以观赏四时植物之代谢。设动物园,以观赏各地动物特殊之形状与生活。设自然历史标本陈列所,以观赏自然界种种悦目之物品。设美术院,以久经鉴定之美术品,如绘画、造象、及各种美术工艺,刺绣、雕镂之品,陈列于其中……设历史博物院,以使人知一民族之美术,随时代而不同。设民族学博物院,以使人知同时代中,各民族之美术,各有其特色。设美术展览会,或以新出之美术品,供人批评;或以私人之所收藏,暂供众览……设音乐院,定期演奏高尚之音乐,并于公园中为临时之演奏。……设公立剧院及影戏院,专演文学家所著名剧及有关学术、能引起高等情感之影片,以廉价之入场券引人入览。①
该词条卒章见志,强调“美育”一事尤其必须对“社会美育”予以高度重视:“要之美育之道,不达到市乡悉为美化,则虽学校、家庭尽力推行,而其所受环境之恶影响,终为阻力;故不可不以美化市乡为最重要之工作也。”②
此后,“社会美育”概念经蔡元培阐扬“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或文章中多次论证而不断得到加强,譬如他在1930年和1932年分别发表的同名“美育代宗教”的文章中均有充分论述。前者曰:
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所以不用美术而用美育者,一因范围不同,欧洲人所设之美术学校,往往止有建筑,雕刻,图画等科,并音乐、文学,亦未列入;而所谓美育,则自上列五种外,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供利用;都不是美术二字所能包举的。③
后者曰:
至于美育的范围要比美术大得多,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幽静的乡村……此外,如个人的举动……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化。④
总之,蔡元培对“社会美育”的建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首先是随着“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提出而发端,继之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接着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得到明确界定,再因入典《教育大辞书》而走向经典化,又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最终作为一个重要的美育范畴而得以确立,成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在蔡元培那里,“社会美育”对“以美育代宗教”说可谓如影随形,数十年如一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蔡元培自倡言“以美育代宗教”之日始,但凡论及这一命题,总是将终结点、完成态归结和落实到“社会美育”的实施和建构之上。由此可见,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其实是一个双线结构,“以美育代宗教”说与“社会美育”两者的互恰关系一以贯之,并行不悖,构成一主一从两大线索。在这双线结构中,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理想的;前者是批判的,后者是建设的;前者是论理的,后者是实施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第一原理的话,那么“社会美育”则堪当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第二原理。
二、陶铸概念:“社会美育”的正名
蔡元培在发表《美育实施的方法》之前并未使用过“社会美育”一词,而是采用“社会教育”的说法,一字之差,在逻辑上二者构成属种关系,因而“社会美育”的界定较之“社会教育”更加精准和确定。这一点正是蔡元培为“社会美育”正名,以“社会美育”取代“社会教育”的根本原因。
在此之前,蔡元培曾认定,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在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社会教育的机关,包括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院、展览会、音乐会、戏剧、印刷品(即书籍与报纸)等。他特别强调戏剧的功用:“随着社会的变化,时有适应的剧本,来表示一时代的感想。又发表文学家特别的思想,来改良社会,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教育的机关。”⑤
蔡元培还对大学进行社会教育的设置提出以下构想:
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如通信教授、演讲团、体育会、图书馆、博物院、音乐、演剧、影戏……与其他成年教育、盲哑教育等等,都由大学办理。①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以上林林总总原先属于社会教育的“机关”,后来都归入“社会美育”的范畴。就此反观蔡元培以往称为“社会教育”的种种“机关”,不难发现其中无不寄寓着鲜明的审美意味和美育元素,这就为“社会美育”的登场拉开了序幕。譬如较早时蔡元培谋求对社会风气的培植,“则远之政体、教宗之所酝酿,近之家风、乡俗之所援系,几席之近,锱铢之微,视听之娱,牙角之讼,无在非社会教育之所涵濡”②。所谓“涵濡”,即滋润、浸渍之意,这已是后来美育所倡扬的陶养情感、陶冶性灵的先声了。又如蔡元培曾以教育部名义通电,请各省注重社会教育,强调“惟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或兼备有益之活动画、影画,以为辅佐,并由各地热心宣讲员,集会研究宣传办法,以期易收成效”。③这就对宣讲标准、选辑资料采用通俗易懂、寓教于乐、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美育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再如蔡元培1921年7月在美国参观考察期间,在对柏克莱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对中西方注重社会教育、提倡陶养人格的美育传统进行了比较,肯定了两者交流互鉴的必要性。他推崇中国古代孔、墨两大教育家,称其教育含有三种性质,即专门教育、陶养德性、社会教育。孔子主张陶养性情,发达个性,其教人之法为因材施教,与西哲亚里士多德相似。墨子陶养人格之法,主张自己刻苦,博爱众人,并包括社会教育,与英国之牛津和剑桥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其成为缙绅之士殆同。蔡元培主张按照欧美教育新法,同时结合中国古代教授法,参酌兼采,扬长避短,达成三个方面:“(一)应包罗各种有用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学科。(二)陶养道德,一面提倡合群运动,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三)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学美国尽量发展。”④总之,中国学校因历史上的渊源,培养人格应比德、法等国更加看重,且因社会需要,亦不能不并重于社会教育。
正是以上由社会需要、教育状况、美育内涵等因素相互交融交织而成的历史语境,推进了蔡元培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关于“社会美育”概念的铸成,从而为这一美育功能进行了“正名”。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支撑,蔡元培在该文中对“社会美育”这一新概念作了进一步说明:“照现在教育状况,可分为三个范围:一、家庭教育,二、学校教育,三、社会教育。我们所说的美育,当然也有这三方面。”⑤而这三者的分工乃是根据实施美育之对象的实际情况而设置的:“学生不是常在学校的,又有许多已离学校的人,不能不给他们一种美育的机会;所以又要有社会的美育。”⑥总之,这一操作对“社会美育”不无学科定位的意义,使之获得了正式的名分、正宗的地位和充足的底气。
三、陶养感情:“社会美育”的旨趣
如果说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社会美育”对“以美育代宗教”说如影随形、桴鼓相应的话,那么“社会美育”恰恰被赋予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精神旨趣,那就是蔡元培在《教育大辞书》“美育”词条中开宗明义对美育给出的经典性定义:“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⑦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首倡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当时以康有为、陈焕章为首的保守势力仿效西方基督教而企图将传统儒学打造成为一个本土的新宗教,这一倒行逆施给当时的教育界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蔡元培奋起而掊击之,指出当时宗教在欧西各国已经成为过气话题,宗教的许多具体内容也已借助科学研究而逐步得到解决,但令人诧异的是,国人中恰恰有将欧西旧事当作新知者,某些留学外国的学生以及国内持旧思想者,将外国的社会进步归功于宗教,套用洋教,篡改教义,以基督教劝导国人,将孔子奉为中国之基督,为组织孔教而奔走呼号,盅惑民众。正是针对孔教逆流甚嚣尘上的局面,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世纪宣言。在他看来,就美育与宗教的关系而论,二者已形成“分”与“合”两派。就“合”者而言,由于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抱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倾向,故“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就“分”者而言,“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出于拒斥宗教激刺感情之弊而崇尚美育陶养感情之利的鲜明立场,蔡元培断言:“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①按此论即“以美育代宗教”一说的由来。
蔡元培对于后来被界定为“社会美育”的审美价值也作如是观,用他的话来说:“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戴嵩所画之牛,韩干所画之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芦沟桥之石狮,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抟噬之恐者。”②凡此种种“社会美育”的具体例证,都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从而构成强劲的理由充足律,为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张目:“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③总之,无论是厘定美育与宗教之关系,还是衡量“社会美育”的审美功能,蔡元培所持的标准如出一辙,那就是以陶养感情、促进人生的精神旨趣作为分水岭。
此后,蔡元培提交的一份关于“创办国立艺术大学”的提案不啻是实施“社会美育”的样本。该提案的重要理由在于,“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其精神旨趣则在于“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蔡元培据此主张,为达到实施美育的目的,“尤应注意学校的环境,以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上之精神”。蔡元培多次表示,就中国的风物气候而言,在长江流域、江浙一带,最适宜建造推行“社会美育”的大学区:“将来若能将湖滨一带,拨归艺大管辖,加以整理,设立美术馆、音乐院、剧场等,成为艺术之区,影响于社会艺术前途,岂不深且远耶!”④该提案由蔡元培主持,于1927年12月举行的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所议“创办国立艺术大学”的成果即为于次年3月成立的杭州国立艺术院。可以认为,这是蔡元培大力推行的“社会美育”从理论到实践所达成的一次完美创举。
四、急起直追:“社会美育”的进展
蔡元培在1908至1911年、1912至1913年两度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求学,期间选修的课程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史等,他尤其重视康德哲学和美学,崇尚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兼修造型艺术等课,对立普斯(T.Lipps)的“感入主义”尤感兴趣,并在课内课外接受音乐、美术的熏陶,期间已经对美育予以高度关注。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感到一切都历历在目:
来比锡大学礼堂中正面的壁画,为本地美术家克林该所绘。左部,画一裸体而披蓝衫的少女,有各民族雏型的人物环拱着,这是希腊全部文化的象征。中部,画多数学者,而以伯拉图及雅里士多德为中坚,伯氏着玄衣而以一手指天,为富于理想的象征。雅氏着白衣而以一手指地,为创设实证科学的象征。右部,画亚力山大率群臣向左迈进,为希腊人权威的象征。克氏又采选意大利各种有色的文石雕一音乐大家贝多汶坐像,设在美术馆庭中。①
留给蔡元培深刻印象的还有莱比锡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剧院、花园、酒吧、名人故居等所蔚成的艺术氛围和文化环境:
此地美术馆,以图画为主……自文艺复兴以后诸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点代表作品。尤其迩时最著名的印象派作家李勃曼,因曾寓此城,所陈列作品较多。其第三层,将各国美术馆所收藏之名画,购其最精的照片,依时代陈列,阅者的印象虽不及目睹原本的深刻,然慰情聊胜无。
德国最大文学家哥德氏(Goethe)曾在来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来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rbach),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普通演《弗斯脱》剧本的,都只演第一本……第二本节目太繁,布景不易,鲜有照演的。惟来比锡因系哥德就学之所……特排日连演第一、第二之两本。我在来城三年,每年届期必往观。②
不难看出,蔡元培后来在大量演说和文章中对“社会美育”的机构设置和环境营造提出的初步构想与往日留学期间对莱比锡大学的美育设施的沉浸式体验一脉相承,二者贯穿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同时,蔡元培也不乏结合本土传统对“社会美育”所进行的创造和开新。在《教育大辞书》的“美育”词条中,蔡元培列数中国古代在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中所蕴涵的美育成分:
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③
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蔡元培回顾民国以来社会美育的进展,指出历来推崇中国文学艺术源远流长者,均肯定其陶冶性情的作用富于美育的意义,不过范围较小,也未曾作普及的计划。但是,最近25年,国人受欧洲美术教育的影响,开始着手各方面的建设,虽成绩不甚昭著,但“美育”的概念已与智育、德育、体育等为教育家一视同仁,这不能不算是一大特色。其实绩也相当可观,在造型美术、音乐、文学、演剧、影剧等方面的建树颇多精彩之处,在美术学校、博物院、展览会、摄影术、美术品印本、音乐传习所、演奏会、都市公园等方面的设置营构也可圈可点。不过在蔡元培看来,眼下社会美育的设施,虽可谓应有尽有,但“较之欧洲各国,论量论质,都觉我们实在太幼稚了”,从而喊出发自肺腑的吁请:“急起直追,是所望于同志。
五、全民抗战:“社会美育”的升华
蔡元培20世纪30年代美育思想的开拓和创新,是与抗日的烽火共始终的。从“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到“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抗战,战争风云在蔡元培发表的众多演说和檄文中留下了浓重的痕迹,也给其“社会美育”注入了勇猛悲壮的内涵,使之达到了新的升华。
首先,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蔡元培对于美育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国难方殷之际,仁人志士往往会将一己的生死利害置之度外。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自感情的。不过虽然人人都有感情,但并非人人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就需要推动人的感情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这就有待于陶养发挥作用。何以能陶养感情呢?那就必须养成美育的两大特性:一曰普遍,二曰超脱。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方能当此生死关头,保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表现出“杀身以成仁”而不是“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而这种勇毅,“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①。不仅如此,蔡元培接着还肯定了“社会美育”在陶养“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种普通职业,以应利用厚生之需要;而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以谋知识与感情的调和。这样,才算是认识人生的价值了。
其次,蔡元培强调文学艺术乃是“抗战时期必需品”③,充分调动“社会美育”的资源来支持全民抗战。列数蔡元培公开发表的篇章,可以发现他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组织和参与有关文学艺术的展览、结社、演奏、表演等社会活动特别频繁,发表演说也相对集中,包括《中国之书画》《就任国立音乐院音乐艺文社社长演说词》《同乐会〈乐器图说〉序》《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展品在国内展览开幕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赴菲列宾展览美术品题词》《欢迎刘海粟由欧展览回国餐会上演说词》《征集国画沟通中印文化函》《在国立戏剧学院演说要点》《在香港圣约翰礼堂美术展览会演说词》等,这些社会活动并非仅仅是文人墨客的谈画论乐、演艺切磋,而是“社会美育”的充分体现,其中若干名篇的发表,当激发无数民众意志为之坚定、精神为之飞扬,义无反顾地投入全民抗战的洪流。就说美术会展作为“社会美育”之一端,当此家国危亡、生灵涂炭之际,或有人认为并无赏鉴美术之余地,而蔡元培则力推美术在抗战时期的重大意义,因为此时最需要的,是宁静的头脑,是强毅的意志。古人笔下所描摹的“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古人所崇尚的“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仅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能没有,就是在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赈济难民者也不能没有,他还特别强调从事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能没有。总之,有了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各方力量方能在全民抗战中担得起一份任务。蔡元培还认为,为养成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固然有特殊的机关从事训练,而推广美育也是养成这种精神之一法。美感本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从容恬淡,超利害之计较,泯人我之界限,“而这样的超越而普遍的心境涵养惯了,还有什么卑劣的诱惑,可以扰乱他么”?一为崇高之美,它又可分为伟大与坚强两类:遥想恒星世界,比较地质年代,不能不惊小己的微渺,描写火山爆发,记叙洪水横流,不能不叹人力之脆弱;但正如美学之“感入主义”亦即“移情说”所昭示,一经美感的诱导,便不知不觉,神游于对象之中,于是乎对象之伟大就是我的伟大,对象的坚强就是我的坚强,“在这种心境上锻炼惯了,还有什么世间的威武,可以胁迫他么”④?
再次,在蔡元培看来,社会美育的要义在于帮助民众达到自给、自管、自卫之目的。小到一身,大到一国,都有这三种目的,譬如国家,所有关于经济的组织,是自给的;关于政治的机关,是自管的;关于军事的编制,是自卫的。蔡元培在1936年3月考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之时,对社会美育又有了新的感悟。面对该校在自给、自管、自卫三大目的上取得的可观成绩,他盛赞这些成绩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社会美育”,包括以学校形式推行的教育如小学、民众学校、短期义务小学、义教试验班、日间短期义务班、劳工自修学校等;以非学校形式推行的教育如图书室、读书会、巡回文库、民众博物馆、民众阅报社、民众茶园、农友工余社、青年进修会、乡村改进会、改进会联合会等;以美术助成的教育如娱乐室、音乐队、唱歌队、工余剧社等。总之,正因为有这许多社会美育的方法和途径,始能产生上述所举自给、自管、自卫的成绩。①
然而,在烽火连天、民族危亡的战争岁月,还应对上述三大目的之一予以特别的强化,那就是“自卫”的目的。蔡元培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数十年来,中国迫于外患的侵凌,不得不力谋自卫。……最近数年,外患频仍。为维护主权,保全领土,不得不举国上下一致动员,共谋国防的建设,以绵续民族的生命。……自为理所当然。”有基于此,蔡元培认为大有重提1912年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所倡导的军国民主义教育的必要性。②而在“自卫”目的上,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也堪称表率。该校设在无锡,学校每一个无锡人都是江苏人,也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每个人所练就的自给、自管、自卫的能力,不但可以应用于一县,也可以应用于一省,应用于全国。而该校设置的机关,堪当全省的模范,也堪当全国的模范。为此蔡元培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敬祝无锡一隅的成绩,能推行于江苏全省,并能推行于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