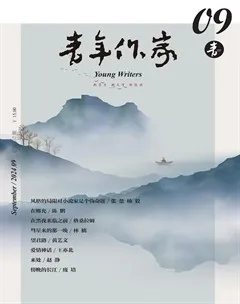山歌
我飞翔,
不安分的狼吞虎咽的灵魂飞翔,
我的行程用铅锤探测不到。
——惠特曼
一
抵达三清山脚下时,已过子夜。黑咕隆咚中,竟下雨了。
住进农家,几十多号人把防潮垫一铺,席地而卧。老旧的房舍,坑洼不平的泥地。睡袋外的耳朵,不时听着雨敲打树叶和屋顶,稀密交织,哗哗的溪流声也从房脚边一波波传来。
早晨醒来,雨还滞留,斜飘在湿薄的空气里。看来只有冒雨登山了。
三清山在眼前,伸手可及,又好像高得够不着。此刻,它只露出一个小角,盘着层层雾霭,朦胧不清。穿上冲锋衣和冲锋裤,三十多斤重的装备也架到了后背,里面装吃的、喝的、穿的、住的,还装着一团热情。驴友们出发了。
迎接我们的是小道。既然是穿越,就要走别人不走的道。残存的石阶、倒下的树木、茂密的杂草都昭示这是一条被遗弃、被封存的道路,通向废弃石阶的是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为了走这道,我们还特意请人打开了那把沉重的铁锁,走后门。铁门洞开,飞雨,落叶,荒草,一条模糊的小路蜿蜒在雨水里,在邀请我们。
雨飘洒,横竖交错,如群蚊般挥舞。冲锋衣红红绿绿,斑斓得像雨中的一只只蝴蝶,几十号人拾级匍匐而上。雨打凉石,水珠弹飞,闪在空中,泛起片片回光。草却异常鲜嫩,在溪边摇曳,昂着头,欢迎着雨水。脚下异常湿滑,尤其是冲锋鞋,不怕踩,不怕水,不怕坑洼,就怕脚底升起来的滑。遇到长青苔的坑石,以及覆水的小木桥,只能蹒跚而行。不时有人摔得屁股朝天。
树,密密麻麻,有些直,有些斜,有些还横向在长。那是一群倒下的树,拦路虎一样横七竖八,根系朝天,网一样裸露着。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几年前的一场龙卷风害的,好些树被连根拔起。因是一条废弃的道,才得以保留了树倒下时的形态,从姿势里还能读出当年的种种悲壮和大自然的无情。我们手脚并用,小狗小猫一样地从树胳膊、树窝里钻进钻出,手上、衣裤上沾满了湿漉漉的污泥。
树被雨雾封存,看上去是糊的,一棵棵似幻影。溪流倒是欢快,声音畅亮,先声夺人,带着凉意的欢腾声在山谷回响,淹没了我们的脚步。雨从天空坠下,在石壁、树顶、树杈飞散开来,变成碎沫子,久久地腾在空中。又一会儿,雨细极了,肉眼分辨不了,但依然在舞,塞满整个空间。那雨丝,就像人的影子,你捉不住它,但它就是存在。你试图躲开,它却越来劲,蜂拥着,往每个角角落落、每条缝隙里钻。不久,眼帘成了水帘,睫毛尖上都在下滴,眼前模糊一片。越擦水珠子越多,管涌一样泛上来。尽管脸上淌水,冰冷了整张脸,但身子里头却异常热乎。汗趁机在衣服里作祟,攻占后背,黏黏的,把整条内衣都吸住。
崎岖的山路并不可怕,怕的是石阶。陡峭的石阶出现时,难度大增。那些近乎垂直的石阶贴在山崖上,最耗费人的体力,对膝盖的压力和人的体力要求也增高。常常走上一段,就会喘大气,心怦怦乱跳。
但此时不能停,因为后面还有队伍跟着。像天梯的台阶通向幽深的高处,朝下看,屁股后面是一个个上扬的头颅,彼此相连又相依。
向上!向前!
二
这些年一直在爬山,对山有感情,向往山,又怕山。我对山的感情是复杂的。
历朝历代的文人都向往山,对山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这是李白笔下的天姥山,飘逸,峻峭又多情。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这又是李白笔下的蜀道。
这些鲜有人迹的山川,某一天突然出现了驴友的身影。他们爬山涉水,挑最难的路走,从刺激甚至恐惧里寻找快乐。我认识几位资深的驴友,一说到山就滔滔不绝,兴奋溢出面容。受他们的怂恿、挑拨和鼓动,我也渐渐爱上了大山,以及山背后的那份神秘与诱惑。
三
我对山的情感最早可溯源到2007年。一个周末,一次冲动。
那天周五,我看报纸——上面登着周末去徽杭古道,我的兴致就被莫名点燃了。报名,租器材,我一下子就融入了这支一个人也不熟悉的队伍里。没有半点准备,全是冲动在背后推动。这是我平生第一回参与户外运动。
第一天是徽杭古道,走了近半天,从浙江境内走到安徽境内。所谓古道,其实只有几小段,也不连缀。小石板铺就的路,渗满青草,也透出年代感的几分古意。几个小时走完古道,飘飘然,一点疲倦的感觉也没有。走完后,还有一个项目,那就是爬清凉峰。我是冲着古道来的,对清凉峰一点不了解。我甚至不知它有多高。
凌晨的月亮半遮着,探在墙角上方的云层里。大伙儿从农家热腾腾的被窝里起来。问去不去?我想了想,说去。一座山,又怎么样呢?不就是爬个山嘛。
在农家喝粥,喝得稀里哗啦。那不是粥,是稀饭,昨天剩下的饭加水煮开而已。喝了,胃热了,精神也提起了。戴上护膝和登山杖,头灯光和电筒光交叉在黑暗里。我们像飞蛾一样趋光,光引导我们,脚步却是在暗处急行军。漆黑裹挟山林,那种黑,像是没了边际,甚至不透风。一条羊肠小道牵引着一支断断续续的队伍。大队人马在走,我也在走。怕什么呢?前面有羊群呢,我只是一只羊。
天在醒来,更像是在替山拭擦,一点点透出光亮来。那片白,起先慢吞吞的,后来突然加速。我的眼不时盯在脚下,看路石、草丛以及那些突然凹下去的坑,一抬头,嘎噔一下,天亮泛了许多。荆棘和茅草时不时会绊住我。我用登山杖作支撑,它成了我的第三条腿,尽可能稳住我,使我在乱石丛中保持平衡。云从孤寂的树枝间冒起,从山的前方探出身来。待走到一个下坡,另一道斑斓的鱼鳞云倒贴在天上,长长的,像教堂穹顶上的彩画。
天空空得异样,云不动,只有这一群人在山脊上不停地晃动。
大地寂静,偶尔会有几声碎鸟声从树丛里溢出。这轻微的声音更衬托出了幽静,我们像走在无声电影里。
太阳近了,就在我眼前这座山的后面。越过山长长的脊梁,就感受到伸过来的阳光,但看不到太阳。山坡似在动,其实那是幻觉,动的是亮色,山的小半截此刻披上了一层新鲜的橘黄。黄色在蔓延,亮光就在坡上一点点翻卷开来,绿压压的树丛被一一上色。温暖的阳光就这样抚慰着清晨的冷山林。
我们在山道和树丛间鱼贯而行,从这座山攀到那座山。
山,曲曲折折,一会儿在羊肠小道,一会儿又进了林地。走在没有路的路上,连手机信号也没有。这中间还走错了路,大伙原地等待,等待向导把我们拉回到正道上。向导是当地人,熟悉地形,他就是正道。走着走着,我突然醒悟,出发前我的观点大错特错,清凉峰不只是光秃秃一座孤峰,它需要经过一座座山绕上去。
绕来又绕去,就这样,我们在不停地盘绕上升。
四
爱默生曾经是这样书写行走的:
“世间的一切都热衷于书写自己的历史……并非是雪中或大地上的脚印,而是印在纸上的文字,如一张行军路线图,多少会更加持久。大地上满是备忘和签名;每一件东西都为印迹所覆盖。大自然里,这种自动记录无尽无休,而叙述的故事就是那印章。”
徒步三清山,我们在半山腰遇上游客,他们是乘索道上来的。这是两支截然不同的队伍,同样是出游,但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一个是轻逸的,日常的;另一个则是沉重的,非日常的。我们这群人就是爱默生所说的试图在这大山里寻找“备忘和签名”。
队伍全副武装,男女混杂,身负重装,被雨水上下夹攻。长长的队列和有力的步伐还是吸引了众多眼球,啧啧称奇的有,感到不可思议的也有。一路上,我们被各种目光包围、吸引,但脚步飞快,阔步向前。
走到这地步,能一览三清山了,但风景在哪里呢?
此时此刻,风景藏起来了,藏在雾霭和雨丝里。水汽夹着雾,盘桓在四周,只能看到山的轮廓,影影绰绰,似有似无。山与我们玩躲猫猫游戏,摆出各种俏皮的形状,似器具,似人,也似动物。山影在变幻,刚看清它的真容以及上面形状各异的树,马上又隐身了。雾大团大团地涌来,越铺越大,直至把旁边的山峰和我们都笼入其中。行前,看过三清山的风光照片,仿佛是梦境,面前一丁点儿影子也找不到。花不见,草不见,挺拔的松不见,漂亮的云也不见。我明白,此刻只有阳光能办到,阳光用力,推开这些雾霭,就能把这些风景重新召唤出来。
傍晚,扎营三清宫门前。雨倒是给面子,竟停了。我们一伙人说笑着开始搭帐篷,架子撑开,篷一点点竖起来,最后形成一个个密闭小空间。
我的帐篷支起了,像顶蓝色的蒙古包。我开始想象这个热闹的夜晚,大地当床,天空为帐。在这道教胜地沉睡一晚,与道教幽远的思想和深邃的历史为伍,我越想越激动。此刻,几十顶帐篷密不透风地扎在三清宫前一块空地上,多姿多彩,如地里长出的一朵朵蘑菇,红的、绿的、橙的、黄的,鲜艳又多姿。搭完后,我寻思去三清宫看看,三清宫是道教胜地,我的瞻仰之心油然而生。
雨突然而至,来得迅猛,密集的雨猛敲地面和帐篷。
我躲在自己的窝里,现在不怕了,有一方栖息地了。喧哗水声绕耳,天在发颤,帐篷外竟有水流了,条条水线在横冲直撞。树影斑驳,天暗地昏,连不远处的三清宫也模糊了。
缩在帐篷里,突然觉得睡袋边有凉意。打亮头灯,光束掠过,看到了一抹水。水在左边一侧,在渗,一点点地膨大。抱着侥幸,我希望雨停,雨却偏偏不停,反而更洪亮、激烈了。雨就在广场中央狂舞。广场上开辟出了更多的水流,击打之下还鼓起一个个水泡,那些泡泡在推挪、漂移,还在闪闪发光。手忙脚乱中,我往右侧看,更多的水在向帐篷发起进攻。水从几个方向冲杀,用一种无形之力翻越过帐篷的底部。整个垫子都浸水了,糟了,糟了,帐篷全沦陷了。
电话通知领队,他跑来,说没辙了,帐篷搭得不好。这是我第一回扎营,没经验,哪想到这样的“好事”轮上了自己。
其他帐篷好好的,安然无恙,只有我的帐篷中招。我一身狼狈。抢救出衣服、背包,胡乱地塞到别人的帐篷里。领队帮我联络当地人员,过半小时来了个中年男子。我灰溜溜跟着他走。看着边上一个个整齐的帐篷,寒风吹上脸来,我又气又不舍。
路上,经过一截木栈道,那不争气的登山鞋成了大滑板。黑暗中,我被腾挪到半空,再重重地砸回地面。我摔了个四脚朝天。伸出手掌,展开来,能感受到昏暗的路灯下满手的污泥水在下滴。
这是个倒霉的夜晚,但也是个奇妙的夜晚。
来到一处建筑工地,进了简易棚,脚手架、水泥和板材堆在墙角。还有一口大锅,露出焦黑的底部。屋顶上,罩了一块红蓝相间的塑料布。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妻,我与他们同住。他们的床与我的床紧挨,我睡这头,他们睡那头。夜风盘旋,塑料布卷起又落下,不停地拍打自己,回声四溢。
那对夫妻躺着,伴着雨声在黑暗里窃窃私语。好奇驱使我,想听清他们的话。但他们说的都是土话,我啥也听不懂。
雨疯疯癫癫,时大时小,反复无常,小的时候静止无声,大的时候又像是在揭屋顶。塑料棚顶经受着风与雨的冲击,哗啦一下,又哗啦一下,好像有整盆的水浇在上面。棚在摇,仿佛随时要塌落。我的同伴怎么样了呢?他们的帐篷会不会被大雨冲走呢?我缩在陌生又温暖的被窝里,担忧这群还在野外的人。
五
有关清凉峰的详情,我是事后翻阅资料得知的。
“清凉峰自然保护区位于安徽东南部绩溪县和歙县交界处,东与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属我国皖南——浙西丘陵、山地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总面积11252公顷,主峰为清凉峰,海拔1787.4米,系浙西第一高峰,清凉峰保护区因此而得名。”
到清凉峰,要经过几块艰难之地。
一叫野猪林。顾名思义,就是野猪的地盘。好在我们人多,不会见了野猪怕,只会野猪见了我们怕。
二是绝望坡。这是驴友的发明,可见这个坡的难度。一个土坡,几乎无草,零乱,松散,坡很陡。陡到什么程度?陡到要手脚并用。人必须像动物一样四肢行动,否则就会失去重心。
三是乱石岗。就是一片乱石堆,经过时不仅要手与脚巧妙配合,而且,爬,钻,跳,挪,各种手段都要用上。
这些都是我没料到的。走到野猪林时,就想撤了,我的脚适应不了这样的行走。但此时回撤有点丢脸,也有点扫兴。内心挣扎,是继续向前,还是勇敢后退,我举棋不定。最后脸面还是胜出,不管了,走下去再说。
走着走着,体力出问题了。身边只有一瓶水。昨天包里有牛肉、面包和红牛饮料,走徽杭古道时,我一口气装进了饥饿的胃里。现在,肚里只有凌晨那一碗稀饭,这碗稀饭的能量在慢慢稀释,转辗中消耗挺大,所剩无几。渐渐地,我的脚不听使唤指挥了,脑空乏,闪金光,该使出的劲使不出来。望着连绵的山体、满是荆棘的山间小道和裸露的岩石,我第一次产生了畏惧。能撑下去吗?我不知道。搁在中途一块大岩石边,我陷入了进退两难。
如一叶孤舟,陷入到了汪洋大海里。
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一阵还靠在一棵树上,停留了许久。山中的树各异,昂首挺立,在一旁瞄着,也仿佛在嘲笑我。其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陌生人,那人像幽灵,背个简单的小包从树林里钻出。我正和两个同伴坐在地上喘粗气,他看到了,靠近,然后蹲下。他说他是安徽人,问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来?说着说着,打开了他的包。一个黑包,斜背在胸口,我的目光越过去沉沉地落进包里。
哇,看到里面的东西了。是巧克力,一包巧克力啊,他竟慢慢地取了出来。
我的目光一直跟着,像遇上了磁场,变得贪婪。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想吃,十分地想。我太饿了,没能量,快搬不动自己了。他或许看出了我的状态,取出几块,举在空中。你们太累了,每人吃一块吧,他说。
我幸福得快要晕了。有生以来第一回,对食物产生了如此的贪念。遇见好心人了!这块巧克力不知是怎么吃下去的,囫囵吞枣,嚼也没嚼就吞了。
吞完,还是盯着他的手,目光黏连,追着他。他依然握着那包巧克力。
能不能……能不能再给一块?突然,我竟这样厚颜无耻起来。
陌生人一愣,有点吃惊,也扫来好奇的一眼。终究,还是给了,他又递上一块。我幸福极了,慌乱道谢,并迅速地下咽。现在,有力气了,我不怕了。
陌生人说,到顶峰还有两个小时呢。我的劲儿鼓了起来,继续朝着顶峰冲刺。
六
终于,登上了清凉峰的主峰。
天是迥异的,颜色像是重新涂刷了一遍。天蔚蓝,又透明又深远。白云列队,静候在远方,目光所及之处雾霭缭绕,仙气飘飘。层层叠叠的山峦,仿佛在捉迷藏,若隐若现。正前方便是黄山,黄山就在最远端的这片云海里藏匿着,又仿佛探出一丁点儿缥缈的身姿。
不到顶峰看不到这无边的云海,也看不到这浩瀚连成片的山峦。登顶让我的胸腔打开,连吸进去的空气也温润、悠长了。
激动过后,袭来的是担心。花了四个半小时登顶,回去还是等程。还能走得动吗?我不知道,也不敢想。不想是不可能的,可想了也是白想。如果说,前面冲顶还有勇气和虚荣心在作支撑,此时这些统统消失了。我已严重体力透支,脚在发飘,人更在飘。此刻,我凝视苍翠的山峦,山冰凉,冷漠,拒我于千里之外。
走,只有走,没有别的出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反应更烈了,脑袋虚无,思想恍惚,浑身像被掏空,连五脏六腑也丢失了。脚仿佛不在脚上,一直在拖,吱吱地摩擦着地面。林木、溪流和云朵正在快速地离我远去,成了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我就像辆快散架的老爷车,汽油到了临界。红灯频闪,身体在发警告。
不时要坐下,甚至躺下身来。
躺在草地上,眼前是片片草茎。一根狗尾巴草弯着腰,那毛茸茸的部位在风里摇摆,扭动着。还有好些我不认识的草在我身下,托举我。我想这样多好,让草护着我,一直托着我。我不想动弹。
登山,食物是最重要的,我恰恰什么食物也没有。还需要经验,我又没有经验,只是凭借一腔热血,胡搅蛮缠。人快要虚脱了,思想呈片断状,身子像麻花一样在扭曲。有一会儿,我甚至闭着眼在走,身体与思想在分离,闭眼的黑暗与事实的黑暗在交汇。我想我可能要倒下了,随时都能倒下。
冥冥中,如有神助,我又遇见了一个给我巧克力那般的人物。在这荒凉、僻静处,竟然冒出个农夫。如幻景般,他头戴草帽,像佛一样坐在树荫下,面前竟有一堆橘子。有六七个之多。那些橘子就像红彤彤的太阳,散发着色彩和光芒。我的目光重新拉直,人在瞬间凝神。救星啊。我跑上前,双手捂住橘子,掏钱,不问价格就全部买下。我要统统吃下,吃个痛快。
同伴的身影也出现了,他们在我身后,同样在艰难行走。我想躲,又没地方躲,他们围了过来,围住了那堆已属于我的橘子。我假惺惺地问别人,内心祈求他们不要,结果是问一个要一个。他们居然全都要。我懊恼地、内心万分不舍地,一一分发。最后,手中只剩一个。
就一个。我为我的假客气后悔不迭。
橘子进嘴,甘露四溢。就这样,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鲜美、最难于忘怀的果子诞生了。
那缕清甜与香喷,一下子滋润了心田。我那枯竭又干旱的胃,顷刻得到了滋润和浇灌。就这么一个橘子,让我的身体激发出生机。有油了,有力了,我的脚步呼呼生风,健步如飞。我被一个橘子的能量震撼到了。
我像从魔术中走出来,全身脱胎换骨。顿觉大片山林在滋生暖意,在招手,在向我敞开怀抱。我飞似地冲下山去。
回撤到蓝天坳营地,遇到了一个资深的驴友。他看到我,露出迷人的一笑,说,好样的,征服清凉峰,成老驴了。事后,我才了解到登清凉峰的难度系数是5级,属中级。我懵懵懂懂,毫无准备,误打误闯,居然爬上了。
这印证了一句古话: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蓝天坳,我连吃四大碗米饭,肚皮变得滚圆滚圆的。回去还要走几小时的徽杭古道,但此时的我已不再畏惧。我知道,我不是战胜了这座山,山是不可能战胜的,我战胜的是我自己。我对自己这身皮囊、脚力以及意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七
“我曾经有过差不多一年生活中没有高山的日子。我被困在剑桥郡的书桌前工作着,丝毫看不到休假的前景。我渴望高山那垂直的高度……一个月末的一天,我失去控制,赶上一趟尤斯顿车站的公共汽车……从火车站,我们搭了便车到凯恩高姆停车场,然后开始朝北方悬崖群黑白色的崖面走去。”麦克法伦在《心事如山》中这样写道。
我也有这样的心绪,亲近山的愿望紧迫又强劲。山就在那里,变幻莫测,似远,似近,奥妙无穷。这些年,陆续跑了浙江、安徽、江西、新疆、青海等地,爬了一座又一座山。有一阵子,突发奇想,居然想去爬雪山了。这个执着的念头令家人恐惧,妻子一次次劝阻。我心里一直惦念着,不能放下,想一睹雪山之巅的壮观与无边。
我会看驴友上传的照片或视频,看他们登上雪宝顶或哈巴峰激动、骄傲的神情与模样。那是享受的一刻,璀璨的一刻。直到有一天,路游的领队毛头说了他们登雪宝顶的事。他说:“我们还算幸运,被雨雪围困几天后顺利登顶,但就在同一天发生了意外。另外一支登山队,遭遇了雪崩,两名队员再也回不来了。”
话语一下子凝固。
行走是有代价的。
从此我那颗放纵、急躁的心稍稍有了收敛,再也没在妻子面前说登雪山的事。
八
但山依然有诱惑。
山有灵魂,有风景,更有人文。在青海久治,我就遇上了这样的景观。
2010年夏,我抵达久治,久治是个小县城,到达那里时正好赶上藏族的煨桑节。清晨,大雨滂沱,洗刷如茵大地。雨稍小,藏民们便穿上节日的盛装,骑马,骑摩托,高举经幡,向绿油油的山顶进发。他们要在山顶举行仪式。从未见过如此的仪式,我心驰神往。
久治海拔四千多米,在这个高度上再去登一座山,难度就不是一点点了。
自然景观可遇,人文景观难求,我的心早已飞了出去。雨一歇,就忽悠几位同伴前往。走着走着,同伴要么坐下不走,要么转身不见了。山顶有几百米之高,途中不时听到山顶上人们的欢呼声,随风飘来,一阵紧似一阵,还隐约看到顶上人的影子。我催着脚步在走,但又不得不停下来喘气,补充一丝新鲜氧气。
此时,山顶有人下撤,仪式似乎就要完成。我急了,竟奔跑起来。高海拔奔跑是十分危险的,会缺氧昏厥。有一阵子,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清凉峰,虚脱,动弹不得。
于是我又想到了放弃。躺在山地上,野草丛里抬起我沉重的头颅,望着那片起伏的呈弧线的山峦,砾石满地,云压头顶,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带着某种新奇。身后有个声音一直在鼓动:上去,再上去。
拖着疲惫的身躯,喘着几倍于平时的粗气,我还是迈开了朝上的脚步。
登顶那一刻,我看到了激荡人心的一幕。一缕青烟,腾空而起。那是桑烟,煨烟节的主角。上百个男人骑在马上,围着幡旗和桑烟在奔腾、盘旋。呼叫声和马蹄声围成一团。周围全是马和人,我湮没在了人马群里。马群沿逆时针方向在快速地转圈。
经幡在风中哗哗作响。一支支扛上来的幡旗,现在已围成硕大的一堆,高高地插在山顶的正中央。人们在祈祷,僧人在颂经。地上一片雪白,像下了一场厚厚的雪。人们正在抛洒龙达,拾起一看,纸上有图案和经文。一声未落另一声又起,此起彼落。
这真是生动的一幕:随着口里的叫喊,龙达被抛到高空,随风飘开,像花瓣一样落下。我在山脚听到的喊声就是抛龙达时发出的。呜——呜——
缕缕阳光从云缝里钻出,光与这土地一样,都是热腾腾的。龙达满地,山顶上像是铺了一层白色的地毯,掩去了原来的青绿。我置身于一片陌生的海洋,声音是陌生的,人群是陌生的,景色也是陌生的。每张脸上都写满了自信和骄傲。他们在喊在叫,声音抛到空中,又回来,再度融入到大自然中。眼皮底下,久治县城错落有致的房舍在远处,声音朝着更宽广的地方传去。
每一座山都有它的文化属性,有人文、故事和历史。我想,探索山特殊的外貌、动植物、地质结构是重要的,但人类思想依附在上面的精神内核,应该更有意义。或许还更迷人,更能激发人类的想象与意志。此刻,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内心澎湃,像眼前的马蹄一样疾速,奔涌不止。尽管只看到煨桑法会的尾声,但这一幕却注定永存。
呜——呜——
我学他们的样,喊出声来。声音不像我自己的,可还是喊了,对着这片辽阔而又深邃的高原……
【作者简介】 但及,浙江桐乡人;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花城》《作家》等刊,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著有长篇小说《款款而来》,小说集《七月的河》《藿香》《雪宝顶》,散文集《那么远,那么近》《心在千山外》等;现居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