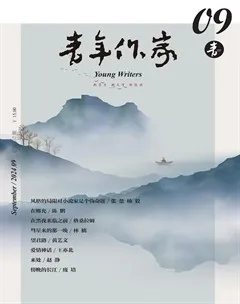荒原·春之祭
2022年3月的最后一天,我忽然想起T.S.艾略特的诗:“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于是我顺手从书架上取下《T.S.艾略特诗和剧本全集》(The Complete Poems & Plays of T.S. Eliot),一张略显苍老、疲倦的脸映入眼帘,下巴肌肉塌陷进去,右手支撑着脑袋——脸上有着大理石般的忧郁。书的扉页上写着购书日期:2017年8月——它在书架上五年了。五年来我想到它的时间不多,只有偶尔为了验证一句诗歌翻译才会打开查阅,书厚达六百页之多,让人望而生畏,每次都匆匆合上,不敢多停留。但是这次我把书搬到了桌上,因为明天就是四月份了,我要开始翻译《荒原》,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
我试着译出第一节《死者的葬仪》。4月3日下午我在温州图书馆做完一期线上直播《春天去看波莱罗》,4日上午去父亲坟头扫墓,在车上我播放马勒《第四交响曲》,真是奇怪,马勒的音乐竟然完美吻合了生活中的场景。最后一段女高音的歌唱“天堂生活”像是为了我今天的出行而写的,油菜花热烈地从窗外扑闪而过,让人忘记刚刚从亲人的墓地上回来。噢,是春天的祭奠吗?一百年前的马勒可没有想到我,而我却在聆听的时候想到了他。艺术与生活是一体。5日我译完《荒原》这首我在大学里开始接触到的长诗。当我译完它后,没觉得它有那么深奥,所谓的“艰深、晦涩、难懂”大多是评论家给的吧。
译完《荒原》,《文学报》上刚好有一则消息《T.S.艾略特<荒原>问世百年》,那么巧,一百年前的1922年艾略特完成《荒原》也是在春天吗?1921年艾略特首次听到了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首舞曲对他影响深远,也包括《荒原》的基调”,到底有多深远?艾略特出生在美国的圣路易斯,它是世界的拉格泰姆之都,艾略特的诗歌有着音乐节拍和声韵的律动,青年时期看过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林德尔·戈登的艾略特传书名是《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渴望成圣,超过成为诗人的艾略特,为什么还不完美?因为他的伟大作品里无不是破碎的人生,他深陷的人间锻炼着诗人艾略特。首先是女人。艾略特的第一任妻子薇薇安有着削瘦的脸庞,眼睛外凸。薇薇安成全了诗人艾略特,毁了男人艾略特。“荒原”与其说是现代文明崩塌的象征和隐喻,不如说是艾略特个人生活的“性荒原”。艾略特和薇薇安相遇时二十七岁,两人都刚从一段失败的恋爱里退出,在一次舞会上女孩薇薇安吸引了艾略特,这次相遇给艾略特的印象之深表现在连舞会时播放的拉格泰姆爵士后来都被写进《荒原》里。他们曾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薇薇安会跳芭蕾、画画、唱歌、写诗,典型的伦敦才女,有着火一样的灿烂,撩拨着矜持的外地青年艾略特。虽然他们各有各的古怪,但对事物都有着犀利如电的洞悉。婚后,两人有过短暂的蜜恋期。但薇薇安患有慢性疾病骨结核,需要靠大把服药维持生命,经常发病,这使得艾略特在婚姻的地狱里煎熬二十年,迫使他皈依英国国教寻求内心的宁静。《荒原》说到底是艾略特悲惨婚姻的一次告白。他用渔王来自比,用《金枝》和圣杯传说给诗歌戴上漂亮的皇冠。所以《荒原》里会有那么多的注解,来自《圣经》、莎士比亚、还有印度的《吠陀经》,让你如坠云里雾里。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荒地里
长出丁香,混杂
回忆和欲望,春雨
催开迟钝的根系。
多么辉煌的开头。四月为什么最残忍?丁香为什么会从荒地里长出?荒地又隐喻着什么?艾略特的这把丁香是他回忆巴黎青年韦尔德尔穿过卢森堡花园向他走来时手里挥动一簇丁香的场景。“将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这句太漂亮了,有法国诗歌中那种浪漫而忧伤的味道。到了第三节诗歌,“丁香”变成了“风信子”:
“一年前你最先给我风信子;
他们叫我风信子女孩。”
——可等我们从风信子花园回来,晚了,
你的双手抱满,你的头发湿了,
这位“风信子女孩”就是艾略特离开美国时的女友艾米莉·黑尔,风信子寓意重生的爱。从1927年到1956年,艾略特的私生活都围绕着黑尔这位艾略特在哈佛结识的波士顿女孩展开。他给她写过一千多封信,在他们三十年的情感中,平均每一到两周都有一次信,这些信到他们两人中后去世那位去世五十年后才会解禁。两人的关系维持了这么长时间,但艾略特在薇薇安死后也不曾娶她。不如说,艾米莉·黑尔是艾略特的贝雅特丽齐,是“一股能够创造新生的爱的力量”。女孩一出场就披上了圣洁的光芒:
哭泣的少女
女孩,我该怎样称呼你……
站在台阶的最高处——
倚靠花园石瓮——
编织,编织你秀发里的阳光——
痛苦又心惊,抱紧鲜花——
将它们掷在地上,转身
你眼里闪现一丝怨愁:
可是编织,编织你秀发里的阳光。
……
一年前我初译这首诗。译至“就这样我愿意让他离开,/ 就这样我愿意让她伫立,哀怨,/ 就这样他愿意远遁”时,连译三个“就这样”,如三重变奏,从“他”变成了“她”,是艾略特与艾米莉的一种分离,是身体与精神的一种分离,是欧洲和美洲大陆的一种分离,但艾略特希望它们走在一起。于是后来,当我们读着《哭泣的姑娘》,想象着她是我们离别的情人,与其相爱,不如完结,不如凝固。
沉默的女士
平静而沮丧
撕裂而完整
记忆的玫瑰
遗忘的玫瑰
耗尽,生机
焦虑而恬静
单一的玫瑰
如今在花园里
所有的爱结束了
……
玫瑰结束了爱情。这首《圣灰星期三》里,艾略特从薇薇安掉头转向艾米莉·黑尔。艾略特是又一个有玫瑰情结的诗人,他不是“有谁梦见过美像梦一样消逝”的叶芝,不是“如你的开放有时让我们如此惊讶”的里尔克,更不是“你是我过往的爱,赞美,冷漠和责备”的哈代,他是T.S.艾略特,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辉,在欧洲和美洲间飞驰演讲,现身体育馆里如同一位超级摇滚歌星引发上万粉丝欢呼,有女人深爱着,且一个比一个爱得深切,晚年又娶了比他小三十多岁的秘书瓦莱丽·弗莱彻为妻,他幸福吗?太晚了,诗人已近暮年。1949年,艾略特为自己的葬礼选择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火焰与玫瑰终成一体。
如果说《荒原》是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那么比它早十年问世的《春之祭》无疑是音乐史上的一次革命。1921年《荒原》还在艾略特心中酝酿的时候,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伦敦科文特花园上演,艾略特赶去看了,这场演出不啻于一颗炸弹在他心中炸响。《春之祭》奇特刺耳的音乐吸引着艾略特,而观众的笑声让他怒不可遏,他甚至拿出雨伞用尖头捅了一下前面的嬉笑的观众。1913年《春之祭》在巴黎首演引起的骚乱在伦敦又重演了一遍,而这次带给诗人艾略特的震撼更加强烈,也定下了他写作《荒原》的总基调。
艾略特、斯特拉文斯基同为哈佛大学诺顿讲座嘉宾,艾略特受聘于1932~1933年,斯特拉文斯基则于1939年受邀,在哈佛开了六场讲座,讲座内容结集为《音乐诗学》,由希腊诗人塞弗里斯作序,这位诗人说:“我懂得为什么斯特拉文斯基在赞赏巴赫音乐的同时,还能留意到那个时代小提琴的松香味,觉察到双簧管的芦苇味。”1956年斯特拉文斯基结识了艾略特,那时他已经非常熟悉艾略特的诗歌,《音乐诗学》也受其影响,1962年斯特拉文斯基为艾略特的组诗《四个四重奏》创作了《赞美诗》。艾略特去世,斯特拉文斯基在对他的纪念里说:“我尊敬艾略特,不仅因为他是诗人和语言魔术师,而且还因为他是语言符号的真正保护者。”
肖斯塔科维奇对斯特拉文斯基有句非常高的评价:“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作曲家中,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我愿意毫无怀疑地称之为伟大。”他们都是俄罗斯的波兰血统,对于斯特拉文斯基这位老友晚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受到当年驱逐他的俄罗斯文化部门欢迎的场景,老肖有段非常有趣的描述:“斯特拉文斯基没有对这些伪君子中的任何一个人伸出手去,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这个伪君子只得去握手杖,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
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里有一章节《向斯特拉文斯基即兴致意》。斯特拉文斯基开创音乐史的第三时,上半时为巴赫所控制,下半时巴赫被遗忘,到第三时才是古典音乐名誉恢复期。斯特拉文斯基领着我们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不和谐音。不和谐音又领着我们来到现代主义的大门口:毕加索、拉威尔、尼金斯基、法雅、马辛、艾略特,他们一个个以全新的姿势挑战传统。斯特拉文斯基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回到巴赫,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对古典美学原则的反思和重新运用。斯特拉文斯基显得更为简洁,明晰,有力,《春之祭》简练了复杂的语言,将和弦与旋律模式简化到最低的程度。这一点上,他和艾略特“去个人化”主张是一致的。
与欧洲千年音乐史相反,芭蕾舞音乐三部曲《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跟现实无关。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来自音乐,从音乐中直接吸取灵感。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功不在于作曲法,不在于配器法,不在于作品的技术手段,而是音乐本身。如他的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中反传统的一笔:木偶人突然有了灵魂,死后以鬼魂的方式盘旋在魔术师的头顶,让人惊悚,由此迈向现代主义。“如果谁倦于此道或干脆在死亡中逃避,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现代主义应整个地置于一个标题之下,这个标题便是——自杀。自杀这种举动带有英雄意志的印记,这种意志面对与之为敌的理智寸步不让”(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而二十世纪的加缪又前进了一步,他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死亡在文学和音乐里延绵不绝,《荒原》里从伦敦桥上鱼贯而入的死人,《春之祭》里献祭的少女,难道我们要唱响的仅仅是死亡留给活人的血腥冷暴力吗?还是我们从死亡本身的梦魇里嗅到残忍的艾草并以此为荣?
《春之祭》,在外语有两种表达方式,英语The Rite of Spring,意为“春天的礼仪”,法语Le Sacre du printemps,意为“春天的献祭”,我偏向法语,能更准确地表达出作曲家的意图。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梦见一位不停跳舞至死的女孩,梦醒后他着手创作《春之祭》,一位少女把自己献给大地换取春天的重生。美是令人惊恐的。何况一位献祭的舞蹈少女。《荒原》是一场性无能、性饥荒,最后雷霆来了,闪电来了,下起暴雨,荒地重新有了生命。《春之祭》里,被选中的少女跳舞至死,成为全曲最震撼的核心部分,斯特拉文斯基以一组打击乐器加法国号的和弦终结少女。《春之祭》在一个独奏巴松管里开启了一个高音区,对于一部伟大作品,开篇很重要,“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让人记住《荒原》,斯特拉文斯基用高音区上的大管引来了春天。
1975年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将《春之祭》搬上舞台,回到原作的献祭仪式,在舞台上皮娜脱去古典芭蕾精致、束腰的舞衣,她用一个形式固定,用一个手势加强,在舞台的分分秒秒里,惊恐万分的年轻女子的脸闪现,女人被男人控制,成为牺牲品。你若看过2011年维姆·温德斯拍的电影《皮娜·鲍什》,你看完前十六分钟,会发现艾略特《哭泣的少女》是其最好的一个注解。
2006年我第一次在上海听现场音乐会,正沉浸于《彼得鲁什卡》梦幻而开阔的旋律时,不和谐音不期而至,一个插入的野蛮节拍将我从优美的旋律大海里钓起,乐队疯狂地开动起来,朝着无限进发。202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梵志澄指挥了《春之祭》,十四年我只听过两次斯特拉文斯基,我的多数时间献给马勒、布鲁克纳、瓦格纳,而那一晚的《春之祭》带给我的震撼不会少于瓦格纳。要知道瓦格纳是斯特拉文斯基批判火力最猛的敌人,他“谴责它的忤逆传统,鄙视它暴发户式的自鸣得意。更是为了揭露其理论的运用对于音乐本身造成的巨大危害。”
1930年斯特拉文斯基写了一首《诗篇交响曲》,为波士顿交响乐团成立五十周年所作,至此,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巅峰之作诞生。斯特拉文斯基从他的“去情感化”转向“情感表达”,这里有几点原因。一是1929年他的伯乐佳吉列夫突然去世,二是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病重,斯特拉文斯基在家里摆满了圣象和烛台。《诗篇交响曲》在这种焦虑下诞生。他说,这不是在交响曲里安了一部诗篇,而是把诗篇交响化了。一位评论家说:“它在我们心中唤起拜占庭一处拱顶内部装饰的镶嵌画……在穹隆高处,耶稣和圣母严峻地俯视下面遭天谴的人类。”从音乐上来看,《诗篇》受到巴赫的启发,重新审视复调音乐,让合唱和器乐处于同一个位置上,谁也不凌驾于谁。
斯特拉文斯基的私生活同样引人注目。巴黎最负盛名的时装设计师加布里埃尔·可可·香奈儿曾出现在斯特拉文斯基1913年《春之祭》巴黎首演上,就坐在包间里,多年之后这首乐曲的作曲家成为她在嘉仕区别墅的住客——他们之间开始了一段焦灼的私情。一位作曲家,他调配的是音符;一位香水师,她调配的是香气。两人相遇了,香水师邀请他和他的一家人到她的别墅里居住。他们在作曲家的工作室里温存,愉快的鸟叫声滑过百叶窗。事后斯特拉文斯基想起贝多芬最后的弦乐四重奏,小提琴同时拨奏出两个音符,一个音追逐着另一个音。一个肉体之爱,来自可可;一个精神之爱,来自凯瑟琳。同一个屋檐下两个女人,斯特拉文斯基曾想摆平她们,但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可、凯瑟琳,Coco and Catherine,两个C背靠背相叠,而他在两个字母C的女人之间徘徊,最后,妻子凯瑟琳的病情使他做出了选择,不得不离开可可。直到他妻子去世,斯特拉文斯基与他相处二十年之久的情人薇拉·苏迪金娜结婚。而可可去世的卧室里摆放着伊戈尔赠送的画像,摆满了白色百合,三个月后斯特拉文斯基去世,葬礼在威尼斯举行,运河里全是黑色的船只。白色和黑色;颜色里的颜色,颜色中的虚无,他俩全占有了。
百年后,一切都归于尘土。斯人已逝,唯有《诗篇交响曲》仍在奏响。我静静聆听《诗篇》的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E小调和弦展开的引子,第二乐章为“双重赋格曲”,第三乐章在赞美上帝的再现中结束。我听的是切利比达克1984年版本,第一乐章3分52秒,第二乐章7分27秒,第三乐章12分10秒,我们必须用这种精确到秒的时间来测量这部《诗篇》的辉煌,从教堂内部来仰望它的神迹……
【作者简介】 郑亚洪,诗人,生于1972年, 浙江乐清人。曾在《人民文学》《天涯》《散文》《江南》《诗歌月报》《星星》等刊发表作品,著有随笔集《天鹅斯万的午后》《音乐为什么》《音乐会见》《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风景》《小村风物史》,译著《你燃烧了我:萨福诗集》等。现居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