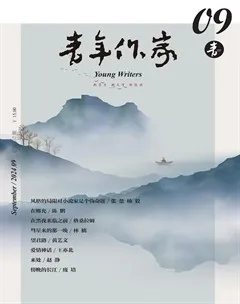爱情神话,或神话的破灭
王亦北的《爱情神话》是一部直面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一位名叫温雅的中年妇女所遭受的种种家庭变故,无爱婚姻又逢丈夫“外遇”,离婚也算水到渠成,可是离婚并没有让自己真正走出婚姻生活的牢笼,而是陷入一种新的困境。除了主人公温雅的失败婚姻,小说还写了她的父辈和子辈几代人的婚恋状况与爱情观,同时还有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这样一个隐形文本。小说名为《爱情神话》,其实是写爱情神话的破灭,更进一步,是探讨在一个情感“真空”的时代语境中,爱情意味着什么。作品表达的是未完成的女性解放命题与女性启蒙诸问题。从爱情出发切入现实关怀,是作家长久以来对人的种种生活和生存困境关注的延续。
未完成的女性主义命题与女性启蒙
《爱情神话》是一部女性题材的小说,小说内容集中在中年女性生活现状描摹上,主要书写家庭生活与情感、婚姻给她带来的各种困扰。有关女性主义的话题一直是文学作品反复书写并讨论的内容,“娜拉走后会怎样”的问题叩问了百余年,丁玲、萧红、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被反复提及。近年来有关女性的话题热度依然不减,“大女主”文化产品流行,“女权”再度成为新一轮的时髦口号。文学作品也继续并反复演绎着女性的命运流转。在这一语境之下再来看这一文本会发现,作品依然是这些书写的延续,同时也预示着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的命题与女性启蒙等等都远远没有完成。
这篇小说的核心事件是一张印有“爱情骗子”的传单,被围观者当成一个真实存在的事件来传播,最后把谣言坐实,就连当事人温雅所在的单位也调换了她的工作岗位。温雅要像男性一样卖力地工作,同时也要面对丈夫、母亲、追求者、子辈、旁观者等诸多人的围堵,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这样的口号在这一刻显得极为苍白。连女性本身都未能结成“同盟”,最为明显的就是自己母亲的不信任与不理解。作家对女性悲惨的命运和困境书写通过一种群体化的描写来呈现。除了温雅,还写到她的一个女友,同样也遭遇婚姻败局,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为了爱情,什么都没有了,温雅也因此为女友抱不平。此外,面对出轨行为,丈夫方强辩解,说他只是玩玩而已,这样的言辞无论是对妻子,还是对出轨对象,都具有很强的戏弄性。小说写了半部女性的悲剧,因为她还有后半生可以选择。但小说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后半生是继续选择委曲求全、遵循世俗的法则,还是重新选择,追逐理想的爱情,答案显而易见。一场大雪突然降临,大雪埋掉了很多的东西,包括温雅全部的来路和归途,预示着最终反抗的失效。
小说还出现了一位男性人物,可以将两者对应起来,他是温雅离婚后试着相处的对象,年龄已经四十大几,却被看作一个“抢手货”,一个优质资源,温雅感觉能得到这样男性的爱简直是一种恩宠。而这个年纪的女性在大众眼中是怎样的一种评价显而易见。小说最后男女主人公大相径庭的心理描写显得十分滑稽,却也是这种观念的表征。女性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中接受了世俗的眼光,接受矮化并矮化自己。不管是在前夫那里,还是在这里,小说都显现出女性的某种依附性,这种依附,是包括很多女性在内的人都认可的,可以说是世俗的通识。温雅自食其力,工作也算得上光鲜,但是“在别人眼中,她也不过是一个靠丈夫养活的女人”,这种陈见根深蒂固,也正是这样的“物质基础”论,使得女性在婚姻中不得不选择向犯了错、违反了婚姻规则的男性低头。
爱情神话的破灭与情感真空时代的来临
小说写爱情神话,其实是在写神话的破灭,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解构爱情。最为明显的是,作者通过人物之口对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这个传颂多年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主人公眼中只是一场阴谋骗局而已。在当前这样的一种环境中,情感真的成为新型奢侈品了吗?小说写温雅从来就不相信爱情,不仅不信,还十分鄙夷。从一开始,温雅就对爱情没有任何信心可言,因此,最后的婚姻悲剧似乎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温雅并非不懂爱情,反而对爱情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堪称爱情专家,但正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却无法去追求,越发显得可悲。
《爱情神话》还有一个隐形的文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作者多次提及这个发生于主人公所在地的古老爱情故事,但是她自始至终都对此没有什么兴趣,甚至还有些反感。有一次在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温雅的内心活动是“爱情是一场阴谋”,这样的描写其实也为她的遭际埋下了伏笔。因为并不是自己一直相信爱情,遭遇背叛感觉失落,反而是她自己本来就不相信爱情,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还要遭受男性的负心,让她更加难以接受。
情感问题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深奥的问题,或许没有谁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有关情感特别是爱情的这些事情都是比较私密性的,可在小说中为何能发展成公众性事件呢?因为情感和女性联系更为密切,女性在感情生活中成为弱势的一方,容易作为被观看的角色,仿佛要接受社会的审判一样。小说中说爱情是不能用现实来衡量的东西,但爱情其实又离不开现实,尤其是爱情最后的归宿是婚姻,婚姻是最为现实的一个物件,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是搭伙过日子,是一地鸡毛、鸡零狗碎。因此,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还有多少闲心真正关注情感本身呢?小说写到温雅对男性变心后便无法再原谅的书写,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情感信仰,可以看做是一种女性的情感洁癖,或者说是独立性追求最为直接的外在体现,但是仔细想一下,这不是最最基本的伦理道义吗?在情感真空的时代来谈爱情,确实是在讲述某种神话,反讽的意味十分浓郁。
情感荒漠化的表现不仅仅是爱情,亲情同样面临严峻的考验。温雅与母亲的关系也是小说的焦点之一。温雅选择成家很大程度的原因是为了摆脱母亲,让自己早点离开父母的家,更进一步,她选择方强也有赎罪的意思,她愿意成全母亲。在小说中,温雅与母亲的关系十分紧张,后面达到反目的程度,有意思的一点是,这场传单风波的始作俑者并没有直接点出来,而是列出了很多嫌疑人,包括自己的母亲,这样的潜台词就有很深的意味。可更有深意的还在后面。小说写到一种无法逃离的命运怪圈。在婚姻遭遇变故时,温雅首先考虑的也是自己的女儿。或许她也将要或者正在扮演母亲之前所扮演的角色,在无意识中成为自己讨厌并要摆脱的人。温雅自始至终都不感激母亲当年为了孩子在婚姻中选择委曲求全,而现在她自己也有意无意中为了照顾女儿安安的情绪选择妥协和忍受。一个被层层社会关系包裹的女性,一个无法遵循自己内心生活的女性,即使她已经完全按照既有的社会法则来要求自己,依然无法摆脱伤害,上辈人的悲惨命运再次轮转到自己身上。
从情感书写出发切入的存在困境思考
王亦北惯于书写人生的种种困顿,从青年困境写到中年困境,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笔法,辅以精密的内心世界描绘,将这种困境写得可感官、可触碰,将人所遭遇到的各种烦恼具象化,并以此为契机,思考更多的现实问题。《爱情神话》没有仅仅局限于单个人的情感遭遇,也写到不同代际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温雅的父母在处理此问题上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即便丈夫遇到新欢,夫妻两人早已没有爱情可言,但是母亲仍然拒绝离婚,而且以性命相威胁。到了女儿这一辈,情况也没有多大改观,当女儿被问及爱情观时,她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狗屁爱情,全都是骗子”,一代又一代人的轮回,命运陷入相似的怪圈。爱情这一个人生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成为一种负担,仿佛不是一般人可以消受得起的。联系到当下的社会现状,年轻的“新新人类”过着他们口中的“低欲望生活”,现实生活的压力逼迫着人们接受情感的荒漠化,爱情,成为一个神话,遥不可及。由此,这种书写就有了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不过,小说整体上还是仅仅局限在生活本身的描写上,对爱情发生与消亡的语境是什么,背后有怎样的东西并没有交代清楚。作家似乎仍是要将这些问题都归结为原生家庭的问题,对爱情的绝望是源于从小耳濡目染没有爱情的父辈所经历的糟糕jrDvrL7Q7X+2uboOwOx9/+MN67SDssrggPvxXje1L5I=的生活,而且因此引发了很深的矛盾,在母亲的眼中,自己牺牲了爱情,只为女儿的成长,而在女儿一边,这些牺牲恰恰成为其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负担,直接影响到成年后的生活。作品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日常生活白描,限于生活流的叙事。比如小说对温雅如何发现丈夫出轨形迹,有着很细致的描写,但是并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的范畴,更没有超出普通人的认知,这样花费笔墨就显得无关痛痒了。还有写温雅为了探究丈夫的出轨对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时,也写得很详尽。这些细节的生活感、现实感十分强烈,可如果没有更为宏观的东西,那这些描写就只是将日常生活搬进了小说而已,文学的异质性和陌生化无从谈起,书写的意义也可能就此落空了。
读完这篇《爱情神话》,很自然地就想起了《伪装成独白的爱情》,这不是说两者有多少关联,而是想指出两者存在的巨大差异,最明显的感受是,小说在爱情之外,还能不能提供一点别的什么。《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是匈牙利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书写爱情的经典文本。小说以四位当事人的独白,回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表达作者对于爱情的理解,也对欧洲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书写,特别追忆了包括作家本人在内的欧洲最后一代贵族的生活样态与文化追求,作者同时在书里留下了自己和时代的影子。而《爱情神话》在破败的爱情书写之外还有什么呢,或许作家本人也未能想清楚这一问题。本不应该如此苛责一位青年作家的一个中篇小说,可是,“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写作者应该朝着最高的目标奋进,每一次的写作方可实现哪怕一微米的进步。
【作者简介】刘小波,青年批评家、博士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批评若干。曾获“马识途文学奖”、第十届巴蜀文艺奖特别荣誉奖等荣誉;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