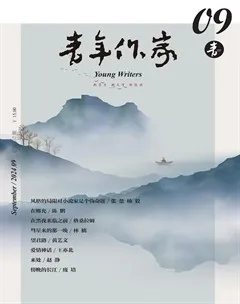爱上一个没有影子的女人
我总是起一个怪异得自己都无法记清的网名,混在一堆怪异的网名中,掩埋自己。因为我认为,起个网名,无所顾忌地干一些事情,可以认为不是自己干的。
“水清清”,这个复古的名字,在一堆怪异的网名中显得很安静。遇到这个名字,仿佛遇到了知已。我和她聊起来,当然,“她”也是水清清自己说出来的。
聊了几句后,她说“水清清”是真名,我问是谁的真名,她说是自己的。
我当然不相信谁会用真名上网,就说:呵呵。
她说:“呵呵”这两个字的主人,一定是个无聊的人。
我说:我们天造地设,我的真名叫余不游。
她说:呵呵。
我说:真的,是真名。
她说:这样挺好,网络只是为了联系方便,不是为了躲藏方便。
我说:难道我们这样就约吗?也才只聊了几句而已。
她说:难道你聊天就真的只是为了聊天吗?
我本想说自己聊天,就真的只是为了聊天,这句经常飘在网上的谎言,被她的犀利撕得粉碎,以至于这次无法说出口。
她选在深夜与我相见,万籁俱寂。在她家小区不远的小路旁,路灯昏黄,将我的影子拖在了面前。她就静静地立着,长发,白衣,一身香气。
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没有影子,不说话,也不看我。
“你没有影子?”
“我为什么要有影子呢?”
她笑着走近我,伸出手,我没有闪躲。我们拥抱了。她暖软的身体有着和我一样的温度。不管是在现实还是在网络中,不管是有影子,还是没影子,我苦苦地找寻,不就是为了寻找和自己一样的温度?
“我们去开房吧。”我轻声说。
水清清摇摇头,笑了,看着我被路灯夸大的影子,说:“你还不如藏在影子里,比藏到哪里都安全。”
她说着,手在我的手上动了起来。
我的手忍不住应和起来,触手处,软润如玉。
我低下头,地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在不断地舒展摆动如同舞蹈。我忽觉羞耻,就这样凭着一个聊天软件,三言两语地约到了一个陌生人,然后相互转身离去,永远不再见?
人自诩为高级动物,却在用智慧的结晶,做回原始的自己。
几片树叶幽灵般撩过我裸露的皮肤,快速滑动到地面。远处的灯火如朝霞般灿烂,却照不透角落的黑暗。
“以后还见吗?”
我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对着她的后背问了一句。声音有点大,在颤抖的夜色里刺耳蜂鸣。太小了我怕她装作听不见。没有影子,她的步伐更加清楚,高跟鞋悄无声息,落地自然。她的身体正自飘动,听见我的话,便如飞机迫降,猛然停下的动作,几乎摇动了我的影子。
她什么也没有说,朝我甜甜一笑,就又开始飘动,走出暗影的身姿,如行云。
我的影子在路灯下忽然变成了两个、三个、四个,有淡淡的虚影,有沉重的压抑,都朝着一个空虚扑了去。
“我爱上你了。”
“不会的。不会有人爱上我,我也不会爱上别人。你们不管到哪里,至少有影子相伴。而我,生下来就没有影子,我注定了只是我自己。”
她说完就走了。如夜风般,只给我留下了肌肤的感觉,面前空空如也。我和自己的影子一起返回,身体轻松,心却疑惑。城市的暗影很短,没走多远就是灯火通明,竟还遇着一两个熟人,打了几声招呼,意兴阑珊返回住处,看到室内熟悉的一切,觉得刚才恍惚如梦一般。我甩掉了衣服,重重地砸在床上。柔软的被褥潮水一般向我涌来,我带着畅游后的轻松和疲惫,沉沉睡去。
阳光是霓虹的噩梦,它敲开窗户的时候,城市费尽心思的霓虹全都散去。
我从聊天软件里删除了她的痕迹。不会有人知道昨夜的一切。我仍然对别人说着我的择偶标准——温柔专一的女孩子。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她的样子。甚至,隔了几天,我便认为,那只是个梦。也许再过几天,便连梦也淡忘了。
也许真的是个梦。每日里阳光铺满一地,影子附随着我,影子和阳光,都如同在梦境里游动的云,伸手可及,却又抓握不住,我又不能说它们不存在,它们明明很重要地存在着,偏就抓不住。我的另一半,她在这个世上应该是存在的,要f2QHfqY5wiwJTCf1yRBa8Q==不怎么叫另一半呢?没有她,我就不是完整的。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明明是属于我的,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我在那场梦后不久的初冬里,进了婚姻介绍所,然后心中空空地走了出来。
没有我要找的人,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谁。我只是在寻找自己的婚姻,婚姻并不能改变什么现状,所有婚姻能带来的,婚姻外都可以有。可我还是愿意将婚姻作为寻找的归宿。
我跟那个没有影子的女人,区别就在这里。我将身体的映射看成了另一个自己,两个自己互相为对方活着,不可分割。结果其中的一个却总被另一个拖累着。
一年后的冬天,空气有些苍白,我拖着疲惫无血色的影子,在公园里观看树叶。有些无情的树木,一年四季都这么绿着,每次来都是一个样子,却还自以为是地摆出一副伟大的姿态。
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我的身后,不足一米的时候才跟我打招呼。
她是老妈托人给我介绍的女朋友。我本来是不想见的,老妈发来信息说她名字里有个水字,至少名字跟我很合得来。这个名字让我顿时有了热血燃烧一样的冲动,冲动很短,只一瞬我就平复了心情。我跟老妈说还是不要见了,名字带水的女孩子,若是真的像水一样无形不易把握,怎么走进婚姻,和美过日子呢?
这仿佛又是我的真心话,不是搪塞逼婚的理由。老妈对我的成熟表示赞叹,然后对她夸赞一番,说她体健貌端品行良善,有过短暂婚史,更是知冷知暖。
她出现的时候,印证了老妈的正确。红衣,白肤,大眼,比阳光温暖的笑容。她朝我微点头,轻启唇,宛转如百灵般歌了一声:“你好,我是李水游,你是在等我吗?”
阳光泼了她一身,红衣上便有了些落叶般的颜色。几片落叶在地上翻动,淡淡的影子如同蝶飞,它们仰看了她一下,像打量一个熟人,她的身子简单地立在那里,身子的前后左右都是落叶的目光。她没有影子。
她向我走近的时候,我悠长的影子,覆盖了那些目光。地面上一片安静。静得只有她的脚步声。脚步声突然停了下来,她的笑容瞬间凋谢。
“我见过一个天生没有影子的人。”我突然就这么说了一句。
“大家都忙着挣钱,忙得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够,还有时间去在意谁有影子没影子?”她一直低头看着地面,看着我的影子。
“我看地面,也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但是我不会在意影子。真正在意影子的,恰是没有影子的人。”
她就笑了,说我挺能用强势的语言掩盖真实的内心。美丽的声音从她火一样的身体里飘出来:“我从没有觉得影子有什么,它在与不在,都不会影响到什么,可是,就因为这个没有用的影子,我变得与你们不一样。”
“有影子的人都在保持自己的完整。”
“你母亲告诉我,你的脸上有一小片胎记,后来用激光烧掉了,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改变呢?也是为了完整?”
我心中一阵恐慌,被人忆起长着胎记的脸,实在是不雅。老妈啊,这事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呢,这不把我自以为美好的形象给打碎了吗?
“那是因为我在乎别人的感受,我不想别人看我一眼,就先看到那个胎记,就像割双眼皮隆鼻梁削下巴一样,用自己的痛苦,换来别人眼中的美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虽然是假的,但是真实的,是无法接受的。只能用假的示众了。”
“我不排斥别人整容,就像你说的,是为了身体上的完美。完美只是心灵上的自由。世上又哪有什么完美?可以认为有影子是完美,也可以认为没有影子是完美。别人的眼怎么看,别人的心怎么想,别人的嘴怎么说,甚至别人的鼻子怎么闻,你们为什么要在意?可你们偏就在意了。我没有影子,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给别人留不下影子,别人也给我留不下影子,我就是我,自由自在,无牵无绊。”
她说着,脸上没有了表情。我怕她会就这样离去,大胆地靠近,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初冬的温度就该这样。我用两只手拉住了她的一只手,她还是挣脱了。
公园里荒草丛生,飞过来几只背着黄黑斑点的蝶,在落叶上一高一低寻找着花香。后来想想,真如梦境一般,要不然初冬的寒意,单薄的蝴蝶怎能承受?可是,蝴蝶真实地存在着,我还记得我的目光随着它们飞舞了好久,而我却不记得她当时的目光在哪里。是啊,她是一个没有影子的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当天的她了。
也许再过几天,就会当这是场梦吧。难道每一个心动的时刻,都只在梦中?这怎么不叫一个向往幸福生活的人,心生恐惧。
我去找我妈,问她那个叫李水游的女孩子住在哪里。
她想了想说:“这个真不太清楚,是跳广场舞的时候别人给介绍的。你中意这个了?”
我说:“是。”
虽然这个字说出口,感觉用了很大力气,但是我还是承认了。其实在我的心中,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她,但是感觉告诉我,我想见她。而且更重要的是,老妈很真实地存在着,她说有她,那就是真有她了,不是梦。
每个人都会做梦,有醒了就忘了的梦,也有忘了就醒的梦。
老妈寻了几天,才找到介绍的中间人。可是那个人已不记得她了,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在别人那里,留不下印象。老妈说,跟做梦一样,好像是有这回事,好像也没有这回事。过了一段时间,她竟然告诉我,就是一场梦,要不怎么会来无影去无影呢?
我说:“她就是一个没有影子的人。”老妈说:“那就是梦了,我肯定不会给你介绍一个没有影子的姑娘,梦由心生,你是不是想找一个没有影子的媳妇,才做出这样荒唐的梦。”
我便也相信了,这就是个心里想出来的梦。要不,她怎么会知道我脸上长过胎记?要知道,世上最能守住儿子秘密的人,就是母亲,她说过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就真的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我又明明记得那么清楚,她也许会说,“记得清楚的,就不是梦吗?”是啊,有时候,做过的梦比发生过的许多事情都记得清楚。那也是,做过的梦,不也就是发生过的事情吗?虽然那些事情只是在她脑海里经过,可脑海ubc0o3VYoEjjvbiSYIh0OBPa7/Y2kO5uy1PwH469nWo=也是她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脑海经过的,跟她的手和脚以及身体其他器官经过的,有区别吗?
梦醒了,本来一切就该结束了。可我沉浸在梦境中不能自拔,总努力地想着一个想不起来的影子。我看着自己在家里在公司在路上在不同的地方,在太阳下、在月亮下、在灯光下、在不同光波中不断变幻着的影子,拉长的、缩小的、浓重的、浅淡的,它们分化出了不同的我,我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一个,只能任由它们随心所欲地出现和消失。原来,我的影子,指挥着我。而我,竟一直以为,它只是我的影子。
人生来总在做很多无用的事,有很多时候,活着就是在做无用的事。我们在为无用的事而努力地活着。比如身体的有些器官,明明努力存在着,却毫无用处。比如影子。
我想割掉它。大概因为它太无用,没有人专门研究如何割掉它。它的价值还不如阑尾和扁桃体。我找了很多家医院,竟然发现只有本地一家医院,专设了一个科室,影子科。医院对它也没有广告更没有明星代言,可见并没有打算靠它赢利。或者,它的存在,也是多余。
我在那家医院里找了很久,才在顶楼找到了影子科。医院的走廊有着天生的肃穆,走在上面总有种冰冷渗进心里。两旁有些绿色的盆景闪烁,面前空无一人。我发现,在这里,影子竟然奇怪地没了。可我的身体依然没有轻松。
她穿着白大褂,面色严肃,就坐在走廊尽头的屋子里。看见她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又开始做梦了。
“因为走廊里用的是无影灯,能暂时让你看不见影子。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所以,你仍然觉得疲累。”她说着,目光掠过我,像掠过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可我分明感觉得出她目光的停留,那样温润,如那夜树下,如那天公园,那几个梦境突然真实地出现了。
她的胸牌上印着她的名字——李水游。
“我可以叫你水清清吗?”
“不能,你是来看病的,你只能叫我李医生。”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容远比胸牌上的笑容灿烂。对一个病人来说,这种笑容加剧了我倾吐的欲望,我对她说出这些天的茶饭不思彻夜难眠。她同情地告诉我,这种情况是影子与身体的不一致,影子认为自己在配合身体,影子不知道身体做出的动作,只是身体的谎言。影子被骗多了,出现了习惯性怀疑,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影子会与身体裂变,到时候恐怕就得送精神病院了。
这让我很恐慌,我可不想住进那里。她看着我惊恐的表情,又继续笑了。她说:“没关系的,不用怕,发现得早,只要把影子切了,就影响不到身体。”
“除了手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我不甘心地问。
“是的,除了切影,没有更好的根除办法。药物只能暂时抑制病情,但是你病因已经种下,不定哪天就会迅速扩散,影子和身体严重交恶的时候,不是现在的医学技术能够解决的。只有在早期,实行切影术,就一了百了。很多人都舍不得,是啊,生下来就有的东西,跟了这么多年,忽然要切去了,当然舍不得。可是与美好的生活比起来,影子又算得了什么呢?该舍弃就舍弃吧。生下来没有影子的人都还是健康的,正常人切掉影子又有什么呢?当年,我和你一样。这个医院的第一例病人,就是我。”
“那你为什么说自己的影子是生下来就没有的呢?”
“生下来就没有,那就是没有了,谁也无可奈何。如果说后天人为切掉的,怕别人认为我不正常。”
“那你也认为,没有影子是不正常的吗?”
“如果多数认为正常是正常,那么有影子是正常。如果少数人认为正常是正常,那么没有影子才是正常。可我们为什么要管认为正常的是多数还是少数呢?”
“是啊。我想只有我们自己。”我伸出了手,她也握了我的手。我的手很安静,她的手却在抖动。
诊室内静静的。没有别的病人和别的医生,只有我和她。室内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没有一点杂音。安静得如同梦境。
“如果怕自己将来会后悔,也可选择切影后冷冻影子,三年内都可以随时再植回去,价钱也不算太贵,只是当时切除出来的病毒,植回的时候,也会被重新植回去。”
“如果你能给自己装一个影子,我就再植一个影子。”
我开始露出健康人的笑容,跟她谈手术的事情,并且愉快地签了手术协议。同意了手术中可能会出现痛死,手术后可能会出现失忆,影子若切不净还可能会出现半影人的后果。
“当然,这种几率几乎没有,但是,手术之前我必须跟你说明白的。”
“但愿是没有,要真有我可完了。”我跟她笑着,心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想,也什么都不愿想了。进去的时候,一道阳光从楼顶玻璃照了进来,将我的影子投在手术室的门上,我无比留恋地看了它一眼,走到手术台,浑身麻木地站在那里。不需要麻醉,我感觉身体已经没有知觉。一道亮光将我与我的影子照得清清楚楚。她坐在电脑前,指挥着一道绿光,一点点地向我和影子之间的缝隙靠拢。
感觉像是一个游戏。我并没有觉得恐惧。好像我只是游戏的旁观者。直到影子在地上变成一片蜡黄,然后慢慢缩成一小片透明的薄翼,我才知道,我已经没有了影子,它已经与我分离。此后的日子里,它将被冷冻起来,等着我需要的时候再将它植回。若不再过问它,三年后,它将成为医疗垃圾,丢在某处,灰飞烟灭。而在前一刻,它还过问着我的身体,影响着我的情绪,甚至左右着我的健康。现在,它只是个单独体了,与我无关了。
我这样想着,想让自己心情沉重,因为毕竟我失去了影子,而曾经我是那么不愿意失去它。也许是因为猛然失去了背负的东西,身体无比轻松,我再怎么想让心情沉重,却都还是轻松。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我决定和她相爱了,而她也没有离开我的意思。我们离开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我们一起游走了很多地方,海滩、公园、大路、闹市人群……蓝天白云青草绿水,花花绿绿的各色人等,都不过是点缀目光的影子,都不过是容纳我们身体的器物。唯有身体各个器官的快乐和满足,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而存在,不就是为了有意义吗?
雪花飘来的时候,人们裹上了厚厚的衣服,躲在结着冰凌的窗后。我和她在雪地里奔跑撒欢,汗水蒸腾,白气围绕着我们,白雪掩埋着我们。
“我们快乐了,别人快乐吗?别人会因为我们快乐而快乐吗?”她忽然停下来,问了这么一句。
是呀,我们应当生而快乐。可是别人也应当生而快乐。
雪地上白光耀眼,这些白光,应该是雪的影子。要是没有这些影子,黯淡的雪,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有的时候,人真的会灵光顿悟。我这个时候,也忽然想到,我们丢掉了影子,可无法释怀别人都有影子。
我对她说:“要不,我们领证结婚吧。”
“我们连影子都没有了,领了结婚证又怎么样,一旦离开几天,都会忘了对方的样子。”
雪上北风行走,一抹轻微的白雾,迷了天空的眼睛。
“你这是抱怨吗?抱怨自己没有影子。”
“不是抱怨,我是在考虑,我们能不能真正地自由?自由是什么?仅仅是去掉了身体的束缚吗?可是血液里还埋伏着许多束缚,亲情、道德、社会……所谓的爱情,是自由还是束缚?”
我看着她,我真正仔细地看了看她。风摆着她的发,飘逸如飞,眼睛中布满空茫的雾水,雾水里倒映着精致的世界。阳光透过层层的阻挡,逶迤不安来到面前,投下片片闪烁的影子。楼房的影子空洞黑暗,柳树的影子歪歪扭扭。我们所站立的地方,便只有这些了。
是的,我们只有我们,没有影子。没有影子的我们,悄然站在雪地上,雪上行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拖着自己的影子。雪消融处,留下水痕片片,却已是固体与液体的区别了,它们继续在茫无涯际的空间里轮回,如同我们来到人世后,发现的,从没停止过的脚步走动。我不知道我静静地观察影子的身体,在她的眼睛里,是不是也在运动。静和动是相对的,此时的她不停左顾右盼,若她为自己静静地思考问题,那我就只能是运动的了。
我离开了她。一个人在大街上行走。路灯昏黄,雪光闪烁。两旁的垂柳竟然青翠欲滴,在白雪上影子婆娑。我忽然想在这夜里,背负一个温暖的影子,唱一首身体摆动的歌。我的影子里住着另一个自己,它承担着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回了家。妈妈开了门,看见是我,先是叹了口气,然后又叹了口气,说:“喝口水吧。”
她没有问我们这段时间的生活,更没有看我的身体。她就那么默默地坐在那,目光空洞,眼睛红肿。我们这段时间的作为,如果在有影子的时候,一定会被非议被指责被嘲笑被谩骂,所幸的是我们留不下影子,便没有这些声音。
不幸的是,我从母亲这里离开后,她一样也想不起我来过。也许她会对着空茶杯想起我在这里喝过一杯茶,可她一样记不起我,我没有影子,我在哪里都是我自己。是的,她会觉得像梦一样,弄不清我是不是真的回来过。我的回与不回,于她来说,便只有思念和悲伤了。
她的思念,还是有影子的我。她的悲伤,是因为看不见我的影子。
这让我害怕,便努力想她。是啊,才分开这么片刻,我便记不起她来。记不起她,那过往的快乐,便如抓不住的梦一样。
李水游看见我回来,便如孩子般无瑕地笑了,说出了孩子一样的话:“我在想,究竟冻在医院冷藏室里的,是你的影子,还是你自己?”
这话让我感到脊背发凉。是啊,自从割影以后,觉得活得没有束缚了,在别人眼前晃来晃去的,别人都无动于衷,可不就是空气一样的影子吗?难不成我已经被冷冻在医院里了,这会儿飘来飘去的只是影子?那么真正的我,再等一段时间,就会被医院当医疗垃圾一样扔掉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
“应该不是,我还有恐惧,影子怎么会有恐惧呢?”我说。
她的脸上不再有笑容,拉着我慢慢地走到镜子前。我步履沉重地走过去。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一直不敢走过去。她拉着我,就像我拖着自己的影子,我们看着镜中的屋子,空荡荡的屋子,没有我们,只有屋子。
“我感觉,有影子的生活,其实也很好。”我小心地说。
我能觉出她手心沁出了冰凉的汗。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眼睛眨也不敢眨,像看着自己的影子。我们开始跳舞,从屋子里到屋子外,我们都这样看着对方,像看着自己的影子。
我轻轻地笑了,附在她的耳边说:“我早几天给医院打过电话,已经授权把我的影子处理掉了。”她说:“为什么?”我拿出手机,翻给她看一个我收藏的页面。
“我能找到你,其实是看了这个新闻,我读给你听,本院李水游医生因为生下来就没有影子,身残志坚,努力学习,终于在影子治疗学上开辟了新路。”
“好久的事情了,我都忘记了。”她低着头,努力去想。
“所以,我是你重新装上的影子。”我抱紧了她。那刻阳光正盛,在匆匆忙忙的万物里,从头顶上将我们合成了一个没有影子的人。
【作者简介】王清海,生于1982年6月,河南南阳人;小说发表于《青年文学》《小说月报》《作品》等刊,有小说被《小说选刊》等转载,著有小说集《他们的母亲》;现居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