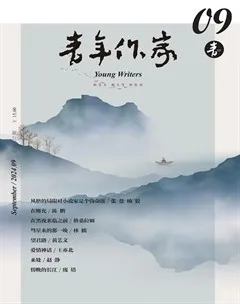槐花开
一
193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天上飘着细雨,上海徐汇区静谧的汾阳路上,一家名为“仁心堂”的诊所前,夜晚的叩门声因过于急促,显得特别刺耳。
当护士小芳打开门时,两个黑卷发、鹰钩鼻、黑眼珠的犹太人夫妇,抱着裹在襁褓里的孩子出现在门口。不待小芳询问,男的用结结巴巴的中文,说了事情的原委,大致的意思是:他们来自上海虹口的犹太难民区,孩子生下来才七个月,腿突然伸不直了,两周里看了好几家医院,说是得了小儿麻痹症,一直不见好转。他们四处打听,得知仁心堂儿科很有名,就找过来了。短短的几句话,这个犹太人说了二十几分钟,才断断续续说完。
看着夫妇两人头发上细碎的雨珠,再看看他们怀里的孩子,小芳没说一句话,无声地让开,用手势请他们进门。
这时,已经有护士通报给院长孙礼。等小芳把他们引进儿科门诊时,孙礼早已坐在桌子后面等待。
孙礼仔细地看了看孩子的腿,用手摸了摸按了按,就给开药了。孩子在仁心堂挂了一周盐水后,腿便伸弯自如。
孙礼说:“孩子得的是炎症,再照小儿麻痹症看下去,孩子的腿就真废了。”
犹太人夫妇当场热泪盈眶,男的脱下帽子,右手握住帽檐中央,上身前倾约15度,两眼注视着孙礼,深深地鞠了一躬。孙礼知道他给自己行的是犹太人最高的礼节,忙站起来还礼。一旁的女人,泪水已经把孩子的襁褓打湿了一大片。
1934年6月,20岁的孙礼从国民党一所军医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南京部队所属的医院,担任院长助理。三年后,193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上士军衔的他因看不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偷偷离开国民党部队,来到上海,凭着高超和精湛的医术,开了一家名为“仁心堂” 的诊所。
诊所设在一座别墅花园里。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别墅的外墙有着独特的古典风格,气质高雅,线条流畅,在形态上给人以轻盈感。别墅内不仅有花园,还有庭院和花房等。
诊所里有十几个护士、五六个医生,西医、中医、骨科、手术室等一应俱全。孙礼在医科大学学的西医,专攻儿科。又因其祖父是有名的中医,他少年时跟随祖父学习,深得祖父的真传,故而他中西医都通。
1937年11月10日,上海的天空被黑色的云层遮住了,太阳一直透不出来。沪松会战中的一位营长,率领他的一个营在抵抗日军第八次进攻时,身中三枪,生命危在旦夕。随军的军医听说他当年所在医院的院长助理孙礼在上海开诊所,他打听到仁心堂的地址,于是连夜把营长送了过来。
几年后,孙礼和他当年的部下见面,两人没有一句寒暄,只是对看了一眼,握了握手,孙礼便吩咐立即上手术台。
手术做了整整五个小时,其中一颗子弹距离心脏部位只有三毫米,单是取这颗子弹,就花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时值深冬,手术完毕孙礼全身上下竟没有一处是干的,全部被汗水浸透,这位营长总算救活过来了。
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很多八路军伤员被抬到了仁心堂,那些日子仁心堂昼夜灯火通明。
仁心堂门口常常有很多穷苦百姓排队等着就医,这些穷苦人家里没钱,有的会挑一两石粮食过来,孙礼可怜他们,不收他们的粮食,又让他们挑了回去。
孙礼的夫人是大家闺秀,姓刘名正兰。他的两个儿子,一个生于1946年5月,一个生于1951年4月,孙礼分别给他们取名孙林和孙庭。
夜晚,没有病人求医时,孙礼会在朝南的书房里,手捧医书静静地坐在藤椅中。这个时候,月光正好透过窗户,照在他白净的脸上。在他面前的书桌上,放有一只木雕的盒子。他平时很少打开这个盒子,也不让家人打开。偶尔诊所开完会,孙礼会端来这只盒子,当着所有医生护士的面打开盒子,盒子里卧着几十颗从战士身上取出的弹头。
每到黄昏,身着旗袍的正兰,会轻轻推开花园的门,怀里抱着孙庭,手里牵着孙林,来到花园的草地上,让他们兄弟俩呼吸新鲜空气。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孙礼在上海开诊所已快二十个年头。
到了五十年代初,上海的繁华更具韵味,所有的建筑和路,如同一幅幅黑白影像,这种黑白影像不带一丝粉饰,如同素描,每一笔的勾勒,都极尽其想象和创造。
这是1952年5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清晨,孙林刚起床,就听到有小贩在窗外唱道:
梨膏糖、小热昏
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
香炒糯米热白果,嫩滑爽口豆腐花
一声声清脆而丝滑的叫卖声,送至他的耳旁。孙林便拽着母亲的衣角说:“妈妈,妈妈,要吃梨膏糖。”
正兰便叫来保姆,让她去买几块来给孙林和孙庭吃。孙庭刚满一周岁,也口齿不清地吐出“吃”“吃”。
刚好是周末,吃过早饭,一放下碗筷,孙礼就对正兰说:“今天带孩子出去玩玩吧!”
正兰有些诧异:“你今天不坐诊?”
孙礼没回答,交代好诊所的事务,抱起孙庭,牵着孙林,先出门了。正兰拿了个小包,赶忙跟着出来。
他们乘上有轨电车,第一站先到了大世界。大世界建于1917年,创始人是昔日上海滩风云人物黄楚九。大世界里应有尽有,孩子在这里玩一趟能高兴好几天。平时孙礼诊所病人多,极少有机会带孩子来。
第二站到的是绍兴路儿童公园。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环境优美的地方。
孙林在公园的草地上追蝴蝶,刚学会走路的孙庭在后边摇摇摆摆地跟着,兄弟俩一脸欢笑。
孙礼有点不合时宜地对正兰说:“是该离开上海的时候了!”
正兰说:“能不走吗?我们没有资产也没有土地,更没有剥削过任何人。何况我们还救过那么多八路军伤员,救治过很多身无分文的老百姓。”
孙礼说:“再不走,可能会连累诊所里的医生护士。我参加过国民党,光这一条也够治我的罪了。”
正兰说:“你当国民党,是拿的手术刀,不是拿的枪,更何况你从没有拿过枪,更没有杀过一个人。”
深深叹口了气后,孙礼不再说话。
正兰也没再发声,只是低头默默地抹起泪来。
这个时候的风像一只手,突然伸过来,轻柔地在孙礼和正兰的衣服上、头发上抚摸,像是一种安抚,又像老友惜别似的,久久不肯撒手。不远处,两个孩子咯咯的笑声,如同鸽哨,划破了天上厚厚的云层,躲在云层里的太阳,腾地跳了出来,公园刹那间明亮起来。
而孙礼和正兰因了内心的雾霾,太阳如何照射,都透不进来。
几天后,1952年5月8日的晚上,孙礼携妻儿以及孩子的外婆,挤上火车,举家往苏北迁移。
这个时候的苏北,正是槐树花开得最旺的时候,洁白的槐花,雪一样覆盖着苏北的各个村庄,淡淡的却又沁人心扉的香气,没有一丝保留地在上空荡漾着,似乎专门为了迎接孙礼一家的到来。
二
苏北是孙礼祖父年轻时落脚过的地方。就这样,一家人于仓皇中在苏北大通口安顿下来。
孙礼在大通口医院继续做主治医生。
1963年农历10月的某一天,在清水县大通口几里之外的朱庄,七点的太阳一冒头,孙礼夫妇一直想要的女儿,念叨了十几年的女儿,降生了。
孙礼给这个宝贝女儿起名孙晓,小名小朵。
小朵出生后,正兰没有奶水,孙礼先后为小朵雇了五个奶娘。
那个时候在农村雇奶娘不是把奶娘请到家里,而是把孩子送到奶娘家里,跟着奶娘家的人吃住。当时孙礼一个月工资38元,奶娘一个月的工钱是13块,为了小朵,孙礼和正兰是豁出去了。
所谓的五个奶娘,是因为有的奶娘奶了小朵几个月便怀孕了,奶水逐渐少了,只好再为小朵换一个奶娘。
他们雇的第二个奶娘只奶了小朵一个月,因怀孕没有了奶水,为贪图一个月十三块的工钱,这个奶娘瞒下不说,私自拿米汤喂小朵。等到正兰过几日去看小朵,发现小朵脸色蜡黄,瘦得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她细问原因,奶娘见瞒不过才说了实话。
把小朵抱回家,整整一天,小朵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孙礼和正兰伤心欲绝,正兰流着泪说:“看来,小朵养不活了,要不把她扔到中山河里去吧。女孩子是水做的,就让她随水流到她该去的地方吧!”
围在旁边的孙林孙庭急了。孙林一边哭一边说:“爸爸妈妈,妹妹还有一口气,不能扔到中山河里。”
孙庭哭得呛住了,一边咳一边抽嗒着说:“你们不能把妹妹扔到河里去,妹妹一定可以救活的,只要再找个有奶水的奶娘,妹妹肯定就没事了。”
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孙庭的话一下子提醒了孙礼和正兰,他们都急糊涂了。
于是正兰连夜抱着小朵,敲开了另一户家中女人有奶水的人家。
这家妇人看到小朵黄瘦黄瘦,眼睛都不睁的样子,不敢收。正兰求她说:“孩子是饿的,只要你有奶水,肯定不会有问题,孩子出任何事我们都保证不要你负责。”妇人这才接下小朵。
三天后,正兰和孙林孙庭去看小朵时,小朵脸色已经变过来,眼睛也睁开了,看到母亲和两个哥哥,竟然张开小嘴笑了。两个哥哥高兴地跳起来,叫道:“妹妹会笑了,妹妹会笑了!”
到小朵一周岁,第五个奶娘没奶后,他们就没再雇奶娘。后来,许多来医院看病的妇女都为小朵喂过奶,这些非正式的奶娘就不知有多少了。小朵其实是喝百家奶长大的,所以村里人说,“孙家这个大小姐,将来肯定聪明得不得了!”
果不其然,小朵很小就表现出了与其他孩子不同的禀赋。
她生性顽皮捣蛋,因为父母和两个哥哥一直宠着她,她做出的事,不但出格且还令人哭笑不得,与男孩子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是小朵六岁那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家里吃玉米团。玉米团是用玉米面做成鸭蛋大小的疙瘩。那时大哥、二哥因为父亲的问题上不了高中,初中毕业后就在生产队里干重活了。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三大海碗冒尖的玉米团转眼就进了他们的肚子——这里说的大海碗是比现在人们家里来客人盛菜的那种碗还要深一点的碗。小朵那时是不吃玉米团的,因为母亲给小朵另备着白面馒头,家里也就小朵一人享受这样的待遇。
但这天中午,小朵破天荒地从锅里捞上来满满一碗的玉米团,正兰看到了,惊奇地说:“朵今天这么乖,能吃这么多玉米团?”
小朵那时很瘦,一向吃得很少,为了小朵能长胖一点,父母想尽了办法。每年立夏这天,正兰会把从七家人家讨来的饭,盛在一只小碗里,让小朵坐在石磙上吃,乡下人说这样小朵就会长得像石磙子一样圆滚滚的。可小朵不知吃了多少人家的饭,最终也没滚圆起来。
见母亲夸自己,小朵非常开心,把碗端到屋后檐下的一小撮菜地旁,满满一碗的玉米团,被她倒进了菜地里。
过了一会,小朵把空碗端回家,正兰高兴地问:“都吃了?”
小朵点点头,从锅里又捞起满满一碗的玉米团。正兰疑惑地问:“你还能吃一碗?”小朵又点点头,继续把碗往屋后端。等小朵再次回到屋里时,看到孙林、孙庭的大海碗里再也没捞到一只玉米团,他们的碗里是稀得能见人影的玉米面粥。兄弟俩就那么嘴对着碗,埋下头吸溜吸溜地喝着。
第二天,正兰去屋后檐下那一小撮菜地旁摘菜,拨开菜棵时,见菜地里一地玉米团,气得回到家来拿起一根小棍子,四处追着打小朵,“你大哥、二哥看到你吃玉米团,开心得情愿自己饿肚子,你可好,把玉米团倒在菜地里,天下有你这样的捣蛋鬼吗?”
孙林、孙庭不仅饱读诗书,琴棋书画也是无所不通。孙林的二胡、孙庭的二胡和笛子,在当地是很有点名气的。只有小朵,身上没有一点大家闺秀之气,更无书香世家孩子的文秀。下河洗澡,上树掏鸟蛋,这些乡野孩子干的,小朵都会干。有一次,正兰被她气得手脚发抖,板着脸说:“一个五六岁大的丫头片子,动不动就爬树把裤裆撕开一个口子,你怎么就不知道害臊?你怎么就不学学你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中,小朵喜欢屁颠屁颠地跟在二哥孙庭后面。孙庭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他书读得多。夏天,一到晚上,村里的中心场地就围满了年轻人。他们坐在树桩上,把唯一的一张椅子留给孙庭,将他围在中间。听他讲《七侠五义》《三国》《封神演义》《水浒》,孙庭讲得眉飞色舞,他们一个个听得也是眉飞色舞。到后来,镇上说书人那里的年轻人也全部跑到了孙庭这里。
小朵因为不完全听得懂,常常会从人群的缝隙里挤到孙庭身边,拽拽他的衣角,挤坐在椅子一角。孙庭怕她摔倒,只能往一边挪。有一次孙庭为了让小朵,正说得起劲,挪时没注意,屁股腾空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大家赶快一起跑过去扶他。其实小朵这样做,无非是告诉大家,孙庭是她的二哥,想显摆一下而已。
三
孙礼年轻时身材修长,玉树临风,白净的皮肤,大而深邃的眼睛,鼻梁高挺,长像千里挑一。正兰说他穿军装时,格外清秀与帅气。
小朵没见过父亲年轻的时候,她是孙礼四十九、正兰四十三岁时出生的。
从小朵记事起,父亲几乎就老了,尽管他的腰依然挺得很直。那个时候,几乎每天,他都要被拉出去批斗。藏在一棵大树后面的小朵,心疼得泪珠一颗颗往下掉,内心却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被叫成“特务”?
晚上父亲挨批斗回来,家里总是坐满了待求医的人,他们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有的看到父亲额头上的血迹时,心疼得偷偷地拽起衣袖抹起泪来。小朵想,既然父亲是“特务”,为什么他们还这么心疼父亲,还为他流泪?
印象中父亲对自己一直是非常呵护的,但小朵还是很怕父亲。因为他不仅不苟言笑,脾气也总是在她毫无知觉时突然发作起来,让她防不胜防。
譬如有一次吃饭,小朵把鞋脱了,脚跷在桌边上。父亲不声不响地走过来,拾起地上的鞋子扔到门外。从那以后,小朵再不敢在吃饭的时候脱鞋子了。
小朵跟父亲亲近的时候很少,只记得有一次,那是在父亲走前的那个秋天。小朵躲在门后,想作弄孙庭,准备在他一进门时,把门后的一根木头扁担推倒,这样就可以砸到他。于是刚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小朵立马躲到门后,在脚步声一进门时,用力一推,扁担直挺挺砸了下去,听到“哎呀”一声叫。
小朵一听声音不对,伸头一看扁担砸在了父亲的左胳膊上,她一下子吓呆了。
父亲看小朵吓得小脸刷白,就安慰她说:“没事,没事。”然后进里间用纱布把臂膀吊在脖子上,出来后用另一只膀子把小朵抱坐在他的腿上,问:
“朵看到过蛇有爪子吗?”
“有呀!没有爪子它怎么爬呀?”
“哈哈,蛇没有爪子,蛇有爪子就是龙了。”
“爸爸,龙是在天上飞的是吗?”
“是的,朵真聪明!”
“朵看到院子里那棵草榔了吗?那棵长得半人高,果子都是刺的植物。”
“看到了呀。有一次我在它旁边蹭了一下,它的果子就都爬到了我的裤子上,还是妈妈把它们一个个拽下来的呢。”
“朵看到过它开花吗?”
“没有。哦,爸爸,小朵怎么从来没有看到它开花?”
“因为它的花很珍贵,如果谁把它的花摘下插在裤腰上,手臂张开就可以飞。”
“爸爸,下次等它开花的时候,小朵去摘啊!”
“哈哈,它的花都是在夜里开,而且随开随谢。所以啊,至今还没有人看到过它的花,当然也就更没有人能采摘到它的花了。”
“小朵可以守在它旁边呀!”
“好,爸爸答应朵,等到来年春天,爸爸一定在晚上陪着朵守在草榔边,等它开花。”
小朵不知道,她这次恶作剧把孙礼胳膊肘上的尺骨砸断了,怕吓坏小朵,孙礼一直忍着剧痛,装作没事。
孙礼最终没有能实现他的诺言,因为他没能等到来年的春天就走了。
孙礼咽气的这晚,风特别猛烈与愤怒,围着屋子不停地嘶叫,打着转不肯离去,一次又一次地敲打着门与窗子,小朵很害怕,仿佛能看到风趴在窗子上向里窥视的表情。
小朵缩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看着几个人用一副担架抬起了父亲,父亲的气喘不上来,他大张着嘴,伸长了脖子。MkZa3eFO2GaBt+dSk1kd5A==孙林在一边一声声地叫:“爸爸,您挺住,爸爸,您挺住!”
孙礼到底没能挺住,在去医院的半路上走了。即便孙林也是医生,最终还是救不活孙礼。是啊,谁能救活一个一心想死的名医呢!
事后,孙礼的一个老友对孙林说,孙礼是服药走的。他前两天曾跟自己提起:“对于一名医生来说,他可以扫大街,可以刷厕所,但他绝不能不拿手术刀,一名不拿手术刀的医生也就没有了生的价值。”
没人知道孙礼服的是什么药,即便对孙林,也是个永远的谜。
父亲走时,小朵没有在人前哭,而是躲在没人的地方,悄悄地流泪。后来正兰说:“朵呀,你父亲走了,你怎么不知道哭呢?”小朵不想告诉母亲实话,低着头走开了。
这年小朵八岁。
孙礼走后的第二天,正是三月末,槐树花仿佛为了祭奠孙礼,商量好似的,在这天早晨一下子全开了。它们站在枝头上,在料峭的寒风里颤抖着,含满露水的面容,似乎隐含着说不尽的悲切。
父亲走后第二年,外婆因伤心过度也走了。
外婆鹅蛋脸,白白的皮肤,长长的柳叶儿一样的眼睛,就连脸上的皱纹也是非常细腻的那种。有时小朵想,外婆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那时小朵因为太小,还不懂得刨根问底去问一些外婆年轻时的事,至今小朵都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小朵跟外婆最亲,听母亲说她生下来只有铜勺那么一点大,她是在外婆的怀里长大的。到她六七岁时,外婆已老得头发全白了,走路也必得靠拐杖一点一点地挪。
外婆的脚很小,两头尖,中间弓起,形状似小船。小朵常常坐在外婆的膝边摸着外婆那双小脚,怜惜地问外婆:“外婆,痛么?”
外婆总是疼爱地对小朵说:“朵啊,它早已不知道痛了,小时候裹它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痛啊,一双嫩藕似的脚,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它裹死,不让它长,我那时就抱着肿成馒头样的脚,不吃不喝在床上整整叫了三天。现在好了,不兴裹脚了,要不朵呵,你可怎么受!”
没事的时候,小朵总喜欢搬个小凳子坐在外婆的膝边,对外婆说要她多吃饭,总怕她什么时候会突然就没了。
小朵说:“外婆,你要多吃饭,你如果能吃两碗,就能像小朵一样在地上跑了。”
外婆被小朵逗笑了,说:“外婆要是能吃上三碗呢?”
小朵说:“那外婆就可以跟小朵一样爬树了。”
外婆被小朵逗得哈哈大笑,说:“你这个朵呀,小脑袋里什么都敢想。”
小朵对外婆很孝顺,那时外婆走路不便,大小便都是用家里的马桶。小朵跟外婆睡,倒马桶的事便由小朵一个人包了。
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外婆大便了,小朵立马就会把马桶端去倒掉,事后刷得干干净净地拿回来。每次外婆看小朵忙里忙外就会很心疼,说:“朵呀,外婆老了,尽给你添麻烦。”
外婆教会了小朵很多生活的知识。
深秋的夜晚,小朵和外婆睡在一个屋子里,半夜时屋子的角落里传来蟋蟀的叫声。小朵就会问外婆:
“外婆你听,什么虫子在叫呢?”
外婆说:“是蟋蟀在叫。”
蟋蟀是书面语言。在苏北,人们习惯称蟋蟀为“油叫子”。可见外婆到底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小朵问:“蟋蟀为什么要叫?”
外婆说:“深秋过了,就到冬天了。冬天冷,人们不能下地干活,只能缩在家里。蟋蟀这是在提醒人们吃吃、省省。”
小朵竖起耳朵仔细听,蟋蟀似乎真的在叫“吃、吃——省、省。”
外婆最疼小朵,也最放不下小朵。有一次,外婆摸着小朵的头,突然说:
“朵呀,你将来会怎样呢?都说人生如节节草,几十年活到老,不知朵将来会过什么样的日子?”
外婆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一口气,说:“可惜外婆看不到了,外婆真想永远守着朵啊!”
小朵看到,外婆浑浊的眼睛里有泪花在闪。当外婆抖抖索索地从衣服的大襟上抽出手帕来擦泪时,那泪已先一滴一滴地滴到了外婆的大襟上。
外婆爱穿深蓝的大襟长褂,这种大襟长褂的纽扣,从左边脖子下顺着左腋一直盘下去,像麻花似的,很好看,很别致。用上海话说,很有腔调。
外婆爱把手帕挂在左边的大襟上。她爱干净,又是大家族出来的,手帕总是一天一换。不像有的老太太,来小朵家串门时,有鼻涕了,伸手在鼻子上一掐一甩,也不管那鼻涕最后甩哪里去了。
夏天的晚上,父亲捧一本医书在他的书房里,大哥、二哥去了朋友家,小朵和母亲、外婆在院子里乘凉。小朵躺在竹椅上,母亲、外婆一边一个给小朵摇着芭蕉扇,看着满天的星斗,小朵会缠着外婆给她讲故事,外婆的故事很古老也很好听。
静谧极了,附近的村庄在或高或低的绿中,显得朦胧而又神秘。一两条弯曲的灰白色的小道穿插在庄子中间,像刚蜕下的蛇皮,趴在那里。目光的极处,小道的尽头,时不时地传来一两声狗吠,给外婆的故事增添了许多地老天荒的韵味。连月儿在柳梢头也好奇地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外婆讲故事。
而这样的夜晚,面对着两个至爱的人,于小朵是怎样的幸福?这是小朵当时体味不到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会热泪盈眶的……
外婆走时,小朵已读二年级。那几天,小朵放学回来,转过前面一排人家,看得见家时,第一眼总是投向自家的房顶。这个时候,小朵的心跳会不断加快,害怕自家房顶上会有外婆的衣服。老家有个风俗,不管哪家死了人,只要一断气,要立即把这个人的衣服扔上房顶,远近的人只要一看到这家房顶上扔了衣服,就知道这家死了人。这叫报丧。
终于,在接下来的一天傍晚,小朵转过前面一排人家,看到外婆的衣服出现在了房顶上。小朵知道,外婆没了。还没等到家里,小朵便号啕大哭起来。
小朵想,此时,外婆如果能够看到小朵这样伤心,她一定会想:“这个朵啊,我算是没白疼她!”
四
正兰在娘家做姑娘时,有下人侍候着,手不提篮肩不挑担,享尽了大小姐的福。嫁进孙礼家后,在上海那些年也是养尊处优,到苏北后她因担忧孙礼的境况,再加上生活的不易,落下了哮喘的病。
在孙礼走后的第三年,正兰也去世了。
正兰走的时候是在初夏。走前,她似有一肚子的话想叮嘱小朵,但她这时已经说不出话。只要小朵放学一进屋,正兰的眼睛就会追着小朵,小朵到哪里追到哪里,追了小朵三天三夜后,她睁着眼睛走了。
小朵不知道母亲已走,端来一碗水对母亲叫道:“妈,你喝水,妈,你喝水。你已经三天没喝水了。”放下碗,小朵把母亲冰凉的手揣进自己的胸口。小朵说:“妈,小朵给你捂手。”
就在这时,屋子里响起了一片哭声。在这哭声里,小朵突然打了一个寒颤,似乎听到头顶“咔嚓”一声,她的天塌了。
给母亲送葬是在一个中午。那天,天上的云厚厚的,大块大块的云由南向北奔跑着,云与云的间隙中,时不时露出一块天空来,那灰白色的天空,是干的、冷的,全然没有平日里那一碧如洗般的水润,像一块拧干了水分的尿布,与遮盖着它的奔跑着的云厮打着。天气就在它们的厮打中一点点地阴冷下来。一支长长的送葬队伍从小朵家西边那条小道转上了通向河南岸坟地的三零八公路。最前面的两个人手里举着白色的挽帐,那是孙庭单位送的。挽帐后面是抱着哭丧棒的孙林、孙庭和小朵,后面是装着正兰的棺材。棺材由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着。棺材后面是一长溜的亲戚和邻居。跟在最后面的是国友。队伍每往前走几步,国友就会从笆斗里抓起纸钱,一把把地撒向空中。转眼间,地面、天空、人们的脚下到处飞舞起纸钱,为送葬的队伍更增添了凄惶。
小朵头上顶着长长的白布,那白布从脑后分成两块拖在地上。完全遮住了小朵。远看,只看到一个白色的小不点手捧着哭丧棒,哭着一声声叫妈。路边几个老太太一边用袖子抹泪,一边说可怜啊,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妈。
母亲走后,因大哥孙林有三个孩子,负担很重,大嫂士芳没有工作,靠孙林在大队卫生室那点公分,养活一家五口,确实困难。再之他早已搬到丈人的那个乡了,当初因为孙礼的原因,孙林才去投靠丈人的。如果再抚养小朵,士芳这边的娘家肯定不会答应。看到孙林在犹疑,孙庭说:“小妹跟我们一起过吧!”
孙林点头说:“难为二弟了,那小妹就跟你们过吧,从小她就跟二弟亲!”
小朵就跟孙庭巧芳一起生活了。
孙庭有两个孩子,巧芳也没有工作,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靠孙庭在镇食品站一个人的工资撑持,生活便很拮据。
短短三年就失去了最亲的三个亲人,小朵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
每日天蒙蒙亮,小朵早早地就爬起来,背着一个篓子去田野里挖野菜回来喂猪。夏天还好,最要命的是冬天,天寒地冻,满地都是霜,不待一棵野菜挖好,手已冻得失去了知觉。将一棵野菜放进篓子里后,要赶忙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哈点热气,再挖第二棵。不然手指头冻僵了,根本挖不动野菜。等到太阳从东边露出脸,小朵已挖好一篓子野菜。回到家,来不及吃早饭,换上上学穿的衣服,拿上二嫂煮的红薯,背上书包,就往学校跑。那时她上学穿的一套衣服,放学一到家就要脱掉,舍不得穿。早晚挖野菜都要换上有补丁,甚至旧到可以做抹布的衣服。
那时小朵虽然才十二岁,已很懂事。平时家里来人烧个豆腐什么的,她从来不伸筷子,偶尔周末孙庭在家,家里煎几块白面饼,小朵也从不动口。过年过节,家里蒸白面馒头,每顿小朵也只吃一个,按她的胃口和肚子,可以吃四五个,但她不能吃,她知道自己不能挣钱,还要上学花孙庭的钱。放学回来,饿了她便抓把红薯干,随后背着篓子就出去了。
一个冬天的傍晚,小朵捡柴火捡得太多了,背不动,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天黑了下来,正是冬天,风没命地刮,把小朵和柴火刮得东倒西歪,小朵又冷又怕,看看远处人家家里那温暖的灯火,想象着人家这时正围在父母亲身边的幸福,想起自己无父无母,无人疼爱无人怜惜,禁不住悲从中来,一个人坐在河坡上哭起来。
有时候,饭桌上看到二哥二嫂有说有笑,小朵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这时她会说天气太热,把碗端到屋后的房檐下,含着泪扒拉着碗里的米粒子,却一口也咽不下。
每逢过年过节,别人家的小姑娘打扮得花团锦簇,喜气洋洋,小朵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个时候,她会一个人悄悄地去到南潮河南岸的坟地。这是一座约有千座坟的坟地,母亲的坟在坟地的中间,要到达必须越过几百座坟。小朵特别胆小,每次来这座坟地都吓得心惊肉跳。那坟一座挨着一座,每越过一座坟,她都是提着一颗心,总害怕坟里会有鬼跑出来拽她的腿。坟地里荒草凄凄,树高而阴森,就连偶尔的一两声鸟叫也是凄惶的。
父母亲和外婆的坟靠在一起,小朵坐在母亲的坟上就可看到父亲和外婆的坟。看着母亲坟上的草,小朵会呆呆地想:草可以一岁一枯荣,为什么人不可以呢?如果人可以的话,母亲就可以活转来了。想到这里,小朵说:
“妈,书上说娘想儿常常想,儿想娘一阵风。妈,不是这样的,我是白天黑夜都想。你和爸爸、外婆也是这样吗?也是这样白天黑夜地想我吗?你有爸爸外婆陪,你一定不孤单,可我就一个人……”
每次,几乎都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小朵才离开母亲的坟。那西下的夕阳,颜色鲜红如血,她常常想,那夕阳是谁的血染的?那应该是小朵的血吧!因为每次想到母亲,小朵的心都在流血。
坟地的坟越来越多,因担心母亲的坟难以辨认,小朵在母亲的坟上栽了一棵小槐树。后来每当清明,大哥、二哥给父母亲和外婆上坟时,就靠着那棵小槐树辨认母亲的坟。
几年后,母亲坟上的那棵小槐树长成了大树。每年春天,小朵再去母亲坟上时,远远地就看到了那棵开满槐花的槐树,那白色的花,洁净而清香。
五
小朵读的高中是一所重点中学,学校在孙林所在的那个乡,当时孙庭跟孙林说好,高中三年,学费他付,小妹高中三年吃的粮食由孙林家供给。
那时的住校生,睡的都是大通铺。春秋天还好,一床薄被一张席子就可以了。到了冬天,同学们都是两人合在一起睡。两个人的被子盖一床铺一床,很暖和。没有人愿意跟小朵合睡,因为小朵冬天只有一套内衣,洗时晾在屋子里,就会看到很多虱子在上面爬。同学躲她还躲不及,谁还会愿意跟她睡一个被筒呢!
躺在一角的小朵,常常会在半夜里冻醒过来。她把自己缩了又缩,直到蜷成一团,却依然抵不过透心的寒,她只能把头埋在被子里默默地流泪。
更令小朵没想到的是,自己第一次去大嫂家拿粮食就碰了钉子。大嫂看到小朵说:“哎呀,她小姑,家里的米早就没了,你不知道,你的这些侄子侄女都跟个小猪似的,可能吃了,地里的那点粮食根本不够他们吃。要不给你一些红薯干吧!”
吃了三周的红薯干后,小朵大便干结,视力也急剧下降,眼睛连书本与黑板上的字都分辨不清了。学校老师把小朵送到医院,医生说小朵营养不良,内火上攻,严重贫血。老师要打电话联系家长,被小朵阻止了。小朵不想让二哥二嫂和大哥知道,大哥这年在县医训班实习,每次回家他都要先来学校看看小朵,问大嫂给了她什么粮食,每次小朵都说大嫂给的米。小朵不想大哥跟大嫂吵架。周末回家,二嫂问小朵大嫂给她拿的什么粮食?小朵也说给的米。小朵怕如果说大嫂不给粮食,二嫂会说,既然大嫂家连粮食都舍不得给她吃,她们又为什么要为她付学费。所以小朵只能两边都瞒着。
大嫂的奶奶知道了自己的孙女连粮食都不给小朵,心疼得一边流泪,一边把家里仅剩的几斤米要倒给小朵,小朵坚决不要。她又给了小朵一点玉米面,小朵拗不过她,只好拿着。于是小朵一天三顿吃红薯干改为了吃玉米糊糊。
一日三餐,每逢学校铃响,同学们一阵风似的往食堂跑时,小朵总磨磨蹭蹭不肯去食堂拿饭盒。即便是拿了饭盒,也总是一个人躲到林子里去吃。她不想让同学看到自己吃红薯干或是玉米糊糊。每次在她吃晚饭时,学校的广播里总会播放《二泉映月》,小朵靠在树身上,任凭泪水和着玉米糊糊,在那哀怨悲怆的音乐里,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咽。
林子后面就是大运河,小朵常常在有月光的夜晚,一个人坐在运河岸边。这个时候周围没有一个人,寂静得树叶掉在地上都能听到。河水在月光下波光盈盈,像小朵常常含满泪水的眼睛。水里的月亮晃晃悠悠,像是要跟小朵说话。这个时候,小朵会想: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孙林每次来学校看她都会说:“你考上大学,我也没钱供你读书,你两个侄子和侄女我要抚养。没有钱再负担你了!”
孙庭从来不说负担不起她读大学,但他的负担也不比孙林轻松。再说孙庭从小抚养自己到现在,于情于理自己读大学也该轮到孙林负担费用了。现在孙林是这种状况,自己怎么办?大学是考还是不考?
小朵抬头问夜空,夜空深邃,却吐不出一个字。小朵低头问水,水也无声,只是默默地往前流。近处和远处的树,也始终沉默,它们都没有答案告诉小朵。
正是春天,槐树花在月光下,像被镀上了一层银,从白天耀眼的白变成银白。每次闻到它的清香,小朵总是想起母亲,它的香味和母亲身上的香味,是那样接近和相似,若有若无,却又无处不在。
六
2023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坐落在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上的一家有名的三甲医院,中医科专家门诊前的长椅上,早早便坐满了人。椅子坐不下,椅子边上贴墙还站着好几个人。这时就听椅子上一位五十多岁烫一头卷发的中年女人,跟她旁边一位年龄相仿的短发女人说道:
“这位孙晓医生是名医,长得温婉端庄,一看就不是出生在一般家庭,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大家闺秀的样子。听说她的父亲三十年代就是上海滩的名医。”
“你知道她?”短发女人问。
“我是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她的事迹的,她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十几年前,就是她把我的哮喘治好的。”
“真的呀,听说哮喘很难根治呢。”短发女人说。
“是呀,我第一次来她这里,就彻底服气了。”
短发女人瞪大了眼睛。
卷发女人继续说道:“她为我把脉后,仔细地看了我的舌苔,然后问我哮喘发作多久了?我说十几年了。她问具体多少年?我数了数说十一年。她又问我发作时什么情形?能不能躺,还是只能坐着?我的天,我看过那么多中医,有很多也是专家,但他们没有一个问得这么详细和具体,把脉看舌苔也是蜻蜓点水似的,有时候甚至问都不问,就直接开药方。而她那天单是把脉、看舌苔、问话,就耗去了四十分钟。我在她那里吃了半年的中药,哮喘便好了。十几年了,一次都没复发过。”
“那你今天来看什么?”短发女人有点好奇。
“我跟你说,你不要吭声呀。我今天来没事,就是想看看她。因为哮喘好了,我也不来医院了,想看她看不到,就只能跑医院来看。”卷发女人声音压得比前面更低。
“那你就在门口偷偷看看呗!干吗还要挂号,浪费钱不说,还占一个位置?”短发女人也降低了声音,有点不解。
“光看一眼哪行?我就是想再听她说两句话,光是听听她声音,我就心定了呢!”
短发女人大概第一次来,不再说话。只是好奇地把头转向门诊那边,想看清里面孙晓的样子。
孙晓走出医院大门时,已是黄昏。这条斜土路离父亲当年诊所所在地汾阳路也就不到三公里的路程。只是孙晓很少去那条路,因为她不能确定当年父亲诊所究竟在汾阳路多少号,再之那里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样子,去了也无法寻根,只能徒增伤悲!
一阵花香袭来,孙晓吸了吸鼻子,转头向西,她看到医院西墙边的一棵洋槐开花了。这几年孙晓才知道,这种能开出又大、又白、又香的花的树的名字叫洋槐。
情不自禁地,她想起了苏北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洋槐,每年三月到五月,那洁白的洋槐花几乎覆盖了村庄,而孙晓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槐花香中度过的!
再吸一口气,孙晓似乎看到了远在苏北的孙林和孙庭,他们终究没能返回上海。现在的孙林,七十五岁了还在县医院专家门诊坐诊,孙庭更是早已成为国家一级编剧,迄今为止创作的七十多部大戏被全国各类剧种无一缺漏地搬上了舞台。
一阵风吹过,洋槐的枝叶轻轻摆动,有几朵槐花轻轻从枝头落下来,其中有一朵落在了孙晓的衣襟上,孙晓就那么由它依偎着自己。恍惚中,她觉得是母亲跟着自己回家来了。
【作者简介】孙思,诗人,籍贯江苏盐城;著有诗集《剃度》《月上弦 月下弦》《掌上红烛》《聆听》《一个人的佛》五部,曾获刘章诗歌奖、鄂尔多斯诗歌奖、中国长诗奖等,另有小说发表于《作家》《延河》等刊;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