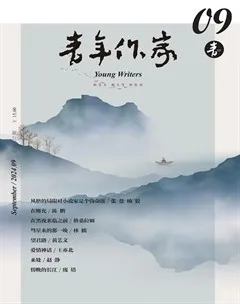在娜允
现在每一分钟
都可能有事情发生
——雷蒙德·卡佛
去娜允之前我联系了刘盐,她是当地最好的诗人(没有之一)。她问我,来开会?我没否认,说,开会不重要,咱们见一面才重要。她笑了,说,欢迎欢迎,我们多久没见啦?我说,十年。她轻轻叫了一声,哟,那么久啦!我说,是啊,你我十年没见过了,我昨天仔细算过,错不了。她说,那更要见一面了。你把车次发过来,我一定去高铁站接你。
娜允,多美的名字,气息独特的滇西南小城,兼具边地的古老沉静和浪漫热烈,以前从昆明坐班车要七八个小时,如今高铁三小时就到。我记得十年前就是在娜允古城门口和刘盐道别的——我们一起参加某文学活动,两天后结束,十多个人作鸟兽散。十年间我们鲜有联络,都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节日问候,再后来偶尔去对方朋友圈点个赞;再再后来,我说的是最近两三年,连点赞都免了。上了高铁,我捋了捋和刘盐的关系,发现我们就快把对方忘了。我打算睡一觉,无奈身后一直有人叽叽喳喳聊天,我掏出博尔赫斯小说集,但是那几位中老年妇女声音太大,你根本看不进去。我索性走到车厢连结处站定,瞪着窗外山峦、溪流、农田和拉毛的方形建筑飞速掠过。后来她们终于消停了,我返回座位,想再读博尔赫斯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抵达娜允的时候天快黑了,刘盐发来微信说她在外面某处等我,还附了照片。我回复她,马上出站。此时站前广场一片昏黑,灯光亮起来,眼前到处是人。我按图索骥,找到刘盐照片上的地点,她语音电话来了,说,怎么没看见你呀?我说,我也没看见你,我就站在卸客区大牌子下面呢,你没看见吗?她说她真没看见,卸客区在哪?她声音又细又小,像一点点往外拉拽。我这才意识到我早把她的声音忘了。太久了。你怎么会记得一个十年不见且交往不深的文友的声音?我说,你发来的照片上就有卸客区啊。你再看一下,我就在牌子下面站着呢。我哪也不去,就站这儿等你。她说,好的好的,我再找找。挂断电话后我有些恍惚,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已经来到娜允,是否真和刘盐联系上了——她是我在此地唯一的朋友。但是,我们的关系真担得起“朋友”二字?我确定?
两分钟后她又打过来,说怎么也找不到我。我只好详细描述我脑袋上方巨大的“卸客区”金属牌长什么样,前后左右有哪些参照物,她总算明白了,大喊一声,说我就在你前面呢。你往前看,一棵大树,看见了没?——果然,左前方有一棵大榕树,但见一个窈窕女子从树后曳步出来,朝我使劲挥手。我也朝她挥手。车灯从她身后射出,一条灰浅色长裙绷得紧紧的,下面一双笔直的小腿,一条深黑浓密的长辫斜在肩头。她走得极快,我看不清她的脸。我迎上去大喊一声,刘盐!
十年了,她没什么变化,大概也因为天色太黑,我始终看不清她,也不太好意思使劲看她,但你能感觉到她的气息,一种草木气味,微香,非常淡,像新鲜雨水的味道。她说,走走走,我车就在那边呢,那边。她带我直奔街角,那里停了一溜车,她蹦蹦跳跳着急往前走,指着一辆白车说,到了到了。我发现车窗大开,刚要拉开车门,她说,不对不对,不是我的车。她尴尬地笑了,我也笑了,说,不着急,慢慢找。她前后找一圈又绕回来,攥着辫子定了定神。这里这里,她终于指着旁边一辆白色丰田。这回对了,我的车,是我的车。杜上兄,请上车。
我坐上副驾,刘盐长呼一口气,发动汽车。她开得不算太稳,有点磕磕绊绊。也难怪,从火车站出来灯光稀稀拉拉的,且车多人多。街道却极其宽阔,甚至过于宽阔了,让你觉得你行进在荒凉的世界边缘——我没料到十年后重返娜允的感觉竟然是荒凉的。十年前的娜允清新明媚,散发着云南边地特有的慵懒,眼前所见也都稍稍溢出,不太像真的。总之当年的感觉,独一无二的感觉消失了,此刻的娜允让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可你又很难说清楚什么地方不对劲。我问刘盐,你都好?她说,都好,你呢,听说离职了?我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不是离职,是下课,二者区别很大。她有些抱歉地笑笑说她也是刚听说,听说杜上兄没有单位了。我说,是啊,没有了,再也没有单位了,哥们儿自由了,想写就写,想读就读。她说,多好啊,多让人羡慕。我问她还在写诗?写啊,她说,不写诗还算诗人?这时候灯火渐渐密集,我们途经一个小广场,音乐震耳欲聋,一群中老年人兴高采烈地跺脚扭腰,像要把破碎的灯光踩得更碎些。刘盐向我介绍广场名字,我没听清,她又讲一遍,我还是没听清。她声音太小了,始终限定在某个低分贝区域,你必须使劲竖起耳朵。她重复三遍我才听明白,倦湖广场——没错,疲倦的倦,不是眷恋的眷。但暗夜里,除了一帮斗志昂扬的中老年人,你无法看见他们身后的倦湖。我笑了,发现湖的名字真有意思,也许就是被几十上百个大爷大妈们不知疲倦地跳啊、蹦啊、踩啊给搞疲倦的。刘盐似乎没察觉到我笑了,聊起今年娜允的房价、肉价,总之比昆明低很多,总之娜允的生活挺惬意的。你看那些大爷大妈,一直跳到十一点多呢,她说。十分钟后我们把倦湖及中老年舞蹈爱好者远远抛下了。我问她,你还是一个人啊?她吃了一惊,伸手撩一下刘海,两手在方向盘上摩挲,像要把什么东西擦掉。是啊,一个人。不找了?不找,为什么找?麻烦。也是,一个人多好。对嘛,一个人多好。我说,我真佩服你的独身主义,十年前你就这样,十年后还这样。她侧身看我,反驳我道,不对,我不是独身主义啊,我儿子都二十了。我大吃一惊,说,是吗?没听你说过啊。她说,又不是什么秘密,杜上兄你一定记错了。哈哈。她的笑声还是那么纤细,像一根蛛丝飘荡在我们之间。我十年前告诉过你的,我有一个儿子,一直有个儿子,我自己把他带大,转眼就二十啦,今年大二。我想说点什么却无话可说。我还不至于蠢到打听孩子父亲是谁,她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沉默片刻,我问她孩子在哪上大学?当然,我意识到我的提问已经晚了半拍。她说河大。我说,什么河大?她说,河南大学啊。哦哦,我说。我似乎走神了。对啊,我说,河南大学,郑州对吧?她没接茬,问我,饿了吗?去吃点东西?我说,悉听尊便。她问我哪天回昆明,我说明天就撤。她说,那今天必须喝一杯啊。我说,我多年不喝酒了,差不多戒了——
小酒吧非常雅致,你很难想象偏远的娜允竟有如此雅致的酒吧。吧台小哥十分殷勤,一口一个哥、姐(实际上,我很可能比他爹的年纪还大)。刘盐点了一桌子吃的,说话声还那么纤细,或者,换一种更云南的说法——软糯,倒也颇具娜允特色,我渐渐适应,不必竖着耳朵了。她劝我来点啤酒。我说,不喝酒行吗?她说,你一个写小说的,还真戒啦?我点头。她说,这还是杜上?她莞尔一笑。我意识到十多年来我和刘盐从未喝过一次大酒。从来没有。似乎我们之间远未亲密到一起喝一次大酒的程度。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刚冒出来的边地诗人,在某次文学活动上羞涩腼腆地躲在一边。对这样的女子,你很难走过去说,嘿,我们喝杯酒咋样?她看似排斥酒精,事实上恰恰相反,边地女子一个个酒量了得,我后来算是见识了。好,那就不喝,刘盐说,喝什么呢?我说,水就好。她说,柠檬水?我自然答应。柠檬水上来了,她接上先前话头,说她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待着,和所有人保持距离,特别是娜允大大小小的作家们。你知道的杜上兄,在小县城,你只要稍稍有点才气,只要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你就很难好好活下去了,那种恶毒,他们针对你的那种恶毒,你能理解吗?我轻轻点头,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嘛。她说,你这是理论,是道理,恐怕你还没真正经历过呢。她忽然有些激动。我拎起肉串递给她,她接过去咬一口,说,她半年前参加的一个所谓文联活动就惹上麻烦,大麻烦。一个中年男人忽然凑上来做自我介绍,说他也是写诗的,读过她发在省刊上的诗,所以,一直记得她的名字。我的名字?她说。男人说,刘盐,盐巴的盐,这个名字太神奇了,是笔名吗?神奇?她说。不是笔名。他说,是神奇,哪个会用盐巴的盐做名字呢?哈哈。她说,这是我爹妈起的,盐巴,人活着离得了盐巴?你每天吃的喝的,离得了吗?男人被问住了,也可能被吓住了,使劲摇了摇头。她说,对啊,拿这么普通的东西为我命名,你不觉得——所以我说嘛,神奇,他打断刘盐。所以你的诗啊,那么容易让人记住。总之那天聊的话题奇奇怪怪的,刘盐说,我不太好形容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脏东西黏在你身上怎么也搓不掉,但是你又有点,有点对搓它的感觉上瘾。你懂我意思吗杜上兄?我说,懂,我懂。她接着讲,更让她奇怪的是从没在娜允见过此人,娜允巴掌大的地方,按理说写诗、写小说、写散文的两只巴掌就能数过来,偏偏从没见过他,他在什么地方发表过东西、在娜允哪个单位上班更是一头雾水。那天活动进行了不到一半她就想开溜——太无聊了,听几个诗人吹嘘自己的诗多么厉害实在让人受不了。她找到主办方也就是县文联领导,说她忽然不舒服,头疼恶心,能否告假先行一步?文联领导将她拉到一边,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告诉她,有人说你在省刊发表了大作是跑去昆明和主编拉关系才上的稿,我警告他们说,刘盐不是这种人,你们莫乱讲。嘿嘿,刘盐,你千万莫搭理这些鬼话。刘盐气得浑身发抖,说,纯属造谣污蔑,往我身上泼脏水呢。领导说,就是就是,放心吧我替你主持公道,不过你还是少往昆明跑咯,免得遭人嫉恨。我气坏了,转身就走。刘盐说,那个男的,那个男诗人追上来,问我怎么了,我没理他。他就在我身后嚷嚷起来,省刊发表几首诗,了不起啊。
这次聚会之后,刘盐再不参加娜允任何文学活动,一个人躲起来安安静静写诗。我说,你做得对,诗人就该拒绝一切活动踏踏实实写,谁也别搭理。就是就是,她笑了,说这件事情没完呢。一天,那个男诗人不知怎么弄到我住址的,突然手捧一束百合出现在我家门口,说想拜我为师。我当场拒绝了他,说我教不了人,也不想教人写作,写作是一个人的战争,自己读自己写。他悻悻地说,你还不知道啊,现在大家都说你和省刊XX主编关系不一般,如果你收下我这个学生,就可以堵上那些人的嘴巴。我说,堵哪个的嘴巴?怎么堵?我收了一个学生,人们就会因此统统闭嘴?他说,你收下我就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啦——刘盐不是没有男朋友,既然有男朋友,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他们都会忌惮三分,看今后哪个还敢在你背后嚼舌根。我让他赶紧滚蛋,我不需要什么男朋友,也绝对不需要他来做我学生兼男朋友,我对他和他的诗没有半点兴趣。他说,行,你收下花。我说,拿走拿走,我不要你的花。他硬塞进来,一溜烟跑下楼。我从窗口扔下去,直接往他脑袋上扔下去……结果,杜上兄你肯定猜到了,此人成了说我坏话最多最狠的那一个,除了到处说他和我谈过恋爱,还说我喜欢他,主动追他,想和他组建家庭云云。总之谣言满天飞。我真想狠狠骂他、抽他、报警抓他,可是啊杜上兄,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再说,我一介女流,向来胆小怕事,对这些谣言毫无办法,你要是真打上门去兴师问罪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岂不是对号入座中了圈套?那时候,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刘盐喝一口柠檬水,又劝我吃点东西,我让她接着说。她叹口气,说那段时间她差点逃去别的地方别的城市从头开始,但是,逃跑能解决什么问题?难道,逃去别的地方就不写诗了?就不和一个个活人打交道了?我决定留下来,不辩解,不吭声,每天写诗。那段时间除了上班、睡觉、吃饭,上厕所我都在写诗,晚上会给儿子打个长长的电话。天天如此。周末照样出门逛街,碰上熟人主动打招呼,没有熟人就拎着菜篮子回家,一步一步稳稳当当走回家。那些谣言还没有变成刀子飞在脑袋上扎在身上嘛,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空气还是这些空气,灿烂,干净,甜滋滋的,这不就是生活?不就是我在娜允的生活?我还要什么生活?我还能去哪里生活?
我把两三只鸡爪认真啃掉。真香。昆明的烤鸡爪哪有如此美味啊。吃完烧烤,我们十点准时离开,她执意送我去酒店,我说,太麻烦你了。她说,千万别客气,你难得来一趟,再说我们六七年不见啦。我说,不不,你又记错了,是十年。真的吗?真的十年没见了?我说,上一次见是2014年,在古城门下。她惊愕不已,说,对对对,我们好像是在娜允古城——对,活动结束,我们在古城道别的。我说,当时有六七个作家。她总算想起来了,回忆着当时的种种细节。之前呢?她问我。什么之前?我说。那天之前,也就是,前一天,我们在哪里?我说,酒店会议室,然后是酒店餐厅和茶室。就是一次乏味的封闭在酒店里的文学活动而已。她轻轻点头,说,真是奇怪,怎么感觉也就一年半载没见呢,太奇怪了,你没什么变化。我说,我老了,很老了,你不要安慰我。她笑了,问我这次怎么有空来娜允?我说,我也一头雾水,是一个很小的活动,不知道主办方为什么非要让我来,非要让我来聆听一下某北京大咖讲怎么写小说。我还用得着他来教我写小说?哈哈,总之非常诡异。不过,我说,这一趟咱们见上面比什么都强,换句话说,你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她笑了,直视前方的双目闪闪发亮。此刻,娜允的魔幻感有增无减,天空一轮弯月,月光下的小城酷似博尔赫斯笔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寂寥神秘,一切都不真实,包括刘盐。你很难说她和十年前的刘盐是否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十年之后她仍是毫无变化的同一个人?她的直觉没错,我们真的有十年没见了吗?
酒店位于某个艺术村落深处,我们迷路了,迷失在一大堆莫名其妙圆不圆方不方的滑稽、丑陋的建筑群落中。来回转悠半天仍不得要领。刘盐的声音更细了,问我,这到底是哪啊?哪有酒店?我们原路返回,周围建筑像一根根丑陋的指头戳向天空。我问她这地方,所谓的艺术村是什么时候建的?她说她也搞不清楚。哎,她叹口气,娜允一直变来变去的,这地方建成应该不到三年吧。我下车找到景区保安问了又问,最终确定酒店方向,几分钟后总算到了。我顺利找到前台,值班女孩迅速为我办好房卡。我转身回去,正式向刘盐道别,说明天再见。好的,她立在黑暗中,站在丰田车旁,浅灰色裙子非常薄,隐约可见黑色胸罩纤细的吊带。晚安,杜上兄。她说。晚安。我说。我看着她上车,掉头,从车窗伸出胳膊朝我挥了三下。我进酒店,上电梯,打开房门,猛见得一条彪形大汉四仰八叉地躺在右侧床上,赤条条亮出肥硕的大肚皮。我吓坏了,结结巴巴说,这是1018房?对方说,对啊,是1018,你是杜上?我说,你谁啊?他说,我老聂啊,我也写小说,咱俩没见过?我说,是没见过。心里暗想谁是老聂?写小说的老聂?慢着,这次活动是两人一间房?居然两人一间房!我惊慌失措——到了这把年纪,我已经很难和任何人共享一个标间了。这恐怕是我最执拗的怪癖之一。我落荒而逃,那位写小说的老聂在屋里喊了一嗓子,喊的什么我根本没听清。
我站在微凉的夜色里给刘盐打了语音,说,我想另找住处,你能回来接我吗?没问题,她立即答道。你就在酒店门口等我,哪也别去。这时候月影婆娑,远处灯火迷离,景区内空荡荡的。所幸那些诡异的建筑大都模糊了。我知道这座边地小城正进入睡眠。前台女孩不时探出脑袋看我。刘盐很快回来了,冲我轻按喇叭。我上车后冲她大笑,说,见鬼了,要我和一个大胖男人睡一屋,不如把我杀了算了。刘盐也笑了,问我,去哪呢?我说,就近找个酒店呗。她说她也不熟,其实她对娜允一点也不熟。我说,没事没事,咱们现找。所幸驶出景区几分钟就发现一家不错的民宿,雪白拱形门,门前带一个漂亮的小花园。我大叫一声,就它了。刘盐靠边停车。进去后不见一个服务生,也不见前台。一个男人走进来,说这是自助旅馆,自助白色旅馆。白色旅馆?我说。旅馆名字嘛,白色旅馆。他说。我问他,如何自助?这个秃顶男看了看刘盐,又看了看我,指了指墙上一个电话让我打过去询问,然后迅速钻进某个房间,消失了。我拨了那个手机号,对方介绍了入住规则,加了我的微信后发来房间智能门锁密码。我正准备上二楼,刘盐在我身后小声道,杜上兄,我就不上去了吧?我回身说,你不想瞄一下房间?她犹豫了两三秒钟,说,好吧。我们一前一后上去,来到房间门口。我用密码顺利开门进去。房间果然漂亮,艺术气息浓郁,白色小桌,椅子很小,也是白色的。床很低,却比普通榻榻米略高一些,看起来宽大舒服。雪白的床单在灯光下有种金属质感,像一块巨冰,又让人想起流淌着奶和蜜的河流。我放下背包,刘盐两手放在身后。我说,不错,这地方,不错。她说,是啊,是挺好的。我说,这床真够大的,那么白。她说,是啊,还真是。她不再说了。我说,行了,谢谢你,刘盐,你回吧。她抬腕看了看表,都十一点半了。我说,太晚了,实在不好意思。你快回吧,我送你下去。她看了看我,两手从身后垂下来,说,你刚才怎么不就在原来那个酒店开间房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她的长辫浓密乌黑,发丝微微卷曲,淡淡的清新气味若隐若现。我被问住了。是啊,为什么不在那家酒店开一间房呢?我没法回答。脑子一片空白。我走了。她低下头说,你早点休息。我们下楼,走出玻璃门,我看着她上车驶离才返回旅馆,一步一步来到二楼。
上床之前我发现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明天怎么安排?刘盐送我来的路上说她明天抽空带我转转,但具体什么时间一概没说。我冲了凉,在雪白的大床上躺下,博尔赫斯的小说看了不到一页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是被微信的滴滴声惊醒的,手机显示凌晨1:13。刘盐说,杜上兄,我不太舒服,明天不能陪你了,抱歉。我答,怎么搞的?吃药了吗?她答,吃了。我说,好的,早点休息,不行上医院看看。她没再回复我。我蒙头大睡,次日一早步行回景区酒店开会,中午给刘盐发了微信,想告诉她,活动实在没劲,已买好晚八点的返程车票。但是信息没发送出去——我被告知对方不是好友。我又试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我想调出她的电话。不对,我没她电话啊,十年前或十年后,我手机里从来就没有刘盐的电话。

【作者简介】陈鹏,小说家,1975年2月出生于昆明,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昆明市作家协会主席;曾获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著有中篇小说选《绝杀》《去年冬天》《向死之先》,短篇小说集《谁不热愛保罗·斯科尔斯》,长篇小说《刀》《那年,我们在阿维尼翁》《群马》等;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