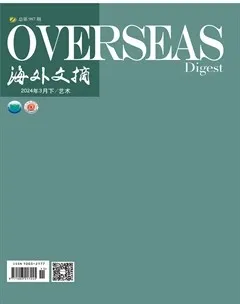韩国与日本的假面舞蹈比较探索




1980年韩国《河回别神假面舞》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1997年举办了第一届安东国际假面舞庆典。韩国《河回别神假面舞》从高丽中叶开始发展至今已有800余年,表演带有一定戏剧性、讽刺性和批判性。日本能剧是产生于14世纪初的传统戏剧艺术,从奈良时代开始逐渐发展壮大,其特征是滑稽剧与抒情剧并行,《翁》是能剧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剧目。作者在日本工作期间,同时在韩国攻读博士学位,具有调查研究的便利条件。本文是具体调查结果的总结。文章从这两部假面舞入手,通过观看演出、调查走访等方式,对其使用的假面具、乐器、服装、舞台结构以及表演内容等进行对比研究,总结两部剧目的基本构成,将其现状清晰地呈现在大众视野中,为我国的假面舞蹈研究与发展增添新鲜的文献资料。
1 《河回别神假面舞》的构成
1.1 表演内容
《河回别神假面舞》全剧共分为六场:第一场舞童戏(为了“净场”所做的驱邪舞)是序幕,也是典型的“肩上舞”。第二场朱机戏是辟邪仪式舞。第三场杀生戏是生活模拟舞蹈,一位白丁出场模仿表演杀牛叫卖的过程,是互动最多的一幕。第四场老媪戏通过织布谣的方式,表现了庶民的艰辛痛楚。第五场破戒僧戏是男女双人舞,通过对娼妇和破戒僧的人物刻画,在表现人性本能的同时,讽刺了违背道德的社会行为。第六场两班与书生戏,通过书生、娼妇与两班的三角恋关系,引出所有人物再次上场,在争执与打闹中结束全剧。通过演员的人物关系与故事剧情的衔接,可以发现《河回别神假面舞》具有完整的戏剧情节和人物形象,充满了现实意义与讽刺意义。
1.2 假面具
韩国河回假面具是以赤杨树为材料制作的假面具,最早可追溯至高丽中叶[1]。面具以深眼窝高鼻梁的风格和左右不对称的设计方法,在假面美术领域获得世界级杰作之称。1964年被指定为韩国国宝(韩国唯一假面具国宝),现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河回假面原有十余种,现存且在《河回别神假面舞》中使用的有2个朱讥、两班、娼妇、新娘、书生、僧、白丁、老媪、夷昧、屏山共11种(如表1),造型逼真。特别是两班、书生、僧等面具与人体结构功能相通,其下巴可以单独活动,活灵活现。
1.3 乐器
《河回别神假面舞》使用农乐器(风物)伴奏,主要有长鼓、太平箫、铜锣、钲和鼓等。长鼓的材质为瓷或木,鼓的头部较宽,腰部细长,使用右手持细鼓棒击打鼓的一侧,左手则空手或持弓形鼓棒击打鼓的另一侧。同时击打两侧称为“双”,仅用鼓棒敲击一侧称为“片”,仅用左手敲打一侧称为“鼓”,短暂敲击并产生滚动声的动作称为“摇”。
太平箫是吹奏乐器,由木制管体和铜口上插入的双簧构成。管体由坚硬的木材制成,外观仿竹节。管体有八个音孔,其中第二个音孔位于背面。铜口由铜制成,用于固定簧片,簧片采用薄竹片制成。由于太平箫没有固定的制作标准,其音调和音高不一致,音量大,音调高,适合在户外演奏。
铜锣(小金)是一种圆形铜制的打击乐器,中心部分发出最大的声音,称为“响音”,稍离中心的部分发出平稳的声音,称为“平音”,而最边缘的部分发出较小或跳动的声音,称为“变音”。在农乐中,根据角色需求,铜锣还分为“母铜锣”和“公铜锣”,各自能发出不同的音色。
钲(大金)是用黄铜制作成的大碗状锣,吊上绳子握在手中,用槌子敲打或绑在木制模具上演奏。把杠的末端用布条缠在木制把手上,多用于军乐、舞乐、佛教音乐、宗庙祭礼乐等。其声音雄壮,与梵钟相似。
鼓的筒多用松树或梧桐树制成,鼓面为牛皮。鼓筒上的图案用于区分鼓的种类(例:宫中鼓多用龙纹样),在祭礼、朝贺、宴享、出行、检阅军队等活动中都会使用鼓,起到与神沟通的作用。
1.4 服装
《河回别神假面舞》的服装非常朴素,接近平民百姓的日常着装。在朝鲜王朝时代,屠夫的地位十分低下,他们戴着平安郎,衣服没有扣子,脚上穿着竹编鞋,十分潦倒。老媪上身穿着露出肚子的白色亚麻赤古里,表现了生活的艰苦。两班戴着正书冠,一身白服,手里拿着扇子,是上流阶层的代表。新娘绿红搭配的韩服,与传统婚礼着装相符。一对朱机穿着白色内衣,手臂上穿着齐膝的铃铛模样的丝绸衣服,背上披着麻布长袍,以模拟神兽模样[2]。
1.5 舞台
《河回别神假面舞》在室内外均可表演(如表2),在祭祀仪式结束后,演员们从祠堂出发,路上边演奏农乐和歌唱,边与观众互动,到达演出场地后随即开始表演。在室外演出没有专门的照明和舞台时,会点篝火和制作龙、凤、龟灯等,达到照明和装饰的作用[3]。观众围坐在地上,中间的空地就是舞台。在舞台上表演时,演员有固定的左入左退的规则,演奏者有固定站位。演出结束后演员们会摘下并手持面具再次上场与观众挥手告别,也有合影留念的机会。
2 《翁》的构成
2.1 表演内容
日本典籍《细流抄》有记载“庆云元年始行大傩”,可见7世纪初已有假面舞表演。在演出开始前要举行音舞、颂谣等形式的“别火”(通过喝酒达到净化身心的目的),在狂言结束后会中场休息15分钟。
《翁》的表演有三个部分:第一场是仕舞,首先上场的人叫仕手,是全剧主角“翁”的扮演者。他围绕赞美上帝和人类而进行诵唱,使用四种或以上的语言,十分多元化。《翁》是唯一一部仕手在舞台之上佩戴面具的能剧,面具戴上之后代表着神之降临。表演中年轻男子扮演千岁这一角色,通过扇子来净化空间,驱除恶灵。舞蹈节奏欢快有力,跺脚的动作,具有感恩大地恩赐和人类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第二场狂言是具有固定情节的话剧,但是演出中不会穿戴面具,演出目的是与观众互动并为三番叟做铺垫。第三场三番叟是以强烈的节奏和动作唤起观众共鸣的舞蹈,当舞者佩戴上面具时,三番叟正式开始。舞者通过模拟播种的动作,同时挥舞铃铛(与神交流的媒介)表现新希望的降临[4]。
2.2 能面具
能面具有600多种,大致分为七类:翁面、男面、女面、尉面、怨灵面、神灵面、鬼神面。男面、女面是具有明确性别的人类角色面具,尉面是老年男性,怨灵面、神灵面、鬼神面都是人类以外的面具,与剧中的角色可一一对应。
能面制作工艺十分严格,不仅尺寸要比人脸小,还要根据模板统一制作,制面师大多都是将工艺代代相传的专业雕刻师。能面颜色素雅(如表3),以白、肉色为主,无特殊花纹或夸张表情。能面似笑非笑,似悲似喜,不同角度能看到不同表情。翁面作为御神体是依据摩多罗神形象设计而成的,寓意圆满福德、长寿之相。
2.3 乐器
能剧的乐器称为囃子,包括笛子、小鼓、大鼓、太鼓等。根据演出风格不同,使用的乐器也有所差异。表演中的指挥官一般由太鼓担任,若无太鼓参加则由大鼓负责。此外,在表演中打击乐器演员会附和呐喊声以作特殊的伴奏,这是能剧表演的特征之一。
笛子(能管)属于吹奏乐器。由7个指孔组成,材质为竹子。竹管内部插入的一根细管叫作咽喉,可发出独特的声响。笛子长度粗细不一、音阶音高也各不相同,此一特殊性为能乐的表演增添了诸多乐趣。
小鼓的鼓身材料是樱花树干,鼓面多选用小马皮制成,鼓身与鼓面由调弦连接捆绑在一起。小鼓声音柔和,通过松紧调弦可以区分出多重音色。因其音色会受湿度的影响而改变,演奏者会利用呼吸、哈气或者喷唾沫等方式来调整鼓面湿度,让小鼓发出不同的音色。
大鼓(大革)的鼓皮由两片马皮制成,鼓身是樱花树干,二者也通过调弦连接。演出前要将鼓皮进行炭烤处理,在演奏时会发出高亢清脆的声音。演奏时需右手带指皮,依靠击打力度来区分高低音。
太鼓是用调弦将两张牛皮和穿孔的欅紧紧绑在一起的打击乐,演奏时放在专用且置于地面的台子上,用双鼓槌进行演奏。当神、鬼、雷等非人类角色登场时,多用太鼓伴奏。
2.4 服装
能剧的着装是根据数百年前的日本朝服制成的,演出时还会配上假发、饰品、折扇等。颜色有深浅红色、白色、黄色等,面料奢华,纹绣多用金银丝线,还会镶嵌金箔、银箔等。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翁》服装,现保管在日本各个能剧博物馆中。其中,19世纪的野宿为淡黄色的长袍,绣着流水木筏、樱花树、凤蝶、枫叶等花纹,现收藏于金泽市能剧美术馆之中。
2.5 舞台
《翁》需要在特定能剧场进行演出,舞台由柏木制成,分为正台、后座、地谣、廊桥四个部分(如表4)。最初《翁》仅在户外进行,而现今能舞台被整体搬进了室内,几乎不在室外表演。能剧场舞台没有幕布,只有一面绘着松树图案的镜板(松壁,源于1615年)。舞台宽约6米,右侧为地谣座,是负责唱词的乐师所坐之处,其后方坐着鼓手和助演,从左侧后座连接着斜向内侧延伸的桥槽上挂着通往舞台的入口帘(上幕)。
3 《河回别神假面舞》与《翁》的比较
两部剧都具有固定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戏剧性特征明显[5]。通过面具的花纹、图案、表情等,能够轻易地分辨出两部剧各自的人物特点,具有说明性特征。《河回别神假面舞》和韩国其他假面舞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乡村假面舞、城市假面舞、宫廷假面舞三种表演风格。日本以《翁》为代表的能剧主要在贵族的要求与引导之下发展成形,目前均为剧场风格。韩国假面舞气氛轻松愉快,观众随时参与互动,舞蹈动作如生活般随性,演出场所不固定。而日本的假面舞风格庄严肃穆,表演程式化,演出中与观众没有任何互动,多为设计性舞台动作,且只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演出。从面具来看,二者都具有固定的人物角色和对应面具,但制作工艺与样式完全不同。从演出内容来看,前者的六个场面之间相互关联,而后者的三段式表演之间相互独立。因此,虽然韩日两国的假面具存在相似性,但表演设定与审美标准皆存在差异。韩国假面舞夸张开放且具有即兴性,日本假面舞具有内敛隐忍的特点,符合其独特的“幽玄”审美特性。
4 结语
在快速的文化交流环境中,通过假面舞蹈了解两国的文化历史,得知了传统假面舞蹈的起源与发展,保障了假面舞蹈文化有效交流。韩日两国假面舞的面具、服装、乐器以及表演内容等,都传袭了各自的传统文化,符合历史发展的传承特性。通过《河回别神假面舞》与《翁》的调研采访,能够正确地探知韩日舞蹈文化的独特样貌,对我国假面舞蹈文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引用
[1] 赵婷.“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化州跳花棚与韩国凤山假面舞的对比研究[J].艺术评鉴,2020(13):77-79.
[2] 贾健.非遗视野下韩国民俗舞蹈传承方案研究——以韩国凤山假面舞为例[J].艺术评鉴,2021(20):26-28.
[3] 诹访春雄.中国的傩戏对日本能乐和朝鲜假面戏剧的影响[J].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19,4(4):64-72.
[4] 강해원.한·일 가면극 전승현황 및 비교연구[D].숙명여자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2018.
[5] 村上祥子.韓国仮面劇と日本伎楽の比較研究[J].比較民俗研究,1991(3):86-123.
作者简介:严慧(1992—),女,河北秦皇岛人,博士研究生,就读于韩国汉阳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