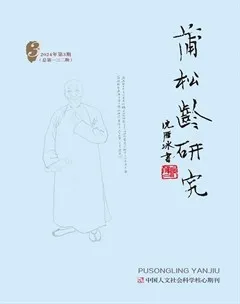蒲松龄《述刘氏行实》的多重解读
摘要: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深切表达了他对妻子刘氏的感念,文字简约含蓄,感情真挚。此文蕴含了大量蒲松龄婚姻家庭以及其妻刘氏人生理念的信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可知蒲刘婚姻缔结的理念基础是德行为重,“不以贫为病”;蒲松龄一生科举之路举步维艰,家中贤妻是他成就背后的坚定支撑;她能体悟“山林自有乐地”,“但知止足”,尤其凸显中华优秀女性的智慧通达。有此根基,刘氏完全可以和蒲松龄平等对话。
关键词:蒲松龄妻;述刘氏行实;婚姻;优秀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志码:A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讲述了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尤其塑造了诸多风情万种的女鬼女狐女妖形象,在古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现实生活中,他有着一位温良贤惠、勤俭持家、明智通达的妻子。对妻子刘氏,蒲松龄在诗文中多有提及,最为详实的记述就是在其妻过世之后所作的《述刘氏行实》,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切感念。文章不长,简约含蓄,但感情真挚,深婉动人。聊斋文化研究者对此文多有提及但未做深入解读,实际此文蕴含了大量的蒲松龄婚姻和家庭的信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详细解读,一方面对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蒲松龄的人生和创作有很多启发,另一方面对我们认识这位蒲松龄背后的贤妻,并加深对中国古代女性的理解也有重要意义。
一、德行在先,不以贫为病——蒲刘婚姻缔结的理念基础
中国古代对男女婚姻极其重视,将其提高到关乎天地万物化生和阴阳平衡,家族繁衍发展和社会礼俗的角度来看待,婚礼的程序也极为繁琐。《礼记·昏义》开篇就明确提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1]188这对后世婚姻制度和夫妻相处之道有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婚姻形态和婚姻文化。
蒲松龄妻子刘氏的父亲刘国鼎是一位有学识的人,在科举考试中多次取得好名次,生有四个女儿,蒲松龄之妻是其次女。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简略记录了蒲刘婚姻的缔结的过程,其中个别细节值得我们深深品味。
松龄父……为寡食众,家以日落。松龄其第三子,十余岁未聘,闻刘公次女待字,媒通之。或訾其贫。刘公曰:“闻其为忍辱仙人,又教儿读,不以贫辍业,贻谋必无蹉跌,虽贫何病?”遂文定焉。[2]250
寥寥数语,道出婚姻的过程。蒲松龄是家中第三子,十多岁还没有定亲,家中听说刘公的二女儿还没有许嫁,于是请媒人说合。对于此事有人“訾其贫”,即诋毁蒲家穷而不看好这门亲事。此类评说也有一定事实依据,蒲家当时的确家道中落。明万历以来,蒲氏家族“科甲相继”,虽然不是非常显贵,但也算得上是诗书门第。可是到了蒲松龄父辈,已经家势衰微。在儿女婚姻大事成败的关键时刻,刘氏父亲的态度成为决定性因素。所幸刘氏父亲并非嫌贫爱富之人,毅然将其次女嫁与蒲家,因为他认为蒲公即蒲松龄的父亲能够忍辱负重,又坚持教儿子读书,不因家贫而耽误正业,对子孙教诲定无失误,家贫又有何妨?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蒲刘婚事就这样正式定下。刘父看重蒲家“不以贫辍业”,反问“虽贫何病”,其远见卓识可见一斑。顺治十二年时,百姓间流传皇宫欲选用宫女,人心惶惶,刘家将信将疑之间,为了避免风波,便将刘氏送到蒲家生活,谣言平息后才回到娘家。两年之后,蒲松龄与刘氏举行了结婚典礼,刘氏正式嫁入蒲家。
细究起来,刘氏之父德行为重的婚姻理念正是中华优秀婚姻文化的一个缩影。为儿女选择婚姻对象时首先看重德行自古有之。《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准备将女儿嫁给其弟子公冶长时,针对公冶长曾经身陷牢狱一事,直截了当做出论断:“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 [3]75即孔子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他曾经被关在牢狱之中,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汉代婚姻缔结更是突出“敬德”,选择婚配对象以“德”为主要标准,夫妻在相处过程中也非常敬重对方的德行。如《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20f4e88a9f0fd28275b127cdba83b0917593dc024d3633a26c6bc844048d85ed,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 [4]2781少君之父正是看中了鲍宣虽家境贫穷但好学有志,才将女儿嫁给他,这与后世蒲松龄的岳父有着共同的嫁女理念。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曾经直言不讳批判当时重门第资财的嫁娶风气:“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 [5]64为防止此种近乎“买卖婚姻”的风气玷污门楣,他特别制定家规,规定颜氏家族的婚嫁,不可攀比门第,宁可选择清寒之家。而且历来家风如此,“婚姻素对,靖侯成规”,即婚姻要找清白人家,这是当年先祖靖侯立下的老规矩:“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 [5]415明代著名理学家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明确指出:“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6]630嫁女儿时首先要选择品行好的男子,不要只顾着索要贵重的彩礼,娶媳妇时要追求知书达理的女子,而不去计较她有多少的陪嫁,否则与卖儿卖女无异。这些历代以来对婚姻首先应该看重品行的理念,对后世有着重要意义。应该说,蒲松龄是受益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婚姻制度的,面对社会上的“嫌贫爱富”“门当户对”观念,刘氏的父亲顶住压力,促成了二人最终结合。《聊斋志异》中一些女子重才情而不计贫富毅然出嫁贫穷书生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人生经历的反映。
二、举步维艰,所幸有贤妻——蒲松龄成就背后的坚定支撑
刘氏之父的婚姻缔结理念着实让人敬佩,由此给蒲家带来了一桩好婚姻,刘氏十五岁正式嫁入蒲家,至七十一岁去世,在蒲家共五十六年。刘氏之父以德行为先看重家教为女儿选择婚姻,实际其女儿本身更是德行的代名词,刘氏之嫁蒲松龄给其艰难生活和创作人生提供了稳固的家庭基础。在《述刘氏行实》中,蒲松龄对她的人生描述简明扼要,但字里行间渗透着浓浓的感激之情。
结婚刚入门,刘氏“最温谨,朴讷寡言”,受到公婆的喜爱和称赞,“谓其有赤子之心,颇加怜爱,到处逢人称道之”。这同时也招致了家族妯娌们的嫉妒和排挤,被迫分家别居。分家产之时,刘氏“默若痴”,具体分配情况蒲松龄也悉数做了记录,其家分得“田二十亩”“荞五斗”和“粟三斗”,各种“完好”的农用杂器都被妯娌们拣走,留下“朽败”的给刘氏。对于住房的分配更是过分,“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蒲松龄与刘氏分得的住房是“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2]250蒲松龄在《悼内》诗中曾言刘氏“自嫁黔娄艰备遭”,不是虚言。而面对生活的艰难,刘氏也不多言辞,其“默若痴”的态度与初嫁入门时的“最温谨,朴讷寡言”完全一致。
但刘氏的沉默不是无能,她在后续维持生活和教育子女方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蒲松龄多年游学在外,连自己都感叹“游人几日在家中”,刘氏的做法是“固贫寂守,然不肯废儿读”,内心最有担当,最识大体。刘氏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想尽办法自力更生。她除荒修院,勉强度日,费尽心思,抚养幼儿。因为老屋“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半夜时常有狼偷袭,吓得“埘鸡惊鸣,圈豕骇窜”,刘氏不敢入眠,只好守着孤灯纺线到天明。同时还省吃俭用,讨好邻居老妇人,为的是老人家能同意晚上来和自己做伴。在饮食上,“松龄远出,得甘旨不以自尝,缄藏待之,每至腐败”。[2]335有了好吃的食物,自己舍不得吃,都放着等丈夫回来,时间一长食物都腐败了。蒲松龄记述刘氏“食贫衣俭”,“衣屡浣,或小有补缀。非燕宾则庖无肉”。年轻时纺绩过度而落下劳疾,年老后手臂疼痛难忍,但依然“犹绩不辍”。最为难得的是,在如此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刘氏从不肯耽误孩子的学业,“怜儿幼,辄昧爽握发送儿出,又目送之入塾乃返”,即天刚亮顾不得梳头就送孩子出门,目送至私塾才回家。正是因为有着刘氏的坚守和远见,才有蒲松龄的“儿孙入闱”,以及“三子一孙,能继书香”。刘氏共生了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十多年都长大成人。刘氏“为婚嫁所迫促,努力起屋宇”,每个儿子一间屋,一亩大的院子逐渐没有了空隙,以前的茅草地都成了草房。后来三个儿子都各自考取功名,能够自立自足。总体来看,儿孙渐多之时,刘氏凭着自己的勤俭,使本来贫穷至极几乎无望的家庭“瓮中颇有余蓄”,“衣食不至冻饿”,子孙各有出路,这与蒲松龄的父辈“为寡食众,家以日落”形成鲜明对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给蒲松龄失意的人生提供了一份相对稳固的家庭保障和心理安慰。
康熙四十八年岁暮之时,蒲松龄结束了自己大半生的塾师生活,回到家乡。他曾写《斗室》一诗描述自己的家,复杂的心绪融于字里行间。一方面房屋很破,“聊斋有屋仅容膝,积土编茅面旧壁。丛柏覆阴昼冥冥,六月森寒类窟室”;另一方面这又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垂老倦飞恋茅衡,心境闲暇梦亦适。癯儒相习能相安,与以广堂我不易”。[7]580细究起来,“聊斋”虽然狭小、简陋、阴暗、清冷,但这也是刘氏一直以来苦心经营起来的容身之地,也正是刘氏一生在尽心维持的家;虽是斗室,但这斗室及其承载的一切,是多年漂泊在外的蒲松龄最后的身体和心灵的归宿;有此归宿,他的内心才感到无比踏实和安适,竟然有“与以广堂我不易”的骄傲和喜悦。蒲松龄曾在《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坦率地描述了他的人生:“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抱酸寒之业,有焰如萤;入炎寂之场,无肠类蚓。半生忍辱,未登长吏之庭;经岁来城,不识公门之路。当清风而觉爽,处陋室以犹安。” [2]95其中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安贫乐道、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骈文体有文学修辞成分,但其中“纳税倾囊,愁贫任妇”之句却是刘氏半生苦心经营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当清风而觉爽,处陋室以犹安”也是蒲松龄晚年真/FNI28/wN7sEJN4lSMYe/8nEx68ciYrLJ5jhB1PqHr4=实的惬意心境。
唐君毅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说:“知天长地久之婚姻之意味。求天长地久,即一形上之感情也。中国夫妇之原不相识,由结婚以生爱情,此乃先有生理关系而后建立精神关系。夫妇愈久,而精神上之关系愈深。” [8]215文学家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寄内和悼亡作品就是夫妻之间感情的直接表达,情真词切,感人至深。晚年的蒲松龄,满怀对妻子的愧疚和感激,写下不少悼亡的诗句。“少岁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飧。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 [2]622自己没有给妻子带来荣华富贵,反而是妻子给自己带来了安稳和舒适。反过来说,这是蒲松龄的幸运,也是其妻刘氏的伟大之处。
在《聊斋志异》中,在一些有着美好品德的优秀女子身上,我们仿佛能够看到蒲松龄妻刘氏的影子,黄氏女如刘氏不嫌贫爱富,珊瑚如刘氏豁达大度,细柳如刘氏任劳任怨。还有许多正面的妻子形象也与刘氏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张鸿渐之妻,在张鸿渐被迫外逃时,独自持家,为儿子安排成家立业。特别在《画皮》篇末蒲松龄借“异史氏曰”明确指出:“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9]121蒲松龄感慨男人心存不良、见色起意的恶行恶果却报应在了妻子身上,王生见美色迷途而被掏心而死,最后却是其妻忍受极度的羞辱和暴力恳求乞丐仙人指点,最终使丈夫重新获得一颗心和一条性命,妻子为男人赎罪、承担责任并拯救其性命。反过来,这是蒲松龄对女性的“妻子”这个家庭角色的肯定。
三、但知止足,悟山林乐地——中华优秀女性的智慧通达
《述刘氏行实》一文不长,但处处动人,蒲松龄夫人刘氏的形象跃然纸上。刘夫人有着中华优秀女性内心深处的勤劳、质朴、善良,还有着心灵高处的理性、智慧、通达。我们从刘氏的几处言论来做分析。
首先,“吾常受人乞,而不乞于人,为幸多矣。” [2]251尽管自己生活艰难,刘氏却毫不吝啬,对需要帮助之人极富同情心,包括以前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兄弟皆赤贫,假贷为常,并不冀其偿。”她不但没有计较以前家族妯娌对她的嫉妒和排挤,也没有计较兄弟分家时的不公,反而以德报怨。即使对方有借不还,她也不放在心上,甚至也没有心存他们会还钱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她的解释也很与众不同:“吾常受人乞,而不乞于人,为幸多矣。”她认为是别人向自己借东西,而不是自己向别人借东西,自己已经很幸运了。这种解释,不是出于一般的温柔和善良,而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对人生得失、对人我关系的理性和智慧。
其次,“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 [2]251蒲松龄对科举曾抱有极大热情和希冀,他在追述家族科举史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万历间,阖邑诸生,食讫者八人,族中得六人焉,嗣后科甲相继,虽贵显不及崔、卢,而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 [2]59但事与愿违,他的科举之路漫长而艰辛。于是针对中年过后的蒲松龄是否继续科考之路,就有了蒲松龄与刘氏这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先是,五十余犹不忘进取。刘氏止之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顾儿孙入闱,褊心不能无望,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漠置之。或媚以先兆,亦若罔闻。[2]251
对于丈夫多年屡试不中,刘氏没有抱怨,更没有嘲讽。但在蒲松龄“五十余犹不忘进取”之时,她直截了当地阻止丈夫:“君勿须复尔!”让他不必再重复过去的老路,其理由是因为如果命中该通达显贵,现在就应已位列台阁了,这个推断出人意料,却也无可辩驳。接着她又继续申明自己对于科举之路的看法:“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此句中“山林自有乐地”来自《魏志·管宁传》中“朝廷之政,与生殊趣,将安乐山林,往而不能反”之句。做一个普通人也自有乐趣,何必一定要去做官以显示权贵为乐呢?言外之意,科举不是人生之乐的唯一来源。言之凿凿,让蒲松龄心服口服,“善其言”。“当然有时看看儿孙都考取了功名,不免又心存不甘和希望,说话间不时流露此意,但刘氏对此“漠置之”,理也不理,其理智与淡然可见一斑。
再次,“我无他长,但知止足。”对于丈夫“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之问,刘氏语出惊人。
松龄笑曰:“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答曰:“我无他长,但知止足。今三子一孙,能继书香,衣食不至冻饿,天赐不为不厚,自顾有何功德,而尚存觖望耶?” [2]251
穆如,是蒲松龄对妻子当面的形容,可见刘氏之品性端庄,也可见蒲松龄对妻子品质的认可。当面对“像你这样端庄的人,不愿意做夫人吗”的尖锐的问题,刘氏表现得极为理性,她回答说“我无他长,但知止足”。“止足”意为停止和满足,“知止足”含有“知止”和“知足”两方面的意义。“止足”二字也并非刘氏首创,其来源可以追溯到《老子》,第四十四章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之句,后世一直有引用并有引申。晋时张协的《咏史》有“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 [10]730,唐代杜甫《盐井》诗有“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 [11]290,明朝谢肇淛《五杂俎》有“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则贫贱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 [12]534等。随后刘氏列举自己的人生收获,“三子一孙,能继书香,衣食不至冻饿”,而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德能够配得上这些上天的很厚的恩赐,怎么还能再要求别的呢?也就是说,对于荣华富贵,刘氏内心并没有特别的渴求。这不是出于对蒲松龄多年科考无果的失望,也不是出于对自己无此命运的无奈,而是她看待人生的通透和达观。
最后,“无做佛事”。刘氏辛勤劳作一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反而因操劳过度落下一身病痛。最后刘氏自知医治无效,临终之时,只有:“我行矣!他无所嘱,但无作佛事而已。” [2]251也就是说只有一点要和家人交代的,就是“无作佛事”,让人读来五味杂陈。
佛事,特别是人去世之后的佛事,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蒲松龄文集中就有三十多篇是为修庙建碑、塑像请神所写的序、疏、碑记等文章,对时人所能理解的请佛礼佛的意义写得清楚明了。如《王村募修地藏王殿序》有言:“盖以斋熏讽叹,是谓善根;建刹修桥,厥名福业。三生种福,沾逮儿孙;一佛升天,拔及父母;所谓无有际岸功德,具慧性者所不疑也。” [13]75《颜神镇报恩寺募修白衣殿疏》甚至有“诵经满载,则灵凤集身;造塔合尖,则石麟入梦” [13]93之句。也正是因为蒲松龄知道世人对佛教的一些教义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所以他在《聊斋志异》中也撰写了一些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故事。刘氏对于这些佛事于去世之人的“效果”不可能一无所知,从刘氏临终特别嘱托“无做佛事”,也可推测当时葬礼时作佛事也是常见之举。
一般认为,刘氏特别嘱托“无做佛事”是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从刘氏一生勤俭持家来看,应该承认可能有这个原因存在。但是依据蒲家当时的儿孙科举成就和蒲家的经济条件来说,早就是“瓮中颇有余蓄”,“衣食不至冻饿”,比早年刚刚成家立业之时的捉襟见肘已经改善很多,要为家中去世之人做佛事应该不是大的问题,刘氏的嘱托还是另有他解。
佛教宗派繁多,义理精微,在信奉佛教的当世,能够在临终之时嘱托“无做佛事”,实际还有一种对生死大义和佛教义理的深刻领悟。蒲松龄在文末回忆了刘氏去世十年前夫妻二人的两句对话及其场景,我们从中可以见出刘氏对死亡的态度和认知。
先是六十时,便促营寿域。或有货柏材者,松龄购之曰:“谁先逝者占此。”刘氏笑云:“此殆为我而设,但不自知何日耳。” [2]251
由此可知,早在六十岁时,刘氏就开始催促儿孙营办坟地。后来有人卖柏木棺材,蒲松龄购下并说了一句:谁先去世谁先用。没想到刘氏笑着接话:“这具棺材应该是为我准备的,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事实确是如她所测,是她先离世,但从这一情节和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刘氏对待死亡的直率和达观。
在《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像刘氏这样文化不高但见识极高的女性,如田七郎的母亲,袁世硕指出田母这一形象“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全文的命脉、精髓之所在”。[14]田七郎的母亲本为山村一位老妇,生活贫困安宁,但在田七郎和武承休交往中,她表现出的见识高超、深明大义的确是非同凡响。
结语
以上我们梳理了蒲松龄简要记载其夫人刘氏的《述刘氏行实》,此作与蒲松龄的其他作品不同,它是记叙性的,也是真实性的,其中有一些生活事件和人物特点在蒲松龄的其他作品中从来不曾记录。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些作品中流露出了对现实婚姻的不满,原因是他的妻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对他的生活照顾周到,但并不理解他的内心,更不理解他的文字。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应该说,从其父以德行为准为其选择婚姻,从刘氏对家庭生活的勇敢担当,从她“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我无他长,但知止足”等对蒲松龄和对自我的清醒达观的认知,就可以知道刘氏即使没有像蒲松龄那样满腹才情写出一些千古奇文,但在生活、生命、人生的智慧和认知方面与蒲松龄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在这个角度和层面上,刘氏完全可以和蒲松龄平等对话。况且,蒲松龄本人也是品行高尚之人,在其《为人要则·远损》中说:“贪财猎色,损人之德行;奇技淫巧,损人之精神。” [2]294晚年的蒲松龄,心境渐趋平和,作诗作文流露着对妻子的愧疚与感激,这也是刘氏做事为人到达一定高度所得,而非一般家庭妇女可以相提并论。今天我们从多个角度解读《述刘氏行实》,纪念蒲松龄夫人刘氏这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女性,拓展对聊斋文化的研究,也加深对中华优秀女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陈戌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清]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翟博.中国家训经典[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7]赵蔚芝.聊斋诗集笺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1996.
[8]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台北:中正书局,1981.
[9][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南朝梁]萧统,主编.昭明文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1][清]杨伦.杜诗镜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明]谢肇淛.五杂俎[M].张秉国,校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
[13][清]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14]袁世硕.《田七郎》:报恩主题的超越[J].蒲松龄研究.2008,(2).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Pu Songling's Liu's Actions
Abstract: Pu Songling's Liu's Actions is a brief account of his wife's life. The text is simple and implicit,but full of sincere feelings. This article contains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Pu Songling's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his wife Liu's lif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culture,we can see that the concept of Pu Liu's marriage is based on virtue,“not taking poverty as a disease”;Pu Songling's life on the roa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difficult. His wife at home was the firm support and facilitated the achievements of Liaozhai;She realized the joys of ordinary life. She didn't care about power and wealth. She was wise and sensible. She was an outstanding woman in ancient China. On this basis,she could talk to Pu Songling on an equal footing.
Key words: Pu Songling's wife;Liu's Actions;warriage;excellent wo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