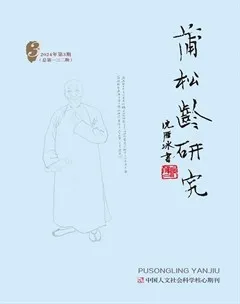犹抱琵琶半遮面
摘要: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是第一个以完整译本形式出版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对后世《聊斋志异》的英语重译和其他语种外译产生了重要影响。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对《聊斋志异》原文的文化话语进行了重构,本文从文本内容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三方面,分析了翟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策略,并进一步探索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寻求译本被英语世界成功接受的有效翻译模式,对当代的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聊斋志异》;翟理斯;文化话语;重构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著名文言短篇小说集,因其丰富多彩的故事、涵盖广泛的主题、典雅而又生动的风格,数百年来在国内家喻户晓,在国外也广为学者译介,是译文语种最多的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外译最早以译本形式完整出版的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的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聊斋志异选》)。《聊斋志异》原文共有短篇小说近五百篇,翟理斯选译了其中164篇作品,如《考城隍》《瞳人语》《画壁》《种梨》等。《聊斋志异》翟理斯译本(下文简称翟译本)自出版以来“其后数度重刊,更兼转译欧洲诸文,于西方代表蒲松龄百年之久” [1]xxxii,时至今日,依然是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聊斋志异》译本。翟译本能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与译者翻译策略的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鉴于此,本文将从翟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角度,借用Mona Baker提出的翻译叙事建构方式,考察分析翟译本的翻译策略,并进一步探索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寻求译本被英语世界成功接受的有效翻译模式。
一、文化话语的重构
文化话语是经过长期文化实践积淀而成的文化概念、文化范畴、文化范式、文化原理、文化论断等的集合体,这种文化话语体系既体现了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彰显了文化的独有特色。[2]44文化话语不仅包含大家熟知的词汇、短语层面的“文化负载词”和“文化专有项”,而且其范围超出了词汇层面,扩展到“话语”层面如谚语、古诗词等富含文化内涵的文本内容,以及“篇章”层面如整个故事的架构、故事主题等。
文化话语的重构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成功与否,是文学翻译作品在译语读者中的良好接受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实现在目标语文化中原作文化话语的重构。Mona
Baker认为,叙事与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每当某种叙事版本用另一种语言重述或翻译,它都会被注入某些叙事元素。译者可以利用建构或重新建构,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来强化或弱化他们介入叙事的某些方面,从而在目的语境中建构叙事,依照特定的意识形态实现对翻译叙事的操控。[3]22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中Mona Baker提出了四种翻译的叙事建构方式,即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时空建构是指选择一个文本,将其置于另一个时空语境中,新的语境将使该文本的叙事更加凸显,并引导读者将它和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可以指对源文本、作家、语种和文化的选择性采用,也可以是对文本内部素材的选择性采用,目的是要抑制、强调或者铺陈原文中隐含的叙事或更高一个层面叙事的某些方面。标示性建构指的是用来指示或者识别叙事中关键元素或参与者的任何标示都有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被译者重新建构,从而达到重构文化话语的目的。参与者再定位是指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以及他们和读者或听众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通过灵活运用表示时间、空间、指示、方言、语域、特征词以及各种识别自我和他人的语言手段来加以改变。无论是在副文本中添加评论,还是对文本内部的那些语言参数进行微妙调整,译者可以通过精心安排参与者之间的时间和社会/政治关系,积极参加当前叙事乃至上一级叙事的重新构建。[4]170-210
二、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文化话语重构策略
本文的研究侧重点在于翟译本文本内部文化话语重构,因此主要从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来分析翟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策略。
(一)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
关于文本的选择,包括译文内部的选择性采用和更高层面的文本、作家、语种和文化的选择,在本文中我们的重点关注发生在译文内部的选择性采用方面。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是通过省略和添加的方式实现的,目的是要抑制、强调或者铺陈原文中隐含的叙事或更高一个层面叙事的某些方面。[4]173
1.省略:由于意识形态、图书审查制度、译者主体性等原因,删除或节译是翻译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翟译本同样有诸多发生在文本内部的删除或节译,在此以《贾奉雉》的译文为例说明翟理斯英译过程中对原文中文化话语的省略。
蒲松龄“幼有轶才,老而不达” [5]169,可以说是终其一生求功名而不得,他对于科举制度有极其深刻的体验。《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对我国古代腐朽的科举制度的揭露。《贾奉雉》便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品之一。
《贾奉雉》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腐朽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中间部分是贾奉雉上山求道而不得,返乡后惊觉百年已过;后一部分则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腐朽堕落的批判。贾奉雉“才名冠一时” ① ,明白“学者立言,贵乎不朽”,却无人赏识,参加科考屡屡落榜。后在郎生的指导下,贾奉雉“集其蕞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中了乡试第一名。考试的胜利带给贾奉雉的不是喜悦,而是羞愧,自觉无脸见天下文人,选择了“遁迹山丘,与世长绝”。因为尘缘未断,他的第一次入山之旅以失败告终,返回尘世却发现百年已过。贾奉雉虽然子孙堂满,但回来后寄居之处“烟埃儿溺,杂气薰人”,所食之物“调饪尤乖”,“夫人恒不得一饱”。贾奉雉不得已再入仕途,得来富贵后,其子孙“皆窃余势以作威福”,最终致使其“被收经年”,充军辽阳。经此种种,贾奉雉终于彻底放下尘世俗念,跟随郎生乘舟而去,再返山丘。
翟理斯在《贾奉雉》的翻译中采用了节译,篇幅大减。首先是对原文第一部分的科举考试直接跳过未做翻译,只在译文开头做了以下简洁说明:
The story runs that a Mr. Chia,after obtaining,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mysterious friend,his master’s degree,became alive to the vanity of mere earthly honours,and determined to devote himself to the practice of Taoism,in the hope of obtaining the elixir of immortality. [6]316译文:故事是这样的,贾生在一位神秘的朋友的帮助下乡试中魁后,对世俗荣誉心生厌倦,决心投身道家修行,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原文中浓墨重彩地描写贾奉雉屡次参加科举不中,在郎生的悉心指导甚至动用法术帮助下,通过考试取得绝佳成绩。这是对科举制度腐朽的讽刺描写,也是故事的重要主题之一。在翟理斯的译文中却用一句话交代完了,完全失去了原文的讽刺和批判主旨。
原文后半部分重点描写贾奉雉返乡后生活窘困,被迫再入仕途,经历种种官场和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后,最终心灰意冷乘舟而去。翟理斯在译文中也全部删除,只保留了贾奉雉在山中的经历以及回乡之后发现百年岁月已过的部分,译者在译文的末尾说明如下:
After which the story is drawn out to a considerable length,but is quite devoid of interest. [6]319译文:此后该故事还有相当长的篇幅,但相当缺乏趣味性。
并以脚注形式进一步说明删减的理由:
This being a long and tedious story,I have given only such part of it as is remarkable for its similarity to Washington Irving’s famous narrative. [6]316译文:这是一个冗长且乏味的故事,我只译出了其中异常亮眼,与华盛顿·欧文的著名故事相似的部分。
译者对于原文中有关科举考试和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的部分全部删除,仅仅留下了贾奉雉上山的经历和下山后世事巨变的部分,和美国文学家华盛顿·欧文的著名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的情节极其相似,把一个深刻批判社会现实的故事删减成了充满神奇童趣的传说。翟译本的《贾奉雉》篇名就是直接采用了A Rip van Winkle,这种翻译策略的采用或许是为了引起译语读者的文化共鸣,同时又降低了译文的阅读难度,对于译语文化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的科举考试等信息,做出了删除处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翟译本没有译出原文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深刻批判,确实是一种遗憾。但从文化接受的角度来看,删改后的故事和译语文化原有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有效地拉近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译文读者可以有更轻松、更熟悉的阅读体验,这又是有利于源语文化传播的。翟译本通过重构故事框架,对原文的文化话语进行了部分删减的重构,省略了原文中对于译语文化读者不熟悉的文化话语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种文化话语重构策略的采用原因何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将详细阐述。
2.添加:翟译本的每篇译文都添加不少译注,从几条至十几条不等,对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解释说明。译注内容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丹方风水之术,葬丧婚娶之礼,不老长生之药,龙蛇狐怪之崇”都在其内。[6]xxii通过这些译注的添加,翟理斯在其作品中准确地传递了多样的中国文化,对纠正当时的西方人普遍曲解中国文化的现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Judge Lu”(《陆判》)中,故事开篇第一句话介绍了故事发生地、主人公的姓名和字,原文只用了非常简短的八个字。翟译本除了译出原文的信息外,为原文中的“字”的概念添加了长达200词的脚注。
原文:陵阳朱尔旦,字小明。译文:At Ling-yang there lived a man named Chu Erh-tan,whose literary designation ① was Hsiao-ming. 注释①:Every Chinese man and woman inherits a family name or surname. A woman takes her husband’s surname,followed in official documents by her maiden name... [6]56-57
为了说明中国姓名文化中的“字”的含义,翟理斯从当时中国男女取名的规则到中国地名的由来和含义,洋洋洒洒200词,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取名规则,由此可见翟理斯的“传播真实的中国文化”着实所言非虚。
(二)标示性建构
标示是指使用词汇、用语或短语来识别人物、地点、群体、事件以及叙事中的其他关键元素,所有这样的话语过程都叫标示。[4]187用来指示或者识别叙事中关键元素或参与者的任何标示都有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被译者重新建构,从而达到重构文化话语的目的。文学翻译中的标题和命名都是非常有力的标示性建构手段。下面将以翟译本中故事标题的翻译和命名的翻译为例说明。
1.故事标题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文本的章节标题常常被改换,用以有效地建构或重新建构叙事,从而拉近或拉远译文与译文读者的距离。改换后的译文标题会引导译语读者对译文做出译者想要的解读。翟译本选译的164篇《聊斋志异》故事,大部分故事的标题都经过了改译。翟理斯根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采用了音译、阐释、意象替代等多种方法,为译文故事重新拟定了标题。下面以《考城隍》《折狱》两篇故事标题的翻译为例:
《考城隍》:Examination for the Guardian Angel 原文故事中的“城隍”是指中国古代道教神仙,主要职能是守护城池和百姓的平安,是天国派往各个城市的守护神。在古代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座城隍庙,供当地民众祭祀城隍神。翟译本采用的Guardian Angel是基督教中服侍上帝的神灵,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人,它们代替上帝在世间守护信徒,古希伯来人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位守护天使。翟理斯用西方神话形象代替了原文中职责与功能与之类似的城隍神。
《折狱》:A Chinese Solomon 《折狱》的原文讲了淄川费县令智断周成杀人案和胡成冤案,翟译本节译了其中的第二个案件胡成冤案。费县令假装定案,称胡成乃杀人凶手,只需找到尸体丢失的头颅即可结案,死者的遗孀即可改嫁。真凶一夜之后就找到了头颅,并要迎娶遗孀,由此费县令将真正的杀人凶手和与其通奸的妻子捉拿归案。Solomon是古犹太王国的第三任国王,智慧超凡,被称为基督教文化中的“智慧之王”,也曾用同样的方法智断了一桩婴儿争夺案。有两个妓女因争子之事找到所罗门王,求他评判。所罗门命人拿刀来,假装要将孩子劈成两半,分给两人。最后断定不同意劈开孩子的妇人为真正的母亲。翟译本将中国小说中的神探“费县令”改译成了基督教的智慧之王,强调了不同的文化传说,体现了相同的伟大智慧。
2.命名的翻译: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中西方语言的命名体系同样也千差万别。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事物名、人名都是特有的,在西方文化和语言中从未出现,这种情况下,译者会采取替换、淡化、模糊等各种方法来达到文化话语的重构目的。下文将以“进士”“诗礼”“翁姑”的翻译说明翟译本的命名重构策略。
在Miss Chiao-no(《娇娜》)的故事中,孔生后来考取了进士,受朝廷封官,携家赴任,翟理斯用doctor’s degree来替换了原文中的“进士”。
原文:后生举进士,授延安司李,携家之任。(《娇娜》)译文:Some time passed by,and then Mr. K’ung took his doctor’s degree,and was appointed Governor in the Gaol in Yen-ngan... [6]26
科举制度属中国古代特有,因此在英语中无法找到与“进士”“经魁”等相对应的词汇。从翟理斯对《贾奉雉》译文大幅节译的情况可以看出,对于科举制度,翟理斯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关于科举的故事内容基本上一删了之,更无需笔墨来额外说明,他并不打算向西方读者介绍与之有关事物,因此,在译文中用西方高等学历中的doctor’s degree 和master’s degree替代了“进士”和“经魁”,以使译文符合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
在Miss Ying-ning;or The Laughing Girl(《婴宁》)中:原文:到彼且勿归,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婴宁》)译文:... she had better not come back. She also advised her not to neglect her studies,and to be very attentive to her elders... [6]72
原文中婴宁的母亲希望她到了表哥家里,学些诗书礼仪,将来也好侍奉公婆。“诗6p+OoG9mSqJA/Kp6+DuKFF1O6buP/sbcFAIG0okq0pA=礼”指的是中华文化经典《诗经》和《礼记》,后世用学诗礼来泛指提升自我的修养。翟理斯的译文采用了上义词“studies”替代了原文中的“诗礼”,舍弃了特指而又传达了原文的中心思想;“翁姑”指的是丈夫的父亲和母亲,即公公和婆婆。中国封建传统思想认为女子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即“三从四德”中的“既嫁从夫”,是封建礼教束缚、压迫妇女的道德标准之一。翟理斯在翻译时舍弃了“翁姑”而选择了“elders”,用长辈这一概念淡化了原文的封建思想,将其升华为一种更为普世的道德行为,避免了译文读者可能会产生的道德质疑,这是非常典型的命名重构策略。
根据叙事的关联性,译者“可以借助关联性向目标话语引入某一具体词语的含蓄意义(这种意义源自它在目标语境的公共或个体叙事中的使用方法),从而淡化或模糊它在原文语境中的相关承载意义” [4]101。翟理斯通过命名重构淡化了原文文化话语所包含的具体意义,引入其含蓄意义,拉近了译文读者和原文的距离,保证了译文读者的阅读节奏不被过度打断或破坏,对于文化话语的重构不失为一种合适的策略。
(三)参与者再定位
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以及他们和读者或听众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通过灵活运用表示时间、空间、指示、方言、语域、特征词以及各种识别自我和他人的语言手段来加以改变。无论是在副文本中添加评论,还是对文本内部的那些语言参数进行微妙调整,译者可以通过精心安排参与者之间的时间和社会/政治关系,积极参加当前叙事乃至上一级叙事的重新构建。[4]202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采用评论、替换、微调等参与者再定位的方式实现文化话语的重构。翻译过程中参与者的再定位几乎都是在文本或者话语内部来实现的,通过再定位,译者可以“不断重塑译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拉远或拉近译作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并确立自己和所译文本之间的位置关系” [7]269-294。下面我们将以翟译本中《娇娜》的典故翻译为例,来说明翟理斯是如何移花接木,以典译典,实现文化话语的等值替换:
原文:生叹曰:“羁旅之人,谁作曹丘者?”(《娇娜》) 译文:“Alas!” said K’ung,“who will play the Mæcenas to a distressed wayfarer like myself?” [6]21
原文中少年建议孔生设帐授徒,孔生觉得人生地不熟,无人作其曹丘,这里的曹丘指的是汉朝曹丘生,曾到处宣扬季布“千金一诺”的优点,使他享有盛名。后世多以曹丘或曹丘生代指荐引、称扬或介绍者。孔生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位引荐人。翟理斯在译文中舍弃了“曹丘”这一富含中国文化典故的人物名字,用Mæcenas(梅塞纳斯)来代替。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æcenas)是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谋臣、外交家,同时还以诗人和艺术家的保护人而闻名于西方世界,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曾蒙他提携。“梅赛纳斯”在西方文明中就是文学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曹丘”和“Mæcenas”均用以泛指引荐人和赞助者,作为不同的中西文化符号,两者有着相通的所指。翟译本以西方典故替换中国文化典故,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二者巧妙融合,在意义内涵上同样生成了同一的文化联想,移花接木的同时又可谓形神兼备;不但拉近了译文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也让译语读者与源语读者达成了心领神会。
三、翟译本文化话语重构原因分析
翻译始终受到文化语境等超文本因素的制约,因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也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的”。[8]3勒菲佛尔指出,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中发生碰撞,译者周旋于两种文学传统之间,心中怀有一定的文化或政治目标,不可能完全中立和客观。[9]6当目标语境中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外译而来的翻译文学则会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地位。此时的翻译文学要想获得主流文学系统的认可和接受,译者会根据当时的社会语境、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目标读者等因素,对原文本进行一定的操控,使之适应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范式,这对翻译文学的接受是有利的。只有在目标语境中获得了接受和认可,翻译文学才有了存在的价值。
(一)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语境
翟理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和黄金时代,英国的国家自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状态。翟译本通过文本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的方式对《聊斋志异》的文化话语重构,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是明智的选择。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道德的重视,并不亚于基督福音救世主义运动中的宗教人士。” [10]252-253维多利亚时期对于宗教的重视,极深地影响了民众的道德风气。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酗酒是道德败坏,放纵欲望更是堕落。这种对于道德的重视和推崇,表现为人民的禁欲主义、自制精神和责任感。这种严谨、勤奋、高尚的道德意识与18世纪的怠慢、松懈的人生态度大为不同。在这种伦理道德规范的潜意识支配下,翟理斯在盛赞蒲松龄文笔典雅优美的同时,也对《聊斋志异》作出了以下评论:
I too had originally determined to publish a full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of these sixteen volumes;but on a closer acquaintance many of the stories turned out to be quite unsuitable for the age in which we live,forcibly recalling the coarseness of our own writers of fi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6]xxi译文:我原本打算出版16卷的全译本,但进一步细读后发现其中有很多故事非常不适合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粗糙低俗的行文很容易让人想起我国十八世纪的庸俗小说。
翟理斯在此所说的,非常不适合时代的故事指的就是《聊斋志异》中大量对于情欲的描写。从这个维度来看,翟译本可以说“纯洁”得如同少儿读物。《聊斋志异》原文中所有与性有关的描述,甚至青楼这种不纯洁的场所,都被翟理斯彻底的删改。这种翻译策略毫无疑问会让原文的文学价值和批判价值有所削减。但从实际的接受效果上看,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语境下,翟理斯的删改策略迎合了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照顾到了当时英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又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促成了《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并使之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
(二)翟译本的翻译目的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相互传递。翟理斯以《聊斋志异》译本为渠道,较为客观地向译语读者展示了真正的中国文化、习俗和信仰,并借以消除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曲解。
翟译本的首版导言曾提到:“一方面能够使西方人更加关注中国;另一方面,至少能够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有些无能而狡猾的作者经常不诚实地把一些错误的观点灌输给读者,而读者也习惯于不加思考地把这些错误当成事实来接受……结果,许多中国习俗不断被嘲笑和谴责,根本原因在于传递它们的人扭曲了中国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对于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准确描写,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中国人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真正信仰与奉行的东西。” [11]xiv-xv在1926年再版的翟译本序言中翟理斯称:“通过它可以加深西方读者对这个辽阔帝国的了解。” [6]xxiii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扶正纠偏的目的,顺利地让西方读者接受翟译本,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大量地借用了西方文化意象,删除了过多的异质和“不洁”内容,保证译本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叙事要求,凡此种种,都是翟译本成为流行西方世界百年不衰的翻译文学佳作的成功秘诀。一部广受好评、历久不衰的经典译作,才能真正成功地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的文化、习俗、信仰和社会生活”。
(三)翟译本的目标读者
澳大利亚籍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认为,中译英文学翻译的译本读者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2]22-26:“虔诚的读者”(committed readers):指喜欢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英语读者;“感兴趣的读者”(interested readers):学习书面英文、从事文学和翻译研究以及批评的中文读者;“公允的读者”(disinterested readers):对文学价值具有普适性期待的英语读者,他们看重的是理解而不是信息,追求文字和审美带来的阅读快乐。在这三类读者中,虔诚的读者和感兴趣的读者的数量一般来说是相对稳定的,他们会积极主动地阅读翻译文学译本,主要关注点在于译本包含的信息。对译本的读者数量和影响范围起到更大作用的在于第三类读者。翟理斯对于第三种读者“公允的读者”的关注,能让文学外译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扩大传播范围。
在1926年版翟译本的导言中,对于可能会将他的译本和中文原文作对比的学习中文的学生,翟理斯特别做了如下说明:
And as various editions will occasionally be found to contain various readings,I would here warn students of Chinese who wish to compare my rendering with the text,that it is from the edition of Tan Ming-lun... that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made. [6]xvii译文:由于不同的版本偶尔会包含不同的选篇,我在此特别提醒那些希望将我的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的中文学生,我的翻译底本是但明伦评点本……
由此可见,翟译本的目标读者是包含了前两类读者的。但从翟译本的翻译目的来看,翟理斯的目标读者绝不仅仅只是喜欢中国文化或者从事研究和批评的学者们,他是要向尽可能多的译文读者普及正确的中国文化知识,纠正大众对中国的曲解。能够达此目的的唯一途径,当然是让更多的读者接受他的译本,欣赏译文的内容。翟理斯曾在不同版本的翟译本译者寄语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与孩子们”“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七个)孙辈”,说明在他的心目中,翟译本是非常具有普适性的,就算是作为儿童或者学生的读本,都没有任何问题。而要达到儿童读本的文体要求,采用文化重构策略来降低译本阅读难度,净化原文的“成人”描写,删减故事内容和修改故事架构,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结论
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翟译本对原文故事的语篇结构、故事内容、文化典故等多方面做出了改译,主要通过文本内容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的策略实现了原作文化话语在译文中的重构,从而有效拉近了译文读者和译本、源文本的距离,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对于纠正维多利亚时代西方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曲解和偏见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翟译本重构原作文化话语策略的采用,一方面是出于对译者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叙事的遵从;另一方面是出于译者的翻译目的的指引,西方读者顺利地接受翟译本,是实现翟理斯向读者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习俗和信仰,并消除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曲解的前提条件;第三个原因是出于译者对译本的目标读者接受的考量,为了使译本适合尽量多样的读者群体,翟译本对原文的故事情节有所删减,调整了原文的叙事节奏,利用注释增添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介绍,增加译本对读者的吸引力。虽然翟译本作为选译本,对原文内容有所删减,并未完整地体现《聊斋志异》原文的文学批判价值和现实意义,向西方读者展示的是一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东方美人,也正是这种朦胧美让《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早期传播之路通畅无阻,顺利地突破了东西文化差异的重重阻隔,得到了西方读者群体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翟译本能够在西方世界经久不衰、广为传译,对之后的《聊斋志异》英语重译和其他语言的外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无可否认的是翟理斯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初衷、严谨的治学和翻译态度、中西文化互鉴互证的翻译手法,对当代的文学翻译依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Pu Songling.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Trans. John Minford. London:Penguin Group,2006.
[2]韩美群.论文化话语体系的多重属性与建构范式[J].思想理论研究,2016,(7).
[3]Baker,M.,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6.
[4][英]贝克(Baker,M.).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赵文静,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
[6]Giles,H. A.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Shanghai:Kelly & Walsh,Ltd.,Printers,1926.
[7]Mason,Ian and Adriana erban(2003)“Deixis as an Interactive Featur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s from Romanian into English”[J].Target15,(2).
[8]BASSNETT S.,LEFEVERE A.,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9]Lefevere,André. 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10][美]戴维·罗伯兹.英国史:1688年至今[M].鲁光恒,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11]Giles H.A.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London:Thos.De la Rue & Co.,1880.
[12]Bonnie S. McDougall. Literary Translation:The Pleasure Principle[J].中国翻译.2007,(5).
A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aozhai Zhiyi by Herbert A.Giles
Abstract: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s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aozhai Zhiyi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a complete translation version. It is popular and enduring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and has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nglish re-translation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of Liaozhai in later gene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Giles reconstructed the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original text of Liaozhai. This paper will adopt 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framing by labelling and 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to analyze the cultural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Giles’ translation,and further explore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strategi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Herbert A.Giles;Cultural discourse;reconstruction